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_西方哲学论文二十篇
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_西方哲学论文二十篇
【哲学论文】导语,大家所阅览的此篇共有296301文字,由姜建君潜心修改之后,发表到美文档!哲学(英文:Philosophy,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是对世界基本和普遍的问题研究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_西方哲学论文二十篇欢迎大家来收藏,希望能帮到你!
第一篇 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_西方哲学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德里达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作的关于“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无论是真实话语还是想象话语,首先都是一种“本源的重复结构”。这种本源的重复比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的区分更古老,它是一切话语乃至一切符号的“共根”。本文详细梳理了德里达的解构过程和解构策略,并指出这种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本原与替补的差异体系,由此揭示了这种解构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
【关键词】符号;真实话语;想象话语;重复;本原;胡塞尔;德里达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speech and the imaginary speech implied in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derrida pointed out that both the effective speech and the imaginary speech are all a primordially repetitive structure. this primordial repetition is older than the distinction, and is the common root of all the signs(including language).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cess and the strategy of this deconstruction, the writer discloses the end of this deconstruction: which is to deconstruct the whole system of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 and supplement in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key words: sign; effective speech; imaginary speech; repetition; origin; husserl; derrida
一、两种话语:实在与想象
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第一章的一开头,胡塞尔就对符号做了一个“本质性的”区分:即作为“表述”(ausdruck)的符号和作为(anzeichen)的符号。Www.meiword.cOm前者指那些自身即具有或意指(bedeuten)着某种含义的符号,后者则指那些自身不具有含义、但却指示(anzeigen)了另外一个对象之存在的符号。胡塞尔认为,这两种符号——或不如说符号的这两种功能(意指与指示)——在实际的交往话语中总是交织在一起。但另一方面,胡塞尔又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又总能够相互分离:比如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独白就是不受指示污染的纯粹表述;而像奴隶头上的“烙印”则是不具有含义的纯粹。[1](27)然而我们又如何能够说独白是摆脱了指示污染的纯粹表述?胡塞尔求助于如下论证,他说:
“在孤独的话语中,我们并不需要真实的(wirkliche)语词,而只需要表象的(vorgestellten)语词[1]就够了。在想象(phantasie)中,一个被说出的或被印出的与此文字浮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它根本不实存[2](existiert)。……语词的不实存并不妨碍我们。但它也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对于作为表述的表述的功能来说,语词的实存与否无关紧要。……诚然,在孤独的话语中,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说,而且,他自己将自己理解为说者,甚至将自己理解为对自己的说者,这肯定也是可能的。……但在真正的、交往的意义上,人们在这种情况中是不说的,他不告知自己什么,他只是将自己想象(vorstellen)为说者和被告知者。在自言自语时,语词绝不可能用它的标志心理行为此在的功能服务于我们,因为这种指示在这里毫无意义。我们自己就在同一时刻里体验着这些行为。”[1](38-39)
不难发现,胡塞尔这里所求助的是两个紧密相关的论证:一,孤独心灵生活中的独白并不是真实的话语,而只是想象的或表象的话语,因此并不实存。而在胡塞尔看来必须是实存的,所以独白不是。二,之所以在独白中不需要真实的、即作为的话语,是因为不需要:“这种指示在这里毫无意义。我们自己就在同一时刻里体验着这些行为。”关于第二个论证涉及时间问题,我们这里暂不讨论。我们看第一个论证。显然,第一个论证隐含了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即:我们可以在“想象话语”与“真实话语”之间作出某种区分。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区分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在进行这种区分之际,我们是否遗漏了某种更本源的现象?我们发现,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对胡塞尔的“独白”理论、进而对他的整个符号现象学进行了解构。这种解构是如何进行或如何可能的?它是否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关于语言符号的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如果有的话——对于西方整个传统形而上学将具有何种后果?让我们来随德里达一道思考,在解构中思考。
二、从想象到再现
首先让我们随德里达一道对胡塞尔的论证做一个“重复”:这是一种必要的重复。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必要:首先,德里达的解构就是从“重复”开始。重复产生差异。我们会在胡塞尔的原文与德里达的重复间发现某些细微的差异,然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德里达的解构得以可能。其次,我们在解构中会逐步发现,重复本身在德里达那里具有一种本源的地位,它从根本上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
德里达究竟如何重复?他这样写到:
“……在孤独的话语中,主体于自身一无所获,也不对自身指示任何东西。为了支持这种在现象学中不断能看到其结果的证明,胡塞尔求助于两类论证:一、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对自己不指示任何东西。我至多只能想象(imaginer)着这样做,我只能自己再现(représenter)自己,有如自己对自己传诉某种东西。在此,这只能是一种再现和一种想象。二、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只能佯作交流,因为我并不需要交流。这样一个过程——自我对自我的交流——是不能发生的,因为它丝毫没有意义;而它之所以没有任何意义,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目的性。心理活动的实存不需要被指示……因为它在当前(présent)时刻是面对主体直接在场的(présente)。”[2](53)
这是《声音与现象》第四章开头的三段文字,对照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第8节的内容,德里达这里的概括基本符合胡塞尔的原意,但在“关键”之处也作了某些引申与发挥,对某些“关键词”的翻译与转渡也作了某些微妙的游戏,从而为他下面的解构埋下了伏笔。
第一步,德里达揭示出了胡塞尔论证中的一个隐含的前提:对语言所进行的实在与想象的区分。他说,当胡塞尔说在独白中人只是把自己想象-再现(此处何以这样写,下文再说)为说话者和交流者时,他似乎就对语言进行了一个根本的区分:实在(réalité)与想象-再现的区分[2](54)。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分,它既是胡塞尔的立足点,也是德里达解构胡塞尔的切入点。胡塞尔之所以认为交往话语是真实的话语而独白不是,就是因为在他看来独白仅仅是“想象”中的话语。所以这里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想象”(vorstellen):一者(独白)是而一者(交往话语)不是,或者说,想象在一者(独白)中是“本质性的和构成性的”,而在另一者(交往话语)中则“只是偶然添加到话语实践上的一种事故。” [2](55)果真如此?人们真能对语言运用这种区分的体系?这正是德里达所要怀疑并全力加以解构之处。然而,在继续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之前,让我们在此稍作停留,重温一下德里达上文对胡塞尔之论证的概括。我们刚才说过,德里达在那里对于胡塞尔的意思作了一些“引申”与“发挥”,而对某些关键词的翻译也作了“别有用心”的处理。但却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构成了他解构得以展开的基础。让我们来重温他的话:
“……胡塞尔求助于两类论证:一、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对自己不指示任何东西。我至多只能想象(imaginer)着这样做,我只能自己再现(représenter)自己,有如自己对自己传诉某种东西。在此,这只能是一种再现和一种想象。”
在胡塞尔原文中,“想象”是vorstellen,德里达这里先用了法文的imaginer来表达,但马上又用了représenter来进行“补充”和“替补”。德里达为什么不仅仅满足于imaginer?为什么要用représenter来“补充”或“替补”? 他要补充说明什么?我们来比较这两个词:imaginer的意思比较单纯,一般就是“想象”、“设想”之义。但représenter就不一样了,它不仅有“想象”之义,更有“表示”、“表现”、“描绘”、“描述”、“演出”、“上演”、“使想起”、“使回忆起”、“使再(出)现”、“象征”、“体现”、“作为……代表”、“作为……代理人”、“再出席”、“再到场”、“再出现”,等等。德里达这里之所以用这个词,就是要利用它所包含多层意思,尤其是它所包含的“想象”与“再现”这双重含义,来补充“imaginer”之不足,以便利用这一“想象-再现”的语义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文要这样写的原因),而从胡塞尔的“想象”过渡到他所要说的“再现”,最终过渡到一切语言的“共根”:“本源的重复结构”(详下)。于是,“补充”最终成为“代替”:作为imagimer之补充说明的représenter最终代替了imaginer:除去上文提到的一处及下文的个别地方外,德里达后来几乎就不再使用imaginer,而主要用représenter来对应于胡塞尔的“想象”(vorstellen),以为他的整个解构铺平道路。
然而问题是,德里达这么做合法吗?当他从représenter中的“想象”之义过渡到它的“再现”之义时,是否太过匆忙?有的学者正是以此置疑德里达之处。比如伯奈特在其“德里达与他老师的声音”一文中就曾问到:德里达是否太过匆忙地把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象或再现(比如:想象、重复、普遍的具体例示以及借助符号进行的再现<表象>)都归结到同一种方式下了?[3](13)这的确是问题。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德里达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德里达并不是要用représenter中的一种含义(再现)来取代另一种含义(想象),而是要利用représenter中所包含的那个“重复”(re-)来引出构成一般语言、乃至一般符号之可能性条件的那个“本源的重复结构”。这个“本源的重复结构”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事后”的“再现”,毋宁说是它得以可能的条件,也是一切想象之得以可能的条件。不过这里不是展开这个问题时候,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解构。
二、从再现到重复
我们说过,这种解构的关键就在于对“想象”或毋宁说“再现”在话语(无论是实际的交往话语还是想象的独白)中的地位究竟该怎么看。德里达首先列举了“人们”(这里显然是指胡塞尔或以他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看法:“人们一开始也许会假定,在交流中,在所谓‘真实的’语言实践中,再现(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不是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它只是偶然添加到话语实践上的一种事故。” [2](55)换言之,在实际的交往话语中,人们也许会认为再现只是一种偶然的增加因素,再现与实在的结合只是一种外在的相互增添。但德里达说:“然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语言中,再现与实在并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互相增添[而是根本上就是二位一体——朱按],因为在原则上不可能把它们严格地区分开。” [2](55)不仅如此,德里达还认为,实在与再现的这种不可分割并不是在语言中产生的,而是说,一般语言就是这种结合,也惟有这种结合才是一般语言。[2](55)显然,如果这个断言成立的话,那么胡塞尔对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间的区分就要受到彻底威胁,进而表述与指号的区分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因为如果一切语言都是再现与实在的结合,那么你胡塞尔如何还能将作为纯粹表述的独白与始终和指示交织在一起的真实的交往话语区别开?而如果这一点受到威胁,那么整个《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也就要受到威胁:因为正是这个“本质性的区分”构成了整个第一研究的阿基米德点。然而,德里达究竟是如何论证他的这个断言的?他的论证站得住吗?让我们继续朝前走。
不过在继续朝前走之前,为了不在德里达的话语迷宫中迷失我们自己,现在有必要强调:德里达此处提出的命题是,一切话语就是再现与实在的这种结合。但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德里达在下文中的论证更多地是证明了再现在一切话语中的原初地位,或再现的本原性,而并没有证明“实在”究竟是如何与“再现”不可分割。特别是在独白中,二者如何纠缠在一起,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我们会看到,这个环节的缺失对于德里达的上述断言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最终会使这个断言成为一个无根的断言。但它同时也使德里获得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结果,那就是发现了重复、再现、踪迹、替补的本原性地位。这个发现对于德里达来说意义非凡,正是由此出发,他才能得以彻底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本原问题,进而解构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3]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德里达的解构。
前文说过,胡塞尔认为独白之与交往话语的区别就在于:独白只是想象或再现的话语,而不是真实、实在的话语。但德里达现在说,即使是真实的话语,也已经以再现和重复(répétition)为可能性条件了。到这里,我们必须再稍作停留。前面说过,德里达为了给他的解构做铺垫,而把胡塞尔的vorstellen翻译或转渡为représenter。现在这种翻译的目的终于显露出来了:正是通过这个représenter,他最终得以引出他所要说的répétition。从vorstellen到représenter,再从représenter到répétition。这就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现在,经过这几番似乎不经意的翻译、改写、转渡,他终于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他说:“实际上,当我如人所说真实地使用语词的时候,不管我是否为了交流的目的……,我必须在游戏开始时就运用重复的结构或在重复的结构中进行,而这种重复的因素只能是再现。” [2](55)为什么语言游戏一开始就已涉入一个重复结构?因为符号(包括语言)之所以为符号就在于可重复:“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符号不是一个符号”。[2](55)因此符号本质上就是一个“本源的重复结构”(la structure originairement répétitive)[2](56):它必须可以重复使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语言符号始终要求着再现、包含着再现。所以德里达认为,这种再现结构就是符号化或符指化(signification)本身。因此,若不是本源地涉入一个不定的再现性(représentativité)中去,我就不可能开始一个“真实的”话语。[2](56)由此,既然真实(实在)的话语已经以再现为前提,而独白作为想象的话语同样也要以再现为前提——正如德里达所说:这是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区分之前的一般符号的要求——那么就此而言,在话语被区分为真实(实在)的与想象(再现)的之前,首先都已是再现的了,或更严格地说,都已经在要求着再现、呼吁着再现、并以再现为可能性条件了。就此但也仅就此而言,交往话语与独白之间的确没有本质的区分。但我们马上将会看到,换一个角度,交往话语与独白之间毕竟还是有某种不可抹消的分别。
三、实在与想象
我们知道,胡塞尔在对独白的描述中,也突出了语言的再现性(想象性),德里达自己也承认这一点。[2](56)然而,德里达认为他与胡塞尔的区别就在于:胡塞尔仅让独白或纯粹的表述依附于作为想象的再现,而德里达所要强调的却是:“任何一般的符号都包含着想象以及它的其他再现性改变”。[2](56)这“任何一般的符号”当然也包含着所谓“真实的”话语。因此在这一点上,德里达当然有理由作下述断言:“当人们承认话语基本上属于再现的范围时,那么不论话语是纯粹‘表述’还是介入到一种‘交往’中去,‘真实’话语和话语的再现之间的区别就变得令人怀疑了”;以及:“由于一般符号本源的重复结构,‘真实的’语言完全有机遇与想象的话语一样成为想象的。” [2](56)但是,德里达是否也有充分理由作如下断言,即:“由于一般符号本源的重复结构,……想象的话语也完全有机遇像真实的话语一样真实” [2](56)?这里难道不是有个非法的跳跃?显然,由于本源的重复结构是一切话语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不仅独白的话语是想象的,而且所谓真实的话语首先也必须是想象的。但我们却无法从一切符号都具有本源的重复结构而推出想象的话语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话语。重复结构对于话语之为想象的话语来说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但对于话语之为真实话语来说,却只是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上文曾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即德里达曾说,一切话语都是再现与实在的结合。现在我们要再一次地问:在独白中,这二者如何结合在一起?独白是想象的话语,而不是真实的话语。这是胡塞尔的出发点。但德里达似乎并没有否认这个出发点。他只是把这一点更推广到一切话语身上。但是,独白的实在性在哪里?我们难道能因为独白和一切话语一样,都具有本源的重复结构,就推论出独白也具有实在性?我们无权这么做,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人和动物都有生命而推论出二者都有思想一样。因为胡塞尔完全可以这样回应说:诚然,就一切话语都具有本源的重复结构而言,独白确实和交往话语是相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实在性上的区别:交往话语既是想象的或毋宁说再现的,同时也是实在的或真实的,但独白的话语仍只是想象的或再现的。总之,德里达最终向我们证明的是:是重复、再现或重复的踪迹,而非实在,才是真正弥漫、渗透于一切话语符号的元素,才真正构成了一切话语符号的共根。这一点可从德里达自己的下面一段话中再一次得到验证,他说:“胡塞尔因而应该在真实交往和作为说话主体的自身再现之间设定一种区别,就像自身‘再现’只能偶然地从外部加入到交往的活动中去。然而我们刚才援引的有关符号的本源重复结构应该支配符号化行为的整体。主体不表现为再现,就不能说话;而再现不是一种事故。没有自身再现的真实话语并不比一个没有真实话语的话语再现更易想象[4]……话语自我再现(se représente),就是它自己的再现(sa représentation)。或更确切地说,话语就是那自身再现(representation de soi)。” [2](64)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是再现弥漫一切,渗透一切,甚至连所谓“真实的”交往话语都难逃其恢恢天网。
所以,德里达这里成功证明的是,不论是独白话语(表述)还是交往话语(),首先都是再现、重复,这个再现或重复就是那个在表述与、指向与指示、证明与指明、独白与交往等等分离之前的更原初的“指引”或“显示”。但是,德里达这里却并没有成功地证明:独白之中也有实在,或想象的话语也有机会成为真实的话语。
四、同一与重复,或重复与本原
任何语言符号,要想能作为符号而起作用,就不仅必须是可重复的,而且必须在如此这般的重复使用中又始终保持为同一个,具有同一性。然而这将是何种意义上的同一性?显然,它不可能是经验实在的同一性:无论是物理意义上还是心理意义上的经验实在。因为在其每一次出现中,符号的物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人的心理体验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这种同一性就只能是观念的(idéale)同一性。[2](56)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本人也正是把话语结构作为观念性来描述的。他说:“在胡塞尔看来,话语的结构只能作为观念性来描述:能指的(比如词的)可感形式的观念性——能指应该始终是同一个而且只是作为观念性才能成为同一个;所指(即含义)的观念性或被追求的意义的观念性……;最后,在某些情况下,保证语言的观念透明性和完美单义性的对象本身的观念性。” [2](58)既然同一性只能是观念的同一性,而且只有作为观念性才能是同一性,所以德里达认为,这种观念性只是同一者(le même)之持存(permanence)的名称和它的重复可能性。[2](58)于是这里立刻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同一性与重复的关系问题:是先有一个现成的观念的同一性,作为一个“本原”,然后才有对它的重复;还是相反,这同一性本身恰恰在重复中并通过重复才得以构成?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看法,答案无疑是前者:总是先有一个“本原”,然后才可能有对它的“重复”。是的,是的。重复总是对某个东西的重复,总是对某个本原的重复。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问:在对那个本原进行重复之前,我们如何知道它是同一个?我们如何确证、确认它的同一性?这确证或确认行为本身不已经首先是一个重复了吗?或者说,不正是通过一个重复、甚至多次、乃至无数次的重复,才能确证、确认同一性吗?“请重新输一遍你的!”的同一性需要重复才能确认。“请签名!”然而这签名的同一性也必须是可重复的而且必然以可重复为前提!所以同一性,从来都不是一个现成存在的同一性,而只能是观念性,而这意味着,它只能是在重复中并通过重复构成。所以这里的观念性也并不意味着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观念或理念世界,仿佛已经有了一个个现成的、自身同一的观念摆在那里等待着重复一样。相反,正如德里达所说,“它完全取决于重复活动的可能性,它由重复构成。它的‘存在’与重复的能力相适应。因此,绝对的观念性是不定的重复可能性的相关项。” [2](58)所以,作为观念性的同一性并不是现成的实体,而是在每一次的重复活动中被当下构成。德里达进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他说:“人们因此可以说,存在被胡塞尔规定为观念性,亦即重复。” [2](58)存在即观念性,观念性即重复。所以存在即重复。而重复又总已经是重复的踪迹,所以存在即踪迹。就是说,存在——它在存在论的历史上总被领会为在场——总已经是踪迹了,总已经是重复的效果了。在重复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存在;在踪迹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本原。这一点,德里达在另外两个解构海德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存在论的文本(“la différance”和“ousia et grammè”)中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4](1-78)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德里达与胡塞尔的关系上。
胡塞尔对德里达的这个结论——而且是从他自己的思想中引出的这个结论——会如何看?说存在即观念性,胡塞尔也许会同意。但说存在即重复,胡塞尔会同意吗?也许他会犹豫不决,他会很难直接同意或直接反对。他之所以难于直接同意,因为如上所说,这个结论意味着对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在本源的重复之前再也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作为“源点”的本原或开端。而这恰是他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心中还保留着古老的本原情结、奠基情结。他还相信总有一个“本原”、一个确定的“基础”:就历史来说,有一个最初的意义本原,所谓历史“不外乎就是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积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5](449)就内时间意识来说,有一个本原,即“原印象”;就客体化行为来说,有一个本原,即感知或呈现,等等。既如此,他又如何能接受德里达的这个结论?但这确实又是从他自己那里引出的结论,而且是完全合理地引申出来。所以他也很难直接反对。虽然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思想中潜藏的这种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却毋庸质疑。我们知道,胡塞尔虽然也是一个观念论者,但他之所以不同于柏拉图的观念论甚至康德的观念论,就在于他的构成思想:观念在他那里并非一个现成的对象,等待着人去认识、去揭示;相反,它是由意向行为在每一次的意向活动中当下构成。被构造的观念对象之所以有同一性,并不是因为这个观念对象本身自在先天地保持同一,而是由意向行为在一次次的重复构造中构造起来。[5]因此,胡塞尔如果直接反对德里达的这个断言,无疑就会重新退回到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而这一点他恐怕更无法接受。这就是德里达的解构之为解构的要害所在:它并不直接摧毁被解构的对象,而是让被解构的对象自己处于自身冲突、自身紧张之中。
五、符号:本源的重复
——未完的结语
就其自身看,符号是一个本源的重复结构。但就符号又总是关于某物的符号而言,符号又是对某物的重复或再现。因此符号总是某种(相对于本原而言的)派生的、替补的东西。这正是符号在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地位之所在。显然,对符号的这样一种规定是以本原与替补、实在与再现、在场与重复之间的界限或差异的确立为前提。但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界限或差异的确立一方面确立了符号的地位,同时又抹去了符号:因为为了维护单纯在场的特权地位,符号最终被看作是派生性的,并最终被还原到在场上去。这就是说,在场哲学“在派生出符号的过程中同时就抹去了符号,在使再造(reproduction)和再现成为对单纯在场的突然变样(modification)的过程中就取消了它们”。[2](57) 所以,“符号在其本原处,在其意义核心之中,就以派生和抹去的意志为标志”。[2](57)但问题是,在场哲学所确立或毋宁说坚信的这条界限:在真实在场与作为想象的再现中的在场之间、在被再现者与一般再现者之间、在所指与能指之间、在单纯在场和再造之间、在感知和想象之间,一句话,在本原与替补之间、在本原与再现本原的符号之间,真的有一条确定无疑的界限吗?显然,在德里达看来,这是可疑的,也正是他要解构的。而他之所以要解构胡塞尔对语言所作的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的区分,正是想由此解构这整个的差异体系——因为正是后者构成了胡塞尔的那个区分的前提。所以德里达写到:“与真实在场和作为想象的再现中的在场之间的差异一道,在被再现者和一般再现者之间、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单纯在场和再造之间、作为表象(vorstellung)的呈现和作为再当前化的再现之间……的整个一个差异体系就这样通过语言被拖入同一解构之中。” [2](57-58)作为对这整个差异体系解构的直接后果,就是(与胡塞尔所表达的相反):表象(vorstellung)本身要依附于重复的可能性,最单纯的表象和当前化(gegenwärtigung)要依附于再当前化的可能性。这样,现在的在场就来源于重复,而不是相反。[2](58)至此我们看到,德里达对胡塞尔解构的真正目的终于显露出来了:他就是要颠倒传统形而上学(在这里就是胡塞尔)对本原(单纯在场、呈现、当前化)与替补(符号、再现、重复、再当前化)之关系的理解,他就是要表明:传统在场哲学所以为的“本原”,并不是真正的本原;传统哲学所以为的“替补”,反倒占据了本原的位置。所以,符号之为本源的重复,并不只是说,重复对于它来说是本源的,而且还是说,它之为重复,是本源的:它并不是对本原的事后的重复,它的重复本身,就是本源性的——传统形而上学所以为、所追寻的本原,反倒以它为可能性条件。由此,以本原问题为基本问题的传统形而上学就得到了彻底的解构。这也许就是德里达的这种解构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然而,要详细展开这一点,就必须涉及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和中心论的解构。但这已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参考文献]
[1]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2] 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凡引该书文献皆参考了杜小真教授的中译(见《声音与现象》,:商务印书馆,1999年,边码),译文有改动处不一一注明。
[3] derrida and phenomenology,edited by william r. mckenna and j. claude evans,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1995.
[4] jacques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 les édtions de minuit, 1975, c1972.
[5]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xx年。
--------------------------------------------------------------------------------
[1] 倪梁康先生译为“表象”。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2] 倪梁康先生译为“存在”。同上。
[3] 这一点此处无法展开,笔者将在别处专门讨论此问题。读者也可参阅拙文“本原与重复——胡塞尔的时间意识本原观及德里达对它的解构”,《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六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年;“文字与本原——德里达的‘文字学’对西方形而上学中本原问题的解构”,《哲学动态》20xx年第4期。
[4] 此句话比较拗口,其实意思就是:真实的交往话语(所谓“没有自身再现的真实话语”)并不比想象的独白话语(所谓“没有真实话语的话语再现”)更容易想象。
[5]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阶段构成思想还没有被突出出来,因此有柏拉图实在论的痕迹,但后期则绝对超越了这种素朴的观念实在论。他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已经明确地说同一性是由构造性的内时间意识之流构造的。
第二篇 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实是性_西方哲学论文
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是指海德格尔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前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学位论文和在大学的讲课笔记。近年来,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注意,相应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在此领域研究比较出色的国外学者主要有克兹尔(kisiel)、伯格勒、范布伦(van buran)等人。就国内的研究而言,靳希平老师对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最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此后一些学位论文继续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1]。在丛刊《中国现象学和哲学评论》的第一辑和第四辑里面的数篇文章,比梅尔、萨弗兰斯基、张祥龙等学者的海德格尔传记对研究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也非常有帮助[2]。
为什么最近在此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或者说,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意义何在呢?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的十年多的时间里海德格尔没有发表文章,因而《存在与时间》的出现似乎很突兀,近些年来,随着海德格尔早年讲演录的相继出版,首先是1923-1927年海德格尔在马堡的讲演录,接着是1919-1923年他在弗莱堡的讲演录,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渐渐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他1927年的著作,乃至三十年代之后的思想。这些早年讲演录的出版不仅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此后的哲学非常有助益,而且这些讲演录本身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正如海德格尔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所讲的,思想在其开端处最有力量。因此随着这些讲演录的出版,对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在上述的讲演录中,1919至1923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时期的讲演录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wwW.meiword.cOm因为,正是在这段时期,海德格尔“发现了他自己,第一次成为了海德格尔”[3],尤其是其中的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稿分外重要。此篇讲稿短小精悍,立场鲜明,海德格尔成熟期以及后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在此萌芽并初具规模,甚至在某些方面论述得更加清楚。
本文所要研究的概念“实是性”[4]是此期讲课的主题词,贯穿全篇。这个概念,不仅在这里,而且在海德格尔其它早期讲演录里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实是性这个概念是理解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一把钥匙。而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学者同样会发现,实是性在《存在与时间》的概念架构中也非常显著。本文主要依据于海德格尔1923年夏季学期在弗莱堡的讲课稿和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以前者为主,引用《存在与时间》中的相关,使这两部著作可以相互发明、相互阐释,力图从实是性这个概念出发展示出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一些突出特点和根本倾向,理解何谓实是的生活,以此为基础,提出重新确定1923年讲稿的内在结构的可能性。
1.1923年讲稿的主旨:实是性的解释学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1923年夏季学期的弗莱堡讲稿是由凯特·布洛克·奥尔特曼编辑的,在海德格尔去世后作为全集第63卷出版(1988年),题为《存在论:实是性的解释学》。英译本由范布伦翻译,出版于1999年。这个讲演录不长,却包含有几十个哲学上的新概念,例如,当下各自(jeweiligen),停留(aufenhalt,whilen),躁动(bewegtheit),被解释的(ausgelegtheit)等等。新词很多的现象在海德格尔其它的1920年左右的早期讲演录和论文中也可以发现。如范布伦在“译者后记”中所说,海德格尔正在寻找和实践一种新的思维风格和语言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他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正在摸索和建立哲学的新开端[5]。学界一般认为此篇讲稿可以看作为《存在与时间》的初稿。海德格尔说,《存在论:实是性的解释学》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第一个注脚 [6]。更有意义的是,这本书的思想不仅可以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中看见,也可以在海德格尔1930年之后的作品中发现。在海德格尔后期作品《通向语言的途中》他再次使用“停留(weilen)”,人的“栖居”,也再次使用“解释学”这个概念。在1961年的论文《康德的存在论题》中,jeweiligen也再次出现。
海德格尔原计划把这门课的题目定为“逻辑学”,因为有别的教授的课程也想使用“逻辑学”这个课题,于是,这门课才有了现在这个题目。题目中的“实是性的解释学”是这门课的真正主题,不过,如果人们把“存在论”理解为是对“存在”这个概念的探究,而没有什么具体的学说,具体的内容,那么“存在论”这个概念作为题目也有其所用。要理解海德格尔此次讲课的主要内容,关键是要理解:什么是解释学,什么是实是性,“实是性”和“解释学”中间的这个“的”(der)所指的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与海德格尔所喜欢的其它一些概念一样,解释学(hermeneutik)这个词语出现于古希腊,与赫尔墨斯神有关,赫尔墨斯神是诸神的使者,把诸神的命令传达给人。海德格尔引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展示了从柏拉图到狄尔泰的解释学的历史,指出解释学在现代变成了关于理解规则的学说,与语法和修辞相关。海德格尔讲,他这里的解释学与那种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不同。这个不同主要在于解释学和它的对象的关系。海德格尔这里的解释学的对象是此在,此在的实是性。
“实是性是一个标记,我们用它来标记‘我们的’‘自己的’此在。更确切地说,这个表达式意味着:这个当下各自的此在在此。”实是性,即我们自己的存在。实是性的解释学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存在作为解释的对象,是对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解释。我们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一般地称之为此在。
此在不仅仅作为解释的对象,关键的所在是,正是此在作为解释的主体。此在具有解释能力,并且需要解释,这个解释构成了它的存在。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使我们可以通达、把握总是我们自己的此在的存在特征,与自身交流此在。这种在解释之中出现的对自身的理解根本不能与那种在认知行为中理解相提并论。在认知行为中的理解是指在现代社会通行的科学所施行的理解。现代科学的理解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站在主体的对面,由主体来认识。在海德格尔这里,解释学和实是性的关系不是那种主客体的关系,彼此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归属的关系。这种相互归属正是“实是性的解释学”这个题目中“的”所指示的关系。这里的“的”表明的是:实是性的解释学,既是对实是性(此在)的解释,也是实是性(此在)所做的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自身就是实是性(此在)存在特征的可能的、分明的方式。这个解释学属于自己的对象。此在解释此在,在这解释中,此在成为此在。海德格尔讲,对实是性的存在论解释,不是要获得对实是性的认知,要拥有对实是性的知识,而是牵涉到一种生存论的认识,对实是性(此在)的解释不是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事情的报告,而是“着眼于在其中发展一种彻底的自知之明”[7]。
海德格尔所显明的解释学不仅使以往的解释学具有了新的意义,也使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的方向与新的内容。在这里,海德格尔选择了解释学作为自己学说的名称,这个选择与胡塞尔选择现象学作为自己学说的名称是一样的,两者想要表明的都是与传统哲学决裂的决心。与胡塞尔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所表明的不仅仅是想要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也表明了他与胡塞尔哲学的距离,表明了他在 现象学的基础上的新的突破。[8]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解释学、现象学和存在论三者的关系做了清楚的说明:存在论是从对象方面讲的,现象学是从方法方面讲的,两者是从不同方面来描述哲学本身,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它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9]。
然而,如果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所表明的只是与现代科学中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外在理解的不同,所表明的只是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所表明的只是此在是解释的主体,解释构成此在的存在,那么,海德格尔哲学的突破性,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就并没有他自己所暗示的那样显著,那样意义重大,因此,这个新的开端就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开端。实际上,海德格尔哲学的全新性不仅仅是上述所表明的那些,真正关键的所在是海德格尔重新规定了哲学运思的事情(sache)。胡塞尔现象学的口号是“面向事情本身”,海德格尔接过了这面旗帜,不过,他这里的“事情本身”已经不是胡塞尔那里的“事情本身”了[10]。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事情是实是性,即我们自己的此在,我们处身其中的实是的生活。
2.实是性: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根本倾向
“实是性是一个标记,我们用它来标记‘我们的’‘自己的’此在。更确切地说,这个表达式意味着:这个当下各自的此在在此,它具有其存在特征,以存在的方式在‘此’。具有存在的方式的此在意味着:不是且从来不是,作为直观的对象和以直观为基础的定义的对象,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纯粹地认知并可以有知识的对象,相反,此在是以它最本己的存在方式自己在此。它存在的方式敞开了并且刻画了这各自的可能的“此”。存在是一个及物动词:存在(是)实是的生活!存在自身绝对不是可能拥有的对象,它依据于自身这个存在,与其自身大有干系。”[11]
这段文字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凝结了全书的精华,需要非常仔细的品味。
第一个词就是实是性(faktizitat)。为什么选用这个词?faktizitat,其形容词是faktische,在海德格尔这里一般与生活经验(lebenserfahrung)连用,构成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在我们研究的讲演录里,更多地只与生活(leben)连用,构成faktische leben,就我们的研究而言,这两个表达式意义差别不大。张祥龙先生指出,实是性这个概念在费希特和新康德主义者那里曾出现过,用来形容最无理性的、“野蛮的”生活状态。海德格尔这里是取其“最原发的”、“在一切概念分别之前”的含义。实是的生活经验,这个表达式显示出狄尔泰和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在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讲演录中,海德格尔认为实是的生活具有三个特征:无区别性、自足性和有意义性。[12]这些特征在《存在论:实是性的解释学》中继续发展,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释,本文限于篇幅,对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讲演录不做更细致的讨论。
根据从《存在与时间》得到的启发,实是性这个概念是与事实性(tatlichkeit)相对的,事实性指的是一种对象的存在,站在主体的对面,可以观察的属性。而实是性指自己的存在,此在的存在,不是对象。“自己的此在这一事实的‘事实性’在存在论上却根本有别于一块石头事实上搁在那里。每一当下各自的此在所是的,此在的事实(factums)的事实性称作此在的实是性。” [13]花开花落,这样的事实可以观察,而自己的存在确是自己无法观察的。实是性,即‘我们的’‘自己的’此在。为什么‘我们的’,‘自己的’这两个词上面要加上单引号?此在是我们的,是自己的,然而,同时,此在也不是我们的,不是自己的。为什么这么讲?此在,这个存在,不是普遍的人的存在,而是特指这个存在,这个在此时此刻停留于此的个别的存在,“当下各自”的此在,指的就是我们自己,并不是别人,也不是所有人。由此可见,此在是我们自己的,然而,我们自己在首先和通常的意义上,在最初和大部分时间,却是处于平均状态,日常状态,我们是按照常人的眼光来思考问题,按照常人的言行来确定自己的言行,“众所周知……” “大家都是这样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分别出自己的此在,此在不是我们自己的。从另一方面讲,在实是的生活中,此在是与世界共在的,处于一种无区别状态,并没有“我们的”、“他们的”、“自己的”、“别人的”这样的区分,因此,在这里“我们的”和“自己的”这两个词要加上引号。[14]
不过,即使“我们自己的”具有如是的双重意义,我们仍然可以说,此在是当下各自的(jeweilig)。什么是“当下各自”?当下各自的原文为jeweilig或jeweiligkeit,jeweilig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为当下的、各自的,例如:der jeweilige konig (当时的国王) ,reisten in ihre jeweiligen lander zuruck (回到各自的国家),从这个词也可以看见weilen (停留,逗留),weile(短时间,片刻),jeweils(当时,每次,总是,各),jeweilig即je-weilig,jeweil-ig。海德格尔在括号中指出当下各自的几种现象:耽搁、停留,不跑开、不逃跑,于此,在此。考虑到海德格尔对动词的喜欢和在此处给出的具体的现象上的说明,jeweilig翻译为“停留在当下各自中的”可能更为恰当,[15]不过这样的翻译似乎过于冗长,本文还是采取了相对简单的译法,不过读者在看到“当下各自”时应该把“停留,不跑开”等意义记在心中。此在是当下各自的,即此在具有其存在特征(seinscharakter),以其存在的方式在‘此’。“具有存在的方式”(seinassig)意味着:不是且从来不是,作为直观的对象和以直观为基础的定义的对象,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纯粹地认知并可以有知识的对象,相反,此在是以它最本己的存在方式自己在此。这里的“存在特征”、“存在方式”都是独属于此在的,是此在的特征,是其存在论结构。此在的存在方式敞开了并且刻画了这各自的可能的“此”,即正因为此在如此存在,此在才是各自的,此在的这种当下各自性才是可能的。海德格尔选用“当下各自”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显示出他不想研究普遍的人性,显示出存在论,实是性的解释学,是以居于某时某刻,某种特殊处境中的此在为其所要解释的事情(sachen)。当下各自这个概念也可以在语言上减少一种偏见,即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是自我(ego),孤立的个人。实际上,这种孤立的自我,恰恰是海德格尔所竭力反对的。
此在的当下各自是以其存在特征、存在方式为根基的,此在的存在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或者说,存在这个概念在此在这里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存在是一个及物动词:存在(是)实是的生活!(sein – transitiv: das faktische leben sein!)” 海德格尔的这个命题令人非常惊讶,这句话不仅在汉语中很怪异,在德语中同样很怪异。因为在西方语言中,存在(being, sein)从来不是一个及物动词。在印欧语系中,存在一般有两种用法,或者作为系动词,连结主词(主语)和宾词(宾语),并没有实在的动词含义,或者,用在“上帝存在”这样的命题中。关于存在这个概念的辨析,文献很多,我们不在此详述,仅就“存在”是否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做一点讨论。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就是说,它是关于某个东西的概念,能够加在一个事物的概念上。它只是对于事物或者对于某些自在的规定本身的断定。”(a598/b626)实在的谓词是指把一个事物的概念加到一个事物的概念上,对后者有所说明、扩展。而“存在”只是对规定的断定,并没有在规定之外对规定论述的主词有新的规定,可以说,存在是一个二级谓词。在上面的引文之后,康德讲到:“在逻辑用法中,它(存在)不过是一个判断的系词。”[16]存在这个系动词区分出主词(主语)和宾词(宾语),而宾词是主词的属性,被归诸于主词。比如在“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中,“人”是主词,“有理性的动物”是宾词,这个宾词被加到“人”这个主词上,是人的属性,命题中的“是”只是起连接的作用。如在“鸟是有翅膀的”这个命题中,有翅膀是鸟的属性。
“存在(是)实是的生活!”如何来理解这个奇怪的命题?我们似乎可以在存在主义那里获得一点启发。梅洛-庞迪在评论存在主义的时候曾指出,存在主义的优点恰恰是要在存在的概念中寻找途径来思考人的条件。“存在”是运动,通过这种运动人在世界上,人介入到物理的和社会的处境中,而这处境也即是人观看世界的角度。[17]
回到海德格尔的命题,存在如何是一个及物动词?谁是动词的施动者?谁是动词的承受者?冒号后面的这个分句指明了存在这个及物动词的宾语:实是的生活。谁是这个动词的主语?只能是此在。此在存在实是的生活。海德格尔在这里以一种形式显明的方式揭示出:有理性的动物并不是人的一种现成的属性,的动物也不是人的一种固定的属性,使用符号的动物同样不是对人的本性的刻画, 人的本性,如果可以称之为本性的话,是人在生活中,在一种操心的活动中,在这种操心中,人与世界首先与通常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世界之中生活,人对自己的存在,或者说,自己的属性已经有了在先的理解与解释。人的属性不是首先有待于实现的,而是首先被给予了,人安居于这种预先的理解中,人在这种预先已经被解释了的存在中运动,按照这种预先的解释而成为有理性的动物,或者的动物,或者其它。
此在存在实是的生活。在这里,此在既是主词,也是宾词,也是主词和宾词的联系。存在实是的生活,使实是的生活存在,去实是的生活,进入到实是的生活之中去。这个“去”,这个“进入”,是与那种客观的态度相对的,是对那些在生活之外旁观的人们说的,是对那些认为世界的首要意义是我们知识的对象的人们说的。而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特征,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此在与实是生活的同一性,此在的存在就是实是的生活。与存在主义相比,海德格尔这里确实认为存在是运动,然而运动不是人与生活的中介,人与世界的桥梁。人不是通过这种运动在世界上,而是,人的生活一直就是运动,此在一直就在世界之中,而且从后面的讨论可以知道,海德格尔这里的运动,在首先与通常的意义上,是被动的,而存在主义的运动是一种主动的运动,或者不做这样的区分。
海德格尔在此命题的最后用的是感叹号,克莱尔(krell)认为此感叹号是讽刺性的,表明的是实是的生活的既是我们自己的又不是我们自己的[18]。从此处的上下文看来,这个感叹号的作用应该是强调的作用,强调我们应该重视实是的生活,强调生活对此在的意义,强调存在作为及物动词的哲学含义。克莱尔所指出的实是的生活的双重性是存在的,但他对这个感叹号的的并不具有说服力。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思想无疑很有启发性,但他的表达方式却不尽理想,从他的思想出发,实际上,存在与实是的生活是同一的,这里生活应该作为动词来理解。海德格尔在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讲课中就是如此强调的。存在实是的生活,只能是一种同语反复。这种语言形式上纠缠显示出海德格尔思想上的纠缠,当时的生活哲学,尤其是狄尔泰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这种同语反复也暗示着他将要抛弃“生活”这个概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不再把生活(leben)作为一个根本的概念,“实是的生活”这个提法也被抛弃了,起而代之的是“实是的生存(existence)”,生存代替了生活,海德格尔在此时认为生活和人这个概念一样,已经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如果以生活作为核心概念,就会使人们联想到生活哲学,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19]
回到海德格尔的主要论题上来,实是的生活。谁不在生活?每个人都在生活。关键的是生活的方式,实是地生活。这样的生活意味着,生活“不是且从来不是,作为直观的对象和以直观为基础的定义的对象,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纯粹地认知并可以有知识的对象”。生活不是对象,生活是我们投身于其中的生活,是以我们的生命为注的一场赌博。我们所以一再引用此处,在于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根本倾向就隐藏于此。
这一根本倾向就是实是性与事实性的对立,非对象性与对象性的对立。海德格尔对德语中的很多介词非常有好感,经常在积极的意义上来运用,惟有“gegen”他深怀厌恶。对象,gegenstand,站在对面,首先设立了彼此的对立。与gegen相对的是“in”,在……之中,不是站在对面,而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里首先设立的是共属一体,对立则是之后的事情。这个in,在……之中,所表明的就是非对象性。所以海德格尔讲:“当下各自的此在的实是的生活就意味着:在一个世界之中”。此在的生活不是站在此在外面的,此在可以进行冷静地观察的对象,而是此在就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主客体的模式,意识和存在的模式,存在是知识的对象,意识是我思、是行为的中心、是自我,这样的模式是必须要避免的。附带地提一句,海德格尔在思想上与胡塞尔的不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仍然执著于对象性,执著于意识和对象的对立。
从上面我们所的段落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海德格尔所持有的以下几个原则:
首要的一点,就是上面所说的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根本倾向,实是性与事实性的对立,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对立,在……之中与站在对面的对立。
其次,从这种反对对象化的原则出发,是反对普遍化的原则,主张研究当下各自的此在。当下各自意味着停留于此,专注于此,不逃避,不从此处跑开。
最后,此在是自我关涉的,自我解释的,此在的存在即在这种解释之中。
这些原则显示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的批评指向,即主要是反对近代以来,尤其是当时,在精神科学中的自然科学倾向。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精神科学却停步不前,其原因在于精神科学的研究方式不对,认为精神科学也应该采取自然科学的普遍化、对象化的研究方式。海德格尔对此是非常反对的,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也专门用一节来与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近代以来以自然科学方式来研究人的存在的科学划清界线。
3.实是性概念的展开:在世界之中
我们在此节中将从上述的这些原则出发,来看一下海德格尔如何根据这些原则来展开他的哲学,具体地解释实是性,具体地解释实是的生活。
首先是对今天的与批判。
当下各自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今天”。今天说的也正是当下,我们的“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仍然对“今天”非常关注,在这部著作的最前面,《导论》之前的引言中两次提到“今天”。可以说,哲学只是今天的哲学,从今天出发,解释今天,唤醒今天。从存在论上讲,今天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生活在今天。
海德格尔在此文中所的今天的两个例子,也即此在实是性的两个例子,是以斯宾格勒(1880-1936)为代表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当时几乎是人手一册,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氛围。
在当时的历史意识(历史哲学)中,过去被客观化一些表达,成为了一个个的文化,这些文化具有统一的风格,这些文化如同有机体一样,有诞生,有成熟,有衰亡。在过去中碰到的是文化的多元性,所有的文化被摆在一起,没有哪一个文化比别的优越,应该一视同仁地对每个文化进行研究。这些过去被看作对象,理论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植物是植物学研究的对象,可以用图表来历史。斯宾格勒主张在历史学中进行一次哥白尼革命,即把历史从特定的观察者所持有的立场中解放出来,去除历史学中的个人偏见,主张研究人类的全部事实。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对待历史(过去)的态度完全是把历史对象化,可以称之为“好奇”(neugier),即完全被对象所牵引(zug),总是以客观的方式来报道历史事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东张西望,从不肯在某个地方多停留一刻,而是四处打量、走来走去,力图要看见每一个东西。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相反的概念是“停留”(aufenhalt),即有所选择,有所坚持,有所深入,在合适的地方品味良久,咬住不放,而不是走马观花。
当时的哲学倾向是空的普遍性:它的任务是定义不同领域中的存在的整体,这些领域中的各自的意识,以及这两者的统一。哲学的主题是普遍的,是一,是存在的整体,这整体包括一切和统一一切。在这种对待存在整体的方式中,主要是排序整理和组织,而排序整理的维度标准是不变的,高于被排序整理的对象,是超时间的存在。在这种整理中,哲学统摄了文化的总体,成为了诸种文化体系所构成的一个体系。在这种整理中,哲学看到的是各种类型,上述历史文化哲学所提供的各种风格。这种哲学是为了历史中的无时间性或超历史的东西而努力,越过单纯的主观而走向客观。这种哲学用“我们大家……”这样的论述方式来提供一种安定可靠,从而想要成为一个合适的避难所,来抵御无家可归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海德格尔认为在这种哲学研究的态度中,人的各自不同的存在被普遍化了,这种哲学的特征也是“无处不在而又无一处在”,在这里,观察者不是被对象所牵引,而是完全地无立场,完全地被自己所牵引,自己引导自己,可以在广义上称之为绝对的好奇。这种哲学所提供的“避难所”只是一个虚假的避难所,虚假的安全可靠,实际上是逃避生活,在生活之外设立了某种先验的东西。
在以上两种对此在的解释中,共同的是把此在作为客观的对象,可以不加任何偏见的加以观察,把此在普遍化为风格或类型。在以上两种解释样式中,有一种基本的现象需要注意,即好奇的现象。好奇,讲的是一种躁动(bewegtheit)。我们要注意这个概念从构词学上是一个被动态,海德格尔在这里展示出,此在是被推动的,被牵引的,此在虽然在运动,但这个运动并不是主动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出自此在的本心,虽然此在可以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但这里这个“想做”是因为一种外在的推动力,此在的这个声明只是表明了此在被一种公共的意见所控制却不自知,还以为自己的生活是有个性的。
就好奇而言,《存在与时间》中的一段论述可以使我们的理解更加清晰:“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仅止为了看。它贪新鹜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跳到另一新奇上去。……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好奇同叹为观止地考察存在者不是一回事。……好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此在在这种存在方式中不断地被连根拔起。”[20]
以上所述是海德格尔从否定的方面来批评实是性的对立面,下面我们来看他的正面论述。实是性的基本现象是“时间性”。“日常状态刻画出了此在时间性的特征。属于日常状态的是此在的某种平均性,常人(man)。在这里,此在的自己性和可能的本真性被遮盖了。”[21]
在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中,当下各自的此在的实是的生活就意味着:在一个世界中存在。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在之中?什么是在世界中的存在?世界是被碰到的,被遭遇到的(begegnet),是作为劳的(besorgte)世界,是离我们最近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个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有所操劳的存在,操心的存在。在操劳中,被碰到的世界展开了。在世界的展开中,世界作为工具,作为用具,用于……。在使用中,碰到的是顺手状态(zuhandenheit),而顺手状态构成了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
最纯粹的日常状态可以被称为:留在家里,在屋子里。这种在家停留,首要地与通常地来讲,不是要观察什么,而是忙碌于某事。在家中,不是如一个物在一些物中间,而是在家中劳作。海德格尔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细致的例子。在家里,我们碰到“一张”桌子。它是怎样被碰到的?人们可能这样来描述,它多重,什么颜色,什么形状,方桌还是圆桌,光滑还是粗糙,等等。海德格尔指出这描述的不是我们碰到桌子的原初状态,在最初和通常的意义上讲,我们最初碰到的是那张桌子(不是一堆桌子中的一张),人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写东西,吃饭,缝纫,做游戏。……它是一张写字桌,一张餐桌,缝纫桌,这是碰到桌子的原初主要方式。另外的例子,一双旧的滑雪屐,与一次大胆的旅行有关;一本书,是别人赠送的礼物,由某人包装的,或是一次不必要的购买等等。在首要与通常的意义上,在我们的周围世界,物从来不是与我们的切己生活无关的,而总是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与我们打交道,要我们处理。
世界的意义就是我们碰到世界的方式,它的何所为、何所用,这就是世界的此。而此在的实是性即是,此在向来已经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中。在操劳中,我们与世界交往、打交道,我们停留于这样的世界中。在我们的停留中,主要的事情不是把世界普遍化,把桌子抽象为作为共性的桌子,或者把世界对象化,把桌子作为知识的对象,作为诸种属性的集合。操劳,可以说是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而好奇则是操劳的一种样式,一种变化了的样式。
在日常状态中,此在有自己的爱好、倾向,有自己的习惯,这种倾向、习惯显示了世界意义的在先性。在这种对世界的熟悉中,人们与世界之间有一种去远的特征,即,此在对这个世界熟视无睹,既亲密无间又相距遥远。人们把自己锁闭在习惯与熟悉中,于是生活变得容易了。
作为日常状态的在世界之中和世界的意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述更为详尽透彻,在此我们不再过多地介绍海德格尔在此讲演录中的论述。下面我们就实是性这个概念的内涵来这篇讲演录的结构,以及《存在与时间》的结构。 [1] 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出版社,1995年;欧东明:《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突破》,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这篇论文研究了海德格尔在1919-1921三年间的四篇讲演稿;成官泯:《海德格尔对“再临”问题的时刻论阐释》,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该文研究了海德格尔1920/1921年冬季学期题为“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
[2]《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迄今已经出版了四辑,是在中国进行现象学研究和海德格尔研究不可不读的一份出版物,涉及到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主要有下面的几篇论文:载于第一辑的:张灿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概念》,张汝伦:《存在的实践哲学》, 洪汉鼎:《诠释学从现象学到实践哲学的发展》;载于第四辑的:梁家荣研究海德格尔1919年讲课稿的论文。相关的传记: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出版社,1998年。
[3] 克兹尔:《海德格尔的起源》,第3页,转引自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xx年。
[4] 实是性(facticity, faktizitat, facticite)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有多种,其多种取舍几乎可以和being这个概念的翻译相媲美。《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陈嘉映修订,:三联书店,1999年)译为实际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存在与虚无》的中译本(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将其译为“散朴性”,在其后的研究中,也将其译为“器物性” (王炜、周国平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卷九),山东出版社,1996年,第253页。)或“受蔽成存性” (:《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杜小真在对萨特的研究中,将这个概念改译为“人为性”,原因如下:一是强调萨特赋予这个概念的“人”的自由介入处境的结果,二是表示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这个概念解释上的差异,三是避免“散朴性”译名的可能含混的解释。(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山东出版社,20xx年,第143页。)在冯契、徐孝通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中这个概念译为“事实性”。其他的一些学者在论文中将其译为实存性、实然性等。本文译为实是性的理由是:首先在于它与事实性不同,其次在于它与事实性的相关性,实是性与事实性的音似与不同,也许,将其译为实事性可能更恰当,但学界一般把德文sache译为实事性,此外,facticity与存在(是)的紧密联系是我们的另一个理由。
[5] 海德格尔: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p.97.
[6] 海德格尔: gesamtausgabe, vol.12: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5), p.90; translated as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192, 转引自:同上书,p.92.
[7]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15;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p.12.
[8] 正是因为海德格尔哲学的这种创新性,所以洪汉鼎先生主张将hermeneutics 译为“诠释学”,以表明与从前的解释学的差异,而张灿辉先生进而主张将其译为“诠释”,见于上述的《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中的论文。两位先生的主张之根据无疑是符合海德格尔哲学之精神的,本文在翻译上的不同只是因为个人的语言习惯。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4-45页。
[10] 海德格尔把现象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把现象学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虽然“胡塞尔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自己仍然需要学习和发展。海德格尔在此讲演录里回顾了现象学的历史,对胡塞尔提出了一点具体的批评。“对胡塞尔来说,科学的理想体现在数学和具有数学本性的科学中。数学是所有科学学说的模范。……基本上,人们没有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偏见。把数学作为一切科学学说的模范是正当的吗?数学是最少严格性的学说,因为它是最容易达到的。精神科学预设了比数学家所能达到的多得多的科学存在。”他提出了著名的“先行具有”这个概念,指出“无立场”的想法是一个幻象, 无立场的看已经是一种看了。“人们必须从原初给予的东西走开,返回到它的基础。”
[11]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7;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p.5.
[12]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xx年。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5-66页,引文与中译本相比有改动。
[14] 这里虽然只是两个标点符号,但涉及到的却是本己与非本己、本真与非本真这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这里出发来尝试着构建海德格尔的伦理学思想。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实是的生活的双重性质,下文会有一点提及,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处于关键的位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需要做的一点说明是,首先要有生活与非生活的区分,之后才能有本真的生活和非本真的生活的区分,只有进入到生活之中,才能体会生活的秘密,只有深切地确知什么是非本真的生活,才能有足够的决心从中走出来,才能有足够的力量从中走出来。
[15] 英译者把jeweiligkeit翻译为一个复合词组:the awhileness of temporal particularity,他认为这个词至少有三个维度:特殊性或个体性;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会、片刻。
[16] 以上两处对康德的引证,均转引自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23-524,532页,海德格尔对此有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是阐发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在此不涉及。
[17] 梅洛-庞迪: sens et non-sens, gallimard, 1996, p.89.
[18] 克莱尔:the “factical life” of dasein in reading heidegger from the start, essays in his earliest thought, eds. t. kisiel and j. van bur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4, p.364, 上文中对“我们的”“自己的”两词上面引号的也借鉴了克莱尔的此篇文章。
[1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4页。
[2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00-201页。
[21] 海德格尔: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85;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 john van buren, 1999, p.65.
[2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74页。
[23] 卡普托:sorge and kardia: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al life and the categories of the heart in reading heidegger from the start, essays in his earliest thought, eds. t. kisiel and j. van bur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4, pp.327-343.
第三篇 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_西方哲学论文
摘要:伽达默尔有三种游戏理论。他关于一般游戏的学说可以概括为“自为”论:游戏是以自我表现为内在目的的自为活动。他关于理解“游戏”的学说可以概括为“融合”论:理解“游戏”是主体意识间互相参与融合因而具有再创造性的循环往复的精神交流活动。伽达默尔将艺术游戏看作理解“游戏”的典型。他关于艺术游戏的学说可以概括为“复合”论:艺术是感性与非感性相结合的复合意识的表现与接受活动,是复合性的理解“游戏”。伽达默尔的三个游戏概念之间以及相应的三种游戏理论的普遍性或适用面之间构成一种由大到小逐层包容的关系。
关键词:伽达默尔;游戏;理解游戏;艺术游戏;自为论;融合论;复合论
伽达默尔是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也是以谈论游戏著称的少数哲学家之一。由于伽达默尔的巨大声誉,他的游戏理论的知名度特别大。但除了少数专业理论工作者之外,一般人乃至相当一部分人文学者对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都不甚了了。为了便于人们了解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并在看清其实质与适用范围的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它,本论文将对他的游戏学说作出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他的游戏思想的总体面貌与内部关系。
伽达默尔是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他是在他的解释学著作中谈论游戏并在阐述他的解释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展开他的游戏观的。伽达默尔眼中的游戏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伽达默尔本人对于游戏的具体论述。
一、游戏的自为性、自我表现性与封闭性
目的论是看待生命活动性质的一种基本方。WWW.meiword.cOM对于生命体的游戏,伽达默尔也是从目的论入手去探讨它的性质的。他说:“儿童是自为地游戏,尽管他们进行表现活动”;“游戏是一种自行运动,它并不通过运动来谋求目的和目标,而是作为运动的运动”。1)(p140)在此,伽达默尔所说的“目的”其实是指(谋求外在事物的)外在目的(与康德等人对于“目的”一词的用法相同),而他所说的“自为”则显然是内在目的的另一种说法。可见:关于游戏,伽达默尔所持的是(与康德、胡伊青加等人一样的)内在目的论的观点。在内在目的论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还进一步将游戏的内在目的或自为性理解为自我表现。他说:“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selbstdarstellung)。而自我表现乃是自然的普遍的存在状态(seinsaspekt)。”2)(pp139-140)在此,伽达默尔将游戏看作是事物按其本性表现自身的活动。这种事物的自我表现活动自然是内在目的的。然而,人类的游戏有时会具有求避赢输与奖惩之类的外在目的,这种现象与伽达默尔的内在目的论的游戏观似乎是不相符的。对此,伽达默尔解释说:“人类游戏的自我表现,尽管像我们说看到的那样,基于某种与游戏表面的目的相联系的行为之上,但游戏的‘意义’并不在于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宁可说,游戏任务的自我交付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表现。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游戏者仿佛是通过他游戏某物即表现某物而达到他自己特有的自我表现。”3)(p139)在此,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的某些游戏中存在外在目的的现象其实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这种外在目的并非游戏的最终或真正目的,而是一种中间目的。相对于自我表现这一最终目的来说,这种中间目的实际上只是用来调动人的表现欲望和能力从而使游戏得以更好地进行的一种手段。可见:从目的论角度看待游戏的性质要从最终目的上去看,而不能从中间目的上去看;否则,我们就可能看不清游戏的性质。
人从事某种活动的目的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这种活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人的表现活动同样如此。伽达默尔说:“游戏并不为某人而表现,也就是说,它并不指向观众。……甚至那些在观众面前表现的体育活动一类的游戏,也不指向观众。的确,这些游戏由于要成为竞赛表现而面临着使自己丧失作为竞赛游戏的真正游戏性质的危险”。4)(140)在此,伽达默尔指出:游戏是表现活动,但表现活动并不一定是游戏。因为:只有自为的也即内在目的的表现活动才是游戏,而外在目的的表现活动并不是游戏。由此,即使表现活动在内容与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如果其目的发生了内在与外在的转换,那么,它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游戏与非游戏的转换。可见目的的内外在性质对活动的游戏性与非游戏性的决定性影响。
受胡伊青加的影响,伽达默尔也谈论过游戏的封闭性。只是,他所说的封闭性实际上就是指自为性。这种自为性意义上的封闭性,对于个人游戏来说是好理解的;但对于参与者已分化为表现者与观赏者的“游戏”来说,则不怎么好理解。因为:这种“游戏”中的表现者可以说主要是为观赏者而表现的;由此,从表现者方面来看,他的表现行为(主要)是他为的而非自为的。但伽达默尔认为:这种游戏的性质应该是相对于由表现者与观赏者构成的交往共同体来说的,而不是相对于其中的某一方来说的。如他所说:这种游戏“是由游戏者和观赏者所组成的整体”5)(p141) ;在这种游戏中,“通向观众的公在(offensein)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封闭性。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6)(p141) 也就是说,相对于由表现者与观赏者共同构成的共同体来说,这种表现与观赏相依互补的活动整体仍然是自为的或封闭的。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发现:对于表现者与观赏者已经分化的表现活动,伽达默尔有时说表现若是“指向”也即为了观众就不是游戏,有时又说正是观众的参与才使得表现活动成为游戏。可见:伽达默尔关于这种游戏的两种说法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实际上,这种矛盾的起因是伽达默尔在不同的地方谈论同一种游戏的时候发生了立场的转换——从个体的立场转换到了共同体的立场。在搞清楚这种立场的转换后,伽达默尔关于游戏的言论中所包含的上述矛盾也就可以得到消除了。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这种不加说明的立场的转换毕竟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因而是应该避免的。
除了自为性意义上的封闭性外,伽达默尔也与胡伊青加一样谈论过游戏在时空特征尤其是空间特征上的封闭性。他说:“预先规定游戏空间界限的规则和秩序,构成某种游戏的本质……。游戏活动的游戏空间是……一种特意为游戏活动所界定和保留的空间。人类游戏需要他们的游戏场所。游戏领域的界定——正如胡伊青加正确地强调的,完全就像神圣区域的界定一样——把作为一种封闭世界的游戏世界与没有过渡和中介的目的世界对立起来”。7)(pp137-138)对于某些(而非所有)集体游戏,人类确实会特意安排在某些专用场所(如剧院、体育馆、教堂等)中进行。这些场所在用途上的专用性以及相关的空间结构上的特征使得这些场所在人类的各种活动空间中显示出某种独特性。这种场所的专用性意义上的封闭性会成为发生其中的活动一种标志。因而,游戏空间上的封闭性可以说是游戏本质上的封闭性(自为性)的一种象征。
二、游戏的轻松愉快性与严肃性
游戏通常都令人轻松愉快。关于游戏的这一性质,伽达默尔说:“属于游戏的活动不仅没有目的和意图,而且也没有紧张性……。游戏的轻松性在主观上是作为解脱而被感受的,当然这种轻松性不是指实际上的缺乏紧张性,而只是现象学上的缺乏紧张感。游戏的秩序结构好像让游戏者专注于自身,并使他摆脱那种造成此在真正紧张感的主动者的使命”。8)(pp134-135)他还说:“游戏的真正本质在于使游戏的人脱离那种他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所感到的紧张状态”。9)(p138)只要搞清楚伽达默尔在此所说的“目的”是指外在目的,我们就可以理解:伽达默尔实际上是在用目的的内外在性来解释活动之所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原因——外在目的活动是被迫的,因而,主体的感受是严肃、紧张乃至痛苦;而游戏目的的内在性则使得游戏者不必受外在目的的强迫,因而感到自由、轻松和愉快。
由于游戏通常都令人轻松愉快,因而,游戏经常被人看成是不严肃的活动。然而,伽达默尔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说:“游戏活动与严肃东西有一种特有的本质关联。这不仅因为在游戏活动中游戏具有‘目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是‘为了休息之故’而产生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游戏活动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甚而是神圣的严肃。但是,在游戏着的行为中,所有那些规定那个活动着和忧烦着的此在的目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消失不见,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搀合(verschweben)……。作为游戏者,同时还意味着这种与严肃本身的关联。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所具有的目的。使得游戏完全成为游戏的,不是从游戏中生发出来的与严肃的关联,而只是在游戏时的严肃。谁不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10)(pp130-131)在此,伽达默尔指出:游戏也有它的严肃性。其中的原因,除了游戏也会间接地与外在目的相关联外,更重要的是游戏也有它自身的目的。而任何目的的实现都需要人们严肃认真地对待用来实现这种目的的活动。只是,相应于目的的不同性质,活动的严肃性也有不同类型。根据目的的性质,我们可以将相对于内外在目的的严肃性分别称为内在的严肃性和外在的严肃性。游戏的严肃性主要是相对于游戏的内在目的的内在的严肃性,但也间接地含有相对于人在其他活动中的外在目的的外在的严肃性的成分。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对伽达默尔的游戏观作一个初步总结:游戏是以自我表现为内在目的的自为活动。游戏令人轻松愉快,但人们对待游戏的态度仍然应该是严肃的。
伽达默尔关于游戏的上述论述基本上是与人们关于游戏的一般经验相一致的,因而并不难理解。然而,当伽达默尔在超出人们关于游戏的一般经验的层面上谈论游戏时,他关于“游戏”的言论就不怎么好理解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伽达默尔关于“游戏”性质的其他言论。
三、(理解)游戏的自我主体性
按照常识,游戏的主体当然就是游戏者——从事游戏活动的事物。然而,伽达默尔却说:“游戏的真正主体(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只有单个游戏者的经验中)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11)(p137)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为了借“游戏”概念来阐述他的解释学思想,伽达默尔赋予了“游戏”一词以不同寻常的新的涵义。当伽达默尔说“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本身”时,他实际上是将游戏解释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模式——个体之间互相参与、融合从而形成一个相依互补的整体的存在模式。在这种存在模式中,个体因为溶进整体而丧失了性或者说丧失了个体主体性,所以,在以这种模式进行的活动中可以说是没有个体主体的。由于这种活动中的个体行为只是整体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如果将整体行为称为游戏的话,那么,整体中的个体行为就不能称为游戏。如伽达默尔所说:“游戏者的行为与游戏本身应该有区别,游戏者的行为是与主体性的其他行为方式相关联的”。12)(p130)他还说:“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它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凡是在不存在任何进行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就存在游戏,而且存在真正的游戏……。游戏的存在方式并没有如下性质,即那里必须有一个从事游戏活动的主体存在,以使游戏得以进行”。13)(pp132-133)在此,我们看到:在伽达默尔的特定游戏观念中,具有主体地位的个体的行为是不能称为游戏的;相反,只有当个体自失于整体之中从而不再作为主体存在时,他与其他个体所组成的整体的活动才称得上是游戏。
用经验科学的眼光看,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活动总是有一个承担者的。如果将活动的承担者称为主体的话,那么,即使在个体不足以称为(完全的)主体的活动中,也还是有一个称得上主体的东西的,那就是由个体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所构成的整体。伽达默尔为什么不将作为活动承担者的整体称为主体,而要将这个整体的活动称为主体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伽达默尔本人对此的解释。他说:“胡伊青加注意到下述语言事实:‘尽管人们可以用德语说‘ein speil treiben(从事游戏)’,用荷兰文说‘een spelletje doen(进行游戏)’,但真正的动词乃是游戏(spielen)本身,即人们游戏一种游戏(man spiel ein spiel)。换句话说,为了表现这种活动,名词中所包含的概念必须用动词来重复。就所有这类现象来看,这就意味着,这种活动具有如此特别和的性质,以致它根本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活动。’”14)(p133)他还说:“游戏的原本意义乃是一种被动式而含有主动性的意义(der mediale sinn)。所以,我们讲到某种游戏时,说那里或那时某种东西‘在游戏’,某种东西一直在游戏,某种东西存在于游戏中。”15)(p133)在很多语言中,游戏一词的用法都具有一种被动中见主动的特性:当我们说“我们做/玩游戏”时,作为主语的游戏者所发出的行为,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包含在作为宾语的游戏之中。由此,在语用层面上,可以说,游戏总是将游戏者及其行为囊括于自身之中。用伽达默尔本人的话来说,也即游戏总是超越游戏者及其行为而成为主宰,如他所言:“对语言来说,游戏的真正主体显然不是那个除其他活动外也进行游戏的东西的主体性,而是游戏本身。”16)(p134)而“游戏的魅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17)(p137) 我们看到:伽达默尔是从“游戏”一词的特殊用法引出游戏的自我主体性的。这种用特定的语用方式来证明游戏的自我主体性的做法,不免让人觉得勉强。实际上,如果引进存在本体论的思想,那么,所谓的“游戏的自我主体性”就会更容易理解。我们知道:传统哲学在存在者的层面寻找世界的本源存在也即本体。然而,存在主义者却认为:具有定性的存在者都是在存在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存在之于存在者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优先性;由此,存在才是存在者的本源也即本体。与传统哲学相比较,存在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进行了一次视角或立场的转换,即从存在者转向了存在,从物体转向了事件;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说,是从主语转向了谓语,从名词转向了动词。这就是所谓的存在本体论。在存在主义的术语中,本体已经是事件而非物体。由此,站在存在本体论的立场上,游戏就可以看成是生成游戏者的活动,也即产生游戏者的事件本体。在此基础上,只要对本体与主体进行互解,我们就可以方便地得到游戏的自我主体性的结论。当然,存在主义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根据这种形而上学所得出来的所谓“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的结论也只能是一种脱离人们关于游戏的公共经验的形而上学,而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结论。实际上,当伽达默尔赋予“游戏”一词以“主体间的相融共生活动”之义时,他所说的“游戏”实际上已经成了理解——主体间的交流活动——的代名词。而他此时谈论游戏的用意也已不在于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人们称为游戏的活动的共性,而在于借“游戏”一词来表达他的解释学思想及相关的解释学艺术思想。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表白的:“我在艺术游戏中发现了诠释学的典型现象”18)(p83);“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而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19)(p130)他还进一步表白:在谈论作为理解模式的游戏时,“我们不探问关于游戏本质的问题,而是去追问这类游戏的存在方式问题。”20)(p131)
让我们注意:伽达默尔在阐述他的解释学思想时所说的“游戏”实际上是指理解活动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游戏,而这种作为理解活动的“游戏”正是伽达默尔所着重讨论的“游戏”。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游戏”的进一步论述。
四、(理解)游戏的参与性、再创造性与中介性
在将游戏解释成主体间的交流活动后,主体意识间的互相参与性就成了这种活动当然有之的内在属性,因为:参与是交流的基础。关于理解“游戏”的参与性,伽达默尔以戏剧为例说:戏剧“是一种本质上需要观众的游戏行为。……在观赏者那里它们才赢得它们的完全意义。”21)(p140)在伽达默尔看来,对于戏剧这样的表现者和观赏者已经分化的游戏来说,表现者单方面的表现活动是不能构成完整的游戏的;这种游戏的完整性有待观赏者的参与。而按照通常的看法,表现者的表现活动就已经是完整的游戏,观赏者的存在与否倒是不重要的。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看法是极为片面的。为了改变人们对于这类游戏的这种片面看法,更为了借此宣扬他的解释学思想,伽达默尔有意识地强调观赏者的参与对于游戏的重要性。他说:“游戏本身却是由游戏者和观赏者所组成的整体。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22)(p141)他甚至说:“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在整个戏剧[观赏游戏]中,应出现的不是游戏者,而是观赏者。这就是在游戏成为戏剧[观赏游戏]时游戏之作为游戏而发生的一种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使观赏者处于游戏者的地位。只是为观赏者——而不是为游戏者,只是在观赏者中——而不是在游戏者中,游戏才起游戏作用。”23)(pp141-142)在伽达默尔看来:“游戏是为观赏者而存在的,”24)(p142)或者说,表现是为了被观赏而存在的。由此,如果没有观赏者,表现也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表现的意义可以说是由观赏赋予的,因此,可以说观赏在整个游戏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无论如何,表现总是观赏得以可能的前提;对于表现与观赏已经分化了的游戏来说,它的完整性总是有赖于表现与观赏的结合。所以,片面地强调观赏在游戏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不合适的。对此,伽达默尔也心知肚明,所以,在说了上述偏激的话之后,他还是承认:“观赏者只是具有一种方上的优先性。”25)(p142)
我们不要忘了:伽达默尔在此所谈的游戏实际上是指理解活动。在此基础上,联系他的解释学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强调观赏在游戏中的作用,实际上还是因为他想借此来表达他的解释学思想。广义地说,任何符号产品的接受活动都是一种观赏活动也即理解活动。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并非是对作者原意的复现,而是接受者的精神世界与原作者或表现者的精神世界互相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说,理解实际上是理解者参与到被理解者之中去、从而使自身与被理解者都发生改变的一种再创造活动。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这种互相参与、融合的特性,必然使得理解活动表现出一种创造性或再创造性。
伽达默尔还将接受者对表现者所表现的东西的参与和再创造称之为“中介”。他说:“我们称之为构成物的东西,只是这样一种表现为意义整体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自在存在地,也不是在一种对它来说是偶然的中介中所能经验到的,这种东西正是在此中介中获得了其真正的存在。”26)(p152)在此,伽达默尔强调:精神产品必须经过“中介”——被接受、被参与、被再创造,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活着的或真正的作品。真正的作品,只能存在于参与者的“中介”活动中。如伽达默尔所说:“中介活动(vermittlung)和作品本身的无区别就是作品的真正经验。……中介活动按其观念是一种彻底的中介活动。彻底的中介意味着,中介的元素作为中介的中介而扬弃自身。这就是说,作为这种中介的再创造(例如戏剧和音乐[表演],但也包括史诗或抒情诗的朗诵)并不成为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是,作品通过再创造并在再创造中使自身达到了表现。”27)(pp155-156)在此,伽达默尔明确地将中介看作是再创造活动。这种再创造活动,既包括改编、表演,也包括阅读、观赏等。伽达默尔反复强调:只有在再创造者的参与或中介活动中,才存在真正的作品。如他所说:“在表演中而且只有表演中——最明显的情况是音乐——我们所遇见的才是作品本身,……作品本身是属于它为之表现的世界。戏剧只有在它被表演的地方才是真正存在的,尤其是音乐必须鸣响。……戏剧(schauspiel,此处被译为“戏剧”的“schauspiel”一词实应译为“观赏”或意译为“阅读”)活动不要理解为对某种游戏要求的满足,而要理解为文学作品本身进入此在的活动。……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中,只在于作为戏剧(同上,应译为“观赏”或“阅读”)的表现活动中。”28)(pp150-151)在参与性和再创造性的意义上,中介性可以看作是伽达默尔眼中的作为理解活动的游戏的根本性质,也是作为“构成物[生成物]”的作品的必要条件。在伽达默尔看来:作为构成物(生成物)的真正作品只能是以游戏也即理解活动的方式存在的。如他所说:“游戏就是构成物(考虑到理解活动的融合性或化合性,此处被译为“构成物”的“gebilde”一词[原义为“所形成的东西”]实际上可以更贴切地译为“生成物”) ……游戏依赖于被游戏过程,……反过来说,构成物(生成物)也就是游戏,因为构成物(生成物)……只在每次被展现的过程中才达到它的完全存在。”29)(p151)
五、(理解)游戏的转化性或同化性
何谓“转化”?游戏怎么会与转化相联系呢?如果依据人们关于游戏的一般经验,那么,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游戏与转化有什么关系。然而,在谈论作为理解活动的游戏时,伽达默尔本来就不是在人们关于游戏的一般经验的层面上谈论游戏的。伽达默尔在此所用的“转化”概念实际上还是用来说明他心目中的理解“游戏”的。
伽达默尔说:“我把这种促使人类游戏真正完成其作为艺术的转化称之为向构成物的转化。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游戏才赢得它的理想性,以致游戏可能被视为和理解为创造物。”30)(p142)在此,伽达默尔认为:是转化使得游戏也即理解达到它的理想状态并使理解的产物得以成为创造物。那么,到底什么是转化呢?伽达默尔说:“转化(verwandlung)并不是变化(veranderung),……发生变化的东西同时又作为原来的东西而存在。……转化则是指某物一下子和整个地成了其他的东西,而这其他的作为被转化成的东西则成了该物的真正的存在,相对于这种真正的存在,该物原先的存在就不再是存在的了。……向构成物[生成物]的转化就是指,早先存在的东西不再存在。……现在存在的东西,在艺术游戏里表现的东西,乃是永远真实的东西。”31)(pp143-144)从这段话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所谓“转化”大致相当于“质变”,而“变化”则是指未超过“度”从而事物还能保持自身性质的“量变”。那么,游戏或理解活动中的这种质变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伽达默尔说:经过转化,“原先的游戏者就是不再存在的东西……游戏本身其实是这样一种转化,即在那里从事游戏的人的同一性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继续存在。……游戏者(或者诗人)都不再存在,所存在的仅仅是被他们所游戏的东西。”32)(pp143-144)如果脱离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孤立地看这些话,我们会感到不知所云。因为所谓的在游戏中游戏者不再存在之类的话实在是太违背常理了。实际上,伽达默尔所谓的“转化”说的仍然是理解活动的融合性与创造性。经过融合,无论理解者还是被理解者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都不再是原来的东西;而且,无论理解者还是被理解者都不再自存,而是在融合以后形成的整体中以互相交融的方式共存。在理解活动中真正存在的就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不断融合并转化为新的整体性存在的过程。伽达默尔所描述的理解“游戏”的这种转化性非常类似于化学中的化合反应:两物化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事物——化合物。如:氢气与氧气化合生成水。在化合反应中,新的生成物来自于原来的两种事物,却已不再是原来的事物,而是一种新的事物,原来的事物在失去自身的同时又在新的事物中获得新生。伽达默尔心目中的作为理解活动的“游戏”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化合反应活动。由于理解“游戏”的参与者在“游戏”中都得失去原来的自我而在新的整体中以组成部分的方式获得新生,所以,伽达默尔说:在“游戏”(理解)中,并不存在(“游戏”之前自存的)“游戏者”,而只存在“游戏本身”—— “游戏者”之间不断互相融合并“转化”为新的生成物的过程。
由于伽达默尔所说的“转化”实际上是指参与“游戏”的各方互相同化从而形成新的整体性存在的过程,所以,为了便于理解,被译为“转化”的“verwandlung”一词实际上不如译为较为通俗的“同化”或者较为专业但却更为明确的“化合”。“转化”概念搞清楚之后,“构成物(生成物)”的概念自然也就清楚了:所谓“构成物(生成物)”就是两种意识相遇后所产生的“化合意识”,也即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意识”。因为“构成物(生成物)”是一种不同于原物的新事物,所以伽达默尔又称之为“创造物”。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伽达默尔所说的作为理解活动的“游戏”是一种精神现象,他所说的“游戏者”与“观赏者”实际上也只是指参与这种“游戏”的人的意识,而不包括作为意识承载者的人的肉身。由此,对于伽达默尔所谓的在“游戏”中“游戏者”不再存在之类的话,其准确的理解实际上应该是:两种意识相遇进入“游戏”(融合活动)之后,这两种意识原来的存在状态就不再存在。 六、(理解)游戏的同在性与同时性
为了说明理解“游戏”(活动)的特性,伽达默尔动用了多个概念从多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同在性与同时性就是伽达默尔用来说明理解“游戏”的另外两个概念。
伽达默尔说:“‘同在(mabeisein)’的意思比起那种单纯的与某个同时存在的他物的‘共在(mitanwesenheit)’要多。同在就是参与(teilhabe)。……同在在派生的意义上也指某种主体行为的方式,即‘专心于某物(bei-der-sache-sein)’。所以观赏是一种真正的参与方式。”33)(p161)在此,伽达默尔明确指出:所谓同在就是参与,也即理解着的精神与被理解的精神之间的融合。关于理解“游戏”的同在性,伽达默尔还说:“同在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主体活动而具有外在于自身的存在(aussersichsein)的性质。……外在于自身的存在乃是完全与某物同在的积极可能性。这样一种同在具有忘却自我的特性,并且构成观赏者的本质,即忘却自我地投入某个所注视的东西。……它起源于对那种事物的完全专注,而这种专注可以看作为观赏者自身的积极活动。”34)(p163)在此,伽达默尔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人在进行理解活动时所可能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实际上就是一般审美心理学中所说的“移情”状态。在“移情”也即伽达默尔所说的“同在”状态中,人会产生一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像是掉了魂似的体验。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忘我体验正是理解活动进入理想状态的标志。
如果说“同在”概念是从某种类似空间的(精神内容)方面来说明理解“游戏”是参与各方互相融合的活动的话,那么,“同时性”概念则是从时间方面来说明理解“游戏”的融合性。什么是“同时性”呢?伽达默尔说:“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构成‘同在’的本质。……‘同时性’是指,某个向我们呈现的单一事物,即使它的起源是如此遥远,但在表现中却赢得了完全的现在性。……同时性并不是同时存在,而是……要完全联系在一起地传达两件并不是同时的事情……,以使这两件事情仍然像某种现在之事(不是作为当时之事)被经验并被认真地接受。”35)(p165)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以理解者的已有的精神世界——内容、结构和期待为基础的,理解者总是从现时已有的精神世界出发去看待有待被理解的事物,而不可能以一种毫无内容、毫无前见的镜子式的纯粹意识去与有待被理解的事物相遇。由此,对过去时代的精神产品的理解,总是理解者以自己的现时意识内容、结构和倾向去同化过去的精神存在的过程。这种同化的结果,使得被理解的过去的精神存在总是呈现为一种现时存在。如伽达默尔所说:“作品产生于过去时代……。作品只要仍发挥其作用,它就是与每一个现代是同时的。”36)(p156)这种在对历史遗留物的理解中所出现的过去与现在同时的现象,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游戏”的同时性。总之,所谓“同在”与“同时”,实际上都是伽达默尔用来说明理解而非一般人眼中的游戏的性质的概念。现在与曾在同时,此在于彼在同在,这就是伽达默尔眼中的理解的真理。
七、(理解)游戏的循环往复性、变异性与同一性
前面所讨论的参与性、融合性、再创造性等是某一次理解活动所具有的性质。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接受者参与到同一文本中去的多次理解活动则具有循环往复的性质。伽达默尔说:游戏“总是指一种不断往返重复的运动,……诚属游戏的活动决没有一个使它中止的目的,而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中更新自身。往返重复运动对于游戏的本质规定来说是如此明显和根本,以致谁或什么东西进行这种活动倒是无关紧要的。……游戏就是这种往返重复运动的进行。”37)(p133)必须注意:伽达默尔此处所说的游戏还是指理解活动而不是一般的游戏。因为:循环运动其实是开放系统的普遍存在方式;具有耗散结构的生命系统的所有活动,实际上都是以循环往复的方式进行的。由此,循环往复性并不是游戏与非游戏的区别特征。联系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此处所说的“游戏”的循环往复性实际上还是在描述理解活动的某种特性,也即所谓“理解的循环”。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循环是重复与变化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永恒不变的圆周运动。就如大自然年年四季循环,但每一次循环中所出现的季节,都不会与以前有过的季节完全相同,而总是有所更新、有所变化。人的精神世界总是在增殖、在演变。而理解是人以当前所有的精神世界(内容、结构、倾向)为基础并以之参与到对象中去的具有再创造性的活动。这样,不同的接受者或不同时空中的同一接受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接受所产生的效果作品就都是有所不同的,这就是理解的变形性或变异性。如伽达默尔所说:“只要表现是指构成物(生成物)本身的表现,并且作为构成物(生成物)本身的表现被判断,表现就被认为是变形。”38)(p158)然而,伽达默尔又认为:同一文本在不同的接受活动中的不同表现在根本上又是统一的。这是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真正(实现了自身价值)的作品并非作者所创作的文本,而是文本经接受者的再创造所形成的主体间的精神融合物。由此,真正的作品只能存在于被接受的过程中。文本的每一次被接受都是其得以成为真正的作品的一次机会、一种方式。如果抽掉每一次被接受的具体形式及其所形成的真正作品的具体内容的话,那么,“文本的被接受”活动也即伽达默尔所说的“作品本身”是不变的,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游戏”的同一性。如他所说:“作品自身在变迁过程中显然并不是这样被成各个方面,以致丧失其同一性。作品自身存在于所有这些变迁方面中。所有这些变迁方面都属于它。所有变迁方面都与它同时共存。39)(p156) ……作品尽管在其表现中可能发生那样多的改变和变化,但它仍然是其自身。……每一种复现对作品本身其实是同样本源的。”40)(pp158-159)由于文本的每一次都有所不同的接受活动都是“作品本身”的实现方式,因而,理解“游戏”的变异性与同一性是统一的。这正如某一节日的每一次都有所不同的庆祝活动都是同一节日的实现方式:“节日庆典活动是一次次地演变着的……,虽然有这种历史改变面,它仍然是经历这种演变的同一个节日庆典活动。”41)(p159)总之:理解“游戏”是循环往复地进行的,循环往复的理解“游戏”是变异与同一的对立统一。这就是伽达默尔从历史的角度对理解“游戏”的理解。
综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游戏”的以上五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他关于理解“游戏”的观点简要概括为:理解“游戏”是主体意识间互相参与融合因而具有再创造性的循环往复的精神交流活动。由此,这种关于理解“游戏”的理论可以称为“参与”说、“融合”说、“再创造”说等。考虑到“融合”一词的概括性最强(融合活动必然包括参与性并具有再创造性),我们可以选择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游戏”的理论命名为“融合”论。
回顾我们关于理解“游戏”的讨论,我们注意到:在理解“游戏”中,伽达默尔还提出过一个“艺术游戏”的概念。为了较为全面地展现伽达默尔的游戏思想,在此,让我们对这一游戏概念也作一个简要介绍。概而言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可以表达为:艺术是感性与非感性相结合的复合意识的表现与接受活动,是复合性的理解游戏。 由此,我们可以将伽达默尔关于“艺术”或“艺术(理解)游戏”的学说称为“复合性的理解活动”论或简称为“复合”论。
讨论至此,我们清理出了伽达默尔心目中的三个游戏概念,即:一、作为自为活动的游戏概念;二、作为主体意识间的参与融合活动的理解“游戏”概念;三、作为复合性理解活动的艺术游戏概念。我们看到:自为论的游戏论是与人们关于游戏的一般经验相符的,因而,我们可以将它看作伽达默尔的一般游戏学说。而融合论的游戏论则与人们关于游戏的一般经验差异较大,因而,我们只能将它看作伽达默尔关于他心目中的特定游戏——理解活动的学说,而不能将它看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游戏理论(伽达默尔眼中的理解“游戏”所具有的性质大多是一般游戏所没有或不必有的)。由于互相理解可以看作交往共同体的一种内在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可以看作交往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目的,因而,按照伽达默尔的“自为”论,理解活动也是可以看作交往共同体自我表现与自我理解意义上的集体游戏的。由此,如果将作为自为活动的游戏看作伽达默尔心目中的广义游戏的话,那么,作为理解活动的游戏就可以看作伽达默尔心目中的狭义游戏,而作为复合性理解活动的艺术游戏则是伽达默尔心目中的狭义游戏——理解游戏中的一个小类,同时也是伽达默尔心目中最典型的理解游戏。伽达默尔心目中的三个游戏概念之间以及相应的三种游戏理论的普遍性或适用面之间构成一种由大到小逐层包容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注释:
1—17、(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8、洪汉鼎.理解的真理.济南.山东出版社,20xx.
19—4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第四篇 海德格尔其人其事_西方哲学论文
向一颗星前行-一唯此一星
——海德格尔《来自思的经验》
说起海德格尔,我先引用舍汉的一段话:
马丁·海德格尔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从许多方面看,他是个没有生平事纪的人。有一次他讲授亚里士多德,开场便说:“他生出来,他工作,他死了”。讲起海德格尔恐怕也差不多。他1889生于德国西南部,除了在马堡工作五年之外,一生都在西南部从事他的工作,1976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然而,在这八十六年扎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哲学界。海德格尔的生平事纪和他的思想历程其实就是一回事。他自始至终生活在他的思想中。所以,真正值得一写的传纪,只能是一部哲学传记,标出他思想的未源与发展。1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梅斯基尔希是黑森林东沿的一个农村小镇。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就在这个小镇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他的母亲也是天主。
海德格尔14岁那年到梅斯基尔希以南50公里外的康斯坦兹读中学,为将来舶牧师职业作准备。他在那里读了三年(1903一1906)后,转到弗莱堡的文科学校上了三年学(1906一1909年)。海德格尔后来说,他在这六年里学到了对他终生极有价值的一切。Www.meiword.Com他在这六年里学习了希腊文,此后,除战争年代外,他每日必读希腊原著。他还学习了拉丁文。他在这段时间培养起对诗人荷尔德林的兴趣,这位诗人的诗句将贯穿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1907年,海德格尔暑期回家度假时,康斯坦兹三一教堂的神父(后来的弗莱堡大主教)康拉德·格略勃,给他带来一本书。那是布伦塔诺的论文《论“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意义)。这本书启发了海德格尔的毕生哲学事业。
1909年,海德格尔到奥地利费尔德基文希的耶稣会见习。但几个星期后即因健康欠佳被辞退。此后他到弗莱堡大主教管区的研究班攻读神学。这里的指导教师仍是耶稣会教士。1909年秋至1911年夏,海德格尔主攻神学,辅以哲学。1911年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至1913年夏他一直留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那时他23岁,在阿尔图尔.施耐德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在他的大学学习时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曾参加新康德派哲学家里科指导的研究班,从而深受价值哲学的影响。他后末回忆说,当时实验心理学大有取哲学而代之的势头,于是价值哲学似乎成了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唯一支柱。对他深有影响的还有天主教的思辩神学。此外还有圣经解释学,从这里引发出海德格尔对一般解释学的关注。在他的大学读物中,我们还可以找出黑格尔、谢林、基尔凯郭尔、狄尔泰、尼采、里尔克、特拉克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他应征入伍.但两个月后即因健康欠佳退伍。1915年至1917年他在弗莱堡从事军邮工作。1915年夏他提交了(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作为讲师资格论文。这部论文与另一篇《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道为他赢得了在德国大学讲课的资格。据海德格尔自述,他在1915年左有找到了一条路。这条峰通向哪里他还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沿途近景。地平线不断转移,这条路时常变得昏暗。
早在海德格尔抛弃神学从事哲学之时起,他就想到哥廷根胡塞尔门下就学,但因经济窘迫不能如愿。事有凑巧,1916年4月1日,胡塞尔受聘到弗莱堡大学继承里科的讲座。于是海德格尔得以亲聆胡塞尔的指教。那时他白天在邮局工作,晚上则在大学里听课或讲课。
1917年海德格尔与艾弗里德.佩持蒂结婚。婚后再次应征入伍,在西线战场服役。1917年10月,马堡菲利浦大学的保尔·那托普教授写信给胡塞尔,告知该大学有副教授职位空缺,询问海德格尔是否具候选资格。胡塞尔在夸奖海德格尔的同时指出他还年轻,缺少研究和教学方面的经验。结果海德格尔落选,m·马待得到这个职位。
1918年,从战场回来以后,海德格尔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教,他在后者的指导下一面学习一面任教。他讲的课程多半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虽然他那时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熏陶,但他授课的侧重点却不完全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还原和先验自我这些现象学主导概念很少在他的课程中受到重视。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要独辟蹊径的倾向是有觉察的。但他仍然很器重海德格尔。1920年11月,菲利浦大学教职再度空缺,胡塞尔遂向那托普推荐海德格尔。结果还是落选了。尼可莱.哈持曼得到了这个职位。
1922年,那托普退休而由哈持曼继承职位。于是菲利浦大学的职位再次空缺。这一次胡塞尔更强烈地推荐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法讲解哲学史的成功也己为德国哲学界周知。只是他好几年始终没发表过什么东西。那托普把这困难告诉胡塞尔。海德格尔得知后,即把一份40页的手稿打印出两份。当时他正准备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七卷上发表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著作。这40页手稿即是这部著作的导论。打印好的稿子他自己留下一份,另一份寄给了那托普。
这份稿子不仅显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知识,而且表现出其哲学思想具有惊人的首创力量。这部稿子从未发表。读过原稿的哲学史家公认它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前身。那托普读了寄给他的那份稿子,不禁大喜,立即回复胡塞尔,盛赞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犹似发现了欧洲哲学的一颗新星。由于海德格尔当时大概同时在谋取哥廷根的一个职位,那托普遂大力担保海德格尔会被马堡接受,以防海德格尔它去。那托普写给胡塞尔和哈持曼的几封信上洋溢着他爱才之切的心情。
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职位。临行前他在黑森林的托特瑙堡山上与友人和学生办晚会告别。关于这次晚会,伽达默有生动的记载。2
在马堡时期,海德格尔开始撰写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专家们从他的早期著作,发表和没发表的,多方搜集线索以求确定这部巨著的来龙去脉。比较确实的是,海德格尔于1923一1924年冬在托特瑙堡自筑的别墅中开始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稿。1925年夏季的讲课稿《时间概念的历史》是《存在与时间》的清楚的雏形。1925一1926年冬季学期问,哈待曼将迁往科隆,海德格尔被提名继承正教授讲座。但按要求,他必须立刻有著述发表。于是,1926年1月29日至4月30日他隐居于托特瑙堡山间,把《时间概念的历史》这一讲稿的笔记整理成《存在与时间》的前240页。胡塞尔其问亦往托待瑙堡度假,与他讨论该书的主要概念“在世界之中”。两份稿子被寄往柏林候审。另一份稿子缀以鲜花、题着“以感激、景仰和友情敬献埃德蒙特·胡塞尔”,作为胡塞尔67岁诞辰的礼物。
送交柏林的稿子退回时批着“不足”。第二年2月,《存在与时间》正式印行,一是在《现象学年鉴》第八卷上,二是作为单行本。书一见世,海德格尔声誉鹊起。半年后,柏林颁发了正教授职称。
1928年11月,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辞去马堡的席位,回到弗莱堡大学继承胡塞尔的哲学讲座。当时他已声望甚隆,首次讲课便有280名学生听讲。然而,他与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
系却越未越不和睦了。
两位哲学家见解的差异早在20年代初就变得相当明显了。但两人的私交一直很融洽,两家人也经常互相走动。工作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已提到一些事实,可见出胡塞尔几乎事事大力提拔后进海德格尔。他很器重这位学生,常称“现象学,海德格尔与我而已”。3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也显得毕恭毕敬。他可以随时读到胡塞尔的手稿,有时也帮助老师整理稿子作出版准备工作。他们两人同领现象学,各有所长,胡塞尔喜好从体系方面穷究基本概念的结构联系而对哲学史既无兴趣也无专能。这后一方面却正是海德格尔的专长。
引起这两位当代德国哲学领袖关系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进入历史纪事的细节,也难确定各因素间的关系和比重。这里只提出三二事实,不敢妄下断语。
上面讲到,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以后回到弗莱堡,声望甚隆。例如1928年新出版的哲学期刊《哲学论丛》的第一期竟全期讨论《存在与时间》。年轻的马尔库塞在这期《哲学论丛》上高呼是《存在与时间》把哲学重新带回到现时代.而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4而胡塞尔在同一讲座上,却从未享此盛誉,这时更被海德格尔这颗新星的光芒掩盖。在哲学界地位的升降又与个人的经历缠在一起。一次大战给整个德国社会、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少评论家就是从当时德国的精神环境来解释海德格尔哲学的。确实.至少粗粗一看,《存在与时间》颇似表达出一种虽败犹荣宁死不折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德意志深层意识中的某种东西浑然应合。海德格尔那一时期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提高,颇有点时势英雄的味道。而胡塞尔却已年老。他有两个儿子,幼子在凡尔登之役阵亡,长子在弗兰德尔前线两度重伤。对风烛残年的胡塞尔来说,20世纪差不多就是末世了。
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也加深了。1927年,胡塞尔受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写“现象学”条目。他把写成的草稿交给海德格尔去修补。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任务,翻新重写,虽然也时时参照胡塞尔的草稿并尽量写得能使后者接受。结果,胡塞尔废弃海德格尔的稿子而单独提供了“现象学”条目。两位哲人时时或面晤或通信争论。在1927年12月的一封信里,胡塞尔断言“海德格尔还不曾掌握现象学还原的全部意义”。5胡塞尔虽然为《存在与时间》的定稿和出版出了很大力,但他既不喜爱这本书也不很重视它的内容。他警告海德格尔不要把哲学弄成了人类学。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偏离了现象学原则,是由于他的神学偏见,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后果把人们普遍驱向神秘主义。在海德格尔这方面,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多种提法本是很难接受的。他一心惦着“存在”,而这是胡塞尔从不感兴趣的课题。两人的哲学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一点胡塞尔后来才肯承认。“不幸我未能决定他的哲学成长。显然他在研读我的著作之际己经干上自己那一套了”。6
1928年,胡塞尔请海德格尔编辑其讲稿《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结果却很不满意。辑成的稿子于1929年发表,海德格尔为它写了一篇引论,写得实在敷衍潦草,对胡塞尔190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竟一字不提。同年,海德格尔把他的《根据的本质》一书赠献给胡塞尔的七十诞辰。7但此书中没有多少现象学的提法,有几个长长的脚注实是在与老师争论。另一本更重头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则献给了舍勒(schder)-一舍勒也是现象学者,却自立门户,因而与胡塞尔龃龉。这本书的题辞却明确称赞舍勒的精神具有“不受羁绊的力量”。该书的内容则离现象学的常调更远。这些书胡塞尔都读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啻己背叛了现象学运动。在他读过的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有胡塞尔1929年写的一句话:“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吾师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这幽默算是苦涩了。
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名地但也足够明确地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论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有点儿讽刺意味儿的是,这一期《年鉴》竟成了《现象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作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明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这些讲演多次重复,听众甚夥,又上了报纸。矛盾公开化了。海德格尔作为学生,先前作出受气的样子,这时也公然与老师疏远了。
1929年7月,海德格尔宣读了他的教授就职讲演《形而上学是什么?》。此文把存在、虚无和人的生存都连在一起,其内容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说毫无关系。这篇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了高度的正面反响。同时,它也指示出海德格尔今后的风格:他的思想将主要通过演讲和授课的形式出现,而不再通过系统著作的方式。
1930年,柏林长格里姆以学生和崇拜者的身分给海德格尔写信,邀请他到柏林任职。海德格尔拒绝了。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魏玛是信任的,他的倾向接近于新兴的主义。在他的课程中,对的关切明显增重。30年代初的德国,眼前似乎摆着一千种可能的选择但又仿佛毫无出路。成了全民族的首要问题。
从上面几页的记述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原来完全是个学者。他所处的社会,无非是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圈子世是从这些人里来的。不料终于把他卷了进去。
1933年4月底,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按照德国的传统,由正教授组成的校委会每年一度选举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首领,一年一选,但可无限期连任。校长名义上受州领导,但州实际上很少干预大学事务。学院自由是大学和两方面都引为高度自豪的德国传统。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纳粹学生组织多如雨后春笋,多方从事右派校园活动。1933年1月30日登台为总理后,纳粹学生更是肆无忌惮。那一年第一任弗莱堡校长是解剖学教授威廉·冯·莫棱多夫。他在4月16日就职后不到两周即被巴登长解职,原因想必是他曾禁止纳粹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反犹文告。解职当天,莫棱多夫与一些教授找到海德格尔.敦促他出面候补校长人选。战后的非纳粹化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披露,这些教授当时相信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将有利于保存部分学院自由和阻止纳粹党的极端破坏行为。晦德格尔同意出面,校委会一致通过。
就任第二天,三名纳粹学生到他的办公室来要求张贴反犹宣传品。海德格尔像前任一样予以拒绝。纳粹学生威胁说要向上级报告。几天后,冲锋队鲍曼博士命令海德格尔立即批准学生的请求,并暗示否则可能解除他的校长职务并关闭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仍未让步。他后来自辩说,这次冲突使他认为要保护学院自扎仅靠他的声望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从纳粹党内部未做工作。
后来,关于他和纳粹党的短暂合作传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查无实据,传碍却很广。海德格尔本人又一直对这段历史不置一词。他也不常有自传式的文字,并多次回绝为他写传的要求。他的沉默只有两次被打破。一是上面提到的:战后法国占领当局为防止漏网纳粹在德国占据要位,力促非纳粹化运动。这运动的一部分是调查纳粹执政期间与纳粹发生过牵连的人士。二是1966年9月,《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海德格尔,其主要内容即关于他与纳粹的牵连。这篇采访依海德格尔的要求于他去世后在1976年第23期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为题刊出。后者可看作海德格尔的自辩,前者是客观调查得出的报告。比较二者,事实方面是大致吻合的,虽然动机等问题永远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对这段厉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熊伟先生译出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8这时只讲个梗概。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有大量拥护纳粹的和与纳粹宣传合拍的提法。他讲到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命运的领袖和卫士”。他预告“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它由于消极而不真。这种所谓‘自由’的意思无非是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他把初入纳粹执掌的颂为“伟大壮严的破晓”。他列数德国大学的三根支柱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他提出要在纳粹运动提供的新可能性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海德格尔后来的自辩大致是说:改造德国大学的设想早已有之,那是与他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的基本判断连在一起的。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已经指出,科学如今纷然杂陈,只还靠大学从形式上维系到一处,而“各门科学在其本质深处的根却枯萎了”。9他后来仍坚持认为德国大学需要彻底改造。至于对纳粹执政的前途,他承认当时确抱有相当的希望。“我当时看不出其它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尤其是社会的态度,”10不过,这篇演说的基本调子却不是让纳粹来确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相反,是要主张让学术领导,让大学教导家。
1933年末地方大学生报曾引海德格尔的话说:“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海德格尔自辩说这是一种妥协,不这样说就无法继续他当校长的使命。但他也承认这不仅是装点门面,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作一种新事物,一种新的可能性。
传说海德格尔参与了纳粹学生的焚书运动,去除图书馆内犹太籍作家写的书,禁止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这些查无实据。海德格尔事实上禁止焚书,在他的研究班上不仅始终引用和讨论犹太作家,而且有犹太籍学生参加。
1938年海德格尔没有参加他的老师犹太人胡塞尔的葬礼。1941年《存在与时间》的第五版抽掉了给胡塞尔的献辞。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很微妙,前面已讲到了。海德格尔承认他来去参加葬礼无论如何在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井为此后来给胡塞尔夫人写信请求宽恕。至于抽掉献辞,则是出版部门考虑到禁书危险而要求的。作为条件.海德格尔坚持保留该书一条对胡塞尔深表敬意的注解。
海德格尔曾向纳粹首长进言讨论改造德国教育。他当时确曾指望上级能纳言施行。结果却未见任何行动。他不无气愤地自辩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和当时纳粹党的长谈一席话就该受到指责,而所有外国却正忙着承认并给他以国际通行的礼遇呢。”11
除这些自辩以外,海德格尔还强调了其它一些事实。他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以前是从不过问的。他出任校长是由同事们怂恿而成。他就任校长只有十个月光景。1933年底,他已看清,他要改革大学的设想由于大学同事的抵制和纳粹党的干预而不可能贯彻。他那时建议由几个年轻有为的教授出任几个学院的院长,未获通过。长则要求他批准两位由党指派的院长。他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声明如果部长竖持指派他就辞职。1934年2月,他果然辞去校长职务,并拒绝参加与纳粹党人新校长交接的典礼。1936年开讲的尼采课已标明与纳粹运动的分手。从此他受到纳粹的排挤、监视和。1944年夏被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挖战壕,他是被征召的教师团体中年纪最老的一个。而兔除500个最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战时劳役的名单上却不包括他。
在结束海德格尔和纳粹牵连的故事之前,还得插入一段他与雅斯贝斯的离合关系。
1919年,雅斯贝斯出版了他的巨著《世界观的心理学》,海德格尔为这本著作写了一份书评,后来人们认为这篇书评是他思的第一次系统表述。雅斯贝斯较海德格尔年长七岁,前六年已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巨著《一般心理病理学》,在哲学界远比海德格尔有名。但他从海德格尔的著述中认识到某种首创力量,遂主动结识海德格尔。虽然两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但对传统学院哲学的反对和对开创新哲学的要求使他们一相处便很投机。他们谈的最多的是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在学长面前话语不多,所以通常是雅斯贝斯滔滔不绝,虽然海德格尔也常插话,引称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这些人的学说雅斯贝斯所知不多。海德格尔精熟于传统,虽然两人似乎都是强调反传统的。对当时哲学泰斗胡塞尔和里科,谈话中也颇多攻击,主要是攻击他们那种学院派教授风格的治学讲学方式。而实际上,海德格尔却把他的主要著作敬献给胡塞尔和里科,这使雅斯贝斯觉得海德格尔不够真诚。又有流言传海德格尔背地里嘲笑雅斯贝斯的《大学观念》一文(1923)。而当面对质时,海德格尔则极力否认。
人们常说,作品是作家的亲生儿女。对其作品的态度.对著作家来说,往往更重于对他本人的态度。海德格尔对《世界观的心理学》所作的评论是圾为严厉的。何况,此书为雅斯贝斯与他夫人共同劳动的产物,难免使雅斯贝斯格外难过。海德格尔从来不与夫人合作著述的,对这一点恐怕很难体会。反过来,雅斯贝斯对《存在与时间》则毫无兴趣,认为它充满新词而无新意,从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虽然研究者们常能证明《存在与时间》对雅斯贝斯后来所著的《哲学》一书的影响。其实,两人的哲学思想本来相去甚远。仅就风格言,雅斯贝斯以灵感为凭而海德格尔一向都主张并实践其深思熟虑的方式。
30年代的纳粹风浪扎两入的关系终致破裂。据雅斯贝斯回忆,海德格尔以前从来流露出纳粹思想。所以,当1933年春海德格尔突然对纳粹运动大感兴趣,雅斯贝斯惊了一跳。春季的一天,海德格尔带了一张纳粹宣传唱片到雅斯贝斯家来放,并主张大家都投入纳粹运动。稚斯贝斯认为这种热情是很愚蠢的,但同时并不很把纳粹运动当一回事。所以他没作什么劝告。但这却是海德格尔最后一次拜访雅斯贝斯了。后来海德格尔卷入得更深,雅斯贝斯私下向海德格尔表示不快,海德格尔没有回答。于是雅斯贝斯以反犹为例力证纳粹之恶劣,海德格尔的回答是:“然而犹太人确实有一个十分危险的国际联盟。”当问到像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如何能领导德国的时候,据说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就看看希持勒那双手,多了不起的手。”雅斯贝斯没有继续与他争辩。他的夫人是犹太人,他害怕纳粹势力的。来往从此中断了很久。1937年,纳粹取消了雅斯贝斯的讲座资格。海德格尔未置一词。1945年后,海德格尔被战后剥夺了讲座后曾写信给雅斯贝斯请他为自己写推荐信。稚斯贝斯是否应承则不得而知。
由于雅斯贝斯一贯深信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他少不了想从海德格尔的著述中寻找其卷入纳粹运动的思想根源。但他没有找到。他不甘心,于是想与他重会。然而,这封要求会面的信从未到海德格尔手里。雅斯贝斯最终仍只好承认他不懂得海德格尔究竟要干什么。他只是相信海德格尔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一般都是非常迟钝无知的。
以上提供的材料远不足据以细致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牵连。不过有几点看法可以提一下。
海德格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者。无论他在著述中怎样对,历史对深感兴趣,甚至不乏上的深见,对于现实,他实在是个门外汉。不少学者,年复一年作着僻远枯燥的研究,心中却具存一团从事的。由于知识广博见解深入,往往还对自己从事的能力颇具自信。然而太过热心应帝王的学者,十之八九弄出不渔不尬的结局来。与学术的奇特关联,于此事实可见一斑。
但是,海德格尔之卷人纳粹运动却又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他一直厌恶平民,憧憬优秀人物主政的往昔,直到晚年仍明言不信任制度。纳粹运动确实颇合他的口味。即使在他对纳粹的实际发展失望之后,恐怕仍怀有不少惋借。研究者们早注意到一个事实:海德格尔后来虽愿辩清自己和纳粹的牵连,却从未正面谴责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深通的文化人士不多;然而大多数单凭其人道思想和人情态度,绝不肯同情纳粹的。你可以说这多数人恐怕太平庸了。可平庸有时竟是我们凡人最高贵的选择呢。
至于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问的所言所行,虽无什么可称大智大勇之处,我们经过的中国人或许也不会责之过苛。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四人帮横行的日子称为时代了。可是在初,多少饱经世故的成人却一面受着折磨一面欢呼着红太阳的新升?多少人曾捂住良心小心地俭举和揭发过亲近的人们?或至少对他们的普难冷漠置之?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海德格尔的又一重要阶段。很多学者相信他的思想正在经历一个转折[kehre],即从以人的生存来规定存在转到以存在规定人的生存。相应地,他对物、文艺、语言等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至于转折的深度和完成时期等,学者们的看法款莫衷一是了。本书在从各方面介绍和讨论海德格尔的思想时,时常会接触到这个转折问题。这里只愿提醒读者,本书介绍的内容有些是海德格尔早期主张而后来放弃了的。本书既从课题分章而不严格按照海德格尔思想的逐年发展为线索,故不可能处处详述每一观点的来龙去脉。不过,总体上说,读者应能从本书的进展大致看清楚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本书有时使用海德格尔“早期”“中期”“晚期”的提法。这些提法只为方便,不含学术评断。“早期”约指1930年前。中期指1930一1946年。
在转折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有《根据的本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是什么》,《真理的本质》,《人类自由的本质》。1935年完成的《形而上学导论》和《艺术作品的本源》可看作转折后的首批重要著作。海德格尔辞去校长职务后.专心于授课。课程内容非常广泛.最突出的则是荷尔德林诗的解释和尼采哲学研究。海德格尔一向以诠释经典著名;从《存在与时间》发表后,他更是不倦地研究西方思想史,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也多在这类研究中透露。他的几个基本主张是:
1)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思想是西方思想最纯正的源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思想弄成了哲学,弄成了形而上学。最初的形而上学虽还保持着希腊思想的伟大精神,但已开始掩蔽存在问题的最初源头了。形而上学的此后发展始终在旧框框里打转,而在黑格尔和尼采那里,形而上学达到顶峰,因而也完结了。哲学的时代过去了。
2)于此相应,酉方历史也是从希腊纯正源头的变异和蜕变。技术一步步地取代了思想,而今已形成了一整个由西方技术统治的时代。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神性的时代,而且一时看不出希望和出路何在。思的任务只能是尽可能揭示技术时代的本质以为神性重临作准备。
3)与思想联盟的唯有诗。因而海德格尔中晚期有大量关于一般诗性和具体诗作的讨论。
盟军解放德国以后,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牵连被禁止授课,直到1951年解禁。这段时期,海德格尔闲居在家,编辑旧稿成书,继续研究诗与哲学。这时期发表的《林中路》文集包括他三四十年代的一批最重要的中短篇文章。有时他也在小范围内讲演,例如1946年在里尔克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以《诗人何为》为题讲演。他这时虽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但他的学术地位已举世皆知。不仅有学生从远方赶来求教,而且学者们也开始了“海德格尔研究”。据一位当时会见他的学者描述,海德格尔的生活环境甚为简朴。“不多几本书。他与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大叠书写纸。他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这些白纸;我觉得,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受到打搅,以便让这些白纸铺上他的文字”。
1951年解禁后不久,海德格尔就退休了。不过他仍作为荣誉教授在弗莱堡授课和领导研究班。他从前的学生包括后来成大名气的伽达默、阿伦特等人。著名的海德格尔学者如比美尔、布格勒等人也都长期亲随梅德格尔研习哲学。学生们的回忆多有当时研究班的描述。据说单单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与亲聆他的授课,其所感所学是无法比拟的。学生们多认为海德格尔之为伟大的教师更甚于伟大的著作家。这也是古来大哲的们常有的。有时让人觉得,思想也像舞蹈一样,是活生生的演历,书中记载下来的,只是舞步的遗迹,就像照片上的舞姿一样。
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从前所著与当时所著大量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册《演讲与论文集》,包括四、五十年代的中短篇。论文集《同一与差异》,海德格尔自抨为《存在与时间》以后最重要的文集。《走向语言之途》,收集了四、五十年代论语言的六篇文章和谈话。《路碑集》,收集了四十年间的短文,标识着海德格尔思路的停顿与行进。20年代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30年代的《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40年代的《尼采》等大部头讲稿也是60年代和70年代发表的。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于出生地梅斯基尔希逝世,终年87岁。
回过头来读本节开首所引的那段话,我们可能各有不同的感想。海德格尔的外在生活确实是相当平淡的。难怪人们常把他与康德并比。革命性的思想,惊世骇俗之论,常常带着一份平俗的履历。存的人生活,有的人提炼生活。德国的教授和思想,法国的学生、主义、运动、时尚。海德格尔从来不承认他和法国存在主义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世人所知的海德格尔,却仍然是这场席卷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宗师。然而,哲人们其实也像我们常人一佯,有他们的悲欢离合,性情和品质,雄心与迷误。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经历与感想,当然只是小巧之见。但细读一人的著述,确实可见其人在其中的。 第二节 海德格尔对哲学的一般看法
海德格尔毕生从事哲学,几无它鹜。对哲学的情态构成了他一生的主情。把他对哲学的一般看法放在这一章应是适宜的。
据传说,希腊的第一位哲人泰利斯好审思天宇星辰。有一天,他仰视天空用心正专,不小心跌到井里。一个漂亮婢女在侧,见状不禁窃笑道:天上的东西,你都一清二楚,偏偏鼻子尖下的东西倒看不见。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了,和哲学一样古老。自柏拉图以后,凡听说过哲学的就听说过这个故事。柏拉图在这个故事后加详说:“凡事哲学者归曾、会被这般取笑。”12海德格尔也有句评论:“真正是个婢女的,也必得有点什么来取笑。”和柏拉图比,这一句有欠厚道了。笑笑就笑笑呗。
我们弄哲学的,闲话中说出自己的专业,别人就说:“哲郭?噢,那玩艺儿可是高深莫测。”我们文明人都讲礼貌,否则我们也会干脆听到嘲笑的。我们可能会想,而今科学昌明,商业繁荣,像哲学这样的老古董难免变得有几分迂腐可笑了。看起来,这嘲笑却是古己有之的。老子不是也说“下士闻之,必笑之”吗?从古到今,从东到西,都是一个样呢。被笑得多了,见怪不怪。不仅此也;迭一笑还成了认识真哲学的标记之一。“不笑不足以为道”呢。柏拉图的话说得一模一样。
这样想下来,海德格尔下定义说:“哲学即是人们本质上无所取用而婶女必予取笑的那样一种思”。13他接着申明,这还不是开玩笑,我们必须记住在哲学之途上,我们当真可能掉到井里而久不能寻到可以踏实立足之地。不是玩笑,这我们知道。因为海德格尔从来不开玩笑。哲学家严肃的很不少,但严肃如海氏者却不多。要思,更要思得透彻;而且,还要思得虔诚。
说起哲学一-。不,不是我们说起哲学,而是要让哲学自己发言。于是,自然而然我们就听到philosophia哲学说希腊语。这不仅是因为philosophie这个词是从希腊传下来的,而且更因为“‘哲学’就其本质是属于希腊的。”14
philosophia这个词来自philosophos。据考证,后一词的赫拉克利特铸造的。他所说的anerphilosophos说的却不是一个从事哲学的人,而是“爱智慧者”[hos philei to sophon]。“在他所使用的意义上,phile[爱]意味着homologein:道如道之自道,合道一道。”或:“像逻各斯有所言说那样言说,应和逻各斯而发言。”15这一应和与智慧谐响。谐响就是harmonia[和谐]。”相交相契浑然合一,这样的合谐就是赫拉克利持所讲的爱,至于sophon,他解释为:“一即万有”[hen panda]。这里的“即”把万有转送于一。一拢集万有。而存在者或万有就其之为存在者而言集拢干存在。“存在是拢集”一-是有所言说的拢集。16
海德格尔相信,一切哲学探索本质上必迂愚不合时宜。因为哲学要么远远超出当今,要么把当今回系到肇始之初。哲学不仅不会把自己弄得合时宜,它反倒是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无怪乎哲学不可能立即听到呼应。如果有一种哲学竟变得时髦起来,那它要么不是真哲学,要么是被误解滥用了。海德格尔自己的哲学应属于第二类。
我们但运哲学之思,便辞别了日常诸务。尼采说:“从不中止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这个人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这话改写成学院句式:“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17这一追问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发问完完全全是自愿的;若说有什么根据,它便神秘莫测地基于自由。哲学可谓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异乎寻常之问。”18
所以,哲学不可能像一门技术那样直接习得。我们无法直接应用哲学,也不能依其是否有用来判断它。但没用的东西仍可能是一种威力,甚至是唯一的真威力。一时得不到呼应的却可以正与一个民族的本真历史在至深处谐响,甚至作为这历史的先声鸣响。那不合时宜的自会有宜之之时。我们因而无能贸然判定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我们该从哲学期望什么。哲学之兴之进含者它自己的规律。我们只知道,在不多的几种可能的创造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必要事业中,哲学是其一。哲学以思的力量开辟道路,拓宽设置标尺和等级的真知,而一个民族全靠这种真知在其历史精神世界中把握和完成自己的实在。这种知点燃一切疑问,从而威胁一切价值观而又使估价成为必需。
哲学这一类本质性的精神形态与其它形态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就难免暖昧而遭误解。这些误解虽古已有之,而今则主要由哲学教授们(海德格尔说:“由我们这类人”)促生。哲学教授们的业务是把古来的哲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这项业务合情合理甚至不无用处。不过,它充其量只是哲学学术(philosophiewissenschaft),虽然它往往充作哲学本身的样子。
在种种误解中,有一种是对哲学要求过多。这种误解以为,既然哲学的鹊的是找到万物的根基,而这一寻求以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为途月阝么,哲学就该为一个民族提供建立其历史与文化的基地。如此奢求哲学常与对哲学的贬低联抉。例如,人们说,既然形而上学无助于为革命铺路,所以根本不要理睬它。这简直就像说因为刨床不会飞就该把它扔撑。殊不知哲学从来不能为历史事变直接提供力量和机会。“原因之一是因为哲学家永远只直接涉乎少许人。何许?创造性的变革家改革家们。”19通过这些人,通过不可预知钠种种途径,哲学渐渐传播开来,直到某个时候降为不言自明之事为止。当然。到那时,哲学中的原始力量早被遗忘了。
另一种误解则曲解了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起作用。有些人认为,哲学为众生建设世界观也好,为科学建立原理也好,反正它该指导实际的和技术性的文化活动,使它们变得容易些,发展得快一些。殊不知,“哲学究其本性从不使事情变得容易些,反而是使它们变得更难些”。20这还不仅因为在日常领会听来,哲学传达方式怪僻甚至疯癫,而且更因为哲学把存在的重担重新加到人身上而使它的历史存在变得更重更难。但沉重却是一切伟大事业,尤其是民族伟业得以生盛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对事物的真知贯遗人的现实,才谈得上伟大的命运。
哲学与哲学家恒处矛盾之中。真理是整全;哲学家却是凡人。要么超凡入圣,要么放弃哲学。骄狂与谦卑活在每个哲学家身上。哲学不提供救治之方。所以,哲学探索并不在寻求某些确定的答案。“思中持久的因索是道路。”21海德格尔钟爱道路这一提法,他在讲课时常建议学生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探索之途而非所讲的内容上。他表明他所讲的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一切是道。”22
对这条道路,海德格尔有百十种。这是条神奇的道路,上下求索,前行后退。而偏偏借后退才能前行。前行却不是进步,而是行到最邻近处。这邻近带我们退后.退到开端处。他又说起这道路不像街道那样按计划笔直修筑下去。“我几乎要说,思钟爱于修建婉蜒奇特的道路”。23筑建者不但回到从前的工地,甚至回头回得吏远。海德格尔不仅从不谈已达到的目标,甚至经常直盲连思的道路还未踏上。从而就有“通向道路的道路”,“辅路”这些。上节提到的海德格尔的著作,也常以道路为名称,如“林中路”,“路碑集”,“走向语言之途”等等。本书不准备专论海德格尔对道路的,只在这里引用《林中路》的题辞来标识我们通往他的哲学的起点: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行其是,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一条路和另一条一样。然而只不过看来如此而已。
伐木人和管林人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走在林中路上。24 注释:
1舍汉[thomas j.sheehan]主编:《海德格尔:其人其思》.chicago,1981.第1页。
2枷达默:《学习哲学的岁月》.frankfurt,1977,第213、233页。
3枷达默:《哲学解释学》,california, 1976,第7页。
4 《哲学论丛》第一期,berlin, 1928,第 16-17页。
5伍德豪斯[r·woodhaus]:《海德格尔批判》,berlin, 1981,第117页。
6 《胡塞尔书信集》,1970,the hague,第41页,1927.1.19倍。
7 《根据的本》首次发表于《现象学年鉴》1929年度增刊,第77一100页。除了刚提到的那篇简短引论.这是自《存在与时间》发表以后海德格尔第一次发表作品。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超趟概念和世界概念。
8 《外国哲学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
9 《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第194页。
10同上书,第194页。
11 《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第202页。
12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74a。
13 《追问物的问题》,第3页。
14 《什么是那-一哲学?》,第30页。
15同上书,第46页。
16同上书,第46页。
17 《形而上学导论》,第15页。
18同上书,第15页。
19 《形而上学导论》,第12页。
20同上书,第13页。
21 《来自关于语言的一决对话》, 第94页。
22第94页。《语言的本质》,第194页。
23 《来自关于语言的一决对话》, 第105页。
24 《林中路》,扉页。
第五篇 尼采的革命_西方哲学论文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当今西方非主义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影响范围冲破了那种通常把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分开的、理论与实践的传统界限。而且,他的学说已经在公众中广为传播,即使在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或从未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中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尼采本人的不为群氓写作的主张相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是一位自诩的颓废者、虚无主义者、无神论者、反教者、经院哲学的反对者,、平均主义和的严厉批评者。他拥护贵族的观念,坚决主张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他甚至劝说男人到女人那里去时要带上一条鞭子。对于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实存主义的神学家、教授、无主义的抽象理论家、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左翼批评家、平均主义的倡导者、和艺术上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敌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以及众多的当代运动来说,尼采今天即使不是惟一的权威人物,至少也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一个人。其中,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多数,似乎都曾经遭到尼采那无与伦比的修辞性力量的严厉鞭挞。
尽管家和评论家们没有在大众传媒中公开谈论尼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人们甚至会说:我们开始认识尼采的革命形象,但我们要按照他的本意去认识这种形象,而不是按照他那些修辞性、伪装的言辞去认识它;我们对尼采革命形象的认识程度决定我们是属于群氓还是被尼采所特别喜欢的司汤达称之为“幸福的少数人”的人。尽管理解尼采很不简单,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解的重要性,不仅仅基于学术的理由,而且关系到共和制的健康状况,它充分证明我们作出这种理解的努力是有理由的。wWW.meiword.cOm
在本文中,我试图以充分引用原文来支持我的的方法去明确表述尼采革命的基本要素,而不采用对细节进行综合阐述的方法,因为后一种方法将需要写一本很厚的书。在我开始披露总的情况之前,让我陈述尼采学说的基本成果。一种要求是由最高的、最有天赋的个人去创造一个由艺术家-战士组成的全新社会,这样一种要求是以美词丽句的力量以及一种坦率和含糊的独特混合体来表达的,以这种方法以至于允许普通人、愚人和狂人认为他们自己就是未来最高贵的人类中的神圣榜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求把毁灭现存社会作为它的前提条件;尼采在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自我毁灭任务方面成功地取得了无数人的支持,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未来乌托邦的名义进行的。对这一点这里不作详细阐述,人们可能注意到尼采的纲领和的纲领之间有非常相似之处。
我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尼采和都讲过,而尼采比更激烈,这是重要的。尼采主张:毁灭西方社会的第一个步骤不是战争,甚至也不是武装起义,而是倡导转变人类价值观的过程。正如黑格尔很有见地的指出的那样,我们是通过人们所崇拜的诸神来了解他们的。尼采宣称自己是异教的醉神狄奥尼修斯的门徒。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身实际上是异教的清醒神阿波罗的潜在门徒。不过,这种实情既不会削弱他的公开宣称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不会给人们将上述两种神混淆甚至等同的做法提供合理性依据。苏格拉底说,哲学是神圣的迷狂,我们决不能把这种迷狂简单理解为醉和醒的混合。醉汉的清醒是不可能精确地分辨幻想和真理的。
有人经常说或暗示尼采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虽然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了证实他不是保守主义者,我援引下面这段话:
有人对保守主义者悄悄地说——人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和今天知道的东西,人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在任何意义和任何程度上一种倒退的构成都完全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没有横行的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必须前进,也就是说,一步一步往前走直到堕落(我的关于现代“进步”的定义)。人们能够阻止这种发展,而且通过阻止发展来堵截并且搜集衰退,促使它更有力并更直接地衰退:人们不能有更多的举动。
这段话由于两个原因是有帮助的。这段话不仅把尼采的观点和保守主义的观点区别开来,而且它还简要地表述了尼采的革命程序。尼采的意图要加速现代“进步”所固有的自我毁灭过程,而不是鼓励回到某种田园诗般的过去。经过说服后自己认为是现代进步分子(甚至是后现代人)越多,就越来得快。然而尼采在他的激进贵族主义和反平均主义方面是一个右翼的革命家。诸如下述的几种说法基本上是有关美学的,这是真的:“在人们吃喝的地方,甚至在他们做礼拜的地方,通常都是发臭的。如果人们要呼吸清新的空气,他们就不该去教堂。”然而,当美感像尼采的厌恶情绪那样强烈的时候,美感就具有直接的后果,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生命的价值因而依存于它的无价值性。但是,这个说法使我们进入了尼采教诲的一个更深的层面。这位艺术家-战士的上述赞扬本身就是一种通俗的教义。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我们。世界是一个自生的艺术品。艺术是运用透视法对混乱变形状态作出的富于人性的和虚幻的感知。对尼采的酒神信徒来说似乎是自由的东西,对尼采的太阳神般的美男子来说却是amor fati,也就是斯宾诺莎的宿命论,或者是我们可以直率地称之为奴隶状态的东西。
尼采对人类存在的想象具有一种梦境,在其中某些人时常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决定他们幻觉的状态。到19世纪那时为止,在积极意义上统治着那种梦境的诸因素之特殊混合物,正经历着一个复杂的变坏过程。如果人们没有结束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将最终产生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称之为最后一批人的人们之千年统治。这些人的绝后状态 被这样的事实所表明,即他们的视觉不时被眨眼所打断,而且他们的演讲又不时被咯咯的舌音所打断。
有鉴于此,我们就能够对人们最经常引用的尼采这句话:“‘真实的世界’如何最终成了虚构的世界”的双重含义作出评价。在这段原文中,尼采概括地叙述了一个历史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由于柏拉图主义、教和近代科学的综合影响,智者对真实世界的信心逐渐地遭到摧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创世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不是价值的轨迹。指出这一点是有意思的:尼采因而把科学规律解释为柏拉图的种种理念,非常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 做的那样。当然,对尼采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它们是诗歌或人类意志的投影。“这段话在下面几行中达到了顶点:“我们已经废除了真实的世界,哪个世界还存在呢?也许是似是而非的世界……然而,不!我们已经把似是而非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一起废除了!(正午;影子最短的时刻;最长谬误的终结,人性的高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场白)。
最长谬误的终结与人性的高度同时出现;这就是说,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述,就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飞走了。极端颓废造就了这个最为极端的颓废者尼采,他又是一位能够洞悉生命本质的人,因而,他有机会通过促进价值观的转变去重新创造生命本质。这种“谬误”( 它也是真理)的顶点在尼采那里所起的作用和在主义那里的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完全否定是全新肯定的必要前提条件。不幸的是,尼采的否定原理并不是完全黑格尔式的;它并不在一种综合而且永恒的或循环的概念上达到顶点,而充其量不过是在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上达到顶点。简而言之,尼采是以一种神话取代了黑格尔的概念,这个概念和精神因而和上帝是同样的东西。先知或诗人取代了概念上的哲学家。
我们正是不得不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去理解尼采最著名也是最晦涩难解的书。我仅仅提供对基本观点的一些评论。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这本书超乎寻常的晦涩难解并非大部分由于它具有一种需要精心解读的隐匿意义,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种意义是故意造成而又必定是不完整和自相矛盾的。它不完整是因为它是对一种全新情况的预言,这种情况不仅无法清楚地加以描述,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依据尼采经过深思熟虑的估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全位于‘人类其他著述’之外”。根据尼采的说法,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永恒轮回。这种学说的意义是查拉图斯特拉和尼采本人共同的任务,即肯定“甚至恢复整个过去这一点”的行动。我要对死亡说:“那曾经是生活吗?那么,好!再来一次!”
查拉图斯特拉和尼采通过让我们抛弃对生活中痛苦和烦恼的不满,教导我们恢复人类存在的价值,去克服柏拉图主义和教(对民众来说是柏拉图主义)导致的天与地的。然而,不要把这种肯定说法与传统的斯多噶派或东方的消极态度混淆起来。这是实现追求力量的意 志所需的前提条件的另一个方面。假如我们不同意这个世界是价值的轨迹这个说法,我们就不能创造。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同意这个世界是无意义的说法,以便认识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自然界或上帝在创造价值。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世界最终出现的混乱过程中被改造的结果,或者用不同的话来说,因为世界只不过是追求力量的意志之投射物或景象,尼采在灵感过多的诗歌语言掩盖下,效法《圣经》的德文翻译,提出了一个高贵的谎言。
这种对永恒轮回的肯定与“对命运的爱”相匹配,必然是矛盾的,或者正如我认为的那样,是与这位艺术家,即新价值观创造者之具有同样渗透力的学说相矛盾的。人们可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题为“康复期的病人”的第三部分一个段落中有效地研究它们这种模糊不清的关系。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们(换句话说,并不是他的人类信徒们,而是对自然界最终作出虚幻解释的各个方面)就永恒轮回对他说出了如下的话:
“啊,查拉图斯特拉……对那些与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所有的事物本身正在跳舞,它们过来,伸出它们的手,大笑,然后逃走——接着又回来。诸事物去而复来;存在之车轮永远转动。诸事物死而复生;存在之年永远流转。诸事物散而复聚;同一座房屋永远在建造之中。”等等。
通过这一段话,正是这些动物对这种永恒轮回的学说作出了解释。查拉图斯特拉说它们是“丑角和手摇风琴”,通过这些东西他表明,它们各自永恒轮回的表现是大众化的,是与马戏团相适应的,滑稽的。他对这种学说的重述,强调他不是一见到人类的苦难就感到厌恶: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并非看到一点点人类的罪恶就感到厌恶。但是,超然的态度显然是脆弱的,查拉图斯特拉告诉动物们说:“我必须再歌唱,我为自己创造了这种慰籍和康复。难道你也必须立即把这种慰籍和康复变成一支绞弦琴的歌吗?”
这种动物关于永恒轮回学说的陈述与查拉图斯特拉的陈述之间惟一的真正区别就是:动物们使这种学说成为公开的或大众化的,而查拉图斯特拉却是把这种学说唱给自己听。我认为,这是尼采关于拯救人类的可能性方面自相矛盾心理的清楚标志。为了拯救人类,真理必须公开,而一旦真理被公开,它就会沦为国家的货币。
所有这些在本文中都是非常明显的。总之,查拉图斯特拉并非与他的动物们交谈,而是与他自己的灵魂交谈。正如他在早些时候所提到的那样:“最终,人们仅仅体验着他自己。”我们能够从这些本文中推断查拉图斯特拉并非真正与他的信徒们对话:这些信徒就像他的动物们那样,是他自己的创造或解释。他们就像是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与之交谈的人物。这样苏格拉底也是柏拉图对人类存在想象中的重新解释的虚构的产物。虽然柏拉图就像尼采一样是自言自语,但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有益于偷听者的交谈方式。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故意的和不完善的原因。象征着权利意志和永恒轮回的鹰和蛇,对查拉图斯特拉来说是合适(right)的动物,“而我依然缺乏合适(right)的人。”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在这个主题中最后的话。查拉图斯特拉没有真正的信徒,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颓废的时代。为了造就真正的信徒,查拉图斯特拉必须首先消灭他自己的时代,然而因此他也就消灭了他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同时又允许查拉图斯特拉的积极学说保存下来,这一点从未被解释,而且我认为也不可能被解释。人们最多能够说出的是,像尼采一样,查拉图斯特拉必须,把自己作为创造性的昂扬行动,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为了信仰的行动,投身于革命的极度混乱中去。顺便说一下,这对左翼的尼采主义来说,是直接的范式。
“同情!对高贵者的同情!”他大声喊道,而他的脸变成古铜色。“那么好吧,那高贵的人已经拥有过自己的好时光!我的痛苦和我对痛苦的同情——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关心幸福吗?我关心我的工作。”
“那么好吧,狮子来了,我的孩子就在近旁,查拉图斯特拉已经成熟了,我的时刻已经到了,这就是我的早晨,我的陶土正在碎裂:现在升起来吧,升起来吧,你伟大的正午!”
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着就离开了他的穴居,强壮而且容光焕发,犹如黑暗的山峦中升起的太阳。
查拉图斯特拉的著作是什么呢?尽管有永恒轮回的学说,但查拉图斯特拉既不能消极地等待也不能再创人们所期望的世界史的。正像我们再三看到的,他必须首先毁灭他自己的时代。如果没有信徒(其本身也必须通过美丽辞藻来被创造),那么这件事就无法做到。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具有破坏性的信徒们不可能与富有创造力的信徒们一模一样。革命的宠儿(而且这必然包括尼采20世纪的信徒们)必定死在创造性的、将要被一个孩子创造的未来之路障上:“可是我说,我的弟兄们,甚至连狮子也不能做到的,孩子能做什么呢?为什么捕食中的狮子还一定会变成一个孩子?孩子是天真和健忘的,是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个最初的运动,是一个神圣的‘是’。”这段话的意思不是指最初曾经是一头狮子,后来变成一个孩子的同一个人,而是指人的精神经历这种变形(正像那头狮子过去曾经是一头骆驼那样)。这就是尼采的历史哲学。
尼采声称查拉图斯特拉比他更强大,从而拥有尼采不拥有的对未来的一种权利。但是,我认为这仅仅意味着:查拉图斯特拉是美丽辞藻的创造物,尼采希望通过这个创造物来为宿命的未来铺平道路,他希望通过这个创造物来与命运认同,并且通过它去影响命运的结果。狮子和孩子的区别是带根本性的;那是毁灭者和创造者的区别。但是,尼采和狮子的区别肯定不是骆驼(三种精神形态的第一个)和狮子的区别。尼采是在人类类型学的普通范畴之外的;尼采像他关于自己说的那样,他是“遗腹子们中”的一位,“这些人们比当代人更难理解,但是他们的名声比较好。”
从什么意义上说,尼采是一位遗腹子呢?尼采作为这些倡导毁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承认他具有夸大的自我描述),难道他也不保证自己著作的普及吗?难道他不会像一个自我构造的法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那样复活吗?而且还要更彻底地说,如果他和他的著作达到了他们意图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消亡吗?难道尼采的真正信徒们不正是他虚伪的或普通的信徒们吗?
第二个问题还要人回答:未来的创造物会带来什么新的价值观呢?这是关于后历史的乌托邦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尼采像一样,属于启蒙运动改革者们的长队,那些改革者们正在回到现时代的起源阶段,他们要么设想进步将是有益的,要么坚持认为进步一定比有缺点的现状更好。在19世纪,信心最终变成了歇斯底里。
从我们研究中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至少能给予部分的回答。尼采认为,每段原文有无限可能的解释。再者,未来哲学家将会说:是“我的判断”,而不是“尼采的判断”。那么我们怎么能达到对尼采的各种原文正确地理解呢?回答这一问题惟一方法就是通过否定下述论题:作者的意图在一段原文所允许的各种理解范围内,是无法分辨出来的。我们终于能够把确定意思和无限解释之间的鸿沟弥和得天衣无缝,这是通过那种关于关键论题是故意含糊争论来做到的。如果以现时代为背景,那么,它们是不可理解的;例如,尼采对道德上的愤恨评论,实际上不是对愤恨的一种赞扬。然而,如果放到未来去考虑,诸如永恒轮回和追求力量的意志的关键论题,是与最有力的意志所选择的那些论题之任何来源相一致的。尼采的正面意思依存于他的解释者的说服力。 当尼采说每个深藏着的事物喜爱伪装的时候,或者说“每种哲学也掩盖着一种哲学;每种见解也是一个隐藏所,每个词儿也是一付假面具的时候”,人们必须从两种意义去理解他。第一,尼采通过出版来隐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尼采同时把深奥教诲和通俗教诲一起陈述。
但是,通俗教诲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致于它令尼采的大多数读者着迷,而尼采是想用深奥教诲说服合适的人们去促进那些着了迷的大众工作。第二,尼采的意思是:不存在任何用来认同对尼采的深奥解释的标准。读者们会发现他们自己的理解水平,是依存于他们所从属的那个“阶层”的。
通过结论,我们记住尼采拒绝太多的东西是有用的。除非存在着高贵人和低的一种自然的区别,否则,人们就不能区别正直和不正直,或者治和乱。要不然,就不可能存在高贵的虚无主义和低贱的虚无主义,或促进生活的非道德主义和使生活堕落的非道德主义之间的任何区别。关于这个微妙点,追求力量的意志太粗糙了,以致不能很好地启迪我们。
我们还应该了解,尼采对他不同性质选区的呼吁,包含激进的和保守的因素这两方面。一个共同反对现代进步自由主义的行动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了。在这里,有一个十分困难的教训,也许不最小心谨慎提防的话,就不应该予以接受。尼采比任何其他严肃思想家更有力地告诉我们:“公平竞争”,或者“了解别人的观点”,必然削弱我们对自己观点的许诺。特别是现在,我们不愿意看到,如果每个人都是正确的,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是正确的。
摆脱这个危险的两难处境之惟一出路就是:理解到不是乏味的平均主义,其本身是一种高贵性的表现,从而也是一种高贵人和低区别的表现。
我想重述上述的最后一点。生活不是数学,在数学里,普遍的正确性至少在原理上是能够获得的。我们不能采取一个无限制的方式一律地把数学科学运用于人类存在,来服务于一种维持自由、公正以及高贵人和低区别的一种学说。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正确性必然地倾向于在量方面被界定,用形式的准确性或作为一个函数来衡量。内容成了无关的东西。激进分子像保守分子一样清楚地知道这点。他们双方都反对人类精神的物性化,不过各自按照很不同的原则。保守分子想把传统作为高贵性宝库加以保存;而激进分子却想把他的高贵性表现在创造行为之中。然而,保存行动和创造行动都带来毁灭。
尼采通过撇开未界定的他那革命学说的内容,除了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求助于酒神陶醉的行动以外,他还能够征集来自反自由主义情绪的整个领域的信徒,左的和右的信徒。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着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构成最高阶层的人的诸因素。但是,为了理解尼采解释者中无论什么人都不能真正具有创造性,因为,“什么事情,都被容许”,所以,我们只需把尼采自己对平均主义的评论运用于这个学说就够了。高贵的虚无主义和低贱的虚无主义是无法区别的。尼采聪明的信徒们如今采取的惟一步骤是谈解释而不是谈伦理。
我要用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本章。我们怎么能弄懂尼采的意思呢?我建议的回答是:不把尼采看作一个存在论者,或一个不自觉的柏拉图主义者,并且也不把他看作是一个古希腊或意大利文艺复兴高等文化的反动代言人,而把他看作正是他想要(在很大程度上)加以严厉批评的那个启蒙运动的一个产物。尼采是笛卡儿、牛顿和伏尔泰的一个信徒。他清楚说明了启蒙运动中具有各种特点的因素之不一致性;即把自然界从朋友转变成敌人,真正地认同理性和数学,并且把上帝从救世主贬低为钟表匠。
然而,尼采也是歌德和斯汤达的信徒,他尊奉艺术家,而且,他本身也具有一种对令人陶醉的精确性和微妙性的美感。心理上的过度精益求精:“就非常优秀的人物而论,一切都是非常优秀的。”精益求精是对的;但是颓废也是对的,而且是一种孤独,这一孤独不是使他与他较高阶层伙伴及现代革命者结合在一起,而是使他与他们隔绝开来了。从这点来看,人们把尼采看作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家可能更有益。在某些方面,他可以与普鲁斯特相比拟,不过,他是按下述方式来做他的白日梦的,这个方式允许他去想象它们的最终的现实性。尼采的孤独将要在他身后被克服,正是因为,这种克服在广义上讲是的。普鲁斯特的孤独决不能被克服,因为这种孤独是向过去以求得到缓解的;它永远是一种幻想,像柏拉图的回忆那样,只导向理解,此外别无它物。
第六篇 恩斯特·布洛赫对梦想的分析及其他_西方哲学论文
内容概要 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在国内研究甚少,在深入领会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本文对梦想这一人生现象如何进入布洛赫的哲学体系、如何在这一体系中得到描述和,进行了扼要的阐述和简明的评析。梦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本真的,一种是本真的,布洛赫从本真的梦想出发,经过一系列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勾勒出一切梦想背后的动力结构,也即指向未来的尚未意识。尚未意识集中体现在希望这一期盼性情绪上。没有希望的人生,是可悲的,不值得一过的。布洛赫把希望和梦想,引入了主义。
关键词 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白日梦,尚未意识,希望
ernst bloch,utopian philosophy,daydream,not-yet-consciousness,hope
(一)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像卢卡奇那样和德国古典哲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却不停留于古典哲学;他像萨特那样对现象学方法深有体会,却不止于现象学;他像马尔库塞那样大量借鉴精神学的成果,却不限于弗洛伊德主义。西方主义一般都可归入某个较大的哲学流派,可以看作是某某思潮与主义的合流,而布洛赫却发展出了一套从研究领域上来讲是全新的哲学:乌托邦哲学(utopische philosophie)。WwW.meiword.cOm
乌托邦哲学以梦想作为自己的研究和阐释对象,这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布洛赫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寻找梦想中积极的因素,也即“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冲力,如希望、期盼等等。希望和期盼是人生最根本的动力,人们最不堪忍受的,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生活。然而,梦想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遭到排斥,它们被看成是无用的、荒唐的东西。“白日梦”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义(大白天做梦)。被生活放逐的梦想不得不遁入艺术领域,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都曾为梦想作过辩护,但是,梦想作为生活之别处(other place)的事实,并没有因此被改变。
自托马斯·莫尔发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1516年)以来,梦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进入社会领域。这类作品或描写神奇的异域,或描写未来的美好生活,以超越社会现有阶段为其精神归宿,以“乌托邦小说”这一特殊的文类流传于世。除开这一纸上议政的传统,在西方还有一系列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因其难以实现之故,常被人目之为乌托邦主义,或乌托邦(中译“空想”)。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现实领域,“乌托邦”一词常带有几分嘲讽的意味,u-topia,作为遍寻地图不见踪影之地,常和不切实际的空想联系在一起。
布洛赫在他的乌托邦哲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系统地纠正人们对梦想和乌托邦的偏见。在布洛赫看来,梦想或乌托邦并不是全然主观,全然虚妄的。作为梦想最真实、最核心的成分,“希望”(hoffnung)在布洛赫的哲学中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布洛赫看来,“希望的法则”(das prinzip hoffnung)是宇宙人生中最根本的法则,这一法则在《希望的法则》厚厚的三卷本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
《希望的法则》(das prinzip hoffnung),写于1938—1947年,修订于1953、1959年,该书的前两卷于1954-1955年在东柏林出版,第三卷于1959年出版,同年,修订后的三卷本由美茵法兰克福的suhrkamp出版社发行。这部鸿篇巨制标志着布洛赫乌托邦哲学体系的最终完成,作为一部关于梦想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媲美的宏大结构,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比拟的浪漫情怀。在这部著作中,布洛赫对人世间大大小小的梦想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阐释。
(二)
布洛赫把“小白日梦”(kleinen wachtr?ume)一章安排在《希望的法则》一书的开头,不是想靠文学性的描写先声夺人,而是另有深意,也即,对人一生的梦想作出描述,从而充分展示有待研究的对象。
所谓小白日梦的“小”,类似于小市民的小,小人物的小,小格局的小。所谓小白日梦,是指缺乏建构性的白日梦,普通人的散漫的白日梦。
布洛赫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命名为bericht,译为英文即report,意思是书面报告或新闻报道。这一部分是布洛赫提交给我们的一份报告,也即,关于人一生梦想的报告。不过,它不是一份万应的报告,它的时间跨度是晚期资本主义(但也谈到非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对象是小资产阶级(但也谈到无产阶级),用布洛赫自己的话来说,它是“关注街头巷尾的常人(den mann auf der stra?e)及未经规整的愿望的报道(bericht)”[1]。
布洛赫是从刚出世的小婴儿开始“报道”的,中经童年、青春期、青年、壮年一直到暮年。
人之初只是伸胳膊动腿,这时候的人和所有的生物一样,有一种盲目的“生命冲动”。对婴儿来说,饿了就要吃奶,得不到就大哭大喊。这种“要”以及“得不到”,使得孩子学会了等待。等待是一种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它开始突破黑暗的“此”(da)。随着孩子们能撕能抓,也即和外物打交道,一种“新”和“他者”开始萌动。到了能跑能跳的年龄,小孩子的愿望便更清晰了、更主动了,游戏把所有熟悉的东西转化为陌生的东西,于是“远方”的意义开始呈现。不过这时候愿望还不够强大,小孩子对陌生的东西还有畏缩的倾向,他们喜欢把自己藏在别人找不到的角落。然而即使在这里,也蕴含着某种希望:对自由空间的渴望。这时的小孩既渴望冒险,又害怕冒险,因此他们常常想象自己住在戒备森严的城堡中――从作业本上的涂鸦可以看出这种愿望的踪迹。
到了13岁左右,孩子们对户外的陌生事物有了更多的渴望。下课铃是他们最喜欢听的,只要一下课,他们就满世界乱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大谈特谈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即便是一个平庸的心灵,在这时节也开始对自己讲故事,讲一些关于好运气的简单寓言。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在此期间蓬勃生长,即使是傻乎乎的小鹅,也开始嫌弃自己的家,女孩子们把玩着自己的名字和发型,男孩子们渴望过上比父辈更为高贵的生活。他们就像格林童话中的小裁缝一样,出门找好运气,体验到禁区的诱惑,所有的东西都焕然一新。15岁的时候,出走的愿望就更强烈了,不过这多少带有一些婴儿期的逃避倾向。
17岁左右,对异性的向往出现了,人生进入了花季。一切都魔化了,像是霍夫曼的童话小说里写的那样,恋人所在的街道和城镇变成了黄金,无形的棕榈树荫庇着她的房子。异性是一个神秘的他者,是能唤起无数甜蜜梦想的他者。这是人生的早春,一切的东西都躁动不安,猛烈的痛苦和剧烈的快乐并存,极度的自尊和极端的自卑共生。这是一个做梦的年纪。
这时的梦不仅仅是关于爱情的,或者说爱情本身就灌注着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年轻人快意地用未来的远景折磨自己,只要能过上应该过的生活,过上迄今未曾实现的真正的生活,哪怕经历风暴、痛苦和电闪雷鸣也全不在乎。在青春的这个阶段,十分明显的是,唯有对未来的共同期盼,才是维系朋友关系的纽带。假如不再有共同的未来,友谊之花便会枯萎。没有什么比看到多年前的校友那样更令人感到无聊了,他们变得像教师,像孩子眼中的大人,像一切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东西。这样一种重逢给人的感觉是,青春时代的理想被背叛了。
这个时节,少女都有一本秘密的日记,大家都好点艺术,每个人都不甘平庸,都想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不过,真正能持之以恒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空有热情,或者像歌德说的那样,缺乏刻划细节的才能。这时候,一切的远方都显得美丽。慕尼黑或巴黎是寻梦的城市,每一个咖啡馆里的年轻人都梦想成为大艺术家。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资产阶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庸乏味。驱力瞄得更近了,也即,人变得更实际了。青春期的梦想被金钱挤走,成年人的白日梦多半是指向过去的,例如:“悔不该……”,“要是当初……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愿望本身并没有减弱,梦想的力量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小市民疯狂地追随纳粹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做着复仇和占有的梦,这种梦并不真正是革命的。如果没有别的释放机会,常人便把心理能量转移到春宫梦中,或者整天梦想当老板。在“副刊时代”,常人对新的追求,不过是好奇和赶时髦。这种新不是真正的新,而是一种重复,对这种“新”的追求,是一种上瘾。人们在街上逛来逛去,在商店的橱窗或走过的女士旁边做着白日梦。商品在闪烁,外衣迷人――这是镜中的白日梦。
人生如白驹过隙,无论在哪个社会中,老龄化都是不可抗拒的趋势。暮年就像严冬,但绝非没有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老了就彻底无用彻底多余了。但是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中,老人或许还象征着智慧和权威。此外,只要人活着,他就在做梦、就在期待更好的东西,即使老了也是这样。对于一事无成的老酒鬼来说,活着就是消磨和打发剩余的时光,对于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说,晚年却是收获的季节,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晚年比其他阶段包含着更多的青春,并在无法效仿的意义上,包含着更多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积攒的。老年人最后的愿望是休息,它穿透了老年所有的愿望。这种愿望属于另一个时代,那时每样东西还不是忙碌的商品,而更重要的是,它预告了一个不再忙碌的时代,也即时代。
看过布洛赫的这份报告,我们有以下两点感受:
1、人生处处有梦,白日梦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心理活动。
2、白日梦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有生气的、属于春天的,一种是坏的、无生气的、属于冬天的[2];一种是目标远大、不断有新在前方涌现、不断上升的、朝向未来的期盼,一种是鼠目寸光、沉沦于当下、沉迷于往事的不思进取。人生是这两种状态的混杂,大多数人,也即街头的常人,属于后一种――虽则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做过好梦,也曾有过理想和抱负。
在这最初的现象描述中,我们已经能看到各概念、各环节最初的勾连。在把这些环节彻底形式化之前,布洛赫首先对以往的心理学知识进行了和批判,借此为哲学的形式化工作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
在布洛赫之前,西方思想家虽曾注意到白日梦这种心理现象,但从未做过专题研究,直到弗洛伊德,白日梦才成为一个理论课题。不过,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中,白日梦仅仅是夜梦的一块敲门砖——“你们要记得我曾想借‘昼梦’来解决梦的问题。”[3]弗洛伊德借白日梦向人们说明,夜梦也是对愿望的满足(wunscherfüllung)。布洛赫肯定了弗洛伊德的这一结论,但他同时也指出了白日梦与夜梦的不同:
“与夜梦不同的是,白日梦可以自由地、重复地选取飘浮于空中的形象,可以是慷慨激昂、夸夸其谈,也可以是胡言乱语、痴人说梦,但也可以是酝酿和筹划。白日梦以一种松散随意的风格来进行自由的思想游戏,可以是思想,也可以是艺术、科学思想,而这种松散随意的风格可以说是与缪斯[艺术]和密涅瓦[事后沉思,玄思]相接近的。白日梦可以使灵感变得完备,而这种灵感无需多加解释、只需动手实施就行了,白日梦还可以建造空中楼阁、勾画宏伟蓝图,而不永远只是杜撰与虚构。即便是在漫画式的夸张中,白日梦者也处在与夜梦者不同的光亮中。”[4]
归结起来,白日梦具有不同于夜梦的三大特征[5]:
1、白日梦者有清醒、完整和自主的自我。即便白日梦者再放松,白日梦中飘浮的意象也不可能反过来控制他。夜梦者则受制于梦中幻象,以幻象为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主要原因在于夜梦中的自我过于孱弱,酩酊如泥,并向孩童期的自我倒退。
2、白日梦不是压抑性的,而是扩张性的。白日梦中的自我虎虎有生气,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错误地把白日梦的自我与孩童的自我等同起来。实际上,即便受创伤的童年自我偶尔会在记忆中渗透进来,白日梦的主体还是有理性的成年人的自我,甚至比其他活动状态下的自我更加强有力。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自我”在夜梦中充当着道德审查官的角色,布洛赫认为,在白日梦中情况恰好相反,自我在饱涨着希望的意念的鼓动下膨胀变大,道德审查基本上处于暂停状态。过分膨胀的自我如果失控,就会变成“妄想狂”(paranoia)。妄想狂与神经症(schizophrenia)不同,后者是一种自我退化现象,即为了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退缩到童年孤独而原始的自我中去,妄想狂与之相反,是自我的膨胀。布洛赫说,在未来设计师或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行列中,往往能找到妄想狂的影子,在妄想狂这种精神病症状中可以发现乌托邦精神歪曲了的形象。
3、白日梦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开放的白日梦往往不满足于虚假的满足,而是向前奔赴愿望实现之地,有如所说的那样,它要“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6]。开放的白日梦预感到人与世界的发展趋势,从而能更深地认识现实、批判现实,这是它具有更强现实感的原因,此外,它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为人设置了一个目标,鼓舞人们朝向世界的改善前进。布洛赫认为,这样一类梦是公开的,不需要像破译夜梦那样去挖掘潜意识中的隐念,只需进一步修正它们,使它们更清晰、更具体。
综上所述,白日梦有非压抑性、自主性、扩张性、目的性等特点。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白日梦者的自我是清醒的。这一自我不仅和求存驱力及发展驱力结合在一起,而且和理性以及现实并不矛盾。这一自我是属人的,与畜类蒙昧的意识有根本的区别,它跃出黑暗的当下,指向尚未到来的蓝色未来。
(四)
在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中,与夜梦和白日梦的区分相联系的,是对“不再意识”(nicht-mehr-bewu?te)和“尚未意识”(noch-nicht-bewu?te)的区分。
如前所述,白日梦这种心理活动是有自我的,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却很少意识到自己在做白日梦。在此,另一种意义上的“无意识”凸现出来,这种无意识与被压抑的过去无关,而是和正在酝酿着的未来有关;这种无意识的活动领域不是夜晚,而是白天,不是夜梦,而是白日梦,它始终面向做梦者本人所认为的新,甚至也面向客观上的新事物。布洛赫把这种指向未来的无意识命名为“尚未意识”,以区别于夜梦中指向过去的“不再意识”。
常人的白日梦是散漫的、遮蔽性的,为了把“尚未意识”这一深层结构揭示出来,布洛赫特意在《希望的法则》第15节的第3小节中谈到青春期、变革年代和创造性活动。我们不难体会到,为什么青春期的憧憬,变革年代的期盼,艺术创造中的神秘预感,会成为突显尚未意识的典型,这无疑是因为这些领域中的梦想更明亮,更有生机,目标也更为远大。这些更真更纯的梦想,向我们揭示出一切梦想的本质:期盼。布洛赫想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22岁那年就完成了一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稿:《论“尚未”范畴》(über die kategorie noch-nicht)。“尚未”,not yet,作为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范畴,牵引出“期盼”中最本质的环节,也即“朝向……未来”。
在诸多期盼性的情绪中,最明亮、最欢欣、最诚实者首推希望。希望是本真的期盼,它最有生气、最接近于明媚的春天――“希望,作为焦虑与恐惧的对立面,是一切情绪中最富人性、最适宜于人的,它指向最遥远最明亮的地平线”[7]。在布洛赫的术语中,尚未意识,乌托邦意识,期盼意识和希望,这四者异名而同谓,共同指向人生背后最深、最强的动力,它们是梦想最核心、最本质的成份。
人生之初直至花季雨季,一路躁动不安,生机勃勃,一步踏入社会却日显晦暗消沉,梦想的力量虽未减弱(心理能量总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其意向对象和意向方式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沉沦”于眼前事物的常人,其意向对象是现成在手的,或者说,是客观上不新的东西。在布洛赫看来,这种沉沦(即陷入“不再意识”)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因而不是永世长存的。然而,即便是满足于现成事物的常人,他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具有一种期盼意识。小市民之所以能够那么狂热地追随,其原因即在这里。在和平时期,热衷于赶时髦和寻找婚外情的常人也仍然是在寻觅某种新东西,尽管这种“新”刚一露面便已然是陈旧的了。
换言之,期盼意识或者说尚未意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属人的精神结构,它可以被遮蔽、可以被歪曲,但无法被彻底消除。尚未意识是驱力(trieb)中的驱力,它构成了人生最本质的动力。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哲学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发现‘尚未意识’并找到一套准确地标记它的符号”[8]。尚未意识是朝向未来的,乌托邦哲学因此可被恰当地称之为关于未来的哲学。
(五)
尚未意识不是一种锁闭在地窖中的无意识,它浸润在清晨的空气中[9],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是可以具有理性的。希望和理性相反相成,“理性离开了希望不能开花,希望离开了理性则不能发言”[10],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希望,也即docta spes[11],有教养的希望。在布洛赫看来,一旦尚未意识或希望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启蒙,它们就能够作为“乌托邦功能”(utopische funktion)发挥作用。乌托邦功能,也即“希望”所具有的预见功能和实践功能,它处在对“尚未形成”(noch-nicht-gewordene)的期盼和对真实未来的预见状态中,处在“尚未形成的美好(事物)”的成形过程中,它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间地带[12],它是“感受‘新’的有条理的器官,即将来临的事物的客观聚合状态”[13]。由乌托邦功能,可以产生具体的乌托邦眼光。所谓具体的乌托邦眼光,也就是和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远大而清晰的目光。至此,常人散漫的“小白日梦”已发展成为目光远大的“乌托邦”,也正是在这里,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开始和重视实践的主义发生联系。
布洛赫很早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用乌托邦哲学“补充”主义的任务。用他的话来讲,这是一个如何解决面包与小提琴关系的问题[14]。在早期著作《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人不能仅靠面包生活,人还应该有灵魂和信仰[15]。为此他试图把拉回到傅立叶,试图往主义里加入教神秘主义的成分,以补救一种排斥了梦想和乌托邦的“可悲而粗鄙的无神论”[16]。
事实上,面包和小提琴问题一直是布洛赫关心的问题。当他从神秘的内省转向客观可能性,从唯灵论转向主义之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取消掉,只不过更换了内容。在1930年代的文论以及论战中,这一问题和现实主义之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例如,在1935年写的《主义与诗》一文中,布洛赫对主义中的冷流,或曰“冷的主义”提出了批评。时代被新闻风格和自然主义占据,简单的现实主义扼杀了精神、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满怀的青年艺术家不满于这种现实,投奔到主义门下,却发现只有告别过去的一切,只有为革命牺牲想象,才能跨进革命的大门。
布洛赫认为,对待梦想的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它会把好的梦想和不撒谎的想象粗暴地拒之门外。与这种主义的冷流不同,布洛赫认为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排斥梦想,学说的要义是“形成和转变”,它惊跑了做梦者,却不会把清醒的想象赶走,清醒的想象原本就是客观形势的一部分,是革命行动的一部分[17]。换言之,梦想并不是美好生活的障碍,反倒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动力。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学生运动中,布洛赫所提倡的“暖”的主义曾如日中天,盛极一时,甚至有学生团体提出要将图宾根大学更名为“布洛赫大学”。图宾根大学曾是布洛赫思想盛行之处,令人感慨的是,关注乌托邦和乌托邦哲学者在今日的图宾根已为数寥寥。从1990年代开始,布洛赫的思想被陆续引进中国,近年来,国内对布洛赫的研究有逐渐增多之势。在一个“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的年代,布洛赫的哲学会不会重新挑起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呢?乌托邦终结了吗?关于这一点,我们一时还不好骤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梦想这一问题大概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梦想是社会人生中永远不可祛除者,对梦想的研究,在我国不是太多,而只是刚刚开始。 主要参考文献:
e.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c1959(英译本the principle of hope,three vol,the mit press,1986)
e.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bloch,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the mit press,1988
--------------------------------------------------------------------------------
[1]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导言。
[2] 用季节来比喻人生,不仅仅是布洛赫及尼采,《近思录》朱子注云:譬如天地只是一个春气。发生之初为春气,发生得过便为夏,收敛便为秋,消缩便为冬。明年又从春起,浑然只是一个发生之气。
[3] 弗洛伊德:《精神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5页。
[4]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14节,第4小节。
[5] 参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14节,第5-7小节。
[6]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7]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13节,第4小节末尾。
[8]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导言。
[9]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15节,第2小节。
[10]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55节,第4小节。
[11]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导言。
[12]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20节,第4小节。
[13] 布洛赫:《希望的法则》,第15节,第20小节。
[14] 参wayne hudson: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p13.
[15] 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第244-245页。
[16] 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第245页。
[17] 布洛赫:《主义与诗》,载e.bloch: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the mit press,1988。
第七篇 创造与心灵: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_西方哲学论文
内容提要: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之问”受到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往往只重视其中“心灵的伸展”这一向度,而忽视上帝的创造这一向度,忽视了永恒之维。我们认为,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这两个向度不可分割,前者规定后者,阐明时间的起源;后者反映前者,说明时间的存在和本质。但总的来说,后一个向度受前一个向度的制约。也就是说,心灵的伸展有一个界限,是不可超越的。当文德尔班强调奥古斯丁的形而上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时,他确认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心灵向度;当吉尔松称之为“皈依的形而上学”时,则是强调“心灵伸展的界限”,即永恒上帝的创造。
关键词:奥古斯丁 时间 永恒 创造 心灵
(一)
时间问题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除了存在问题外,恐怕没有别的问题能比时间问题更能把西方哲学从古代到现代如此经久牢固地贯通起来。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哲学在时间和存在问题上的贡献远比人们想象的重要而富有个性。我们暂且撇开存在问题不论,在时间问题的追问史上,奥古斯丁就做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以研究存在与时间问题而著称的海德格尔就曾在其演讲“圣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中这样开头:“在西方哲学中有三种关于时间本质的沉思是里程碑式的: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是奥古斯丁的;第三种来自康德。wWw.meiword.coM”([1](p.16)奥古斯丁被看作除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外最重要的三位伟大的时间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虽然不喜欢教哲学这个名称,但他却如此推崇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说明他认可其哲学家身份,至于奥古斯丁的教神学家的角色不容置疑,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可以推断,奥古斯丁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然而,我们事实上很难把他的思想区分得如此泾渭分明,说一部分是哲学思想,一部分是神学思想。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就体现出教哲学的特色。所以,我们在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时,就认可了教哲学这个称谓,论述时间的两个向度之水融关系,凸现奥古斯丁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个性化品质和突出贡献。
至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现代意义,除了海德格尔外,胡塞尔、罗素等人也都纷纷肯定。著名的现象学专家rudolf bernet说:“这一点(胡塞尔十分重视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的阅读)并不奇怪,因为他在其《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描述中,研究了奥古斯丁的时间及其所隐含的前提,并且可能深受鼓舞,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胡塞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的眉批和注释。”[2]( s.ⅺ)[1](s.16)
胡塞尔本人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时间意识的是心理学描述和认识论的一个古老包袱。深切感受到这里存在的巨大困难,并几乎为此付出绝望努力的第一个人是奥古斯丁。”[3](s.70)[1](s.15)
罗素曾经把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和他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si fallor ergo sum)”一起看作是作为哲学家的奥古斯丁最纯粹的哲学理论。他说:“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忏悔录》第十一卷是最好的纯粹哲学作品。”[4](s.434) 他还说:“比起希腊哲学中所见的任何有关理论,这个理论[时间理论——引者]乃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它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自从康德以来这种理论曾广泛地为哲学家们所承认——包含着更为完善、更为明确的论述。”[4](s.436)尽管罗素认为“奥古斯丁的主观时间说取消了上帝创造时间说”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教神学家蒂利希说:“从哲学上说,时间学说是他[奥古斯丁——引者]的最大成就,因为在这里,他真正开始了关于时间概念的思想的。”[5](s.180)
hans poser也说:“奥古斯丁的提问听起来很现代,而且的确如此,因为它不只在中世纪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例如存在主义、生存论与生命哲学那里,在海德格尔以及萨特那里,同样在柏格森、胡塞尔和ricoeur那里仍然具有主导意义。”[6](s. 27ff.)[7]
可以看出,作为中世纪思想前驱者的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在现当代获得了空前的声誉,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原本不像这些现代人所解读的那样是“纯粹哲学的作品”。他们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教哲学特征,把时间理解单一化为心灵的伸展这一向度,忽略了上帝的创造这一时间向度,即时间首先和万物一样来自永恒上帝的创造,这是上帝绝对自由意志的体现。因此,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最初的意图是要证明上帝的永恒和超时间性,为上帝的绝对自由辩护,即便心灵向度,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是绝对存在,上帝是超越时间的,只有人的存在才是在时间中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奥古斯丁试图通过时间的心灵化,也就是说通过把时间与人拉近来拉开时间与上帝的距离,从根本上把上帝从希腊人的物理学时间[作为自在之流的时间——引者]中解放出来。”[8](s.25) 可见,奥古斯丁时间观中存在两个向度——受造的时间和作为心灵伸展的时间,作为受造的时间,它与上帝永恒的超时间的创造相对;作为心灵的伸展的时间,它与人的存在与自由紧密相关。我们认为,前一个向度体现了上帝的预定,后一个向度体现了属人的自由、人的存在处境及其命运,两个向度之间是有张力的,即上帝的绝对自由与人的相对自由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关系自康德以来就被平面化了。正如hans poser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时间理论和永恒概念无关,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莱欣巴哈,无论是皮亚杰还是爱利亚斯[elias],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无论是bieri 还是deppert都不使用这个概念。”[9](s.17-50)尽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情况有些复杂,但康德起码在理论哲学中也在极力抽掉时间的永恒维度,只从纯粹理性的主观角度谈论时间,认为作为认识图型的时间是“先验想象力的产物”。这是和康德的哲学使命分不开的,他为了给人的自由进行辩护,竭尽所能,连本属于上帝的能力也归之于人了[吉尔松语]。因此,在康德那里,“时间只是人的时间。”[8](s.26)我们试图通过追述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希腊背景,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说明现代哲学家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理解有失偏颇,遗忘了其教哲学的身份,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还时间观之本来面目。
让我们先来看看希腊人是如何看待时间问题的。人们通常把希腊哲学的时间理解说成是物理时间观。我们侧重从时间与永恒的关系角度,考察一下这种时间观与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关联。
(二)
罗素在比较教与希腊世界观的差异时指出:“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不是受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相反,圣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4](s.434)。可以看出,希腊时间观的特征是由其宇宙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有什么样的时间观。
hans poser 指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和奥古斯丁就是一些规定着中世纪时间反思的思想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本质性的辨别框架。从一开始,时间和时间性在与永恒的关系中就被看作基本的对立一极。这分三个阶段:第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初始状况;第二是柏罗丁的新解释;第三是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9]
首先,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在描述造物主的创世时指出:“制造一个运动着的永恒的影像,于是他在整饬天宇的时候,为那留止于一的永恒造了依数运行的永恒影像,这个影像我们称之为时间。”[10](s.288)。简言之,柏拉图把时间看作是“永恒之运动的形象”。他认为,时间的出现伴随着“天”,即与开始创造宇宙一起出现,宇宙终结时它也结束。柏拉图之于奥古斯丁的意义在于:时间与创造的关系问题被作为主题加以讨论。例如,他说:“天是按照永恒的模型建构的,意在使之尽可能与永恒相似,这个模型是永恒的,所以被创造的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时间中存在。这就是神在创造时间的念头和想法。”[10](s.289)两段引文中已经隐含奥古斯丁时间问答的两个向度:创造的和心灵的。
亚里士多德为了反对柏拉图的时间观,在《物理学》中把时间看作是“不动的推动者和记数的奴斯”,规定为“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11](s.117)他在运动的范围内讨论时间。在第四卷中他就把无限制的因而也非受造的时间看成是循环运动中有一定比例结构、可以度量的东西。不过,这还是产生了与永恒的关联,但首先通过天体运动的确立而得以连接,这在《论天》中更明显。
当然,在时间概念的讨论中,对西方思想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发生在从希腊到中世纪的转折关头,这是通过柏罗丁出现的[7]。他既不同意柏拉图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运动形象”的观点,也拒绝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看作是“不动的推动者和记数的奴斯”的观点,而把时间规定为“世界灵魂的运动”。他认为,“时间不可能是运动,因为在时间中不可能有快或慢,而且被度量的不是时间,而只是一个时期”[12](iii.7.5.)[9] 。不过,时间也不可能产生于某种绝对静止的东西,因为(按照莱布尼茨的话说):“理念本身不活动,活动的是心灵(ideae non agunt, mens agit),因此,其形象就被看作无时间的生命,即灵魂”[12](iii.7.11.)[9]。而且,时间不在世界灵魂之外。hans jonas认为,“如果不安的心灵返回到其本源,那么,时间就会停止,而它的持存,只有在天的运动归于停歇的时候才可能。” [13] (s.295-319)[9]在柏罗丁看来,时间是不依赖质料及其运动的。
《九章集》第3卷第7章专门论述时间与永恒问题。柏罗丁认为永恒也是一个派生的概念。“永恒不再是什么基础的东西,而是似乎从基础的东西中流溢出来的。”[12](iii.7.3)[9]而时间也不是什么永恒的摹本。他解释道:“灵魂首先把自己时间化并作为永恒的替代物而创造了时间,可然后呢,它也使如此形成的宇宙处于时间的桎梏之下……因为既然宇宙是在灵魂中运动——因为除了灵魂外它没有别的运动场所——,那么,宇宙也必定在灵魂的时间中运动。因此,时间就是永恒借助于灵魂的自我运动的产物。”[12]( iii.7.11)[9]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把时间描述为其运动中由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形式过渡的灵魂的生命,那不是很好的说法吗?如果永恒不断地以同一性方式不变和完全无限存在,而时间是永恒的摹本,与我们的宇宙跟来生的关系相适合,那么人们必须在生命的处所那里开始另一种生活。生命具有灵魂的巨大力量。……在灵魂之外不能确定时间,正如在存在者之外很少能确定永恒一样。……时间就在灵魂中与灵魂共在,正如永恒一样。” [12]( iii.7.11)[9]
至此,希腊关于时间的考察已经越来越接近奥古斯丁后来的视野(心灵的伸展)了。在时间问题上,从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到柏罗丁再到奥古斯丁,遵循了自外而内再向上的发展理路。柏罗丁有句名言:“控制就是时间,宇宙在时间中。” “时间本身不是尺度。……就其本质而言,时间并不以度量为目的,它是非-尺度。宇宙的运动就是度量时间的尺度,时间不是运动的尺度,由于其本质,而只是附带性的”[12](iii.7,12)[9] 。
这样,柏拉图作为神话的“得穆革”为世界灵魂的精神性运动所取代。这种运动同时与时间一起存在。被创造的宇宙和度量时间的人都分有了这种运动。
(三)
以上是我们对希腊时间概念所作的一个概略考察。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时间观包括三个问题:时间是否存在,是什么,怎样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上帝的创造成为经验事实,时间的存在似乎是自明的;但是什么的问题却需要一番努力才能回答,这就是时间的存在和本质问题。
首先是创造的向度。他是在《创世纪注释》这一视野下提出时间之问的。预设上帝是最高的存在、万物的创造者,受造物是其最高存在的证据[vestigia des magnum est.]。时间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就是时间的受造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奥古斯丁时间观出现在第十四卷以后,因为那是“从时间出发理解时间” ①[1](s.21),似乎时间问题只和本卷14-28章有关,其实不然。我们暂且不说整个忏悔录(甚至奥古斯丁的全部思想)都和时间问题不可分,即便是第十一卷中,我们认为1-13卷同样重要,对于理解奥古斯丁时间观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和29-31章(包括12和13卷)一起构成了时间观的创造向度,它规范心灵主体向度的方向。
奥古斯丁在第11卷第1章开门见山:“永恒为你[上帝]所有” [14](s.231)。永恒只是上帝的属性,因为它是创造者,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时间。第4章的论见更为传神:“天和地存在着,它们呼喊着,他们是受造的,因为它们在变动和转化”(ecce sund caelum et terra,clamant,quod facta sint)。[14](s.234)天地通过呼喊来展现自身的存在,这种自身展现的就具有了现象学的特征②[1](s.19)。而且,“受造存在” 的属性表现为“变动[mutari]和转化[variari]”,而这种变动和转化正是天与地以及一切类似存在者的现象学特征。变动和转化意味着运动,而一切运动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这典型反映在下一句:“然而,不是受造的、但却存在着的东西,在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先前[ante]不存在、因而是变动[mutari]的和转化[variari]的。”[14] (s.234)两相对照,一切隶属于变化的事物,都是以前尚未是,以后将不再是的事物。以前和以后之间横亘着一个现在,这样的事物只有现在才是③。
这样,奥古斯丁从上帝的永恒与创世出发,论及世界(连同心灵)的受造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存在”。第五章讨论的是“如何”创造的问题。gilson指出,“在奥古斯丁眼里,世界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起源,或者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或者他以自己的实体创造了世界。”[15](s.332)按照gilson的,“从无中创造”意味着:“上帝想要万物生成,万物就生成了”[15](s.333),就是圣经上说的“要有光,就有了光”。正如奥古斯丁说的“因此,你一言而万物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14](s.236)道是永恒而无声的言语,与有声的变化的言语不同,无先无后,存在于一种不动的永恒中。这里的道也是元始(principium)。
总之,上帝意志是万物唯一的原因。上帝的创造是超时间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上帝的创造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上帝创造的时刻问题。奥古斯丁在批驳摩尼教“上帝在创造之前做什么”问题时,对上帝创造的时间性问题作了自己的解释。关于永恒与时间关系的论述,集中在第13章。他认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在天地创造之前没有世界,也没有时间,所以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那时候”在干什么的问题是无意义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上帝也不在时间上超越时间。“你是在永远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来到后即成过去。”“你的日子,不是每天,而是今天,因为你的今天不离明天,正如也不跟随昨天一样。你的今天就是永恒。” “你创造了一切时间,你在一切时间之前,而不是时间不在某一时间中。”[14](s.241)这段文字非常精当地反映出永恒与时间的复杂关联。
第一个向度集中地围绕时间与永恒的关系展开。dorothea günther指出,永恒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无限的时间,时间能否被理解为有限的永恒这两个问题,前者是伪问题,与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解相左,但后者却似乎是可能的。何以见得?
对前者的否定可以按照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如果说永恒是无限的时间,必然被设想为正在消逝的时间段之无限系列;其次,必然被描述为一个在自身中滞留的时间,即当下的滞留[nunc stans];而这和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是相左的。
但是,设想时间是有限的永恒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时间完全可能被作为“永恒的一瞬[vestigium aeternitatis]”[16](s.81)。奥古斯丁始终是从永恒出发演绎出时间的。追问时间的本质必须以寻找永恒为前提步骤,正如 dorothea günther引用hansgeorg bachschmidt的观点所表达的那样:“问题总是从上帝的永恒——对奥古斯丁是静止的顶点,一切都必然与之相关——这一本体论背景出发。这样,他也就在这种基本构想的指引下回答‘时间何以可能’这一形而上学的问题,并试图从永恒出发推演出时间的本质。”[16](s.81)这让我们想起费希特后来把康德的范畴从本原行动中推演出来,而奥古斯丁从上帝的创造行动出发进行时间推演,要比费希特早了整整1400年。而康德尽管非常强调时间在纯粹理论理性中的作用,但对其出身始终未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演。“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而且影响深远,但若没有永恒这一维度,也就到不了本质的问题。
蒂利希也是从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上理解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的。他说:“奥古斯丁认为,创造与保存是同一个事物;世界一时一刻也不能于上帝。实在的形式、规律和结构并不使它成为一个的实在。这使得上帝和世界这两个实在的一切神的固定成为不可能。上帝是持续不断地与世界相关联的根据。”[5](s.180)世界之存在的根据就是上帝及其创造行动。所以他接着说:“说到有限性是存在和非存在的混合物,或非存在呈现于任何有限事物中时,我就是与奥古斯丁关于任何事物都处在不可度量的虚无深渊的危险之中的陈述有关系。” “时间对上帝是无效的。时间如何在创世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时间是与创造世界一同创造的;它是世界的形式。时间也和空间一样,是事物有限性的形式。”[5](s.180)。
(四)
11卷前13章主要讲了永恒与时间的关系,阐明了时间的受造本性,从而和希腊的物理学之自在时间告别。从14章开始,奥古斯丁通过时间的心灵化转向完成对希腊物理学时间观的更加彻底的形变。“时间就是心灵的伸展”这一回答不仅把时间的存在和时间的本质区别开来,更使人的存在和本质区别开来。时间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其存在已然是事实,但是,其本质却是开放的,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时间经验中存在,原罪和救赎表现了这种开放性,彰显出人的自由意志与时间的内在同一性。当然,这种开放性说明人的本性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并非没有自由可言,它完全可以“充分伸展”,但是,这种伸展毕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来自于时间的第一个向度。所以,无论心灵怎样在时间中伸展,都注定是要回归上帝怀抱的,正如《忏悔录》第一卷第1章中所讲的那样:“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14](s.3) “时间的心灵化”这一转向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自由意志问题进入哲学的视野。
于是,奥古斯丁给自己的任务是要“克服”(remotiv)这种时间的受造存在,即消解上帝存在乃最高存在这一预设,构造一个非受造的存在概念,这样,他就从“内在时间性”入手,建构其哲学的存在范畴。这一任务分两个步骤完成,14-20章时间的存在与不存在;21-28章是讲时间本质问题。
在第14章中他就根据日常时间经验以否定的语气提出:“可是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14](s.242),要给出“是什么”的回答的确困难,但“是否存在”的问题不难回答。所以他自信,时间是存在的,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尽管时间本身受制于时间性的事物。“没有过去的事物就没有过去,没有到来的事物就没有将来,没有现存的事物就没有现在。”[14](s.242)也就是说,在日常时间经验中,过去的东西和过去、现在的东西和现在、将来的东西和未来之间还没有分别。如果什么问题涉及时间的存在,那么就必须搞清楚,这里的存在概念有何含义。“因为一过去,就不存在。而只能说:这现在的时间曾是长的,因为作为在场存在者它曾经是长的。既然它尚未过去,以至于未存在过似的,而且因此曾经是那种能是长的东西,但是,随后已经过去,同时不再是长的,因为它不再存在。”[14](s.243)可见,奥古斯丁把时间的存在定位于现在,时间的不存在指过去和将来。
但是,这样会产生一个困难,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时间之存在性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把时间三态统统转换为“现在时”(也是现在是),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种时间都纳入心灵中,作为现在的三种不同方式,即现在的记忆、现在的知觉[注意]和现在的期待。奥古斯丁把他的时间问题直接和我们各自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表象相联系。这就表明:我既没有过去,因为过去正在过去;我也没有将来,因为将来还不在我面前。我之存在的一切是我存在之当下[gegenwart meines daseins]。 可是我应怎样才能说到“长或短”的持续呢?很清楚,这不仅是存在问题,也是认识问题,涉及一个正在认识的主体。
奥古斯丁总结道:“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是,既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本来不可以说有三种时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也许在本来的意义上可以说,有三种时间,过去事物的现在,现在事物的现在,将来事物的现在。因为这三者都存在于心灵中,我在别处看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注意,将来事物的现在是期待。”[14](s.247)记忆、注意和期待这种认识论的概念对理解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时间的心灵化转向,其实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之“在时间中的存在”,这种在的方式便是记忆、注意和期待。这三者反映了三一上帝的形象,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呼应上帝的永恒,人不能成为永恒,却期待着、希望着永恒。
真的要回答出时间之伸展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时间的度量问题。如前所述,时间与变化有关,而变化的含义就是延伸,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一种形相到另一种形相,其过程表现为时间三态。可是,“既然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则过去和将来如何存在呢?现在如果永远是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现在之所以是时间,是因为它走向过去;那么,我们怎样说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时间走向不存在,否则,我便不能正确地说,时间不存在。”[14](s.242)在此,奥古斯丁区分的是时间与永恒,现在作为时间的存在性是因为它的变化——成为过去和将来。这有些费解,其实从中引出了时间的长短问题,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如何度量时间。第15章中用归谬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长的,尤其是现在的长短问题,他通过现在的一百年、一年和一天,进行了时间的无限划分,最后说,“现在是丝毫没有长度的。”[14](s.244)也就是说,在理性思辨看来,任何时间都没有长短,因此是不可度量的,但在经验看来,时间是有长短的,起码过去和将来是有长短的,因此,时间是可以在现在进行度量的,这样,就可以说形成了时间度量问题上的经验与理性的悖论。关于时间是否可以度量的问题,周伟驰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17](s.179-181)。通过时间度量问题的推论,最后得出核心结论:我在度量时间时,既不是度量过去,也不是度量将来,也不是现在,因它们统统没有长度;我度量的是时间本身。可是,我用什么来度量呢?是用或长或短[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或快或慢]吗?不是,我是用心灵的伸展去度量时间本身,所以,他说“时间是心灵的伸展”[14](s.253)。而且,“因此,我所度量的不是已经不存在的字音本身,而是固定在记忆中的印象。”[14](s.254)从时间度量过渡到时间本质问题,从度量时间到度量记忆。而记忆、注意和期待既然是时间三态的心灵伸展,那么,时间除了是心灵的伸展外,就不是别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和柏罗丁不同,奥古斯丁试图把一个物体的运动和时段的度量分开,尽管这是二重的。度量时段的每一个尺度都是相对于被选择的标准而言的,因静止把时间理解为单纯的伸展[extensio]。相反,在度量时间时仅涉及心灵中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14](s.254)
前面我们说到时间的存在问题,虽然奥古斯丁当时试图通过把过去和将来转换为现在而使时间获得存在性,建构出哲学上的存在概念,但直到第28章,这个任务才告完成。他说:“将来尚未存在,怎样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经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这是由于在心灵中有三个阶段:期待、注意和记忆。所期待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认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待已经存在于心。谁否认过去已经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于心中。谁否认现在没有长度,只是倏忽即逝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14](s.255)核心思想是:时间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心灵的伸展。
这就是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第二个向度。然而,当奥古斯丁试图通过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经验去认识时间时,似乎就没有给永恒留下空间。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我们自身是在时间中经验永恒,即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之“永不消逝的永恒”,永恒的事物就是时间中的无时间者,这就是上帝的永恒。“在永恒中没有流逝,而整个就是现在的;但是,没有什么时间整个就是现在。”[14](s.240)在此,奥古斯联系自己的经验:“一切过去的事物都被将来排挤出来,而一切将来都产生于过去的事物,一切过去和将来的事物都是出自永远的、受造的现在。”[14](s.240) 因此,伴随着一种持久的现在经验而来的就是这种观点,我们在此“匆忙中抓来的是永远保持的永恒之光辉”[14](s.239)。这正是全新的、完全变化了的理解时间问题的入口处。我继续经验到时间,同时经验到无时间性的现在,这种现在在其无时间性中注视着永恒。这种无时间性的现在,同时就是上帝创造的现在!上帝“并非在时间上在先”,而是“在持久现在的永恒上先于一切过去的事物,并且跨越一切将来,因为它是将来,当它到来时,即将成为过去。” [14](s.241)
奥古斯丁的论证在这里与柏罗丁类似。因为在时间前没有空虚的时间——说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干什么,是可笑的。时间伴随着创造、在创造中存在,只有在创造中伴随创造,时间才使得上帝之永恒和人的有限性之间充满张力。这是奥古斯丁一贯从有限性出发而得出的一个立场。他认为,在无时间的现在之把握中就已经暗含着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把握我们的有限性和上帝的永恒两者,不论这在其永恒的重复中被思想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还是被看作时间性的扬弃。但无论如何,这种时间不是单纯的度量单位,而是完满实现了的现在性——即上帝的现在。于是,kreuzer巧妙地总结道:“上帝永恒之现在不是时间的他者,而是其内在形式。”[7]
(五)的确,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第二个向度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脱离第一个向度而存在。当奥古斯丁以这两个向度和希腊传统世间观告别的时候,心灵化时间却始终无法摆脱时间的受造身份,心灵的伸展有个限度,这就是创造的限度,人的在时间中存在,就是以记忆、注意和期待的方式,或者“存在、认识和意志”[14](s.295)的方式存在着。然而,这种存在方式充其量是内在(immanent)的,而不是超验的(transzendent)。时间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在奥古斯丁的存在论秩序中只是相对的存在,只有上帝的存在才是绝对的,才是“大有”(magnum est)。如前所述,时间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关,心灵的伸展体现了属人的意志[不只是意志,还有存在、记忆、理解、期待和爱],永恒之现在与上帝的意志有关。正如他说的:“只有你是绝对的存在,同样,只有你才真正认识。……我的灵魂不能光照我自己,也不能浇灌我自己,因此只有到你生命之泉边,同样也只有在你的光明中能看见光明。”[14](s.301-302)在谈到心灵伸展的限度时他这样说:“任何时间,任何受造之物,即使能超越时间,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①[14](s.257)
对此,hans poser指出,“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再次在时间与永恒的紧张关系中达到了高峰,不过是在完全交付给近代的一个自我在其作为其存在意义建构的时间经验中的主体化中达到的。于是,不仅是奥古斯丁的问题,而且他的解决方案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中世纪思想,尽管是以世俗的形式。因为如果意识是时段的唯一居所,而且,如果时间的设定是通过上帝发生的,那么,一种彻底的世俗化只能是:把时间设定本身改设为现象的可能性条件,正如(在康德那里)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在与范畴的图型化的联系中置于主体,而且,从那里出发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人是什么?”[7]
我们认为,这种认识相当深刻,也很准确。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把握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定位及其对后世可能的影响,防止被人主观地误解。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充分估计到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跨时代意义之后,话锋一转,立即指出:他自己的时间意识纯粹是现象学的,排斥客观时间的纬度,即排除本来在奥古斯丁那里的前提性条件——时间问题的永恒维度,因而造成了永恒与时间之张力关系中的“短路”现象。不仅在他这里,在康德和海德格尔那里,都缺少了永恒的维度。康德暂且不论,因为他的哲学和教之间的关联还是不好确定的。不过,海德格尔就比较明确,从他反对教哲学这个术语一直到他改造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解,都可以看出他的哲学品质,是向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复归。他把上帝的永恒仅仅理解为更本源的和“无限的时间性”。他把传统时间观中的永恒转换为他的时间性概念,这样,“永恒与时间”被“时间性与时间”代替了[18](s.482)[19](s.487)。这样一来,海德格尔就和早年的奥利金一样,陷入将上帝的永恒设想为时间的无限延伸的窘境[17](s.17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在现代非常普遍。正如hans poser所言:
“哲学家不必为神学家的事操心,但是他却不得不看到,整整两千年来,时间概念是紧紧伴随着永恒概念而被人们讨论的:两者彼此互相关联。j. durandeaux 就把永恒问题形容为一切问题的问题,它只是在消极的表述上阻挡我们前进,当死亡作为这个世界本来的现实而出现的时候。在这种观点中夹杂着一种广泛触及宗教和神话起源的传统,这种传统转向了生存论,使永恒重新与人类思想的有限性相关。如果说海德格尔,而且不止是他,像胡塞尔、柏格森或者霍金都想从这种涉及永恒的传统中解脱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精神史过程,追随这一过程有助于时间的理解,而且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史边缘现象:鉴于对永恒性概念的否定,j. l. borges 认为,我们大家统统成了唯名论。”[9](s.17-50)
尽管后人对奥古斯丁的时间哲学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但由于他的时间理解(包括其它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会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广泛兴起,而受到具有后现代视野的宗教哲学家们(如hans jonas)和科学哲学家(如c. fr. v.weizs?cker )的高度注意。当然,仅就目前人们广泛认可的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效果史人物来说,无人能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相比。当然,他们的哲思视阈不同,对奥古斯丁的理解也就不同。正如herrmann指出的那样:“对胡塞尔来说,奥古斯丁正在通往内时间意识的路上;对海德格尔来说,奥古斯丁正在走向此在的生存论时间性之途。”[1](s.200)我们暂且不能深入讨论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现象学特征,也不宜惶论两位现象学大师对奥古斯丁思想的改造之得与失,但无论如何,通过他们二人的直接引证和评价,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奥古斯丁的思想已然活在了现代甚至当代哲学中,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herrmann, friedlich-wilhelm v.: augustinus und die ph?nomenologische frage nach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1992.
[2] r.bernet,einleitug.in:e.husserl,texte zur ph?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tseins,hrsg.und eingeleitet v.r.bernet.philos.bibl.bd.362.hamburg1985.
[3] 胡塞尔: 《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
[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
[5] 蒂利希:《教思想史》,香港,汉语教文化研究所,2000.
[6] kurt flasch: was ist zeit? augustinus von hippo. das xi. buch der confessiones. historisch-philosophische studie. text - übersetzung - kommentar,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93.
[7]hans poser, zeit und ewigkeit bei plotin und augustinus, cramer; vortragsreihe zeitbegriffe des mittelalters, tu, fu, hu, ws 98/99. 感谢 poser 教授提供未发表的电子版,并允许作者提前引用。
[8] 黄裕生:《时间与永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9] hans poser, zeit und ewigkeit——zeitkonzepte als orientierungswissen, in: h. m. baumgartner, das r?tsel der zeit. philosophische ysen, freiburg/br.: alber 1993, s.17-50.
[10]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三卷,,出版社,20xx.
[11]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中国大学出版社,1991.
[12] 《九章集》.转引自hans poser, zeit und ewigkeit——zeitkonzepte als orientierungswissen.
[13] h. jonas: plotin über zeit und ewigkeit, in: politische ordnung und menschliche existenz. festgabe für e. voegelin, münchen 1962, 295-319.
[14]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63.引文根据j.p.migne编的patrologia latina(paris,1841) 酌情进行了改动。
[15] stefan gilson, der heilige augustin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e lehre , aus dem franz?ischen übersetzt von p.philotheus b?hner und p.timotheus sigge o.f.m.1930
[16]dorothea günther,sch?pfung und geist,studium zum zeitverst?ndnis augustins im ⅺ.buch der confessiones, amsterdam-atlanta, ga1993.
[17] 周伟驰:《记忆与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
[18] m.heidegger, sein und zeit, achtzehnte aufgabe,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20xx.
[19] 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第二版。
第八篇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_西方哲学论文
大致说来,法国二十世纪哲学有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布伦茨威格(l.brunschvicg,1869-1944)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相互竞争的时代(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阶段是以萨特(j-p.sartre,1905-1980)和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1908-1961)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3h时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六十年代初);第三阶段是以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1908-)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福柯(m.foucault,1925-1984)、德里达(j.derrida,1930-1994)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3m时代(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第四阶段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的兴盛(利奥塔[j-f.lyotard, 1924~1998]、布尔迪厄[p.bourdieu,1930-1922]等)与现象学的复兴(列维纳斯[e.levinas,1906-1995]、利科[p.ricouer,1913-]、亨利[m.henry,1922-20xx]、马里翁[j-l.marion,1946—]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自六十年代初以来)。应该注意的是,前后阶段的进展并不以“飞跃”的方式出现,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学运动其实贯穿了全部四个阶段,但它在各个阶段的地位和表现具有很大的不同。
一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自二十年代初起,学术界开始了引进德国现象学的努力。Www.meiword.coM施皮格伯格告诉我们,当现象学在法国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柏格森森主义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而布伦茨威格则代表着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对立面。[1]梅洛-庞蒂也谈到,在萨特和他本人完成哲学学业(一个是1928年,一个是1930年)前后,法国哲学思想只有两种主导性的势力,即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两股势力。但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是布伦茨威格的思想”,而不是柏格森的思想。原因在于,布伦茨威格的哲学尽管“相当浅薄”,但他因为掌握了大学哲学教育及教师资格考试的权力而享有“权威”地位,而柏格森因为没有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故影响有限,或者影响还不十分明显。梅洛-庞蒂同时认为,柏格森更为重要,因为他为后来的人指明了一条与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通过布伦茨威格导致的观念论相反的方向。[2]阿隆(r.aron,1905-1983)则提到,当时可供选择的权威只有三人,即柏格森、阿兰( é.c.alain,1868-1951)和布伦茨威格。他同样承认了布伦茨威格的主导地位,与梅洛-庞蒂不同的是,他“从正面意义”上认为布氏在索邦是“权威的权威”,并表示,“他的著作使我们不能不有所尊重”,“它包纳了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3]暂且把谁是“权威”放在一边,问题在于,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都认可了对现象学的引进。就柏格森主义而言,无论是胡塞尔本人还是法国现象学的早期代言人都看到了柏格森思想与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思想的某种相似,许多人甚至过分强调了这种相似,其结果是,德国现象学“很容易被放宽的柏格森主义通过”;就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论而言,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差不多称之为“新笛卡尔主义”,而且强调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这些无疑都投合布伦茨威格[4]——因为他的基本思想是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混合而成的。
根据施皮格伯格的看法,在引进德国现象学方面,最初的工作是由一些“外来者”进行的:一种情形是在德国传统中培养起来的阿尔萨斯人,比如胡塞尔的学生、神学家海陵(j.hering)和齐美尔的学生豪特尔(c.hauter);第二种情形是一些曾在德国学习过、后来到法国的或波兰学者,主要有科瓦雷
(a.koyré,1892-1964)、g.古尔维茨(g.gurvitch,1894-1965)、闵科夫斯基(e.minkowski)、科热夫(a.kojève,1902-1968)和a.古尔维茨(a.gurvitch,1901-1973),其中包括对现象学持反对态度,但却成了传播现象学的动力的舍斯托夫(l.shestov,1866-1938)和别尔加耶夫(n.berdyaev,1874-1948);第三类是从德国来到法国的学者,比如狄尔泰(1833-1911)的学生、舍勒(m.scheler, 1874-1928)的朋友、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敬慕者格罗修桑(b.grothuysen)和舍勒的学生兰兹贝格(p-l.landerg)。[5]在发表于1930年的博士论文中,列维纳斯总结了在此之前现象学在法国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他表示:“除海陵的著名工作外,在法国几乎没有对胡塞尔进行过研究,做文献史的清理工作因此是非常容易的。” [6]除谈到海陵于1925年出版的《现象学与宗教哲学》一书外,他还谈到了德尔波(v.delbos)的《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及其纯粹逻辑观念》(1911)一文对《逻辑研究》第一卷的评介;舍斯托夫在《什么是真理》(1927)一文中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性主义的批判;古尔维茨发表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的《德国现象学哲学》(1928);他本人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论胡塞尔的》(1929);格罗修桑在小册子《尼采以来的德国哲学》(1927年)中论述胡塞尔的章节等。[7]
在这一以引进德国现象学为主的阶段,更具有意义并因此为随后的法国现象学奠定更好基础的应该是列维纳斯和马塞尔(g.marcel,1889-1973)。列维纳斯是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但接受的是法国高等教育。他于1923年至1930年就学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此期间曾经到德国进修过,并直接接受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教诲(1928-1929);他以关于胡塞尔的直觉理论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和同事一道翻译出版了胡塞尔在巴黎的讲座《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年);在弗莱堡期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对他影响尤其深刻,被他看作是哲学史上最好的四五本书之一。[8]当然,他后来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马塞尔则是法国本土的学者,他于1927年发表的《形而上学日记》被看作是法国现象学的最早成就,他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位即便不引进德国现象学仍然会导致法国现象学的“的现象学家”。[9]梅洛-庞蒂在1936年发表了针对他的《存在与拥有》的书评,肯定了该书对于生存现象学或身体主体问题的贡献。在1959年的一次访谈中则告诉我们,在马塞尔的那些最初作品中,比如在他的《形而上学日记》中,甚至在其更早发现的一些文章中,肉身化主题以某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获得了强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就是我的身体”。[10]这样看来,法国在引进德国现象学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独创性源泉。
在谈到法国对德国现象学的引进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批判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及其在那个时代的代理人布伦茨威格,引进者们并不完全接受强调纯粹意识和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的胡塞尔,而是对他加以某种改造,甚至出现了更为关注舍勒和海德格尔的情形。施皮格伯格这样指出:“在开始时,胡塞尔决不是法国对于现象学感兴趣的中心,因为他几乎被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声望超越了。事实上,法国接受现象学的历史几乎是德国原来现象学历史的颠倒。[11]比如就翻译出版的顺序来说,如果撇开胡塞尔在巴黎的演讲稿,首先是舍勒的作品,然后是海德格尔的作品,最后才是胡塞尔的作品的相继出版。胡塞尔确实是后来者,直到1950年才有著作《观念》由利科翻译出版。舍勒的作品第一个被译成法文,其《怨恨的人》于1933年在法国出版,梅洛-庞蒂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他在1935年为该书写的长篇评论,名曰《教与怨恨》。舍勒对于情感的关注,对知识、思想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无疑比强调纯粹意识理论更投合法国人。海德格尔则是第二个有著作被译成法文的现象学家,除了他的一篇文章和一篇演讲于1931年在法国发表外,1938年还有一部篇幅很大的文集由科尔班(h·corbin)在法国翻译出版。舍勒也是第一个访问法国的著名德国现象学家,他在1924年和1926年两度访问法国,而胡塞尔1929年才有法国之行,海德格尔对法国的访问则迟至1955年。然而,由于舍勒过早去世,具有历史意识的海德格尔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产生了第一位的影响,尤其影响了人们对现象学性质的判断,人们甚至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没有什么区别。列维纳斯对现象学的最初接受其实就带着海德格尔的痕迹:尽管他最初关注的是胡塞尔,其博士论文和最初译作也是关于胡塞尔的,到德国留学也是冲着胡塞尔去的,但是一接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马上就觉得后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并让自己的胡塞尔研究带上海德格尔色彩。他在访谈中表示,“就寻求把胡塞尔表述为已经洞见到关于存在的本体论而言,我关于胡塞尔的直觉理论的工作受到海德格尔的极大影响。” [12]
二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3h时代的一批著名哲学家把的法国现象学推进到辉煌的顶峰。法国人并打算单纯地引进德国现象学,而是一直在酝酿自己的别具特色的现象学。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塞尔已经开始了“运动”,但真正的应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三年,这与萨特由于受雷蒙·阿隆的影响对现象学产生狂热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他于193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象学,并于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到德国进修一年,听胡塞尔的讲课,阅读和研究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则要迟一些,分别发表于1939和1936)。回国后,他开始自己的现象学研究,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想象》(1936),这些努力使他成为的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看来使现象学法国化并根据胡塞尔的思想创立法国现象学的主要功绩应归于萨特。特别是由于他发表于1936年《哲学探究》上的第一篇论文,以及他写于1936-1940年间的论想象与感情的单行本著作。” [13]梅洛-庞蒂正式接受现象学要迟于萨特,他最初主要借助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来研究知觉的本质,但逐步接受了现象学方法,这在1933年和1934年开始有所表现,在完成于1938年、出版于1942年的《行为的结构》则获得了初步体现。1939年的卢汶查阅胡塞尔未刊之行,应该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萨特是这个时代的旗帜,而梅洛-庞蒂在现象学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萨特。他们各自的巨著《存在与虚无》(1943)和《存在与时间》(1945)的出版,把法国现象学运动推向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法国引进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同时,黑格尔主义在法国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不仅如此,在具有法国特色的现象学中,新黑格尔主义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被称为3h时代,即法国哲学受到以“h”为姓氏第一个字母的hegel(黑格尔,1770-1831)、husserl和heidegger强烈影响的时代。从这三位德国哲学家获得主要思想资源的一代法国哲学家,都在二十世纪初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广泛影响,尤其以萨特、梅洛-庞蒂为其突出代表。德里达将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看作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式的人类学”,[14]这表明萨特集中体现了3h的影响。这一代哲学家实际上与柏格森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清算了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或意识哲学。于是,法国本土的柏格森主义与外来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一道,形成了法国哲学的一个新的时期。“3h”一代的影响在战后达到顶点。在这一时期,“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是教的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唯灵论或非唯灵论的价值哲学,左派或右派的人格主义,经典主义的共同土壤。”而这种共同性源于它们“对黑格尔(对科热夫那样阅读《精神现象学》的兴趣)、(k.marxm,1818-1883,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优势地位)、胡塞尔(强调其描述的、局部的现象学,忽视其各种先验问题)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人类学阅读”。[15]
引进黑格尔主义的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是,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主义变得十分重要,而黑格尔哲学则是思想的重要来源。由于这种引进明显地走向对具体经验的关注,于是成为克服新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利器,并为现象学-存在主义顺理成章地加以利用。法国现象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存在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法国哲学家更重视具体经验而不是纯粹意识。斯皮格伯格评价说:“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融合起来,这使现象学更为协调,并且富有人性,其程度和方式甚至使现象学脱离了胡塞尔的先验的主观主义,脱离了舍勒的形而上学,脱离了海德格尔的反主观主义的存在思想。” [16]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并没有直接地阅读黑格尔的浩瀚的原始文献,他们往往是在科热夫、伊波利特(j.hyppolite,1907-1968)和让·华尔(j.wahl,1888-1974)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实用地采纳某些东西来为现象学-存在主义作论证,他们充分地发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及在此之前的工作,创造性地利用他关于人的具体经验方面的论述,比如苦恼意识之类。法国哲学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或“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甚至是“一位存在主义化了的黑格尔”。[17]比如,梅洛-庞蒂十分看重黑格尔的地位,他在1947年讲道:“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例如主义哲学、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哲学、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精神哲学的源泉。”[18]
既然是以现象学为主导的时代,3h中的胡塞尔无疑应该唱主角,并产生导向性影响。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胡塞尔的引进并不是单独的,而是伴随其他人物一道进入法国思想舞台:“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不能与发现一些外国思想分开,如对克尔凯戈尔(s.kierkegaard,1813-1855)的发现(让·华尔的著作),对后康德主义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和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的发现(让·伊波利特,柯热夫和盖鲁[m.gueroult,1891-1976]的著作),以及对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现(波利策[politzer]])。”[19]其次,胡塞尔的引进甚至不是首要的,而是按照“舍勒、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这一顺序。[20]由于法国人更关注具体和感性,并因此远离抽象和思辨,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舍勒对情感、海德格尔对生存在世的关注,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第三,就算随着的现象学运动的展开,胡塞尔本人的思想日益重要,但对他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但尤其倾向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从回归生活世界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通过怠慢胡塞尔已经发表的一些东西,法国哲学家或者说研究者可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感受到的不是接触一种新的哲学而是认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21]3h时代的哲学家明显抑胡塞尔而重海德格尔,与此同时,他们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向解释为生存论指向。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和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均源自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当然,他们两人都力求克服海德格尔此在的主体离心化外倾向,都坚持某种人道主义主张。
按照梅洛-庞蒂1959年在一次采访中的看法,生存哲学有四个重要主题,一是“肉身化主题”,二是“感性世界主题”,三是“我与他人的关系主题”,四是“实际上与他人主题相同”的“历史主题”。[22]如果把第四主题合并到第三主题中,那么就是三个重大主题。唯一没有提到的是“语言主题”,这其实是由梅洛-庞蒂本人最早倡导的。当然利科对于象征问题的探讨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主题,但他只是在3m时代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解释学转向。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但立场并非完全一致。这是由于他们对胡塞尔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特罗蒂尼翁的看法, “在现象学的共同语言之下形成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哲学家”,他们“两个人都从胡塞尔那里受到启发,但绝不是同一个胡塞尔,读的也不同样的书。萨特的胡塞尔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的胡塞尔;梅洛-庞蒂的胡塞尔则是各种未出版的著作以及《经验和判断》中的胡塞尔,是《笛卡尔式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的胡塞尔,是关于时间的内在意识的各种学说的胡塞尔。” [23]萨特在追忆梅洛-庞蒂时指出:“我们谈到这些必不可少的词:现象学,生存。我们发现了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我们都过于个人主义倾向而无法共同展开研究,我们在保持各自的情况下猜测对方。独自研究时,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理解了现象学的思想,而在一起时,我们在对方眼里都成了含混的化身。我们都从自己的工作出发把对方的工作看作是出人意料的、有时甚至是恶意的曲解。胡塞尔既使我们保持距离又维护了我们的友谊。” [24]比如,尽管萨特强调身体的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纯粹意识的强调中,而梅洛-庞蒂把超然的纯粹意识抛在一边,确立了身体主体的中心地位;又如萨特强调自在与自为的对立,而梅洛-庞蒂始终要求一种含混的第三维度。他们两人一度关系非常密切,但最终因为与哲学上的分歧而中断友谊。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塞尔,现在还要指出,波伏瓦(s.de beauvoir,1908-1986)、伽缪(a.camus,1913-1960)、雷蒙·阿隆等人也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密切相关。波伏瓦以小说的方式推进存在主义主张,她的论著《一种含混的道德》(1947)在伦理和他人问题上有其重要见解,作为萨特的长期伴侣,她始终捍卫他的“盟主”地位。伽缪以小说和戏剧的方式表达其现象学-存在主义主张,他对于荒谬和自杀等问题的探讨有其独特地位,他的哲学作品《西西弗斯神话》(1943)和小说《局外人》(1942)等作品的出版无疑对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具有推动作用。他最终与萨特决裂。阿隆本人在接受德国思想时,徘徊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及韦伯(m.weber,1864-1920)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之间,但他明确地表示,“通过研究现象学,我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相对于我的新康德主义教育的解放。” [25]。阿隆对萨特接受现象学具有推动作用,他本人同时借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东西来探讨历史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他最先与萨特决裂。另外还需要注意到列维纳斯和利科两位哲学家,他们属于3h一代,都对引进德国现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致力于自己的现象学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主要作品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而是在3m时代,其影响更在3m时代之后。列维纳斯在这一时代完成了《从生存到生存者》(1946)等作品,开始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利科在这个时代主要翻译出版了胡塞尔的《观念》(1951),同时致力于意志哲学的研究,这是一种与生存哲学和身体哲学相关的研究,代表作是《意志哲学:1、意愿与非意愿》(1950),《意志哲学ii:有限与有罪》(1960),《历史与真理》(1955)等。
三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3m时代的一批光芒四射的著名哲学家让现象学从主流思潮退出,现象学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暗淡的时期。梅洛-庞蒂的英年早逝,萨特在与列维-斯特劳斯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利科未能入举法兰西学院而福柯却成功进入,这些都表明现象学时代没有争议地让位于结构主义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首先,萨特、列维纳斯和利科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全无作为。事实上,列维纳斯和利科的许多独创性工作都是这一阶段进行的,比如前者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和《对他人的人道主义》(1972),后者的主要著作《解释:论弗洛伊德》(1965)、《解释的冲突》(1969)和《活的隐喻》(1975)的发表,尽管其效应或影响要在后面一个阶段才显示出来。他们两人都在继续现象学思考的同时,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并因此在困难时期寻找着现象学的出路:一个致力于他人、他者、他性的现象学探讨,一个实现了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其次,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回顾这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我们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从现象学到结构主义的断裂,而是应该同时清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能够简单地断言两者完全对立,甚至简单地认为后者取代了前者。在3m时代,语言学模式获得了普遍的应用,主体的命运完全被纳入到了无情的语言游戏中,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恰恰为这种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引导线索和帮助,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语言现象学。反过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野性思维、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又对梅洛-庞蒂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在3h时代已经发表出来。第三,现象学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列维纳斯、利科等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家,但法国现象学学派的范围还可以扩大,结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也都可以归属于这一流派。[26]当然,后面四位;福柯批判胡塞尔强调先验主观性,并因此把一切强调主体优先性的方法名之为现象学方法而予以批判,但在我看法,他关于经验、知识和权力的理论类似于某种还原的努力,尽管不具有先验的指向。黑格尔的情形更为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在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黑格尔被抛在了一边,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就谈到了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普遍的反黑格尔主义”。[31]然而,在某些人,比如德里达那里,还为黑格尔保留了一席之地。德里达说过,他一直试图超越黑格尔,但始终发现黑格尔在前面等着自己,于是干脆做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并对扬弃进行扬弃。
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可了把德里达归入现象学圈子。他对现象学的兴趣是非常显然的,他翻译胡塞尔的《论几何学起源》并写了长篇序言;他写了考察胡塞尔符号学思想的《声音与现象》(1967);他的“解构”概念通常被认为源自于海德格尔的“分解”概念;他对传统概念划上一个叉的做法也来自海德格尔,如此等等。按照多斯的看法,萨特和梅洛-庞蒂通过对活的经验和知觉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而“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他通过对现象学最终基础的考察,并没有推导出主体已经死亡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范围内推导出了主体的有限性。[32]至于福柯,很少有人同意把他也同样归入现象学圈子。然而,他的许多思想都有现象学的影子。他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去世之前还说,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由于阅读海德格尔”。[33]这句话出自他去世三天后发表的名为《道德的回归》的采访,显然是在重视个体生存的伦理谱系学意义上来考虑海德格尔的影响的。把经验(体验)作为“经验-知识-权力”问题的基础,显然是对现象学-存在主义重视生存体验的倾向的某种发挥。主体终结论否定的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大写的主体,纯粹意识主体,与此同时,它要求关注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即自我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身体经验、非理性经验的关注表明,他和梅洛-庞蒂的思想具有许多共同性。 四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哲学出现的是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因此可以看到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真正说,我们看到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象学的杂然共存。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主义的象征依然健在,文学领域和符号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仍有其生命力;福柯进入其关注审美生存或伦理生存阶段,似乎从结构主义经后结构主义重新回到了现象学起点;德里达把他的解构指向、法律、社会领域,不断扩大其地盘,他对身体、他者等问题关注,似乎与现象学有某种牵连;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德里达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许是利奥塔,他先是接受现象学的影响,并写有名为《现象学》(1954)的小册子,然后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对精神学有相当的研究,他最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状况》(1979)是其经典之作;布尔迪厄同样是一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均有其贡献,他曾经广泛阅读过萨特、梅洛-庞蒂和胡塞尔,赞赏梅洛-庞蒂对人文科学和生物学的兴趣,研究过“感情生活的现象学”,但表示自己“未真正进入存在主义状态”,他尤其看到了结构主义对社会学有“关键作用”,他自己“也在作品中尝试探索社会学思考的结构或与之相关的方式,但尽一切努力抵制纯粹时髦的结构主义形式”[34];与后现代主义同步或者稍后,列维纳斯和利科的现象学探讨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在知识界的重新得宠让人觉得现象学已经卷土从来;当然,亨利和马里翁才真正意味着现象学的复兴。
关于这个时期的现象学进展,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提到列维纳斯。他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旅程(从我们描述的第一阶段直至本阶段)才得以享受达到目的地的欢欣。他关注绝对他性,号称既超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又超越于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论,最终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一种关注他人的人道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发表于1961,《对他人的人道主义》出版于1972年,但产生影响则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另一本重要著作《别于存在或超越本质》(1990)及其他一些著作或论文集在八十年代以后陆续结集出版,不断提升其影响。接下来应该提到利科,尽管他在第二个阶段才上路,同样也经过了漫长的旅程才获得承认。在3h时代,他因为对意志和恶的研究而被归属于生存现象学家之列;在3m时代,通过接受结构主义的一些资源,利科实现了其思想的解释学转向;在我们所说的综合的时代,他的《时间与叙事》(1983-1985)、《作为他者的自我本身》(1990)等作品则在综合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哲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两位在这个综合时代越来越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学家。一位是年龄稍长于福柯的米歇尔·亨利,他是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着有《显现的本质》(1963,1990重版),《身体的哲学与现象学》(1965,1987年重版),《:卷一.关于实在的哲学,卷二.关于经济的哲学》(1976,1991纳入丛书),《心理的谱系》(1985,1990年重版),《物质现象学》(1990),《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2000)。从其作品的发表情况可以看出,他在3m时代开始逆潮流发表作品,但真正产生影响则开始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也因此属于综合的时代。他的哲学处于现象学传统中,“他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出发,评论并批评它们,致力于一种关于生命的形而上学。”它涉及到的是“绝对的内在”或“肉”的生命的内在性,它对立于一切“超越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也被纳入此列),同时也根本否定胡塞尔强调内在意识的哲学,并因此“把现象学态度彻底化”。[35]亨利和梅洛-庞蒂都使用肉身化(incarnation)、身体(corps)和肉(chair)等词,但着眼点很不相同。按他的意思,肉和身体都是肉身化的形式,前者主要涉及人,而后者推而广之涉及到宇宙万物。在《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一书的《导论:肉身化问题》中,亨利告诉表示:在最初的意义上,肉身化涉及到地球上的全部有生命的存在者,他用corps一词专门指称物体的肉身化形态,而用chair一词来指人的身体或他的肉身化形态。应该说,就把身体与物体区别开来而言,他的看法与梅洛-庞蒂并无二致,当他说如下一段话时,尤其如此,“我们的肉不外是那能够感觉外在于它的物体、能够触摸它而不是被它触摸者(它感觉到它自己、容忍它自己、服从它自己、支撑它自己,并且根据始终再生的印象拥有自己)。这因此是物质宇宙中的外在物体、惰性物体原则上所不能够的。” [36]问题在于,他似乎没有梅洛-庞蒂的眼界“开阔”,不愿意承认宇宙有“灵”,万物有“灵”。而梅洛-庞蒂认识到,恰恰因为有可能被等同于被动的、惰性的物体,才应该把(肉)的“活的”、“生机的”含义推广到宇宙中去,使肉身化在整个宇宙中获得体现,因此有了身体之“肉”、语言之“肉”、世界之“肉”的表述。
另一位是新生代的现象学家让-卢克·马里翁。他是法国著名的笛卡尔研究专家,以关于笛卡尔的研究获得国家博士学位,是法兰西大学出版社的厄庇墨透斯(épiméthée)丛书主编(第一任主编是伊波利特),《笛卡尔通报》的共同创立者,在国外,他事实上继任了利科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教席,在国内,他继任了因为列维纳斯而著名的索邦形而上学教席。马里翁的现象学有其笛卡尔研究背景,他发表过许多关于笛卡尔思想研究的作品:如《笛卡尔的灰色本体论》(1975),《笛卡尔的白色神学》(博士论文,1981),《论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棱镜:笛卡尔本体-神学的结构与界限》(1986),《笛卡尔式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1991),《笛卡尔式问题ii。逻各斯与上帝》(1996)等。他对现象学学评价甚高,他在1989年表示:“从基本的方面来看,现象学在我们世纪担当了哲学的角色本身。” [37]他的现象学是关于赠与现象的研究,其中容纳了天主教信仰。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作品中:《偶像与距离》(1977),《没有存在的上帝》(1982),《还原与赠与: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现象学》(1989),《可见者的交织》(1996),《被赠与:论一种赠与的现象学》(1997),《添加:饱和现象研究》(20xx),《色情现象:六个沉思》(20xx)。他认为“被赠与是先于被构造的环节”,“被赠与先于一切解释,支撑它,这使得它们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使得它们彼此成为丰富的。”[38]可以看出,马里翁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才真正开始其现象学之旅的,但其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年富力强,他应该是前途无量的。列维纳斯1996年去世,亨利20xx年去世,德里达也于20xx年告别人世,除了硕果仅存的92岁老一辈哲人利科外,在法国现象学传统中,不到六十岁的马里翁目前应该是最有影响的现象学家了。 注释:
[1][4][5][9[[11][13][16][17][19][20]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
第593-594,594,597,620,597, 601,59-60,611,58,60页。
[2][10][22] 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951-1961,éditions verdier,2000.
pp.250-252,p.254,pp.254-257.
[3][25] aron,mémoires: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julliard,1983.pp.38-39,p.68.
[6][7] levinas: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librairire philosophique j.vrin, 1963.p.5,pp.5-7.
[8][12] levinas:ethique et infini,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et radio-france, 1982.p.33,p.36.
[14][15] derrida :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2.p.137,p.138.
[18] merleau-ponty :sens et non-sens.éditions garlimard,1996.p.79.
[21][29]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éditions garlimard,1945.p.ii,p.ii.
[23] 特罗蒂尼翁:《当代法国哲学家》,三联书店,1992,第39-40页。
[24] 《merleau-ponty》,les temps modernes, № special 184-185 ,1961.p.307.
[26]高宣扬:《布尔迪厄》,生智出版社,20xx,第10-11页。
[27] descombes :le même et l’autre :quarante-cinq ans de philosophie fran?aise(1933-1978).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9.p.3.
[28] merleau-ponty : la structure du comportment. puf/quadrige,1990.p.191
[30]让·华尔:《存在哲学》,三联书店,1987,第9页。
[31]德勒兹:重复与差异,p.22.
[32] 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编译出版社,20xx,第26页。
[33]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v.éditions garlimard,1994.p.703.
[34]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出版社,1997,第1-6页。
[35][38]huian et monier:visages de la philosophie.arléa,p.106.
[36] henry : incarnation :une philosophie de la chair. éditions du seuil,2000.p.8.
[37]marion:réduction et donation:recherches sur husserl ,heidegger et la phénoménologie.puf,1989.p.7.
第九篇 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及传统存在论的存在本原观的解构_西方哲学论文
摘要:西方哲学从开端以来一直将存在视为最终的本原或根据。德里达对这种传统的存在本原观进行了解构。他认为,存在远非最终的根据或本原:在存在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延异”;而存在自身,也早已是“踪迹”。
关键词:存在 踪迹 延异 德里达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曾说:“……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arche(本原),aition(原因),prinzip(原理)。】……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1](68-69)存在——根据、本原、原理。的确,这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始终未变的存在规定。于是,追问万物本原的哲学最终成了存在论,存在的意义也成了西方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存在真的是最后的根据和本原吗?通过对包括海德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传统存在论的解构(déconstruction),德里达发现,存在远非最终的根据和本原。在存在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延异”(différance);而存在自身也早已是“踪迹”(trace)。
一、 踪迹:对“在场-不在场”的绝对超出
但对传统存在本原观的反思从后期海德格尔就已经开始了。海氏后期不仅继续前期的存在之思,而且还给存在打叉;不仅重视在场,还重视非在场;不仅继续思考“本己”(eigen),还追问使“本己”得以可能的“自缘构”(ereignis)。wWW.meiword.com如果说,海氏前期的“思想的事情”无疑就是存在;那么海氏后期关于“自缘构”、“打叉”以及打叉后留下的“踪迹”(spur)的思想还是存在之思吗?它是对前期“存在之思”的深化、因而本质上仍属于存在的时代(epochen),抑或从根本上已超出存在时代或至少摆出某种想超出的姿态?但又是以何种姿态?通过对不在场的思考吗?但不在场根本上不仍是在场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踪迹的追问?然而踪迹在他那里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是否已取代了存在而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主题?这些暂且不谈。此处关心的是,德里达将如何看待海氏思想中这种复杂的局面?
以他一贯的解构策略,德里达说,海德格尔思想中存在着双重指向:时而是从当前(présent)出发,追溯关于作为在场状态(anwesenheit)之存在的更本源的思想;时而质疑这种本源规定本身,把这种规定思为终结(clôture):希腊-西方-哲学的终结。这后一种思想方向思及wesen,它甚至还不是在场(anwesen),它超出于在场(présence),它在古希腊之前或超越于它之外。[2](75)
在德里达看来,海氏思想中的这“两种文本、两种姿态、两种视角、两种倾听方式,同时聚集又分离”。[2](75)但这双重姿态真的是“同时聚集又分离”吗?若从海氏思想的整个道路来看,或许它们并不是同时存在、相互交织的双重姿态,而是一个从前者不断向后者返回的姿态:从非本源的“当前”向本源的“作为在场之存在”返回,再从在场向比“作为在场之存在”还要古老、甚至超出存在时代之外的东西后退。但这并非此处所要关心的。我们关心是,正是在德里达对海氏的这种划界中,德里达自己的“思想的事情”显露出来了:那就是他所说的比“作为在场之存在”还要古老或者还要晚到的“事情”。
然则这究竟是何种事情,竟至比在场还古老,甚至在存在时代终结之外?它是不在场吗?不!德里达说,“那被给予我们以在终结之外进行思考者,又并不就是单纯的不在场(absent)”:“不在场或者不给我们以任何东西以供思考,或者还只是在场的否定方式”。[2](76)因此,德里达说,这是一种对于“全部可能的在场-不在场”的“绝对超出”。但虽然如此,它仍然“要以某种方式具有意义”,只是由于它已超出在场-不在场,所以它之具有意义就是以“形而上学本身不可能提出的方式具有意义”。[2](76)那么,这种绝对超出于在场-不在场的不同于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德里达说,这就“是”以踪迹之“名”被思考的“东西”:“为了超出形而上学,就必须有某种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之中,所有的这种踪迹都继续作为符号,只是不再指向另外一种在场,也不是指向在场的另外一种形式,而是指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本”。[2](76)
也因此,这样一种踪迹也就不再能被形而上学或哲学予以思考:“任何一种哲学因素都还没被准备好去把握它。它就是那逃避把握者。只有在场才能被把握。”[2](76)为了彻底避免重新沦为在场的命运,这样一种踪迹甚至还得必须再次涂抹“它自身”(elle-même)(或译“它本身”)。为什么?因为一旦它不把“自身”涂抹掉,它就重新拥有一个“自身”,就会重新对于自身而在场,就会重新在在场中被把握。而如此一来它恰恰就不再“是”踪迹:踪迹之为踪迹恰恰在于它抹消自身而指向他者。所以德里达说,“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方式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它必须被描述为对踪迹自身的涂抹。踪迹作为它自身的涂抹而自我产生。逃避自身、逃避那有可能将它保持在在场之中的东西,此为踪迹之所固有。踪迹既非可知觉的,也非不可知觉的。” [2](76)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德里达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整个现象学基本精神——回到事情“本身”——的解构。对事情“本身”的信念是现象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无论是胡塞尔的“悬置”还是海德格尔的“拆构”(destruktion),其针对的都是偏见:或者是自然态度的偏见,或者是传统存在论的偏见。他们都没有对“事情本身”这个前提表示过怀疑。而德里达所要解构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学的前提。这一点早在《声音与现象》中就已涉及。德里达在那里写到:“与现象学让我们相信的相反,与我们的欲望不可能不相信的东西相反,事物本身总是自我逃避的”。[3](117)但事物逃避之后必竟还有踪迹。踪迹不是本身,没有本身,因此超出了以回到事情本身为使命的现象学的范围:“踪迹超越于那把基础存在论和现象学深刻地连接在一起的东西。踪迹总是延异着,从来没有自我呈现。它在自身呈现中涂抹自身,在发出回响之际震聋自身,像在延异中书写自身、铭刻自身的a一样。” [2](24)
涂抹自身的踪迹已不再自身在场。不仅如此,甚至连通常以为的在场,也已经是踪迹了。
二、 在场的踪迹化
自《存在与时间》以来,海德格尔一直认为存在被西方形而上学遗忘了,而这种对存在的遗忘实质上也就是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的遗忘。同时,由于存在在西方形而上学中总是被经验为在场,所以对存在-存在者之差异的遗忘,又成了对在场-在场者之差异的遗忘。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说:“但存在之事情乃是去存在(或是)为存在者之存在。这一神秘多义的第二格的语法形式指示着一种发生,在场者的一个出自在场的来源。但是,凭着在场和在场者这两者的本质,这一来源的本质始终还是蔽而不显的。不但于此,而且甚至连在场和在场者的关系也始终未经思考。从早期起,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各各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始终被遗忘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被遗忘状态。”[1]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连差异的“早期踪迹”都被磨灭了。他说:“存在之历史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因为存在——随其本质,随其与存在者的差异一道——抑制着自身。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唯差异双方,即在场者与在场,才自行解蔽,但并非作为(als)有差异的东西自行解蔽。相反地,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显现出来,并且在一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渊源。”[2]
让我们在此稍作停留。
“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但不仅差异被遗忘了,“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海德格尔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差异虽被遗忘了,但本来还有踪迹——差异的早期踪迹——留下?而现在,就连这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还是说,“差异的早期踪迹”就是指差异本身?差异,或者说差异的分环勾连本身,就是一道踪迹,而且是早期踪迹?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这早期踪迹复又被擦去了。然则又是什么把这早期踪迹重又擦去?是否这种擦去又没有留下新的踪迹?如果真的连这种早期的踪迹都被擦得无迹可寻,我们又如何能经验到差异的这种被遗忘?所以,事情必然是,虽然连差异的早期踪迹都被擦去了,但毕竟还是有踪迹留了下来,只要我们还能经验到差异的这种被遗忘本身。
而这也正是海德格尔自己不得不承认的。他说:“可是,唯当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护在存在所达到的语言中——这时,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差异才能进入一种经验之中。”[4](57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在叙述了对早期踪迹的涂抹之后,海德格尔因此就能够以一种无矛盾的矛盾的方式,记载、会签对踪迹的确认。[2](26)差异的早期踪迹被涂抹了,但有一道新的踪迹留了下来。踪迹被重新确认了。于是形而上学的文本中其实已充满了踪迹。然则这新的踪迹是如何留下的?“……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这说的是什么?差异随在场揭示自身之际就已留下踪迹——这说的难道不是:在场已经是踪迹?是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而遗留的踪迹?难道不是:在场已经是踪迹了,已经是涂抹的效果了?而这也正是德里达从其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与它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迹化(tracement)是“相同的”,这迹化必定保存了它所抑制或抛弃的东西的标记,[2](25)即保持了早期差异的标记,于是成了新的踪迹。由此德里达就能够说,差异的“早期踪迹”虽然丧失了,然而这种丧失自身复又在一个文本之中被庇护、保藏、注视、推迟,以在场的形式,以本己性的形式,而后者自身复又只是一种书写效果。[2](25-26)在场原来只是迹化的效果,书写的效果,是一种涂抹了差异的早期踪迹的踪迹。于是在德里达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就被颠倒了:在场成了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它不再是最终的所指。它成了一般化了的指称结构中的一个函数/功能。它是一道踪迹,一道涂抹了[差异的早期]踪迹的踪迹。[2](25, 76-77)
早期差异虽然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而揭示自身,但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无论如何,差异都没有作为这样一种差异而被命名出来。因此,差异之澄明也并不能意味着差异显现为差异。”[4](578-579)同样,在场虽然是迹化的效果、书写的效果,是踪迹的踪迹,但在场毕竟不是作为“踪迹本身”显现。换言之,虽然在场是踪迹的效果、踪迹的踪迹,但踪迹“本身”并不就是在场。踪迹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在场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给予踪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或命名。正如德里达所说:“必须要认识到:对踪迹的所有规定——人们给予它的所有的名称——都属于那遮蔽了踪迹的形而上学文本而非属于踪迹自身。” [2](77)当然,不属于踪迹自身,并不是因为踪迹好像真的有一个在场的、现成的自身。恰恰相反,“没有踪迹自身(elle-même),没有本己的(propre)踪迹。” [2](77)踪迹之为踪迹,恰恰在于它总是要抹去自身,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否定自身、涂抹自身的“悖论结构”,否则它就不是踪迹而又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实体”了。[2](25)
这就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构”:海德格尔已看到在场-在场者的存在论差异总是被遗忘了,也就是说,存在(在场)总是被当成了存在者(在场者),因此他总想从存在者(在场者)“返回”到那被遗忘了的本原或根据:存在(在场)。但毕竟,他尚未看到那被经验为在场的存在自身也成了踪迹,成了踪迹的踪迹;他尚未意识到,在场、本己性自身正是这种踪迹的效果、书写的效果。他虽然也已思及了踪迹——既思及了差异的早期踪迹,也思及了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本身仍留下的踪迹——但他毕竟没有看到,或即使隐约看到了却没有充分自觉到,踪迹恰恰构成了对任何一种本原的解构——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任何本原都是在本己(本真)意义上的永远自身在场的本原。但即使如此,他对踪迹或涂抹的艰辛丰富的探索,毕竟极大地激发了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更为彻底的解构。[5](83-84)当然,近代以来思及踪迹的思想家并非海德格尔一人,但对德里达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海德格尔。这正如德里达自己所说,人们总能够在形而上学的话语中识破这种处于延异运动中的踪迹,特别是在现代哲学话语中,比如尼采、弗洛伊德、勒维纳斯等,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的文本中:它激发我们考问当前的本质,当前的在场:何谓当前?何谓在其在场中思考当前?[2](24)显然,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当前或在场的本质,在德里达看来就是踪迹。而这种思想恰恰是由海德格尔激发出来的。
三、 比存在还古老的延异
把在场解构为踪迹,并没有最终解构掉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因为,虽然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存在总是被理解为在场,但存在自身并不就是在场。所以要彻底解构存在之思,还必须直接对存在进行解构。为此,德里达诉诸于他著名的“延异”(différance)。
“延异究竟是什么?”
这是许多人向德里达提出的问题。但德里达之所以诉诸于“延异”,恰就是要解构这个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中的“是”(存在)。正是在这种解构中,延异与存在的关系才被澄清:延异所要动摇的正是这个“是什么”中的“是”、即存在的统治。
德里达说,延异处处动摇和质问的是存在——作为在场或存在者整体(étantité)的存在的统治。[2](22)正因为延异动摇的是存在,质问的是在场,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用存在和在场来述谓延异:“延异不存在或不是(n’est pas,is not)。它不是一个在场的存在者,无论这个存在者多么卓越、唯一、重要或超越,如人们希望的那样。” [2](22)而且,说延异不存在,不是在场者,也并不等于说延异是不在场者:因为即使是不在场者,也已经是了。但延异根本就不“是”,它不去“是”——它要动摇的恰恰就是这“是”的统治。或更严格地说,它总是在是的同时又涂抹是,让是成为踪迹。与踪迹一样,或毋宁说作为踪迹,延异超出于在场-不在场的对立之外。但同时,德里达也承认,延异对“作为在场或存在者整体(étantité)的存在之统治”的动摇,恰恰是通过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存在论差异才得以可能。他说,如果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不在某种程度上被打开,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也不会被理解。[2](22)何以如此?因为延异动摇的是存在的统治,或作为在场的存在的统治。但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存在-存在者或在场-在场者的存在论差异的打开,存在如何能重新被唤回?又如何能再去动摇它?所以延异正是“通过”存在论差异而可能。
然则,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延异与存在论差异就是一回事,或用德里达的话说,延异就“定居在存在论差异的间距中”?对于这个问题,德里达说,“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2](22)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具体来看。
一方面,德里达说,就其自身的某一面而言,延异当然只是存在或存在论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déploiement)。延异的那个a就标志着这种展开的运动(mouvement)。[2](23)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这里竟说“延异自身”(elle-même)!延异有自身吗?他不是一再说延异没有自身,而且恰恰是对自身的解构吗?这是德里达的笔误吗?抑或相反,是他故意耍的一个花招?因为,如果不是就其自身而言,延异如何能是,而且“是存在或存在论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déploiement)”?不正是在存在的时代,才有自身可言吗?所以延异、踪迹在存在论中,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中早已获得自身了。正是由于获得了自身,延异才成了存在论差异,成了此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而踪迹才被经验为在场,在场才被经验为在场者。也正因此,把延异经验为存在论差异,就仍还处于形而上学之内,一如把踪迹经验为在场也同样处于形而上学之内一样。所以——
另一方面,德里达说:“关于存在的意义或真理的思想,把延异规定为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差异,在存在的问题视域中被思考的差异,不仍是延异的内-形而上学的效果吗?延异的展开或许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时代性。” [2](23)注意,德里达说,延异的展开或许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换言之,延异或许有另外的展开形式。所以德里达接着说:“或许我们必须尝试着思考这前所未闻的思想,这沉默的迹化(tracement):存在的历史——它的思想卷入到希腊-西方的逻各斯,一如它通过存在论的差异产生出来——只是diapherein(区分)的时代。因此,我们甚至就不再能够把延异的展开称作‘时代’(époque),时代性的概念属于作为存在历史之历史的内部的东西。既然存在除了把自己隐藏在存在者中之外,从来就没有一个‘意义’,从来没有被如此这般地思考和言说,那么,以某种极其陌异的方式,延异就比存在论差异或存在的真理还要‘古老’。正是在这个年代(âge),人们可以把它称为踪迹的游戏。这种踪迹不再属于存在的视域,但是它的游戏却带来存在的意义并为之划界:踪迹的游戏或延异,它没有意义且不存在。……对于存在于其中游戏着的这个无底棋盘来说,没有持存,没有深度”。[2](23)
如是,延异就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而是干脆别于存在。它比存在还要古老。当然这种古老并不是时间意义上。其实它要说的或许就是:一切显现出来的存在,貌似坚实稳固的事情本身,其实早已经是踪迹,是踪迹的游戏的效果,是延异的效果。我们能把握到的只能是在场、存在,只能拥有关于存在的真理。
延异处于存在时代之外,并非形而上学所能把握。然则我们该如何思考、如何命名这别于存在者,这处于外部者?然而,问题或许首先是,它能否被命名?命名意味着什么?命名,给予一个名字,一个专名:proper name,一个本己的、固有的、专有的名字。然而,何种东西才能有资格获得这种专名意义上的名字?难道不是那首先已有其本己、固有、专有之(propre,eigen)性的事物吗?因此难道不是那已先有其自身者吗?然而,以延异之名思考的东西有其本己、固有、专有之性、之自身吗?没有!延异恰恰是对自身、本己的解构。德里达在“延异”一文中曾经专门加了一个注释讨论在场、本己、自缘构、存在论差异与延异的关系。他在那里指出,如果在场的礼物是自缘构(ereignen)的所有物(eigentum),那么延异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本己化(propriation)过程:它既不是肯定(自缘构:appropriaton),也不是否定(自褫夺:expropriation),而毋宁是别一回事(l’autre)。自缘构构出一个“自身”、一个“自己”。德里达指出:存在、在场与本己化(-propriation)之间组成了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eigentum”起到了一种不可还原的作用。但延异恰恰是对“eigentum”、对“自身”、“自己”的解构。所以德里达的延异不仅不是海德格尔前期说的存在,而且也不是后期说的自缘构。它完全是与此无关的别一回事(l’autre)。
所以这别于存在者、外于形而上学文本者,本不可以命名。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命名了。不是吗?我们不是以延异之名在思考它、言说它吗?而延异,作为名字,却已经是形而上学的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对于我们来说(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引者),延异仍保持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名字。它在我们的语言中接受的任何名字,作为名字,都是形而上学的。当这些名字把对延异的规定言说为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差异时,情形尤为如此。[2](28)那有别于存在者不得不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不得不在我们的语言中接受名字。因此,连延异这个名字也是形而上学的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德里达这里是如何在拼命地想通过撞击语言的界限,来显示、暗示、指示某种超出形而上学语言、超出形而上学文本之外的东西或事情。[3]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比存在更古老、不断地涂抹自身、延迟自身、在替代链条中自我脱位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名字可言,所以连“延异”也不是它的名字:“‘延异’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纯粹的命名统一性”。[2](2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才说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无论是词还是概念,都已经预设了某一个自身同一或统一的意义,已经预设了自身性、同一性——而这恰恰是“延异”所指的那回事要进行解构的。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
[2]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paris : les édtions de minuit, 1975, c1972.
[3] jacques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4]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1996年12月第一版。
[5] jacques derrida:de l’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éditions galilée, 1987.
being and trace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to heidegger,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lways regards being as the last origin or ground. derrida deconstructed this traditional view. he said that being is not the last origin or ground: being itself has always been the trace, and there is also differance before the epoch of being.
keywords: being, trace, differance, derrida, heidegger
--------------------------------------------------------------------------------
[1]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第24页;海德格尔引文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1996年12月第一版)第577-578页,译文有改动,参见heidegger:holzweg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0.第359-360页。
[2]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第24-25页,海德格尔引文见《海德格尔选集》578页,有改动,参见heidegger:holzwege, 第360页。
[3] 《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25章)等,可与之相参。
第十篇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_西方哲学论文
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义、、全球主义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1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www.meiword.com2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3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4
1250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在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似乎只有在一个商人的视角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才能发现中国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l、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繁复,然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记述当地的物产、建筑、道路、行船与桥梁。中国城市,无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
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一个充满财富与权力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出现,自有其欧洲文化本身的背景。如果说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与其说反映了契丹的形象,不如说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幻想。从中我们既可读到模糊的中国形象,也可以发现投射到中国形象中的西方中世纪文化所压抑的欲望与恐惧。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读另一部流传广度几乎与《马可波罗游记》不相上下的东方故事——《曼德维尔游记》。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119种。遗憾的是,作者曼德维尔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虚构的,他将关于东方的新知识与西方已有的旧传说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表现了中世纪晚期西方通俗文化层次上的东方意识特色,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中,塑造了类型化的契丹形象或东方形象。
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了。曼德维尔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大汗有100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 曼德维尔在教义与骑士道视野内改造契丹形象。一部游记与一部英雄传奇在中世纪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文类界定,就像虚构与真实也没有什么客观的尺度一样。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契丹传奇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文本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的形象,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象征。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关系。当他们议论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遍地财富、城池众多、道路纵横时,他们也在体验自身的缺憾、压抑与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向往。5
二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6,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延续的。蒙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说,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直到伊比利亚扩张,从“世界上最远的海岸”(指中国)带回最新的消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的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门多萨神父的《大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托邦。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门多萨神父奠定了大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是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7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8
三
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问题是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不仅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原型的文化程式。从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美化;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神话,最后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来。解释这种形象及其传统的意义,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早期的中西关系之外,还有西方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 9世纪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10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的时候,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也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中国潮”。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中国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教神学。莱布尼茨曾说: “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 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11
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之争、之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12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潮”在启蒙运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
四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更多地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它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文化策略与逻辑。文本是唯一的依据,而作为文本的语境出现的现实,在此也不是指文本所反映的现实对象(如中国),而是构成文本写作的社会语境与话语策略(西方文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启蒙运动中中国形象逐渐转变,造成这种观念变化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与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可以这样说,真正使中国形象改变颜色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启蒙运动文化观念本身的进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开始大革命,封建专制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楷模了。二是西方扩张中与中国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象;二、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赛义德在对东方学概念进行限定性说明时,强调异域想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13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也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密关联。
首先是西方现代扩张史上中西权力关系的变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扩张的历史,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蒙元世纪西方人走向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出现了。1250年是西方人的世界知识的起点,也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起点。蒙元世纪西方的大旅行瞬间开始又瞬间结束。蒙古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又将西方压制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知道新航路发现,西方扩张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时开始。他们征服了美洲,但在亚洲的经历却并不顺利。葡萄牙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西方扩张势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可以说,直到18世纪,东西方势力对比中,东方相对而言依旧强大。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满清帝国。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
中国潮在欧洲出现的那个世纪里,西方扩张进入了一个停歇与调整期。165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西方扩张的第一次已经结束。西方进入东方的扩张势力,基本上被阻止在东方帝国的海岸上。这种直到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此时,欧洲已经能够大批生产瓷器,工艺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无须再大量地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进口。瓷器的价格跌落了,进入寻常百姓家,漆器壁纸的欧洲产品甚至比中国进口的还优秀。英国人喝茶上瘾,商人们大量贩运茶叶,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与广东的直接贸易,茶税从世纪初的100%降到世纪中的12、5%,茶价一路下跌, 1750年英国年进口的茶叶已达到3700万磅,茶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饮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他们将印度的运往中国贸易茶叶,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易中亚洲从出口成品到出口原材料,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军事优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殖民劫掠贸易时代。试想一个贫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国家,能够令人仰慕令人重视吗?欧洲的中国形象与欧洲的中国茶同时跌价。人们可以追慕那些富裕先进的国家民族的习俗风格,但不会效仿落后堕落的国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风格。
1750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东西方关系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75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扩张的第三波开始。同时,衰落出现于所有的东方帝国,首先是萨菲王朝,其次是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世界格局变了,英事与经济实力已强大到足以打破旧有的平衡。在整个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及时避免了革命的消耗,又放弃在欧洲争取霸权,他们一边发展国内经济,一边继续海外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美洲与印度战胜了法国人,普拉西战役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化统治的建立,对英国本土来说,有助于完成工业革命,对东方扩张来说,赢得了打开中国的基础。首先是英国人用印度的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次是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赢得了战争,西方持续三个多世纪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临近完成。在世界现代化竞逐富强的进程中胜出的西方,还有可能继续仰慕一个愚昧专制停滞衰败的东方帝国吗?
其次,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变化,也是中国形象转型的重要原因。现实世界中西方物质权力关系,影响着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是有其深远的现实与经济原因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西方文化心理本身的结构变化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它并不一定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空间。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提出,考察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又相互关联。14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认同与世界规划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又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事征服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东方神话也是理解西方历史上中国崇拜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文化背景。
东方神话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两希传统(古希腊与希伯莱)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结。古希腊文明来源于近东文明,对于东方世界,古希腊文化心理中既有恐惧又有向往。这种心理延续到中世纪,恐惧来自于威胁,向往则指向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印度与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的契丹传奇又将这种东方向往转移到中国。中国变成西方想象中的世俗天堂。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运动中达到。
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作为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形象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的文明,甚至以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一、“古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三、西方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500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五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15;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义与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16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准备了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12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750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那个靠恐怖的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效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世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专制愚昧、停滞野蛮的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8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即可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17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于启蒙运动后期的法国与英国,到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最完备的解释,从而作为标准话语定型。它既表现为一种具有教条与规训意义的知识,又表现为具有现实效力的权力。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的停滞,进可以为殖民扩张提供正义的理由,退可以让西方文明认同自身,引以为戒。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只有靠其他民族的冲击。进步是人类历史的法则,停滞是取得共识的“中国事实”。一旦这些问题都确定了,西方入侵中国就可能成为正义之举,在观念中唯一的障碍,如今只剩下人道主义在历史中设置的道德同情。
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概念取代进步概念,避免了启蒙思想的温情,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残酷过程,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中,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的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成。
犹如进步与自由是启蒙大叙事的一对紧密相关的肯定性概念,停滞与专制也是一对紧密相关的否定性概念。笔者追溯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所谓“观念史过程”,指出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收编”中国形象。首先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勉强断定:“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然后是尼古拉?布朗杰的《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断定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专制主义的。黑格尔则毫不客气地总结:中国政体是东方专政政体中最坏的,中国是“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十足意味着它是东方专制国家的极端形式,奇特意味着中国的专制政体自有其特色,就是家长式专制。专制的“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西方思想界不断确定中国形象的东方专制主义内容。东方专制主义形象最后不仅被纳入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而且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代表。黑格尔标志着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视野内的专制主义神话的终结。
的专制主义形象一旦确立,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不断确定、丰富,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作为话语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的中国的视野与个别文本的话题与意义,以致于实践领域的中西关系或西方对华政策。话语指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特定主题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话语假设语言与行为,观念与实践都是不可分的,话语不仅决定了意义与意义表现的方式,还决定了行为的方式,甚至行为本身也是话语。西方的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就为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福柯认为话语中知识/权力是不可分离的,知识不仅假定"真理"的权力而且使权力变成真理。一旦你确立了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如果再将中国形象定位在专制与野蛮上,西方掠夺性的野蛮战争就获得了"正义"的解释与动机。
六
我们在三个层次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探讨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在何时又如何生成的,在什么社会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其次,西方关于中国的中国形象叙事的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以及该体系在空间上的扩散性与时间上的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表现出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成为一种文化程式,又如何控制个别文本表述的;最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暗含的权力结构,它作为知识与想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渗透权力并发挥权力,构成殖义、、全球主义的必要成分,并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与文化霸权的。
时代西方在东方主义话语体制中表述中国,黑暗、愚昧、堕落、残酷、恐惧,永无变化的停滞与单一性,不可改变的野蛮……如此类型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在传教士的社会历史著作中,出现在文学家的虚构作品中,也出现在哲学家严肃的思考中。不同叙述者可以有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背景,有不同的动机与方法,应用不同的本文形式甚至讨论不同的主题,但他们表现的中国形象,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西方从1750年前后开始经营起的反面的中国形象,最终完成在两次战争间,而且一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什么变化。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东方学作为一种学科知识是如何向权力领域“分配”的。构筑东方专制主义形象的是哲学与学,构筑停滞的帝国形象的是历史学,与此同时,人类学视野也在构筑所谓中国的国民性神话,塑造出另类化丑化的中国人的形象,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格局中确立所谓的人种志特点。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反思19世纪人类人类学知识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时发现,它与西方的殖民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研究将西方赋予殖民地民族的种种“他者”特征“本性化”为所谓的民族性格,从而将历史秩序自然化。18
西方构筑的停滞专制的形象,是西方的一部分。塑造一个被否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不仅赋予西方者以某种历史与文明的“神圣权力”,而且无意识间竟可能让西方霸权秩序中的受害者感到某种“理所当然”。这种定型化或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同时出现,不仅说明现实权力结构在创造文本,文本构筑的他者形象也在创造现实,巩固这种秩序。这是话语的权力层面。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表述西方集体无意识中文化他者的话语,都超越了所谓观念诉求的客观认识与真伪之辨。西方的中国形象,1750年前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最终不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是西方文化本身的变化;不是西方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西方的表述差异问题。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文化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的机制。
曼海姆对人类知识进行的社会学发现,一切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其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者是乌托邦的,或者是的,其差别只在于知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的,而的功能是维护现实秩序的;乌托邦指向未来,而巩固过去。乌托邦与,在历史过程与逻辑结构中,都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转化的范畴,与现存秩序一致的统治集团决定将什么看作是乌托邦(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思想);与现存秩序冲突的上升集团决定将什么看成(关于权力有效的官方解释)。如果上升集团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成为统治集团,它曾经拥有的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乌托邦可能转化为,而也可能取代乌托邦。19
曼海姆依旧在“知识”意义上乌托邦与,而保罗·利科尔则直接将乌托邦与的运用到“社会想象”中。因为知识本身就在表述人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直接用“社会想象”可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就像阿尔杜塞用想象定义20。利科尔指出,社会想象实践在历史中的多样性表现,最终可以归结在乌托邦与两极之间。乌托邦是超越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而则是整合的、巩固性的社会想象。社会想象的历史运动模式,就建立在离心的超越颠覆与向心的整合巩固功能之间的张力上。21
曼海姆与利科尔有关社会知识或社会想象的两极类型理论,为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解释框架。1750年之前美化的中国形象,是一种充分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寄托着西方文化不同层次的理想,教士、哲学家、家与商人们,都在用中国形象表现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不满与期望。启蒙运动后期,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乌托邦转化为,西方社会想象不再是用中国形象衡量并批判西方现实,而是以西方现实为尺度衡量并贬低中国。低劣黑暗的中国形象,从各个方面,宗教、道德、、经济、哲学,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证明西方向中国殖民扩张的正义性。如今,传教士反复强调中国人道德败落、心灵阴暗,证明教拯救中国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哲学家们一再中国社会贫困、专制、历史停滞,甚至种族低劣,这样,西方征服中国并改造中国,就成为文明征服野蛮、自由与进步取代专制与停滞的启蒙正义之举,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17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这次转折并非一劳永逸。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并非从此漆黑一片。19世纪高峰时代,曾经美好的中国形象,作为东方情调隐入浪漫的、纯粹文学性的幻想中。美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主义审美期望中复活了。这是另一种启示意义上的“孔教乌托邦”,其社会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是超验神秘的或非理性的。正如所有关于异国情调的幻想一样,是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我们认定有关中国的离奇神秘、异国情调的幻想,也是一种乌托邦。它放弃了启蒙运动中试图进入现实权力中心的那种冲动,以美学的形式与现实形成“疏离感”, 在现实权力的边缘反叛中心。审美幻想与既定现实的距离,是“自由的距离”。在那个遥远的浪漫空间里,幻想的可能瓦解现实的体系及其基础。22
现代性既表示一段时间,又表示一种明确对应着该历史时间的观念。这种观念由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方面构成,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它出现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已基本形成。其中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意义是:以自由批判的理性为主导,追求知识与财富,通过教育与达成社会和谐,完成历史的进步。现代主义的核心意义是现代性造成的社会断裂,可以通过审美批判超越。23美好的中国形象的特定侧面,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期望中显现出来,遗憾只是影响的范围与时间都非常有限。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关于“他者”的想象性表述,其意义与功能,表现在西方文化自我向他者“投射”的关系上。正如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空间。”24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肯定否定两种类型间反复,实际上是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调节自身,实现其颠覆与批判、维护与确认西方文化自我的功能。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者是美好的、乌托邦性的,或者是被否定的化的,超越颠覆或整合巩固,意义都在西方文化本身。我们的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观察到中国形象的断裂与延续,看到话语意义变迁的 “潜在的语法”。
七
我们很容易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下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此定义的前提下开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将七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看作一个连续性整体,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延续变化但又表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的、由各种不同的印象、想象、比喻、象征、观点、判断等构成的织品。在这一整体性的中国形象话语中,许多思潮是纵横交错的,同一素材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中,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论是断代还是专题,都难以做到界限清晰,不仅素材是相互交织的,观点也相互关联。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中国形象的转化,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发生在1750年前后,启蒙运动的时代。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依旧表现出两种类型,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25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传说与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中开始,但同时也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让黑暗的中国形象边缘泛出光亮。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种最初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在30-40年代赛珍珠的小说与亨利·卢斯主持的《时代》、《生活》对中国的报道中,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但这段“闪亮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到60年代中国形象又逐渐由暗复明,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我们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其中反复出现两种极端类型表现出的二元对立原则以及两种相反的中国形象对西方文化认同与超越的功能,才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宗旨。“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70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 80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的阴影中,80年代是“后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然而,新幻象在一夜间破灭,9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又进入新一轮的否定化阶段,世纪末的像世纪初的“论”一样,令西方感到恐慌。
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可能断裂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甚至完全相反,也可能在变化中表现出某种原型的延续性。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26 20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另一位研究者发现,20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27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前景产生怀疑。《被误解的中国》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点在30-70年代间。科林·麦克拉斯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修订版,1999)则写到90年代末,重点在20世纪最后20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20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两极间的剧烈摇摆,转折点在1989年。麦克拉斯认为20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世纪间最复杂的,明暗毁誉参半。28实际上我们从20世纪中国形象整体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整体上看,20世纪最后25年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恶化”的。80年代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的恐怖故事的阴影中,90年代又笼罩在6、与中国威胁的阴影下,在20世纪内,它是50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是1750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的继续。
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形象的。这种原型是具有广泛组织力与消化力的普遍模式,任何外部知识都必须经过它的过滤与组构,变成可理解的形象。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形象这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使任何中国的“事实”本身都失去自足性,必须在既定原型框架中获得改造与装扮,以充分西方化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滋养西方人的想象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国,这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或异域,只有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时,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
中国形象塑造了西方文化想象的异已世界。它帮助西方文化确定自身存在的位置、意义,确定他们自己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或许西方文化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现实,除非是中国成为一种虚构,成为他们能够观照自身、理解自身的幻镜,让他们从中看到他们欲望的天堂或者恐惧的地狱。在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像在19世纪殖义浪潮中一样,中国作为他者,依旧是被排斥、被否定、被贬低、被恐惧的对象。西方未曾改变,中国形象也从未被改变过。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极权主义倾向,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21世纪的第一年,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为中文版的《的崇高客体》写的序言中说:“我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多少?把中国置于难以捉摸的神秘他者之境,这种貌似谦逊的姿态难道不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神秘化吗?因而惟一要做的诚实之事,就是以此“前言”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与这个他者建立起真正的关联?”29 注释:
1 马可·波罗时代之前,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笔者在《永远的乌托邦》一书里,也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但这些传说毕竟虚无缥缈、难以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的传说,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一则是因为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发明”中国,一时间出现许多表述中国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或话语性,不外是重复强调大汗的帝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二则,此时出现的中国形象,不仅指涉明确、特征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大的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期,虽然强调点有所变化。三则,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
2 参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
3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斯记》(1436-1480年)。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文体有历史、游记、书信、语录体的记述(后者如《万国通览》),还有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既有高雅的拉丁语,也有通俗的罗曼语或法-意混合语。至于文本的内容,既有记实、也有虚构,而且经常是记实与虚构混为一体。
4 《欧洲与中国》(英)赫德逊著, 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137页。
5 详见《契丹传奇》,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xx年版。
6霍尔研究文化的意义时使用“表述”(representation),他认为“表述”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参见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ited by stuart hall,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chapter ⅰ, “the works of representation”。
7详见《大》,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xx年版。
8详见《孔教乌托邦》,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xx年版。
9 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
10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y adolf reichwei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 1925,p25-26.
11 《莱布尼茨和中国》,安文铸等编译,福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12详见《世纪中国潮》,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xx年版。
13 《东方学》,(美)爱德华· w· 萨义德著.,王宇根 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14参见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l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by henri baudet, trans, by elizabeth wentholt,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15 笔者认为,西方现代的起点在1250年,而不是1500年。参见拙文《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粤海风》20xx、3。
16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又称元叙事(meta-narrative),指统摄具体叙事并赋予知识合法性的某种超级叙事,如启蒙运动构筑的有关现代性的一整套关于理性、自由、进步、等主题的宏大叙事,不仅确立了知识的规范,也确立了权力的体制。因此,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 参见《后现代状况》,(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17 参见拙文《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xx、10。
18 参见《帝国》、《第二人类》,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xx年版。
19参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 著,黎鸣、李书崇 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四章。
20阿尔都塞认为是“表现系统包括概念、思想、神话或形象,人们在其中感受他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参见“reading‘capital’” by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 “introduction”。
21 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 by paul ricoeur, edited by george h. tayl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p194-7.
22 参见拙文《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文艺理论与批评》20xx、1
23 参见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by gerard delanty, sage publications, 2000, chapter 1: the discourses of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moderni and fin-de-siecle socialogy.
24 《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蒯轶萍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02页。
25 参见《龙的幻象》,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xx年版。
26 《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27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y steven w. mosher,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上述观点参见该书第1-34页:“prologue”与“introduction”。
28 参见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by colin macker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t ii: western imag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9《的崇高客体》,(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编译出版社,20xx年版,“中文版序”。
第十一篇 列维:知识分子的使命_西方哲学论文
一
列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 ),是法国当代哲学中一个重要流派“新哲学”领袖人物。他是一位揭示法兰西思想意识的人、犹太人团体的代言人、左派分子、自由悲观主义者。他著述勤奋,作品频出,影响巨大,至今已出版了以下著作:《民族主义与革命在孟加拉》(1973)、《人面兽行》(1977)、《上帝的遗嘱》(1979)、《法兰西思想》(1981)、《原则问题》(1983-1999)、《头脑中的魔鬼》(1984)、《亚洲印象》(1985)、《知识分子颂》(1987)、《夏尔·波德莱尔的最后日子》(1988)、《自由的冒险历程》(1991)、《最后的审判》(1992)、《男人和女人》(1993)、《危险的纯洁性》(1994)、《萨特的世纪》(2000)等。除了写作,他还积极投身于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和活动,很有萨特的生活风格,一直生活在法国媒体聚焦之下。
《自由的冒险历程》(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une histoire subjective des intellectuels),宣示了列维的知识分子主体史观,反思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追思了知识分子与自由、冒险间的秘密关系,为我们理解“20世纪”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哲学视角,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WwW.meiword.cOM它聚集着法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名流:诗人、作家、画家、教授、历史学家、哲学家……本书一问世就立即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
二
什么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属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是理智的化身。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说某人是知识分子,意思是说,他(或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掌握一定学术文化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记者、编辑、工程师等都可归入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之中,其中不乏博雅之士。他们是有才智的人,是聪明人和智者,是天才,不是“大老粗”,有理智、智慧、智力、才智,有精深的知识,有特强的理解力(理智能力),善于推理和思考,其直接任务是理解、从事智力活动,或脑力活动,或思维活动,或精神活动,使所为之事理智化和打动人的理智,其行为具有理智性。他们强调理智、理性的重要性,崇尚凭理智行事,主张唯理智论(唯智论或理智主义)和智力至上。他们是唯理智论者(唯智论者或理智主义者)。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理智上,都是卓尔不群的。总之,知识分子是智力、理智、知识的在者、象征或代表。
知识分子一词,在英语中,即intellectual,在法语中,即intellectuel。法语intellectuel来自拉丁词intellectualis,正式进入法语的时间是1265年,这时还只是一个形容词,意即与智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相关的特性,指“智力的”、“理智的”、“精神的”、“知识的”,与moral,représentatif,spirituel同义;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把它与“脑力的或思维的(cérébral)”明确联系起来,指某人具有过多的智力和精神的东西或智力生活(脑力生活)占主导地位,于是,那些献身于智力生活的人被称为“脑力劳动者或思维劳动者(travailleurs intellectuels,cérébral)”,与“体力劳动者(travailleurs manuels,manuel)”相区别。有了这一认识,形容词intellectuel才有向名词intellectuels即“知识分子”这一层含义靠近的可能性。可见,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人才把intellectuels看作一个阶层即“知识阶层”。这是一个十分新近的发现。至于intellectuelie和intellectueliste的出现就更晚了,前者出现的时间为1853年,后者为1876年。intellectuel作为名词,与clerc,intelligentsia(intelligentzia),mandarin同义。
不过,clerc一词除了指知识分子外,还指教士、神职人员(clergé)、文人、学者、书记、文书、办事员;此词来自拉丁词ecclés,clericus和希腊词cleros,十五世纪时指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即lettré(文人)、savant(有学问的人、博学者、学者、科学家)、expert(专家、行家、能手),即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intellectuel。能配称为savant的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某学科,在某领域造诣很深。intelligentsia是个俄语词,在历史上指沙俄时代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mandarin指中国古代的官、官员,转指名士、要人、闻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儒生、儒士)”、“士人”,即读书人(有时也叫“士大夫”或“士子”或“学子”或“士民”),其中会做文章的人则叫“文人”,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其中出现了“霸权势力”,这一势力横行于文学界、艺术界、界。我们今天称作“学霸”。
中国历史上的“儒”、“士”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汉语里,“知识分子”是个译词,即是对intellectuel的翻译。这表明,它大大晚于法语词intellectuel。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现代称谓的意识相当晚。但究竟起于何时,今已无从考掘(考古)。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儒,古时对读书人、学者的称谓,博洽多闻者就是儒,也指分化于巫、史、祝、卜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人(知识分子)。儒士是崇信孔子学说者,儒生是通经之士,都可指一般的读书人。可见,读书人就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而儒又意谓柔(顺)、愚昧、缓慢、懦弱,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柔顺、愚昧、缓慢、懦弱之辈。士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阶层:一是指先秦时期贵族的最低等级,位居大夫之下;二是指古代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是四民(士农工商)之一;三则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林、士流、名士,在这一层含义上,士即儒,即智能之士、学问之士。这三个方面的“士”品德好、有学识、有技艺,同为国家之本、天下之用。可见,儒和士当是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最早称号。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益于人类(生民)、宇宙(天地)、往圣、万世、人生、社会的栋梁。
三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特征。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所描述的法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为自由而冒险的战者。知识分子大多有自由的天性,愿意为这自由冒险。知识分子冒险的历史也相当漫长。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必求人格的、精神的、思想的,是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知识分子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创造者,人类文化因他们的劳动而产生、发展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他们在精神上占据了人类的制高点,其超前思维引导着常人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以自身的思想规尺衡量常人社会、社会人、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务。他们生存于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之间。这决定了他们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创建理论与参与社会,或者说,写作与战斗。写作是冒“理论”或“文本”之险,战斗是冒“实际”或“军事”之险。社会事件让知识分子卷入其中,让他们成为风云人物。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开头就提出知识分子及其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知识分子的历史究竟源起于何时?或者说,“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名称何时出现?澄清这一问题就是为“知识分子”正名。法语词intellectuel作为名词,指谓法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或读书人)这一阶层,还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之后的事情。1898年发表于《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的《知识分子宣言》标志着“知识分子”之名(概念)从此确立。这个宣言是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发表的。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举动。这一举动使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可以广泛和解而具有共同追求,使本具贬义的称谓上升为一种荣光、一种象征、一面旗帜。和解就是欢乐的婚宴。“知识分子”的含义是深刻而明确的,不再是肤浅而暧昧的。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敢于正面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崇尚知识,知识是和解的基础,即是说,他们正是站在“知识”这一共同基础上接受了“知识分子”这一新称谓。可以说,左拉一代掀开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一词开始于左拉时代,在法语史上具有深刻意义。法国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美好时代”。
在法国知识分子这面伟大旗帜下,聚集着数目惊人的“智识分子”。如果说,19世纪末采取某种和道德立场的作家还只是个案现象,那末,在20世纪则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除了作家外,还有画家、教授、诗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把参与评论国家事务视为分内使命。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新型人物。他们为自由而战斗,努力使自己回复到自由王国去。这一回复过程是一个冒险历程。他们在正义、真理、善良与国家之间调停,在自由王国与空间来回奔忙。为此,他们在哲学、神学、、媒介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成为勇敢的人。这意味着作家、画家、教授、诗人“有时能够也应当停止写作或创作(peuvent et doivent s’arrêter parfois d’écrire ou de créer)”[1],以参加社会活动。可以说,写作或创作有时能够而且应当服从社会活动,并为其服务。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有浓厚的色彩:仅仅埋头写作是绝对不够的。他们要为生活创造最大的可能性条件,参不参加社会活动成为道德问题。战斗与写作一样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继续存在的条件。如果知识分子在某一天失去战斗就像失去写作一样,就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失去存在的价值。
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社会”这个居所的“居主”,就必须继续写作和战斗。写作和战斗都是他们切入社会居所(制度空间)的直接路径。写作还是战斗?有时必须作出果断抉择。写作与战斗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双重在者,有时也使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
四
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何为?”这个问题。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宇宙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对于列维来说,具体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时代何为?”我们应当如何领会和把握这一问题?答案应是怎样的?“时代”在这里具有冒险特征,是指栖身于自由冒险历程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自由冒险时代是令人惧怕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冒险的加剧变得更加令人惧怕。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历程中必须承受和亲历自由冒险的恐怖绝境。他们是出入绝境的在者。战争使世界转入完全的黑夜之中,自由冒险者的冒险也随着进入深渊泥潭。海德格尔在《林中路·诗人何为》一开始就借用了荷尔德林的问题:“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并进一步指出:
“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2]
神的末日、上帝之缺席以及神光之熄灭意味着世界进入黑暗(黑夜)时代。没有上帝的黑暗时代无疑就是贫困时代,也是一个缺乏基础的时代。世界丧失了基础,就掉进深渊泥潭。诗人自属知识分子群落。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自然包括诗人的使命。冒险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与贫困时代的诗人何为,具有一致的意义。“诗人何为”仅仅是“知识分子何为”的局部性问题。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这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3]
由于世界进入黑夜、掉进深渊泥潭,因此,知识分子必然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冒险:或写作或战斗。当然,他们最好进行有效的写作和战斗,写出有效的作品,争取胜利的战斗。他们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也听任冒险的摆布,他们的存在进入冒险状态。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冒险,一切以冒险为中心。冒险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冒险这一日常生活是他们的基础。知识分子作为冒险者,其冒险就是最高的自由意志。
作为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如若它们被抛弃了,那么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如若它们仅只被消灭了,那么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只是就所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的无保护之中。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4]
天平意味着权衡、均衡、摇摆、踌躇,冒险往往把冒险者(如列维的知识分子、海德格尔的诗人)带向天平,使冒险者处于这种或那种状态,也使冒险者进入游离状态。因为冒险途中多迷途,迷途就是歧路、岔道,所以天平状态实际上是危险状态。冒险者必须在天平上把握住自己,因此不能处于不安全之中。安全地存在是冒险的先决条件,而冒险又是为了获得安全的存在与创造和平环境。这是一个有目的、有条件的回复过程(永久重现)。知识分子在冒险过程中必须寻找安全的居所和保护伞。这种居所不仅指住处,而且指国家、组织、集团,甚至某位要人、某种靠山。他们在居所相互依靠、相互合作、相互利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为这种居所冒险,他们的使命与整个居所及其各个成员息息相关。
五
在冒险的苦乐园,贡是一个突出代表,代表一个自由冒险的时代。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贡时代”。贡作为党的伟大作家对法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重大问题是主义问题,当然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或上的问题。他在法共扮演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角色,这完全是他的肉体存在。列维关心的是,他做了什么事?想了什么事?能对此说些什么?这么重要的大作家以法共为安身立命之所,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当然他经历了不断寻觅的冒险,由达达主义而超现实主义、无主义终至主义。20世纪法国的大作家中许多人都在寻找“安居工程”,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就下决心定居下来,如马尔罗象征戴高乐主义,纪德即背叛者,加缪象征正义,萨特象征信仰,莫里亚克只不过是个坏孩子。
贡为什么最后找到了“主义”这个居所?因为布勒东禁止他写小说,而党需要他写小说,于是他选择了党,以过受到保护的安全生活。安全生活是当时的人们的梦想。要获得这种生活,就必须首先投靠某个重要组织:或法兰西学院、或内阁、或议会,但它们对贡都不合适,于是他选择了党。加入党,贡受到保护,可以认真写作,安心生活。可以说,小说和生活成了他选择党的理由。这种理由同时成了他冒险的动力。当然,从总体上看,超现实主义者和主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贡。尝试过多种生活(也是矛盾的、冲突的生活)成为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时尚,但是难以同时得兼,多数时间只能二者或多者必居其一。
列维关注的关于贡当时的状况及其所作所言,可以他的朋友埃德蒙德·夏尔-鲁所言为据:
j’ai trouvé aragon profondément troublé, se demandant ce qu’il fallait croire et ne pas croire, et déjà tout à fait conscient que ce ne serait pas les thèses officielles du parti communiste qui pourraient le convaincre. ces thèses, vous les connaissez! on parlait de provocation. d’ingérence de la cia… et en fait, grosso modo, de la responsabilité américaine dans cette intervention. alors, bien sûr, aragon ne marchait pas. il était trop européen, trop civilisé (et bizarrement civilisé, si vous réfléchissez combien son horizon avait été limité au début de sa vie à paris, et même à quelques quartiers de paris), il était de naissance trop européen pour ne pas sentir qu’il y avait quelque chose d’autre, là-dessous, d’affreusement grave. je crois que ça a été un tournant qui ne l’a pas déstabilisé, ne l’a pas rendu moins communiste, mais qu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fait douter de l’urss.[5]
我发现贡极度不安,寻思应该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他已完全意识到他无法信服法共官方论点。这些论点,您是知道的。他们谈论过挑衅、美国情报局的干预等。事实上,大概是指美国在这次干预中的责任。当然,贡没有跟上这种论点。他过于欧化,过于开化(如若您考虑到他在生活之初的视野只局限于巴黎,甚至只限于巴黎的某几个市区,就觉得他得到了一种古里古怪的开化),他生来就过于欧化,以至无法觉察出其中玄机,并且极其严重。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没有使他发生任何动摇,他仍然信仰主义,可是,这使他开始怀疑苏联。
形势把贡带到了乡下别墅,贡是孤独的。孤独使贡置身于不安状态:把他带上了信与不信的天平上。他站在这一天平上摇晃不定,一不小心就从一端滑向另一端,甚至摔倒。这是人生重心的偏离。信与不信都是一个信仰或信念问题。信此还是信彼,是应当认真寻思的,因为这是一个居所、家族、路线问题。站在天平上的贡是够呛的。信与不信的天平意味着冒险、危险、摆动、抛弃、解雇、均衡、比较、补偿、悬而不决、犹豫。不安的贡正处于这种种情形构成的复杂状态,眼前一片混浊紊乱,思想昏昧,心绪不宁,已经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不知道往那里走,法共官方言论也不足信。他成为一个整天慌张发窘的在者。在关于挑衅、干预和美国责任的讨论中,贡因过于欧化而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恰恰是他的转折点。转折点联结着之字形弯道或曲折迂回的弯路,也联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反方向,标志着车削、转动、转向、翻转、绕过、转变、表达、变成等。它标志着方向、重心和意志的分配,分配不同,结果就不同,犹如转动钥匙,对转动的方向、重心和意志作出左右不同的分配,其结果要么开要么关。分配应当符合意愿的要求,不能与要求相背离,否则结果必与要求相左。这个转折点虽不能动摇他的主义信仰,但已使他开始对苏联抱持怀疑态度。
贡行游于天平上,是一位超现实更甚者或冒险更甚者,即超-超现实主义者,在超现实派的道路上比统治者布勒东走得更远更快。他也许是冒险时代的作家、诗人的先行者,他的命运可以证明这一点。
性自由冒险把知识分子引入“出”与“不出”的矛盾境地。自由冒险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无可选择地参与时代,投身,必须忘记所知的一切,如德苏条约、集中营……这是为了某种形势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事务成了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服务。为此,他们以前确立起来的原则倾刻化为乌有。不过,他们一旦成为战斗作家(作家),其想象力、创造力、智慧和才华就会荡然无存。事务偷走了作家的时间。时间失去,年华飞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明知如此,却执意想继续当作家,只是免强写作而已。他们已经失去了小说(创制出真东西)的权利和时间。最明智的选择是退笔从政。作家在介入期的作品量少而质劣,介入期即作家作品的萧条期。作家只有摆脱介入,才能恢复行使自己的完整权利,才能重返自由的精神领域。不然,时至晚年会真正感到气怒和烦心,因为逝水年华永不复现,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业被延搁而终无实现之日,青春曾为政务而耗尽,中年和晚年悄悄来到了面前。人生充满幻灭。
六
另一位冒险者马尔罗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即“知识分子何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列维是马尔罗的崇拜者。这不奇怪,因为马尔罗迷恋冒险,令人着迷,恰恰符合作者胃口。马尔罗何许人?他生于1901年,死于1976年。其正式身份是法国作家。他除了写作外,还从事社会活动。1927年加入法国党,同年广州起义时访问了中国。小说《征服者》反映亚洲的觉醒,《人类处境》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希望》则反映了他亲身参加的西班牙内战。还有作品《反回忆录》、《蔑视的时代》、《沉默的声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阿尔萨斯游击队。在戴高乐执政期间,他担任新闻部长和长。他在西班牙飞行中队的某些战役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作为一位作家获得了战争体验,并梦想成为战争领袖。当年在马尔罗身边工作的人、飞行中队最后的幸存者诺通认为,马尔罗神气而有才华,举止非凡。马尔罗就是马尔罗。他所领导的西班牙空军中队人员都是左派分子,处于无状态。中队运作不靠任何纪律、任何强制,其成员充分体验了自由。他还充当过前机枪手,这种躬亲实践是一种冒险。他带领空军中队去西班牙的目的是革命,至少使革命成为可能。他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奥尔维尔、帕索斯之间的立场相反。他比他们勇敢,但没有他们清醒。马尔罗的一生充满传奇、神秘、冒险色彩,犹如历史画面中的阴影。
人们对马尔罗在西班牙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马尔罗是个撒谎大王,去西班牙仅仅是为了积累传记素材,对其参战的实效性和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人认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忘却的。列维显然是站在马尔罗一边的,认为不少人心存偏见和恶意,并为他辩护:
elle a joué un rôle, parfois crucial, dans quelques-unes de ses batailles. honneur à malraux le combattant. honneur à malraux le condottiere. connaissez-vous un autre écrivain qui se soit rêve-et vécu-chef de guerre?[6]
它(飞行中队——引者)是起了作用的,有时在一些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荣誉归于战士马尔罗。荣誉归于雇佣兵队长马尔罗。您还见到过另一位梦想并亲身体验过担当战争首领的作家吗?
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尔罗的勇气和胆识,像这样的作家只有他一人,因为他领导的飞行中队是临时组成的,装备极其简陋——飞机破旧,状态不好,孤立无援,在战争初期差点全部阵亡。然而,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表现出英雄本色,为战争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十字路口上路标性的。可以说,马尔罗及其飞行中队成员是冒险的代表,他们的冒险已经达到了极致,因此,荣誉归于马尔罗,是应该的,它也属于他所领导的飞行中队全体队员。荣誉是对有功者的奖赏,象征着体面、光荣、敬意、贞节、礼遇、地位、等级、伟大,是对耻辱、讽刺、贬低、怀疑、偏见、恶意的清算和颠倒。只有立功者才能撞开荣誉之门而获得荣誉,才能被载入西班牙战争史册。立功者只有告别耻辱才能亲近荣誉。亲近意味着告别的就绪,意味着从撒谎家向大英雄的过渡,是对战斗事实的证明。
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说家、伟大的反叛知识分子。可是,他当上了部长,参加了法兰西联盟。他改宗了。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骂:恶棍、变节者、分子,但对马尔罗来说,只过知识分子生活是不够的。人的一生就是经营荣誉的历史。马尔罗十分明白,20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对峙的历史,于是,冒险地选择了通往国际主义英雄的道路。然而,他的算计出现了严重失误。主义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是国际的。这就是主义的民族优先原则。他为自己塑造的国际使者形象实际上是冒险的影子,在国与国之间奔波忙碌。战争让他看到了和听见了一切可怕的冒险故事。他与戴高乐结好,把自己视为诗人、奴仆、作家,而把戴高乐看作君王、领主、伟人。在法国,多数作家是失败的家(作家的失足),而多数家是失败的作家(家的失足)。知识分子不是当家的料,家不是当知识分子的料,否则,必然都是半瓶醋。行为的作家与著书的家之间难以存在永久和谐。只能以一个领域的失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胜利。知识分子最终发现自己选定的对象的凶恶面目时,会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伤口都有了,够痛的。
我们还可找到另一改宗的例子,即巴莱斯的情况。巴莱斯是马尔罗的导师,也是布鲁姆和普鲁斯特的导师,在与文学倾向上从一端走向了另一端,长着民族主义的头像和面孔,成为当时巴黎最受推崇的作家,冒着史无前例的危险。他从世界主义者立即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愚蠢的爱国者和沙文主义者),公开反对德雷福斯,只相信土地、死者、根、种族、血统。这令他的信奉者们极度失望。他从崇拜者们中间溜走了。“巴莱斯”简直是冒险的代名词。这就是著名的“巴莱斯效应”。冒险是知识分子成为显要人物的必经之路,冒险世界是专名的战场。知识分子是自由冒险的存在者。在冒险的支配下,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荒诞而矛盾的言行。可以说,改宗后的巴莱斯是一个新人、一个知识疯子。突如其来的改宗对他自己来说无疑是痛苦而困惑的(因为这一革命性改宗是一次大手术、一场生死决战、一种事关荣辱的选择),对他的崇拜者们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震撼着后人。也许,他认定他有权对自己的头像和面孔进行有意的重新分配,以图新的探险和提供双重面孔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时代的与文学的倾向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捉住了他。
七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荣誉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或回避荣誉,也不能过分追逐荣誉。荣誉应当是符合正义的理性追求目标。荣誉和行为应当配称。荣誉是对正义行为的证明和肯定,是对非正义行为的反驳和否定,与耻辱相反。可见,荣誉与正义相关,它把人带向社会义务领域,带向公职,带向公众,带向事功,要人过公开生活或公共生活。追求荣誉就必须首先追求并且过公开生活,抛弃隐秘生活。知识分子进行自由冒险就是过公开生活,马尔罗的行为足以表明这一点。
冒险生活使人的内在性格外化。冒险必然切入社会的“公开场所”或“公共空间”这一宽广领域,使人的生活公开,而公开化解隐秘,为隐秘者推开窗户,铺设通往窗外世界(社会、国家、机关、公众……)的道路。冒险允许隐秘者进入窗外世界,同样允许窗外世界进入隐秘者之中。知识分子通过冒险把自己牵引向社会,使自己进入公开状态而成为公开者。冒险是知识分子从书斋从象牙塔切入社会的直接途径。冒险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使自身他化的过程,使自身获得一种复杂的外在关系。外在关系的获得标志着人处于公开状态。人一旦处于公开状态就成为受监视者,其一切言行都受到公众的监视,于是,公开的人开始时时处处十分注意和检视自己的言行,相当在意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与此同时,公众也开始比以往更加留意其言行,时时刻刻执持批评态度,以更加挑剔的眼光看待公开的人。
冒险生活即公开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或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它把人从隐秘生活中牵引出来,使人进入公众中,使人由隐秘者成为公开者或公众人物,使人进入荣誉之途。只有公开者才能处于冒险状态,冒险状态则是对反公开者的否定,是对隐秘状态的告别。隐秘者对立于公开者。隐秘封闭和拒斥了荣誉,而公开是对隐秘的扬弃,使公开者向荣誉敞开大门。荣誉仅仅是身外物或外壳,因此,我们绝不能违背正义而巧取荣誉,更不能将一切荣誉都搜罗到自己名下,也不能为了荣誉而荣誉,成为荣誉的奴隶;我们可以失去荣誉,但绝不能丢弃正义;否则,荣誉如同废物粪土,一文不值。
蒙田写道:
应该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去打仗,并耐心地等待奖赏,你只要做了好事,不管如何隐秘,都会得到奖赏,即使是行善的想法,也会得到报偿:正直的人做了好事会感到心满意足……我们的心灵要起到自己的作用,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内心,只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它叫我们不要害怕死亡、痛苦乃至耻辱;它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忍受失去孩子、朋友和地位的痛苦;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它也会让我们在战争中去冒生命的危险。[7]
有朝一日,人总有一死。冒险者自然是总有一死的人。冒险意味着受伤、致残、牺牲、死亡,意味着告别生命,即进入毁灭性深渊。毁灭性深渊是绝对深渊。冒险者们是不怕掉进入这绝对深渊的,因为他们早在冒险之前就把生命抛至脑后,冒险的勇气超过了生命本身。冒险更大胆,意愿更大,意志力更强。绝对深渊是冒险者的最低线。每一位冒险者一旦踏上冒险的征途就会掉进这个深渊。这个深渊的确深不可测,随时敞开着,让人进入。勇敢而无私的冒险者意愿把它变成永恒的居所。在冒险之前,冒险者们必须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时刻准备着身陷绝境。这要求冒险者们必须摆脱私利,具有勇气和毅力,甚至愿意为冒险献身。
海德格尔如是说:
那冒险更甚者并非出于私利和为个体本己之故而冒险。他既非试图获得好处,也非沉溺于自私自利。尽管他们冒险更甚,但他们也不夸张任何显著功绩。因为他们冒险更甚只是凭这么一点点,即他们“……秉气勇毅……”。他们在冒险方面的“更”就有如游丝般难察的气息那样微小。从这种提示中不难得出谁是冒险更甚者。[8]
这充分表明,冒险重于生命,冒险行动胜过冒险者本身,冒险者全凭勇毅而不出于任何私利我欲。冒险使知识分子成为冒险的存在者。
八
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是自由冒险历程中涌现出来的又一大奇迹。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党成为时髦,超现实主义者中不少人都是党员,后来又退出。列维指出,劳动社会学创始人纳维勒是超现实主义的最后见证人。超现实主义阵营拥有一批著名人物:佩雷、布勒东、阿尔托、贡、洛特雷阿蒙、纳维勒、贝尔尼埃、巴塔伊等等。其中,布勒东居于领导地位,既严肃又好讽刺,不喜欢肤浅的玩笑,好摆权威架子。尽管纳维勒与布勒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情感化分歧,还是把友谊关系保持到底,但与贡等人没能保持良好关系,不再来往。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观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纳维勒与布勒东发生冲突后有十年未见。有一天,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小型会议上相见,几乎相对而坐。当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差不多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只有布勒东一个人举手(其实是举起了一个指头)表示反对,却一言不发便起身走出了咖啡馆。[9]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背影。这个背影是矛盾、主宰、权力、立场、信念的象征。
列维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反现代文明的,主张忘却超现实主义及其运动。关于作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je crois, moi, que les écrivains sont des êtres uniques. je crois que leur univers intérieur est également unique. je crois que leurs démons,leurs fantômes, leurs phantaes n’appartiennent vraiment qu’à eux. je crois que, lorsqu’ils prennent la parole, ils ne le font au nom de personne et peut-être même à l’adresse, à l’intention de personne. je crois enfin que cette croyance est d’une absolue bité puisque c’est en elle que se reconnaissent, depuis maintenant quelques siècles, la plupart de ceux, petits ou grands, qui pratiquent la littérature ou, au moins, y réfléchissent. pour tous ceux-là, pour tous ceux qui se souviennent de ce que l’expérience littéraire a pu avoir-et a encore-d’irréductiblement singulier, il y a là une raison de plus, et pas la moindre, d’oublier le surréalie.[10]
我认为,作家是独一无二的人,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样独一无二,他们的恶魔、幽灵、幻影的确仅仅属于他们本身,他们讲话时,这样做也不是借用任何人的名义,甚至也许并不想向任何人说清楚,这一信仰是绝对平凡的,既然至今数个世纪来,大多数搞文学或思索文学的人,不管他们是名人还是一般人物,都奉持这种信仰。对所有这些人而言,对一切没有忘记文学经验有过且仍然拥有无法消除的独特性的人而言,这里有着忘却超现实主义的又一个并非枝节的理由。
布勒东绝不允许任何人做有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如巴塔伊具有摇摆不定的危险信念,也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走回头路,而阿尔托更是一个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和立场。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常常互相诅咒、侮辱、谩骂、抨击、贬斥、争吵,充满污垢,极尽粗言之能事,把口头斗争和粗话推向崇高的文坛。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开除了与己不和的人:纳维勒、贝尔尼埃和巴塔伊(他们是孤立地进行愚蠢的文学冒险之徒)。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如一,必须具有完整的品格、全面的身份。他们对本书作者列维一代影响巨大,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同代人。超现实主义者具有好战精神,把不同路线上的人交织在一起。超现实主义对冒险的贡献之一是树立宗派精神,主张集体冒险。超现实主义者信奉弗洛伊德,但就群体观念而言,倒更像荣格主义的信徒。他们自以为是创造与天才相结合的浪漫主义者,但事实上实行恐怖的专制主义和好战策略。在今天看来,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文学恶梦,是一场幽灵战争,是荒唐、混乱、矛盾、恶毒的组合运动,因为它对思想推行警察式管制。让我们忘记它吧。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指出了超现实主义独创性的四大特点:[11]
第一、 超现实主义者是在文学与的双重效应的影响下成为作家的;
第二、 他们并不是主张介入的诗人,文学也不附属于;
第三、 他们同时关注着写作与战斗之间的关系;
第四、 追求善和完美。
列维进一步指明,未来的任务在于催促一种现代精神的出现,它将丝毫不依赖前卫派的主题、措辞、非思想手段。[12]超现实主义者试图将文学与协调起来,强调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认为造就了文学家。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与到社会上积极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写作与战斗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见的秘密关系,甚至具有一种先定的和谐或一致。超现实主义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保持这种方式。
人们也注意到,在超现实主义运动周围还出现了一些小团体,其中巴塔伊主持的“社会学学院”较有特色。这个团体主张几乎什么都谈,恰恰不谈社会学。可见,这是一个反讽性团体。布勒东引导人们为他者梦想,巴塔伊则强调人们替他者讲话。当团体中某位不在场时,巴塔伊就代言,犹如代他签名或为他者梦想一样。代言(替他者讲话)是为他者梦想的翻版,是具有冒险性的替补。顶替者最终是否翻供?本来的讲者为什么不在场?顶替者与不在场者之间具有何种关系?文本的作者其实也是替他者讲话,很少让他者自己出来讲话。因为团体成员实践集体性一致性游戏,实践的结果都必须签署每个人的名。这样的签名行为处处存在。
九
在举世闻名的阿尔及利亚事件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列维在书中主要举出了社会学家阿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和加缪、以及让松和布朗肖。
“阿尔及利亚”这块法属领地(法国把它作为自己的海外省),被视为分子、贝当分子与其他坏人的杂居地。作者把一位法国小学教师(小知识分子)莫诺罗因起义而死视作一种象征。莫诺罗远赴阿尔及利亚传播法国文化,成为法国自由、、人道的 “神秘英雄”、“神圣人物”。当时众多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就是保卫普遍的意义。比如原反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成员里维撰文指出,如果阿尔及利亚脱离欧洲,就会给它的国家和带来灾难和衰亡。德拉维涅特是一位典型的殖民地人道主义者。最可憎恨的是完全由杀手组成的秘密军队组织,它常常在“抵抗运动”的大旗下展开其种种活动,实际上犯了不少血腥罪行。大旗与罪行使历史成为一个远比人们所想要复杂得多的东西。错综复杂的历史会变得模糊不清,好人与恶人的界线在历史中也无法确定。历史一旦落入恶人之手,就会成为其借口。恶人必然会在历史档案中抹去他们曾经干过的形形的坏事,甚至粉饰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在历史简单主义者看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善恶之战。
列维如是说:
dans la réalité (celle à laquelle se sont trouvés confrontés les vrais acteurs de l’histoire se faisant) un événement équivoque, hasardeux, dont il faudrait pouvoir recréer toute la part de contingenc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contingence, oui. pour une histoire de l’ambiguïté. face à un événement dont la première vertu aura été de troubler les repères et de faire vaciller les certitudes, je ne conçois qu’un discours:celui qui, loin de la réduire, rendrait ses droits à la confusion.[13]
事实上(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面临的事实),这是模棱两可而又具偶然性的事件,应当重现全部偶然史。的确是一部偶然的历史和一部模棱两可的历史。对于历史事件,首先要打乱历史事件的标记并动摇历史事件的确定性,我仅仅认为绝对不是简化历史,而是恢复历史的混乱权利。
阿龙对阿尔及利亚事件采取了什么立场?介入便是阿龙的立场。他被捧为“介入模范”。他的这一立场选择的确是一种英雄行为。他与萨特达成共识。他既不喜欢也不对阿尔及利亚打赌,也不把革命病毒带到法国本土。他的介入立场源于一种理论、一种经济考虑,也源于历史哲学的思考。[14]
列维指出,阿龙的立场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论:殖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殖民并不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可避免的运动;至于经济方面,殖民化既是发达的根源又是危机的根源,阿龙发现了殖民化正在导致法国的贫困化;阿龙的立场也自然有他的历史哲学观念,具体体现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引论》中,即明确指出,欧洲统治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时代,而法国不再有能力成为殖家。不管怎样,阿龙看到了法国人与其遥远的“海外省人”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使法国和阿及利亚的一体化理念成为不可能。
阿龙认为,使别国殖民化是很花钱的事情,与其这样,不如把钱用于法国本土的发展。因此,他必须尽快离开阿尔及利亚。对于家的失足,那些介入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处于常识环境和事实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人类、社会、历史和宇宙负责。当时的欧洲人流行地说:不是和主义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就是和主义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对此,知识分子们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于是,有的要主义,有的要主义,有的则都想试一试。天真的知识分子易于迈入歧途。对阿龙来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做人方面,人们都把他视为道德化身。他时刻保持着非凡的理性冷静,曾想与他的小同学萨特展开对话,但后者总是回避。他有三部代表作存世:《历史哲学引论》、《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和《克罗兹威茨》。
莫里亚克虽然在1952年声明过他将把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为正义、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但他想的是摩纳哥,而非阿尔及利亚。当然有迹象表明,他也极其关心阿尔及利亚,因为他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况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态度又如何呢?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报告会上的插话颇令四座惊诧。他说:“在正义与我母亲之间,我将选择我母亲。”这是一句没有事先出现在讲稿里的话。为了堵塞找茬者的嘴,不得不如是说。当时在座的人们以为这是加缪的应急性幽默,因而给予支持。这句话得以广为传诵。加缪当时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和造成的场面一定美极了。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固有的勇敢。让松觉得加缪的话相当可怕。事实上,加缪一直在揭露贫穷、酷刑和殖义。他的立场不止在书里,更在大街上。难怪人们说,加缪是正义的象征。让松和布朗肖也都有各自的明确立场。他们的生命都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了。
十
列维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亲纳粹狂人德里约在法国把德国纳粹推向了极点,把捧到了顶峰。德里约在1935年纽伦堡纳粹期间有“极佳表现”,简直可以得到的“勋章”。在大会开幕的早晨,他谈的是“伟大”、“冲动”、“力量”和“快乐”,在晚上欢呼的人群中,他欣喜若狂,激动得要死,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积极介入阵营,皈依主义,参与反犹活动。他对纳粹分子极尽殷情和忠诚,以别人不可比拟的方式紧跟。多么荒诞和恬不知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冒险。纳粹时代是造就狂人的时代。德里约是个典型的极端纳粹分子,但是他给人们留下温和或暧昧的假象。正是这一假象使他取悦于人、吸引人,有着某种魅力甚至德行,拥有相当的优待和特权,产生了某种巨大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当惨败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历史和人生都到了转折点。德里约的勇敢是在脆弱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其严重错误在于把军队看作革命军而非占领军,把视为文明传播者和导师。其实,和他的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诞生的反常而恐怖的怪胎。
列维写道:
ses « idées » ont triomphé. enfin: elles ont à demi triomphé. car si l’ordre allemand régne en europe, si le mélange de la « grande vie grecque » et de la « grande vie du moyen âge » qu’il a reconnu en poméranie a triomphé presque partout, si ce magnifique déploiement de jeunesse, de force, de santé qu’il admirait à nuremberg est en passe de gagner l’essentiel de la planète et si, en france même, nous avons, grâce au ciel, fini par nous mettre à bonne école, il reste encore à faire, hélas, pour que la victoire soit totale.[15]
他(德里约——引者)的“思想”已经获胜。不过,只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既然,要是德国制度在欧洲起支配作用,要是他认同的波湄拉尼的“伟大希腊生活”与“伟大的中世纪生活”的混合物已经几乎到处都获胜,要是他在纽伦堡所赞赏的青春、力量、健康的出色表现即将遍布全球的主要地区,要是在法国本土,幸亏天助,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唉,要想大获全胜,尚需努力。
在30年代,德里约开始如同试毒一样尝试主义,后来上了瘾,便变成了主义者,并且在反犹道路上越行越远而成为极端的排犹主义者。他的言行和罪过是不可宽恕的。青年时代的德里约与超现实主义者如贡、布勒东等人甚至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表明超现实主义运动存在着许多问题。超现实主义与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秘密关系呢?这也许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课题。
德里约把主义思为一种左派运动,于是主义是红色的、的。因此,主义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在德国,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也必将成为法国的民族。主义越过德国进入法国和别的国家,这就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场革命运动。他还将德国法西欺军队视为未来欧洲的希望,德队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声音传播给整个欧洲。他所喜欢的正是主义的破坏性方面以及、地震和灾难。他始终认为,的理想是为建立一个新世界铺平道路。这就大错特错了。
纳粹主义想使世界年轻化,纳粹主义者有着严重的青春魅力情结,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年轻化被神化了。使一切旧事物旧人物年轻化成为所有人的使命。主义正是以神圣的年轻化和使命的名义出现的。其厌旧情绪简直达到了顶峰。主义者把青春和力量、健康、美丽视为同一回事。青年人必须战胜老年人。这是十分危险而狂热的青春意志,是青春面具里的野蛮行径。这是典型的青春至上论,是极权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童年少年青年与中年老年不能互相排挤,更不能成为斗争的充足理由。“青春”不能成为一个人特定年龄阶段的专用词,除了肉体青春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青春。只有精神青春才是真正永恒的。
十一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女人在知识分子史中的影子。即使女人不从事写作,不成为作家,也会成为男人和男作家的图腾。这种图腾是建立和维系社团圈子的绳索,进而把男人们紧紧拴住。佩尼奥、奴葸、嘉拉、西蒙娜·布勒东……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与男人们(比如贝尔尼埃、苏瓦林、巴塔伊、……)狂热地玩一种多角恋爱游戏(也是一种自由的冒险历程),身兼数职,善于建立关系网,善于调停和选择,喜欢联系、接通和交流;她们本就是一张巨网,各自联系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处于男人们的边缘和中间地带;她们是心灵上和风格上的世界主义者、磁铁、舷梯、卫星、管道、新闻发布者,容易打通各种关节;她们还是世界、宫殿、城市、普遍和绝对,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冒险,可以说,女人是冒险的真正源泉,是冒险家手中的王牌。[16]这些正是女人的魅力所在。男人则通过女人进行较量、形成对峙、发生争吵、出现争夺。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较量、对峙、争吵和争夺。男人与女人彼此具有天生的欲望,人是欲望机器。男人可以拼命追求女人而使其成为冒险伴侣。只要女人一出场,男人的全部冒险史就行将完成。许多作家为女人写作,依凭女人安身立命,因女人而写出了杰作,如费兹杰拉德《夜温馨》、布勒东作品、海明威作品、乔伊斯作品、马尔罗作品……他们的生活也因女人而大放异彩。即使女人不动一笔一字,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会不朽;然而,女人一旦委身于作家就面临着多种结局:或被娶,或被弃,或被诈,或被抢,或被骂;她们在作品中的名字和身心形象已经被幻化虚化了,不能获得真实的再现;作品也不是她们的传记,她们不够传主的格。冒险让女人付出巨大代价,女人因此造成自身的不幸。
十二
萨特这个人怎样?萨特的情况相当复杂。在萨特那里,两种矛盾的象征并存:知识分子的完美无缺的象征和知识分子的蒙受耻辱的象征。他既是最好的人又是最坏的人,既是最光荣的人又是最可耻的人。他因错过了法国抵抗运动而在自己提出的介入理论领域做了许多事情,甚至过多。从德国战俘集中营回到了法国,过上正常生活,当时的萨特还不是伟大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者),而是渺小的萨特(只是《恶心》和《墙》的作者),他的名字还没有分量。尽管他一回到法国就寻找他的朋友们,并把他们聚集起来,打算大干一番,最后还是白干了。在伟大的马尔罗面前,他只是个天真的小伙子或幼稚的童子军,被认为是犹豫不决或等待时机的晚期抵抗分子。会见马尔罗后,只好羞愧尴尬地上路回家。作者认为,萨特是个野心家,在利益与信念发生冲突时,会倒向敌人一边,比如出现了著名的《苍蝇》事件,这一事件无疑是萨特一生的污点。列维对萨特的再思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萨特是否对社会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17]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的又是历史的,它是的历史,是历史的,是历史在现实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福柯最感兴趣的是“现时问题”,强调哲学研究人自身所居的现时世界。
十三
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语言的宣传者、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都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是自由冒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或准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抽象背影。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社会风云中掉入深渊,并以失败告终。伟大的知识分子死了。
在列维看来,知识分子冒的是“自由”之险,表现在两个方面: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冒自由之险就是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冒险者作为冒险的存在者,与一切别的存在者具有相同的方式。冒险者之为冒险者的方式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冒险是一种存在方式,把冒险者引向存在者,把冒险引向存在。海德格尔在解释里尔克诗后指出,里尔克没能回答“冒险者冒何险?”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海德格尔十分关心的。海德格尔写道:
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也即说,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从存在之圣殿(temple)方面思考,我们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何险。他们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唯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18]
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语言”,语言把知识分子引向道说,语言把他们引向了写作或革命理论;除了语言,还有实际,现实把他们引向了战斗或革命实践。他们不仅冒语言之险,而且冒实际之冒险,或者说,不仅冒写作之险,而且冒战斗之险,即是说,不仅冒革命理论之险,而且冒革命实践之险。对他们来说,语言是冒险的自由居所,冒险是语言的自由居所,因为他们冒的是自由的险,即,冒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之险。“写作”、“战斗”、“自由”等等,都是字词,通过它们,知识分子通达它们所指向的领域——社会领域或语言以外的领域,因此,他们不仅仅道说即写作。当诗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承担起写作与战斗的双重使命。因此,“知识分子何为”远比“诗人何为”宽广。可见,知识分子是在写作与战斗的双重冒险中显现自身的。写作与战斗互为桥梁,互相符合。冒险者冒自由场所的险,语言是自由的居所,自由是语言的居所。冒险者栖居于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中。冒险者通过“写作”、“战斗”、“自由”这些字词走向它们所指:写作行为-写作成果、战斗行为-战斗成果、自由理想-自由现实。在它们所指向的区域,冒险者成为写作与战斗的存在者。知识分子冒险更甚者,必须写作与战斗;作为写作更甚者,必须战斗;作为战斗更甚者,必须写作。写作与战斗就是存在。
冒险者的冒险或冒险性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显现对象。这个对象也必须通往公开状态。知识分子作为冒险的存在者正是在这一公开状态展露才华的,在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成为自由的居主(自由的写作者与战斗者)或自由的存在者。
知识分子作为分子,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以高科技生产为特征的知识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越来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体力劳动者本身也成长为有知识、有科学、有技术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商相结合。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成为有体力的脑力劳动者,也有利于工农成为有脑力的体力劳动者,还有利于进一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甚至自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和大众肩负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试图主导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知识兴国的今天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风骨与品质,应当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自觉崇尚智慧、知识、真理、识见、理智与理性的权威的知识分子,具有精神、自由思想、社会责任感、理性判断、、批判、怀疑、良知、创造的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是“高极的”知识分子,区别于那些低级庸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大小之别,常言“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如同大作家与小作家之别。智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此外者(低极庸俗的知识分子)就是小知识分子。
[1].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435.
[2].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73。
[3].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76。
[4].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86。
[5].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46-247.
[6].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194.
[7]. 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中卷),马振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页320-321。
[8].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302-303。
[9].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64.
[10].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92.
[11].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75-77.
[12].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79.
[13].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75.
[14].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77-278.
[15]. 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122.
[16].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229-231.
[17]. 参见bernard-henri lévy ,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372.
[18].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316-317。
第十二篇 近来欧洲哲学思想中的关注_西方哲学论文
对于哲学家来说,关注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学家趋向于忽视这么一点,即大多数哲学在哲学家们对城邦和整个人类事务领域消极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中有其根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那些世纪里最为丰富的哲学最少得到哲学地思考,因为自我保护和对专业兴趣的彻底维护一样,常常阻止了哲学家们对的关注。开始这一思想传统的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它造成了哲学家对城邦的谴责。纠缠着柏拉图,并且一直作为最初的哲学而给出了许多答案的这些问题是:哲学如何保护自己并从人类事务中解放出来?什么是哲学活动的最好条件(最好的形式)?尽管答案各种各样,但他们都趋向于同意以下几点:和平是共和国最高的善,内战是所有罪恶中最糟糕的恶,永恒是判断形式的最好标准。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的领域是这样一种事务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行动,正确地说(比如说,不是法律的执行,不是规则的运用,也不是任何别的管理活动,而是开始一些其结果无法预测的新事情),要么是多余的,要么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传统哲学趋向于从人类动物必须跟其他人一起生活这一必然性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方面,而不是从人类的行动能力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方面,它趋向于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关于最能适合复数性这一不合时宜的人类境况的需要的条件,以及至少最能让哲学家不受到它干扰地生活的条件。在现时代,我们几乎听不到这样一种古老的探求了。尼采直截了当地说,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小心地隐藏在群众中,也就是说,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即平庸的心智对它感到满足,同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时时意识到它。WWw.meiword.CoM1人们趋向于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探求消失了。
换句话说,我们的学家们由于特殊的兴趣,总是趋向于忽视帕斯卡尔的评论中的真理的重要实质,他的评论说,我们只在华丽的学术包装中思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诚实的人,像其他人一样和他们的朋友玩笑,当他们自己消遣的时候,他们才写《法律篇》和《学》,以此来娱乐自己。他们生命中的这一部分是最不哲学和最不严肃的。……如果他们就而写作,这就好像是在为疯人院制定规则;如果他们表现得在谈论重大问题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说话的那些疯人们自以为是君主和帝王。他们讨论那些原则是为了使得他们的疯狂的危害尽可能地小。2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著作的许多段落中警告他们的学生不要过分认真地对待人类事务,这一点就可以证实这一陈述,而且这甚至对他们之后的那些人也有效。
当代的思想,尽管它在表达的清晰有力上不能与过去相比,但是它认识到人类事务形成了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产生真正的哲学问题的领域,而不仅仅是由一个源于完全不同的经验的规则统治的生活领域,它在这一方面与传统背景区别开来。实际上,没有人还真正地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明智的人,他们从事件中所认识到的一切是世界的愚蠢。这一转变了的态度给一种新的科学带来了希望。3这会受到了,之前从未这样阅读过,9这样,大量真正的现代哲学就包含在对过去的伟大文本的解释之中。更何况关于传统的权威是否崩溃的约定是不可改变的事件,这些解释中所显露的直接性和生命力,很显然为在五十到七十五年前所产生的许多枯燥的哲学史所缺乏。那些认为要回到传统的人不能,也不想逃离现代思潮,因此他们的解释经常带有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标记--他是最先以一种新的眼光阅读古老文本的人之一--尽管他们可能完全拒绝海德格尔自己的哲学原则。无论如何,这种关于过去思想的所有尚存的形式的当代观点,如果按照亚历山大式的标准来看,它如同现代艺术的自然观一样,是惊人地新颖、变形和歪曲现实的。
恰恰是天主教哲学家比几乎所有其他的现代哲学流派为思想的问题作出了更多有意义的工作,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像法国的马里坦(maritain)和吉尔松(gilson),德国的瓜尔蒂尼(guardini)和约瑟夫o皮佩尔(josef pieper),这些人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天主教的范围,因为他们能够唤醒人们对几乎已经丧失了的关于古典和永恒的哲学问题的重要性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盲目性,以及他们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免疫性。他们的缺点在于,他们实际上走在上面提到的道路相反的方向上。他们给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几乎只是对 古老的真理重述,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的明确肯定的方面是不够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避开了真正的问题。由于问题存在于传统不能预见其窘困之中,所以整个重述的计划也是必然的。因此,回到传统似乎就是给脱节的世界重新排序而已;它意味着对过去的世界的重建。而且,即使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可能的,那么由一个传统所支配的许多个世界中的哪一个应该被重建的问题,只能通过随意的选择来回答。
为了避免这样的困难,传统的拥护者们已经表现出减少这些引起他们对的关注的经验倾向。下面的例子被选了出来,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某种模糊的一致。
o极权主义统治的现实几乎只是被描述为它的方面,而被理解为世俗宗教,它要么是出自世俗化的异教和内在论,要么被认为是对假定的人对宗教的永恒需要的回答。这两个方面只要简单地回到正确的宗教,似乎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这种解释缩小了实际所犯下的罪行所带来的震惊,避开了现代社会中在极权主义(但不限于极权主义)那里显得最为明显的方面提出的问题--否认宗教的重要性和表现出一种绝然冷淡的无神论的倾向。
o几乎只有天主教哲学家不只是在社会正义的意义上来思考劳动问题,这是真实的。然而,通过把古老的术语积极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或者劳作和闲暇应用于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等级秩序无法用来处理全新的普遍平等的境况,它是我们当前的困难之源,因为它不仅仅包括作为个人的工作者的平等,也包括与所有其他人、甚至是他的上司的劳动活动的平等。这就是当我们说生活在一个固定职业者的社会时,其本质上所意味的东西。
o最后,当代事件的全球特性--根据吉尔松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这显然区别于历史开端以来到这之前的一切10--似乎使得建立一个普遍社会几乎成了必然。反过来,只有每个人都坚持一个能够联合所有国家的原则,普遍社会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个原则平等地超越了所有的国家。可选择的方案似乎只能在极权主义(主张全球统治)和教之间,在它的历史上普遍社会的观念(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一种有效形式)是第一次出现。然而实际情形的危险又被缩小了,问题似乎被认为是无害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自由概念至少其方面在复数性之外是不能理解的,而且这个复数性不只是包括不同的方式,而且还包括不同的生活和思想原则。一个普遍社会只能是意味着对自由的威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非统一的条件下,每个国家都有其价值,每个国家都必须对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可能犯的罪行和错误承担责任(不是道德上的,而是朴素的实在性)。
这样的评论可能听起来比它们想要表达的更具有批判性。照目前的和社会科学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哲学中的传统趋向,因为它对关键的问题持续意识明显地免于现代各种各样的废话。在争论之中似乎很难记得一个人说过了些什么,但是哪怕他们只是恢复和再次表述了古老的问题--所关于的一切是什么,那就足够了。他们已经使得古老的回答陷入了混乱之中,尽管这对于造成混乱的穷困来说还完全不够,但是对于澄清和不断地强迫给我们一种重要性和深度的意义来说,他们肯定是最伟大的一个助益。
法国存在主义者--马尔罗和加缪为一方,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另一方--以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和他们那强有力的无神论之前的所有哲学的公开反对,构成了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现代复兴相反的一极。他们对当代德国哲学家的著作的依赖,尤其是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依赖,有一些夸张。他们诉诸于只是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在法国变得非常重要的某些现代体验,而这些经验在德国的二十年代就已经为更老的一代清晰地表达。对学院哲学的突破,这甚至在一战前就已经由德国的西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所准备,法国比德国要晚二十年。然而在今天,这种突破在巴黎要更为激进得多,在那里大部分重要的哲学著作由大学之外的人写作和发表的。此外,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在法国并没有多大,倒是强有力地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德侯爵的影响。但是这些与黑格尔和在法国的影响相比则显得不怎么重要了,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德国。不过,即使稍稍一瞥,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表达风格和形式是清一色的法国式道德剧(moralistes),笛卡儿哲学那极端的主观主义在这里可以找到它最后的也是最为激进的表达。
在我们的上下文中,法国存在主义者是从不同于现代哲学的其它思潮的角度出发,因为他们把对的关注置于他们著作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对窘境给出一个恰当的哲学回答,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对历史趋势和发现它们的哲学重要性既没有特别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在行。相反,他们认为是解决哲学窘境的方案,在他们看来,这些哲学窘境通过纯粹的哲学术语是不能得到解决,甚至不能得到足够清晰的表达。这就是为什么萨特从来没有完成(或者再次提到)他在《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的结尾提到的道德哲学,11相反,他写了一些戏剧和小说,并创办了一个准性的杂志。他们整个一代人都试图从哲学逃入;在这一方面领先的是马尔罗,他在二十年代说到:一个人总是在自己那里发现恐怖……幸运的是,他能够行动。在当前的环境下,真正的行动,也就是说,开创某种新的事物,似乎只有通过革命才是可能的。因此,革命扮演着……永恒生活一度扮演的角色;它拯救了那些进行革命的人。12
别试图教猪唱歌,这样不但不会有结果,还会惹猪不高兴!
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主要是出于哲学的而不是社会的理由,存在主义者全都是革命者,他们积极参与生活。萨特和梅洛-庞蒂把修正了的黑格尔的主义当作一种革命的逻辑,而马尔罗,尤其是加缪,他们坚持的是一种没有历史体系或者一种没有详细明确的目的和手段的反叛,用加缪的话来讲就是坚持做lhomme revolté,坚持做一个反叛者。13这一差别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他们最初的动力--前者为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冲淡了这一动力,后者则保持着更大的纯粹性--是一样的:问题不是当前的世界处于危机之中和脱节,而是人类存在是荒谬的,因为它提出了被赋予理性的人类不可解决的问题。14萨特在无意义的存在面前的恶心,比如,人们在绝对命运和世界的被给予性面前的反应,这与他对猪猡(salauds)、资产阶级庸人的憎恶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自满地相信他们生活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之中。资产阶级不是开拓者的形象,而是假定了一个近似形而上学意义的自满的猪猡(salaud)形象。15当人意识到他被宣布为自由(萨特语)而投入到行动之中--就像克尔凯郭尔投入到来自普遍怀疑的信仰当中去一样,这个时候脱离这一情形的道路才开辟出来。(存在主义者这一投入行动的跳跃同投入信仰的跳跃,其笛卡尔的起源是一样明显的:其跳板就是在不确定的、不连贯的和不可理解的宇宙中的个体存在的确信,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信仰能够说明,或者只有行动能够赋予人可理解的意义。)当人发现他自己不是被给予的自己,而是通过投入(从事)能够成为他所选择要成为的人。人的自由就是:人在混乱的可能性的海洋上创造出他自己。
如果这种虚无主义情形中的拯救,或者通过行动从思想中的这一拯救,发展出了一种哲学,这会是一个显然的矛盾。在最正式的意义上,我们甚至不能期望它能够清楚地阐明原则,更不用说给选择指明方向了。作为哲学家,法国存在主义者能够通达到这么一点,在那里只有革命行动,通过对一个无意义世界的意识转变,才能消解内在于人与世界之间的荒谬关系的无意义性;但是按照他们最初的问题,他们不能指出任何方向。从纯粹思想的角度来看,他们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带有伟大的徒劳(英雄的无益)的特征,这一点在加缪和马尔罗那里最为明显,他们在一种极度蔑视他们的无意义的精神中赞颂古老的美德。因此马尔罗坚持认为,人应该通过勇敢地蔑视死亡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是因为所有源于萨特和梅洛-庞蒂他们自己采用的哲学的解决方案的幻想特征,就像是置于其上一样,尽管他们最初的动力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来自于主义的,但主义是他们行动的框架。一旦他们认为自己以基本上相同的主张而脱离虚无主义的绝境,他们在圈中产生分歧和采用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行动的领域里,只要承诺革命性的改变,其他一切可以完全任意。这一点就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所有这些,对于哲学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而且这常常看来就像有些绝望的孩子们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人们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不过,事实上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对法国的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他们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感到有责任在日常的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他们编辑报纸,在上演讲。无论人们可能怎样反对他们,他们重视对学院哲学的拒斥和对思辨立场的放弃。把他们与主义或戴高乐主义或者他们参与的任何运动区别开来的是,第一,用一位见多识广的英国作家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从未通过诉诸固定的原则来寻求对他们的推理的证实,16第二,他们的革命从未主要地针对社会的或者的境况,而是针对所谓的人的境况。按照马尔罗的说法,勇气挑战人的道德境况;在萨特看来,自由挑战人的被抛入世界(这是一个从海德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概念)的境况;根据加缪的观点,理性挑战人不得不生活在荒诞之中的境况。
他们共同的特点,也许最好被描述为行动主义的或者激进的人道主义,这一特点并非妥协于人是人的最高的存在这一古老的主张,这一主张认为人是他自己的上帝。在这种行动主义的人道主义看来,出现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通过多数人的一致努力,一个不断地反抗和揭示人的境况的虚伪性的世界得以建立;反过来,这将使得人性,一般认为是理性的动物,发展到建造一个现实的位置,在那里人可以创造他自己的境况。于是,人将会在一个完全人性化的、人造的现实中行动,如此,人类生活的荒诞性将不再存在--当然这不是对于个体而言,而是对于生活在人的技能之中的人类而言的。至少,只要他活着,他就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根据他自己的理性而言是一致的、有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他公然反抗上帝或者神祗,就像他们的有限性不再存在那样去生活,即使他作为一个个体也无望逃脱这些有限性。如果人决定他自己像一个上帝那样生活,那么他就能够自己创造,成为他自己的上帝。人尽管不能自己创造自己,但要为他的所是负责,从这一悖论出发,萨特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人因此必须成为他自己的创造者。17
这一通达的方法的乌托邦成分,或者更准确点说,这一通过行动来拯救人的精神的尝试的乌托邦成分,是显而易见而用不着指出的。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非常熟悉--在极权主义的政体那里,不幸的是,不只是在那里--通过完全改变传统的境况来改变人性的企图的情况下,以人的境况为代价来拯救人性的企图还会出现。在现代科学和中,所有对于修整人的多种形式的实验,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社会而改造人性。认为这两种相对的企图是同样注定失败的,在我看来恐怕是过于乐观了。由于其固有的不可预测性(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灵魂的黑暗)--哲学地来说就是他无法像其它事物那样被定义--人性更可能屈服于修整和改造(尽管可能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而不是人类境况自身,这是在所有情况中都依然存在的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地球上的生命完全是赋予人类的。
与法国存在主义相比,现代德国哲学(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三十多年前就处于最为显著的位置)对的关注则不那么直接而令人难以捉摸。在那里,信念几乎没有任何位置,甚至关于的具体哲学原则也是显然缺少的。不管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对哲学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们的贡献只能在他们的哲学本身之中寻找,而不能在他们关于同时代的事件上采取的明确立场的著作或者文章中寻找,也不能在他们对于时代的精神状况18的含蓄地(因而总是有些含糊地)批评的著作或文章中寻找。
所有我们在这里论述到的哲学家之中,雅斯贝尔斯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信服康德的,这在我们的背景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康德是少有的几个不适合于之前我引用的帕斯卡尔的评论的哲学家之一。在那三个著名的康德问题之中--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第二个问题在康德自己的著作中占有一个关键的位置。康德所谓的道德哲学在本质上是的,就他把立法和判断的能力赋予所有的人而言,根据传统,这是家的特权。在康德看来,道德活动就是立法--以我的行动原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方式行动--一个善良意志的人(他的好人的定义)意味着他经常关注的不是对现存法律的服从,而是立法。这一立法的道德活动的指导原则是人类的观念。
对雅斯贝尔斯来说,与吉尔松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事件是,人类从他作为一个乌托邦梦想或一个指导原则的精神存在中浮现出来,而进入一个永远当下紧急的现实。因此,康德一度认为未来历史学家的哲学任务就是写一部世界主义意图的(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19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雅斯贝尔斯近来一直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在试图这样做,也就是提供一个哲学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范围的团体的适当基础。20反过来,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中,交往构成了存在的中心,而且实际上等同于真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哲人恰当的态度就是无限交往的态度,这意味着对所有真理是可理解的信念,也是对去揭示和倾听真理的善良意志的信念,它们是真正的人的共同存在的主要条件。交往不是对思想或者感情的一个表达,对于交往来说,这些都只是第二位的;真理本身是交往性的,在交往之外不存在真理。就真理必定是交往的必然结果而言(如果交往确实获得真理),思想尽管不是实用的,却是实践的。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实践,而不是一个个体在他自我选择的孤独中的表演。就我所知,雅斯贝尔斯是唯一一个曾经反对孤独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孤独是有害的,他甚至想研究每一思想、每一体验、每一主体,它们对于交往意味着什么。它们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交往?它们诱使人孤独还是人交往?21在这里,哲学成了许多真理之间的中介,这不是因为它掌握了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唯一真理,而是因为只有在理性的交往中才能够使得每个人在孤独中相信的东西成为人为的和实际的真理。同样在这里--尽管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哲学失去了它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傲慢;在某种意义上它倾向于成为康德曾设想的对于每个人而言的生活的婢女(ancilla vitae),也就是说,在高贵的夫人前面掌灯,而不是列队跟在她们身后。22
尽管雅斯贝尔斯的世界主义哲学与吉尔松和其他天主教思想家一样,是从人类现实的同一个问题出发,但我们还是很容易从中看到雅斯贝尔斯采取了一个与他们相反的立场。吉尔松断言:分离我们的是理性;联合我们的是信仰,23如果我们把理性当成一种单独的、内在于我们的能力,当然这是正确的--当我们在公共意见的大路之外开始思考时,我们会获得完全个人性的结果。(先天的理性会自动地向所有人叙述同一个事物的观念,要么是把理性的能力误解为一种纯粹的形式的机械论,一部思想机器,要么就预先假定了一种实际上从未发生的神迹。)信仰被理解为这种主观主义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主观性跟感觉的主观性没有什么两样--的对立面,它一定是某种能从外部团结人们的客观的现实,通过启示,认识到唯一的真理。在未来的普遍社会中,这种团结因素的困难在于,它从来就没有存在于人之间,而是在人之上;地说,它迫使所有的人在一个原则之下拥有同等的权威。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的优势在于,理性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纽带,因为它既不完全在人的内部,也不必然在人之上,但是,至少在实践的现实中,它存在于人们之间。不想交往的理性已经是不切实际的。为了认识雅斯贝尔斯的理性定义回溯到了非常古老且真实的经验,我们只要提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双重定义--人是的动物和理性的动物(dz?on politikon and logon echon),就他是的动物而言,他有言说的能力和理解的力量,也有能够让自己被理解和说服人的能力。在另一方面,似乎很显然的是,交往--这个术语同根本的经验一样--其根源不是在公共的领域,而是在我与你的私人相遇中。这种纯粹对话的关系比任何别的关系更接近于思想的原初经验--在孤独中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比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关系所包含具体的经验都更少。
就而言,雅斯贝尔斯哲学的局限主要是因为那个在历史上一直困扰着哲学的问题。这在于哲学总是单个地论述人的这一性质,然而,如果任不是存在于复数中,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或者用利一种方式来表达:哲学家的经验--就其是一个哲学家而言--是孤独的,尽管对于人--就他是的而言--孤独是一种基本的、然而也是边缘的经验。也许就是--但我只是暗示这一点--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它在许多方面处于他哲学的中心,构成了走出这里困境的一个步骤。因为海德格尔把人定义为在世界之中存在,至少,他坚持给与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哲学的重要性,如果人不是主要地被理解为与他人共在,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而且海德格尔自己已经完全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哲学一直都超越和忽视了24最为直接明显的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海德格尔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有意地避免使用人这个术语,而在他的后期论文中,他则倾向于使用从希腊人那里借来的有死者(mortals)一词。这里重要的不是对有死性的强调,而是复数的使用。25然而,由于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达他在这一点上的立场的含义,所以从他对复数的使用中解读出太多的意义可能有些过分。
在当代哲学较为困扰的各个方面中,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个人之间的差异比他们拥有的共同点要更为显著得多。无论什么时候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讨论,哲学的混乱都可能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以致于有意义的对立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外行来说,如果常常显得好像所有这些思考和新的尝试发展和创造出了一种同样的思潮,那么这种观察就包含了一定数量的真理。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对哲学相关性的一种确信,而不同于另外那些人,他们试图轻视哲学问题的紧要性而代之以某种科学或伪科学问题,比如的唯物主义,或心理,或逻辑斯蒂,或语义学,或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这种反对当前时尚的消极的团结一致从一种共同的恐惧中攫取力量,这种恐惧就是在现代世界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哲学和哲思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上面,我说过,哲学已经离开了著名的象牙塔,哲学家已经放弃他是社会中明智的人的位置的主张。内在于这种对传统位置的放弃的,也是对哲学生机的一种自我怀疑,在这种意义上,对的关注已经成了哲学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
看来,从对的关注遁入到历史的解释这种黑格尔式的逃离不再可能有了。它所默许的假设就是,历史事件和所有的过去事件之流都是有意义的,尽管有恶的和消极的方面,但是它们给哲学家那回溯的一瞥揭示了意义。黑格尔可以根据指向自由的辩证运动来解释历史的过去历程,从而来理解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o波拿巴。在历史过程中通过历史指向越来越多的自由的实现,今天,没有什么显得比这更为可疑的了。如果我们根据趋势和潮流来看,其对立面显得更为合理。此外,黑格尔调和精神和现实的巨大努力,完全依靠于协调以及在每一个恶中看到某种善的东西。只有且只要极端的恶(在哲学家之中,只有康德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经验。)没有发生,这种努力还是有效的。谁敢把自己与灭绝营调和在一起?或者,在他的辩证法在奴隶劳动中发现意义之前,谁敢玩那正-反-合的游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在现今的哲学中找到类似的主张,我们要么因为其内在地缺乏一种现实意义而不信服,要么我们开始怀疑坏的信仰。
换句话说,当代事件的全然恐怖,以及未来甚至更为恐怖的可能事件,在我们提到的那些哲学家之外。在我看来典型的是,没有一个哲学用哲学术语提到或者这种经验背景。似乎在这种对恐怖经验以及认真对待它的拒绝中,这些哲学家就继承了拒绝承认人类事务领域的这一传统。惊异(thaumadzein),对作为是其所是的惊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哲学的开端,然而他们却甚至拒绝把它当作哲学的初步条件来接受。对人可能做的以及对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的无言的恐惧,在许多方面涉及到对感激地无言的惊异,从中产生了哲学问题。
一种新的哲学的许多前提--它们多半存在于哲学家转向领域的态度之中,或者存在于哲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中,或者存在于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中--已经存在,尽管乍一看来,他们显得关注的是传统障碍的消除,而不是一种新基础的建立。其中雅斯贝尔斯的真理形成和海德格尔的普通日常生活,与法国存在主义者通过坚持行动来反抗古老的哲学对行动的怀疑一样--不知道它的起源,也不知道它的结果:因此行动有什么价值吗?26对于一种新的哲学来说,关键的是对思想的意义的探究;也就是对从来就不是单独的存在的思考条件和意义的探究,在我-你关系被补充进对人性的传统理解时,这种基本的复数性还远没有得到探究。这种重审需要与经典的思想保持联系,如同在当代天主教哲学的许多变种中呈现给我们的那样。
但所有这些只是前提。一种真正的哲学最终不能从趋势的,部分的妥协和再解释中产生;也不能从对哲学自身的反叛中产生。像所有其他的哲学分支一样,它只能源于一种原初的惊异行为(thaumadzein),它那惊异的且追问的冲动现在必须(比如与古人的教导相反)直接领会人类事务和人类行为的领域。固然,哲学家来实行这种行为,由于他们对未受到干扰的存在的兴趣和对他们在孤独中的专业经验的既定兴趣,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素质的。但是,如果他们让我们失望,那么还有谁可能成功呢。 【注释】
1 vol.5, the kr?ner pocketbook edition, blicke in die gegenwart und zukunft der v?lker, no.17. cf. also morgenr?te, no.179.
2 《思想录》(pensées),no. 331, translated by w.f.trother, harvard classics, 1910.
3 这是埃里克o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新著的书名,《一种新科学》(a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这本著作的目的是恢复柏拉图意义上的科学。
4 das ding, in gestalt und gedanke, jahrbuch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sch?nen künste, 1851,146.
5 《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26节和27节。[在这一演讲的第一个手稿中,阿伦特提供了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观点:]如果不对他的世界概念及其关于世界的有一个详细的报道,对海德格尔思想可能的相关性的清楚阐明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海德格尔自己从来就没有清楚地表达他的哲学在这方面的含义,而且在一些例子中他还运用了一些有内涵的术语,这些术语十分可能误导读者相信他在研究那些反对的哲学家的古老偏见,或者在研究现代的人们从哲学逃进的草率。前者可以在海德格尔常常使用的对作为自我和本真的存在的对立面的常人(das man)和公共意见或者他人的找到证据,按照这一观点,公共现实的作用就是隐藏真正的实在和阻止真理的显现。后者可以在他对决心(entschlossenheit)的解释中得到证据,它,由于被理解为一种存在状态,似乎缺乏一个对象。就我们的目标来说,比这些概念远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确定为在世界中存在。
6 etienne gilson,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cité de dieu, 1952,151.
7 沃格林是这样一种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没有限定为任何一个具体的教会或者学派。在他看来,柏拉图的理念作为可见世界的不可见的尺度,后来通过尺度自身的显示被证实。参见《一种新科学》(a new science of politics),68-78。
8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us,1936,ⅰ,5.
9 同上,ⅱ, 394,在对赫尔德的论述中: so hatte noch niemand vor ihm gelesen.
10 gilson, op. cit., 1ff.
11 见《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1943)的最后一句话:所有这些问题,把我们推向纯粹而非复合的反思,这些问题只可能在道德的基础上找到答案。我们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研究这些问题。 (toutes ces question, qui nous renvoient à la réflexion pure et non complice, ne peuvent trouver leur réponse que sur le terrain moral. nous y consacrerons un prochain ouvrage.)
12 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 in english, mans fate, 1934.
13 这是加缪最后的一本书的书名:《反叛者》(lhomme revolté),1951.
14 关于人类存在的荒诞性,特别参见加缪的早期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论荒诞》(essai sur labsurde).
15 萨特战前的小说《恶心》(la nausée, 1938)可能是对这种态度最给人深刻影响的描述。
16 埃弗里特ow. 奈特(everett w. knight),存在主义的,见1954年8月的《二十世纪》(twentieth century)
17 关于这一行动主义的人道主义,见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e est un humanie, 1946)和m. 梅洛-庞蒂的(humanie et terreur, 1947.)
18 这里的引文是雅斯贝尔斯1931年发表的一个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潮流的的标题:《时代的精神状况》(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在他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vom ursprung und zeil der geschichte),发表了对于现代世界的解释的第二个部分。这两本著作都有了英文本[《现时代中的人》(man in the modern age, 1951)和《历史的起源和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1953)。]尽管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但是在海德格尔的《林中路》(holzwege,1950)可以找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相似关注,其中的论文世界图像的时代(die zeit des weltbildes)尤为明显,这一论文的许多方面在他最近的演讲对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见die künst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jahrbuch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sch?nen künste, 1954.
19 见他的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1784.
20 这是他的历史哲学和前面引用的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vom ursprung und zeil der geschichte)中提出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论点的主要意旨。之后,雅斯贝尔斯就一直在做哲学的世界历史的研究。
21 uber meine philosophie in rechenschaft und aulick, 1951, 350ff.
22 这里的译文借自卡尔oj.弗里德里希翻译的《永久和平论》(eternal peace, 1948)。
23 gilson, op. cit., 284。
24 ein blick auf die bisherige ontologie, dass mit dem verfehlen der daseinsverfassung des in-der-welt-seins ein uberspringen des ph?nomens der weltlichkeit zusammengeht, sein und zeit,65.
25 [这一演讲稿的早前的版本还接续说:]哲学在处理的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障碍,就是它总是谈论单一的人,就好像那里有一个人性的东西一样,或者就好像最初只有一个人生活在地球上一样。困难一直就是,人类生活的整个领域的存在只是因为人的复数性,因为单个人根本就不是人这一事实。换句话说,所有在传统哲学那里开始的哲学问题,由于其单个的人的概念给断绝了。
26 thus nietzsche in wille zur macht, no. 291.
第十三篇 克洛维尔: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_西方哲学论文
1.走向一种哲学的逻辑
1912年到1916年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中他探讨了盛行的主要逻辑理论,并涉及到逻辑在一些学说——新经院主义、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主义”(先验逻辑或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奥·屈尔佩(o.külpe)的“批判实在论”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1]在所有这些观点中,范畴理论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受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康德的激发,逻辑理论试图说明使得经验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概念,以及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于是,逻辑学并非仅仅研究论证的形式特征,作为先验逻辑学或“真理的逻辑学”,它包纳了知识论和科学的所有基本问题。即便是新经院主义者(他们将逻辑学从属于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通过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先验问题而展开的,虽然他们想重新赋予“先验的”这一术语以中世纪的超越性(transcendentia)所包含的前康德主义内涵,以恢复作为规定存在者的范畴的本体论意义。[2]海德格尔对这一讨论的最为原创性的贡献,即他1915年的《教职论文》及1916年关于它的“结论”(“即范畴问题”——译者注),显示了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和新经院主义的逻辑学之间寻求一条道路的紧张努力。
这个主要文本,[即《教职论文》或《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译者注]重新审视了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粗略说来,即确定逻辑和语法的关系。海德格尔已提出过这样的论点:“逻辑学的真正准备性的工作并非是凭借对表象的起源和组成的心理学研究,而是凭借对词语意义的毫无歧义的界定和澄清而赢得的。wWW.meiword.cOm”(《全集》1卷186页)[3]但是何谓意义呢?这一准备性工作同哲学的结合要求从范畴上将意义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思维的符号区分开来,这转而要求一种普遍的范畴理论。海德格尔受到“现代[逻辑]研究的视角”(《全集》1卷202页)的明确引导,在《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中进行的重构,其目的就在于阐明这两个问题。[4]司各脱的范畴理论使得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意义(significations, bedeutungen)研究的首要意旨是……作为有效意义的真理”(《全集》1卷307页)。由于转向真理“不可避免地要求确定意义领域和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全集》1卷307页),所以海德格尔就设法保留了司各脱的范畴的本体论特征。但是海德格尔在这个主要文本中所进行的重构与其说是受了存在论观点的引导,毋宁说是受了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论的指引。因为(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所指出的)逻辑学是“理论的理论”(《全集》1卷23页),它有(正如他在1915年所说的) “超出可认知的或被认识的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全集》1卷279页)。逻辑学是第一哲学。
但是在《范畴问题》中出现了另一条注释,这是海德格尔在1916年发表关于邓·司各脱的书时附的一条简短结论。在此海德格尔对“范畴问题的系统结构”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准备性的审查”,它又引出了“这个问题及其背景的基本潜力”(《全集》1卷300页)。这个主要文本中的论述已经是“严格概念式的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它“有意识地排除了一系列更为纵深的形而上学问题”(《全集》1卷400页),有“对知识问题进行形而上学解决”的要求(《全集》1卷403页)。“如果从长计议的话”,哲学,包括逻辑学,不能“缺少它的真正眼力(optic)——形而上学”(《全集》1卷406页)。这样,由于对“形而上学”解决办法的需求,逻辑学的“绝对优先性”似乎被打了折扣。先验逻辑必须在“超逻辑的背景”中被审视(《全集》1卷405页)。因此,《范畴问题》确认了预示着一种形而上学的三个问题域,根据这种形而上学,已经抛弃了心理主义和语法主义的海德格尔相信能够恢复逻辑学的哲学意义,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
让逻辑学重获哲学意义的筹划并非仅限于海德格尔的学生时代。在他的1912年关于逻辑理论的评论中,海德格尔问道:“何谓逻辑?”,并回答道:“在此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问题面前,这问题的解决留待将来”(《全集》1卷18页)。十五年后,在他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课程中,海德格尔依然吁求一种“逻辑自身问题的彻底概念”(《全集》24卷252页)。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无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拉斯克的范畴理论,都没能公平地对待在“事情本身”的下,在对逻辑的哲学探究中出现的“本体论问题”(《全集》24卷253页)(这也暗示了他的早期作品所受的两个主要影响)。如果毕竟要“使逻辑再次进入哲学”的话,人们必须首先克服黑格尔的“本体论向逻辑学的还原”,并且审问何谓逻辑,何谓逻各斯的存在(《全集》24卷254页)。
两年前 ,当海德格尔开设他的题为《逻辑学——真理之追问》的讲座课程,通过批判当代“学院逻辑”将“所有的哲学,即所有的发问和探究”(《全集》21卷12页)都置诸脑后的做法,就已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作为一门在哲学专业内安逸的学科,逻辑“科学”实际上是无根基的,它自身的对象、它的科学领域一片混乱。把它界定为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也就是关于论证、言说、句子和命题的科学,并没有将它与其它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区分开来,除非人们补充说逻辑学特别地与“关于真理”的逻各斯有关。其它科学通过在方上探讨它们的对象来寻求“真的东西”;严格说来,只有逻辑学才是真正的关于“真理”本身的科学(《全集》21卷7页)。因此,如果逻辑学“想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形式,一种哲学化的逻辑学”,那么它“最为应当关注的”不是进一步发展技巧,而是“真理的源初存在”,即成为真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全集》21卷12页)。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就是通过确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逻辑和存在问题之间建立起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由康德予以革新的关联。
当海德格尔在1916年确认范畴问题的潜力时,真理概念就已经支配着他的观点了。但是他对一种“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全集》1卷402页)的吁求仅仅是点明了《教职论文》和它的“结论”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诉求表明了它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主要文本中的论证却排除了一种新经院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将形而上学聚焦于真理问题,就保持了主要文本中“作为逻辑上有效的意义的”真理之优先性,这是一种批判主张,但却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那种将形而上学完全从属于逻辑学的企图。[5]这样,先验逻辑真理论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有计划的迈进设定了条件,但是他所主张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牵强妥协却不能保留了。要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最终还是要诉求于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对于如何看待范畴问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些论点:本文就试图说明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这就要求,首先以通向真理的先验逻辑方式揭露出它们的起源。
2.真理问题
康德已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做了区分,他指出:形式逻辑为真理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条件”(没有它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同自身相一致),而先验逻辑则提供了没有它们我们的思想就不会“与任何对象相关联”的条件,所以它是“真理的逻辑”。[6]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先天句法,那么后者则与其先天语义学有关。承认了“关于真理的名义上的定义,即真理是认知与其对象的符合”7,康德的范畴就成了作为一致或符合的真理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一框架内,新康德主义者和新经院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呈现为下面的问题:是否真理的逻辑学需要在“本体论的真理”(ens tanquam verum),也即在作为判断的尺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奠基。能对一致性给出一种纯逻辑的解释吗?双方都承认仅仅真理的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性把握,对被认知者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但是如果去认识就是去把握思想和事物、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1914年对森特罗尔(sentroul)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引用此书中“真理问题的二律背反”(antimony in the problem of truth) (《全集》1卷51页)的说法来说明这个问题:“或者人们拥有为真理所必需的比较的两要素,即思想和事物,但却没有比较它们的可能性;要不就是人们可以进行实际的比较,但却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全集》1卷51页)。在第一种情况下,判断和思想被视为一种实在的现存者(real existent)、某种主体的行为,而对象则被视为是于认知过程的同样实在的现存者。但是,由于比较自身恰恰是另外一种主体行为,因此即使作为一致性的真理被赢得了,要知道(know)是否确实如此也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设定,一种在判断和被给予知觉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但是由于被给予的东西不能先天地被确证为真实的事物,因此比较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进行的。
由森特罗尔倡导的新经院主义的解决办法求助于本体论真理的观念,即“‘所是的东西’与‘所是者’之间的一致性的”形而上学“关联”(《全集》1卷52页)。在此,判断被认为与一种 “客观的对应物”相一致,而这种对应物“以某种方式必定是事物本身”。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不是什么解决办法,他问道:“何为客观的对应物?它的客观性何在?”(《全集》1卷52页)。于是海德格尔提出了经典的新康德主义问题。虽然他也想走向一种存在论真理的理论,但他发现前批判哲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是不充分的。它的“认知对象”的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赘疣”(《全集》1卷50页),它也没能公正地对待实际科学:“甚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主义哲学也没有导向科学的理论。”(《全集》1卷53页)。海德格尔不想借助于返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
这样还剩两种可能性:怀疑主义,否则就是对一致性的纯“逻辑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揭示了对象是如何可能被认知的同时保持了它的真正先验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判断的]有意义的内容可以有效地决定判断的对象的话,那么判断是真的或是假的。如果存在(res)被理解为对象,而认知(intellectus)被理解为决定性的有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古老的真理概念——认知与存在的符合(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就能以一种纯逻辑的方式被解释(《全集》1卷176页)。这又如何能够避免二律背反呢?显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象”。如果它被形而上学地理解,那么结果是教条主义;如果将其理解为主体的表象,那么结果就是怀疑主义。要让知识是可能的,逻辑的对象就必定是事物本身;不过,这事物本身与认知有一种本质的(先天的)关联。
在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中,对象的逻辑特征成了一个主导性的问题。范畴理论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对象性的理论(《全集》1卷 216页)。在真理问题的范围内,它必须提供那些让人理解何为(are)对象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们能作为衡量知识的尺度。由于此问题预示了下文的探讨,这里就先行指出海德格尔的观点的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这个二律背反部分地涉及到这样一个见解,即以现象学的 “充实”(erfüllung)观念来代替“比较”这一有误导性的隐喻。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指出的那样:真理是一个“‘意向性思想’是否被对象所充实”(《全集》1卷35-36页)的问题。但是,为了充实判断,对象必须是什么样呢?关于这一点,以上这个见解什么也没说。什么是认知性关联?海德格尔以如下的反心理主义的论题开始:判断是“有意义的内容”(significative content),它既不是心理行为也不是语法结构,而是“有效的意义”(valid meaning)(《全集》1卷31页)。有意义的内容就能够是真的或是假的。到1915年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决定判断是真是假的东西,即对象,是“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是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the intuited state of affairs simpliciter)(《全集》1卷273页)。
于是,第二方面就涉及到这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对被给予性的诉求使得海德格尔的立场同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区分了开来,但是如果被给予的东西仅仅是“主观的”,那么它也会招致相反的指控,即怀疑主义。逻辑的对象不能仅仅是事物,但也不能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上的实在表象。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是被给予之物的意义。真理的二律背反要求一种关于有意义的(meaning-full)对象的先验理论,它是形而上学的和生理的-心理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前提。这样,在“结论”中被筹划的“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就将是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形而上学已经设定了对象的先验逻辑概念,那么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如何能够解决知识(真理)的问题?这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是一个难点(aporia),它的要点在他作为范畴问题的视域而予以探讨的三个问题中得到了反思。
3.对象和对象领域
第一个问题——“范畴理论的基本要求”——是“将各种对象领域纳入到在范畴上不可还原的区域中去”(《全集》1卷400页)。一个对象领域,粗略说来就是一门科学理论依之而进行数量化的集合,是一种当代逻辑学意义上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先验逻辑的兴趣首先在于确定在这些领域之内及其之间的范畴关联,在于在其“特定的结构和构造”受“范畴”支配的“区域本体论”(胡塞尔)或“实在领域”之内安置对象(《全集》1卷210-11页)。8
范畴为每一对象都提供了“逻辑位置”。只有依据某种“秩序”,“位置”才有意义,因此“有其逻辑位置的东西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特定的关体相适应”(《全集》1卷212页)。任何一种“在可想见的范围之内”的现象都在逻辑空间中占有一个位置。在化学中被认知的某一特定事件,例如一个碱基反应,就通过在受自然范畴支配的逻辑空间(或实在领域)中被给予——被显示为具有——一个位置,这样它就成了化学领域的对象。9范畴属于科学的理性结构,并且提供了构造对象的原则,这些原则使得科学成了一种“对客观的东西的理论阐释”(《全集》1卷208页)。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会认为将逻辑空间纳入不可还原的范畴领域如此重要呢?
部分说来,这是他与新康德主义内部的一场争论的关联在起作用。那托普的马堡学派关注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形成了一种大体上遵循着康德的范畴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就是能够被归入范畴,这与范畴和对象的种类无关而有其形式的有效性。10但是海德格尔也参与其中的里凯尔特西南德国学派,提出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研究范畴的方式。它认识到,例如,在历史中为知识奠定基础的概念并不与那些适用于物理学的概念相一致。狄尔泰对历史理性批判的吁求和胡塞尔对心理学中的非自然主义范畴的要求,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作为科学理论的逻辑学必须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而且康德的也是如此)“似乎只是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种类,而非范畴自身”(《全集》1卷211页)。范畴既不能从对被思考的那种对象进行抽象的思想中“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求助于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立场而“类推地”确立起来,它们只能被现象学地揭示。在对各种科学的根基的反思中,“不可还原”的实在领域显示着自身(show themselves),并如是地“被展示着”(《全集》1卷213页)。11
不过除了这一内部争论以外,对于划定范畴区域来说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紧迫的原因。如果逻辑学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对于对象的理论阐释”,那么逻辑学的对象属于哪一实在领域呢?真理问题需要一种对象的逻辑理论,而且如果此理论要成为真理论,那么它的原则就必定适用于它自身:“因此逻辑学自身要求它自己的范畴”(《全集》1卷288页)。如果逻辑学要澄清(包括它自己的)关于对象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就“必定有一种逻辑学的逻辑学”。这一问题从总体上关系到这第一个问题的视域以及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
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直接背景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宣称,揭示了将逻辑判断(在其中我们“非常容易和直接地遭遇到逻辑学的特有对象”)等同于判断的心理行为所具有的荒谬性(《全集》1卷166页)。12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论证反对将它等同于句子(“语法形式”),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认为行为和词语属于变易着的、可感觉的现成存在者的范畴领域,而判断则显示出自身还包含着“同一的”东西,它“使得它能以一种持久性和不可变易性而被体认到”,相比之下“心理实在则只能被说成是短暂的和不稳靠的”(《全集》1卷170页)。海德格尔将逻辑学的这一对象,即判断中的同一性因素,称为“意义”(sinn)。但是,意义属于什么样的实在领域?意义的范畴是什么(《全集》1卷171页)?
意义问题“在整个哲学史上,从来就未曾以一种完全有意识和有意义的方式被给予过它的应得之地位”(《全集》1卷24页)。如果说后来海德格尔是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框架内来阐释它的话,那么他在此寻问的则不是存在的意义,而是意义的“存在”,也即它在逻辑空间中的位置。对作为逻辑学对象的意义的现象学把握,意味着对第三种实在的确认,而这种实在是在可感觉(心理-物理的)和超感觉(形而上学的)存在者之外的。对于这种实在,“洛采已在我们德国语言的宝库中找到了确切的表达”,即“除了‘它是(is)’以外,还有一种‘它有效’(gilt)”(《全集》1卷170页)。意义,逻辑学的对象,并不存在但“行得通”(hold),也就是“有效的”。它既不是可感觉的也不是超感觉的,而是“不可感觉的”。这样,在意义和任何存在着或发生的事物之间有了一种存在论差异。意义“不必存在而有效”(holds without having to be)。
这个词来自埃米尔·拉斯克13,因为虽然有效(geltung)概念最初是由洛采引入的(并且以某种形式几乎被所有反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所接受),但主要还是拉斯克对它的阐释影响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拉斯克以一种新的两个世界理论取代了传统的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可以想见的宇宙”被分为存在的和有效的。范畴理论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它解决了逻辑范畴是形而上学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是心灵的思维形式(康德)这一问题。范畴两者都不是,它们属于“有效性”的领域。14第二个并且对海德格尔来说决定性的意义是,它确立起了意义超出于任何和每一对象领域的“先验的”优先性。既然范畴不是思维的形式而是意义的形式,那么逻辑的领域就是不受限制的。在范畴有效性之外,没有任何“存在者”(包括形而上学的存在者)领域是“元逻辑的”(metalogical)。如拉斯克所言,“形而上学也许可以被证明完全是一场骗局和一件荒唐之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的、逻辑的思考有能力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范畴理论“根本不能判决这一问题”(lp, 125页)。这样拉斯克的逻辑学于是就消解了康德“批判的”[对形而上学的]放弃并恢复了“真理的无限领域”(lp,125页),这一观念回响在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学“超出于所有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的谈论中。于是,意义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拉斯克的(和海德格尔的)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
意义(sinn)这个词语最初是被用来标明逻辑判断的,但是真理的二律背反已经指向了这一概念的扩展,拉斯克在其《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中着手进行了这一工作。在拉斯克看来,逻辑范畴体系与对象自身的对象性有关(lp,29页),因此,“意义”这个词应当适用于后者,即先验逻辑的对象。判断的意义是一种“衍生的”、第二位的、人为的构造。“绝对意义上的”意义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或关联”(lp,34页)。这种统一不是现存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原事态(urverh?ltnis),“在可感觉范围内获得的任何一种关联都不可与之相比拟”(lp,175)。
如果被先验逻辑学所理解的对象因此是范式的(paradigmatic)或原型的(urbildlich)意义而非再现的(nachbildlich)意义,那么范畴和质料之间的原事态这一意义概念,对于非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说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是它,而非诸如实体或主体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才是“存在者的”首要的“哲学修饰”(philosophical epithet)(lp,123页)。但它是一种特别先验的观念,直接经验和经验科学的话语都无法理解它。它所涉及的只是拉斯克所谓的对象质料(lp,122页);人们只是“生活”于意义领域之中,却没有 “认识到”它本身(lp,191页以下)。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逻辑学家把现存对象刻画为意义”,那么在对暗中使我们的一阶(first-order)认知性把握得以可能的东西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范畴形式本身(lp,123页)。依据对存在/有效性的区分的理解,我们把握了作为形式的范畴,所以在先验逻辑中我们能“认知”作为意义的对象。15
海德格尔明确地采用了拉斯克的范畴形式概念,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先验哲学中,形式概念都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它并不总是“清晰地和特别是毫无歧义地被理解”(《全集》1卷223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形式具有“作为心理的、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实在的构造原则这样的形而上学意义”,也即是说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实体。但是如果形式是一种实体,而且如果它被认为是将实体构造为实体的东西,那么就会有一种无限倒退(《全集》1卷221页)。康德在逻辑的东西的领域内将形式概念抬到了权能这样的决定性位置上(《全集》1卷223页),但是他没有决定性地摆脱心理主义。16而对拉斯克来说,范畴形式只有“有效 ”的特征,而且由于有效总是对某物有效(hin-gelten),所以形式在本质上就与特定的质料关联在一起。因此,说形式能够存在(亚里士多德)或者通过思维能被赋予质料(康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如果存在着诸多的形式(有一张范畴“表”),那么区分的原则必然在于质料本身。由拉斯克的这一“对形式的质料决定”(material determination of form)原则可知,范畴的“发现”,如海德格尔所要求的那样,将是一件经验现象学的事情(lp,63页)。
质料决定原则意味着不能以黑格尔的方式将对象扬弃到(逻辑的)概念里去,即使是在黑格尔主义化的新康德主义的无限上升中也不行。但是如果形式不是对象的一个现成的组成成分,例如就像一棵树的枝杈或基因(dna)是它的组成成分一样,那么它的“有效”如何被理解呢?拉斯克回答说,形式“只是一种与质料相关的、特定的、客观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lp,69页),只是质料自身内所固有的某种秩序。17它是一个“澄明的契机”(moment of clarity),借助这一契机事物同质料相一致的方式被“照亮”了(lp,75页)。对象质料不能被还原为逻辑形式(“泛逻辑主义”),而是内在于逻各斯的(logos-immanent),它在形式之内就如在它的意蕴关联之内一样“被持有”(“逻各斯的泛统治”)(lp,133页)。同样,对海德格尔来说,形式既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实体的现成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澄明的契机”;范畴给对象质料“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带来了“更多的澄明”。它只是“与对象的某种意蕴关联”,只是质料自身的排列或卷入(《全集》1卷224、225页)。作为“被给予者中一个秩序的契机”,范畴使被给予者成为“可把握的、可认知的、可理解的”,也即它“有效”(《全集》1卷224页)。这样,对海德格尔和拉斯克来说,形式都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一个可理解性原则,但它属于质料本身而不是首先通过思维的构建活动才出现的。
这种关于逻辑形式及相应地关于原型意义的对象的观点,使得拉斯克的真理概念更为牢靠。严格说来,认知、判断只能说是“与真理一致”或“与真理相反”,因为它们是在经验知识的主观过程中,通过对对象的“人为的”解构而出现的。使这种相反或一致被衡量出的东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作为“超对立的”(übergengens?tzlich)意义的对象自身,它超越了真与假的对立。18对象是有效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体,它可恰当地被称为“真的”:“特定的对象就是特定的理论的意义统一体,就是特定的真理。”比如,“时空对象是真理”,虽然它们不是“认知、判断、命题”,而是“原型领域内的意义统一体”(lp,41页)。因此,拉斯克的先验对象概念满足了上面开列的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所需要的条件,也即是说,它显示出对象在判断中是如何能够作为真理的尺度而从原则上起作用的。这么说的理由是,如果“对象自身无非是意义”,那么由此可知“意义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判断的意义和事物本身之间怀疑论的距离)“就等于意义和意义之间的距离”(lp,43页;lu,394页)。
对拉斯克要揭示原型对象(范畴形式和质料)的要素是如何被纳入判断的结构中去的企图,我们在此不能再加审查了。19在此介绍的拉斯克的观点只是用来提示出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对象的思考的思想来源,并为确定他的解释中有何新的东西做些准备。拉斯克使得海德格尔以一种批判的、逻辑的方式形成了对存在论真理的新经院主义式的诉求,但他没能彻底地解决这个[关于真理问题的]背反。
海德格尔将司各脱的存在论的真理学说——存在(ens)和真理(verum)的可转换性——明确地表达在了一句逻辑成语中:“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真的对象”(《全集》1卷265页)。虽然怀有同新经院主义一样的诉诸存在论真理的动机(也即是说,将事物本身作为判断的尺度整合到逻辑中去),但是海德格尔的重构用基于有效性之上的逻辑思考代替了后者的形而上学“赘疣”。说每一对象都是一真实的对象并不是做了一个形而上学论断(一个形而上学论断总是与超感觉对象质料有关,而非与对象有关)。它只是意在显示范畴自身的范畴本质,意在确认与有效性自身相关的意蕴关联,也即“与认知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全集》1卷267页)。但是如果不涉及认知主体,那么这一意蕴就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作为范畴和质料的统一体的对象,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意义统一体是真的(《全集》1卷268页),即使“在纯粹的被给予性中意识可被导向‘真的东西’”(《全集》1卷285页),但海德格尔还是强调指出:这对象“实际上只包括”(《全集》1卷271页)那些在判断中能被明确地端呈出来,并结合到意义统一体中去的要素:“真的东西在认知中构造自身”(《全集》1卷271页)。通过“主体的取位(position taking)行为”,在范畴上被构造的“真的”对象,“即随其特定的实在形式一起被给予的对象质料的有意义的内容”,就被“纳入到了判断中来”(《全集》1卷270页)。
看起来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的要素现在已然齐备。通过第三种“实在形式”,即有效的意义,范畴理论已在对象之中被奠基。对形式的质料决定观,无需还原主义就澄清了各门区域性科学的认知对象,而且无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或康德怀疑论的拒弃,它就确立起了“逻辑意义的优先性”。但是这一对存在论真理的重塑是否是充分的呢?对象被纳入认知——作为“真的”对象的先验意义所依赖的那意蕴关联——如何被理解?出于“结论”中的未竟任务的第二点所暗示的原因,海德格尔发现他在此必须超越拉斯克。
4.逻辑与主体性
范畴问题的第一个视域是划定意义的对象领域[所属]的实在区域,但没有第二个视域,即将其“嵌入主体和判断问题”(《全集》1卷40页),它是不能被赢得的。真理的逻辑要求填补司各脱(从而当代的新经院主义)及拉斯克(从而当代的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所具有的某种空白。只要范畴理论依然像拉斯克的理论那样,将全部目光都集中于“真正的先验性”(“未被任何主体性触及的”对象),它就尚未揭示知识作为认知是如何可能的。20二律背反将依然会出现,因为“要比较判断的意义和实在的对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全集》1卷273页)。拉斯克的对象意义的要素和判断的意义的要素之间的同构(lu, 394页)只是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需显示此同构是如何被给予的。
与拉斯克相对,海德格尔现象学地阐释了这一问题。认知不是比较而是充实(erfüllung)。这也就是说,被给予的对象、“被给予的有意义的内容、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是“判断的意义的尺度;后者从它那里获得它的客观有效性”(《全集》1卷273页)。但是这意味着,拉斯克的逻各斯的内在领域(作为原型意义的对象的所在或“澄明”)的被给予性必须被逻辑地加以定位。如果不涉及主体,对对象的逻辑澄明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存在论真理必须奠基于早已被司各脱指出过、“被正确理解的内在性概念”之中(《全集》1卷273页);存在和真理的可转换性蕴涵着拉斯克的论题“‘逻辑的存在者’和对象的可转换性”(《全集》1卷279页)。但是对于海德格尔/司各脱来说,逻辑的存在者(从先验逻辑观点来看的对象)是一种生命中的存在(ens in anima)。这不可能是一种现成的、实在的心理实体,不可能是一种活动或表象,而只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意向对象的意义’(noematic meaning)”(《全集》1卷277页)。
对于海德格尔对知识和对象之间的意蕴关联的理解来说,提及胡塞尔是非常关键的。意向对象,也即被给予的有意义的内容,无非就是在反思的第二意向(secunda intentio )中被把握到的事物本身,在这第二意向中意识不是(像在 原初意向[prima intention]中那样)被导向“在其直接实在性中的实在对象”,而是“被导向它自己的内容”(《全集》1卷279页),也即真实的对象“的”可理解性,并从而也被导向它的范畴结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认知的对象和对对象的认知之间的区分归属于内在性的领域,这种领域是受反思的和非反思的意识之间的(现象学的)区分支配的。“实在样式间的首要区分是意识与实在之间的区分;更准确地说,是在实在性的非有效样式间的区分,而这些非有效样式转而又总是能在以有效性为特征的意义背景之内并通过它而被给予”(《全集》1卷279页)。如果说“只是因为我生活于有效性领域之中,我才能知道关于存在者的事情”(《全集》1卷280页)是正确的,那么说只是因为能反思这样的“生活”,我才能知道有效性领域的事情,这也是正确的。
有了他的现象学的内在性概念,海德格尔就能够“在主体和判断问题的范围之内”来安置拉斯克的范畴有效性理论了。如果范畴——海德格尔在此称之为“对可经验的东西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要素和资源”(《全集》1卷400页)21——并非来自对实在者的“复制”,而是“相关于”质料而安排秩序的原则,那么需要解释的,大略地说来,是它们的充实的需要(erfüllungedüftigkeit)(拉斯克)或语义学的质,以及它们对某物的有效(hin-gelten)或对质料“的”持有(holding)。在拉斯克将有效性视为一个不可还原的先验范畴的地方,海德格尔就指出它必须被奠基于意向性之中:“意向性是逻辑领域的‘规定范畴’”(《全集》1卷283页),也即“决定秩序和划定逻辑学领域的契机”(《全集》1卷281页)。如果不把逻辑的这一“主体方面”考虑进来,那么一种范畴的“客体逻辑”理论“必定依然是不完备的”(《全集》1卷404页)。
范畴是“对象的最为普遍的决定因素”,但是提及一个对象就已牵连着主体了(《全集》1卷403页)。首先,在生活的“单纯被给予性”中,意识“朝向‘真的’状态”(《全集》1卷285页);其次,人们要“意识到它是真的、有效的意义,就只有通过判断”(《全集》1卷285页)。于是,范畴理论遇上了传统的被给予性和“述谓”问题(《全集》1卷403页)。对象是如何作为有效意义(“‘真的’状态”)被给予的,以至于通过作为“取位”的判断主体的“成就”,主体就能够“意识到意义”(《全集》1卷285页)?述谓活动及其内在逻辑构造——判断的意义——如何能对超验的对象(“实在的非有效样式”)有效呢?这一问把人们从范畴理论带到了意义理论,因此必须在此对之置而不论。但是在“结论”中海德格尔总结道:只有“从判断开始”,“范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于‘思想之外’的)有效性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因为“不把 ‘主体逻辑’考虑进来,即使谈及内在的和先验的有效性也毫无意义”(《全集》1卷404页)。
当海德格尔引入“投射”(projektion)一词来探讨一个对象领域是如何被范畴所构造时,他就已经触及了主体逻辑问题,虽然他并没有展开。例如,只有通过将它们投射入一个受范畴支配的“同质媒介”或“生活元素”(lebenselement)之中,我才能计数极为特殊的对象质料,如“两棵树”(《全集》1卷255页)。当司各脱为了区分被给予性的样式(存在[essendi] ,意识[intelligendi],指示[significandi])而诉诸主体或“行为”时,他就暗示了主体逻辑,而胡塞尔则为海德格尔指明了这一点(《全集》1卷321页)。22但是在司各脱那儿也有一个空白:他缺少一个“精确的主体概念”(《全集》1卷401页),加之经院心理学处于主导地位的“客观的-意向对象的导向”(《全集》1卷205页),这意味着司各脱从没有完全地将客体逻辑(范畴理论)与判断中的被给予性,以及客观性的构造这些主体逻辑问题完整地结合起来过。23
如果说中世纪的逻辑学最终没能将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立即指出,当代逻辑理论同样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比较了两种对立的现代观点——屈尔佩的批判实在论和新康德主义的先验唯心主义——以此表明二者都没能够成功地澄清认知和对象之间的关联。
批判实在论的观点在认知的经验的(心理的)方面和理性的(范畴的)方面之间做了区分,并坚持认为后者,范畴,使我们得以从仅仅“设定”(poisiting)一个先验对象(在主体被给予性的基础之上)进展到对之进行一些如实的述谓。24这避免了心理学的唯心主义,因为[按其观点]范畴不是作用于知觉的被给予物的联想的原则。但是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屈尔佩的观点,“被认知决定的实在世界的对象”并非如实地“呈现在知觉中,并非仅仅在意识中被给予,而是首先通过认知的过程,尤其是通过科学研究而被把握”,而且这也恰好正是马堡(形式的)唯心主义的首要观点:认知的对象不是被给予者,而是通过科学的不断探索而被赢得的有效判断,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理念(idea)。由于没有认识到判断问题(被纳入它自己的科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对于“客观性的奠基”所具有的意义(《全集》1卷403页),批判实在论是不够批判的。25
但马堡唯心主义也未获成功,虽然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首先,通过把空间和时间处理为范畴,它规避了被给予性问题。随着康德的先验美学的这种逻辑化,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形式唯心主义没能“将对形式的质料决定原则与其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集》1卷404页)。如果范畴从质料那里获得它们的意义,那么除了现象学地诉诸不同类型质料的被给予性,它们就不能被理解。其次,出于对心理主义的恐惧,它将意向行为(noetic)或行为的领域贬斥到“理性心理学”中的范畴构造的地位上。但是如果质料并非首先被给予“理论的”主体,而是被给予投身于前理论的、实际的世界生活的意识,那么这种对“客观有效”思维的形式重构就会错失在其中可觅得范畴之起源的那个维度,也即处于“生活”中的可理解性或澄明。
是拉斯克最接近于克服了当代实在论和唯心主义的缺陷。以其被从质料上决定的范畴形式理论,他“毫无疑问地赢得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全集》1卷405页)。但是质料如何决定形式的问题——原事态的所在——最终开启了一个“新领域”,在其中拉斯克不能“对可感觉质料和非可感觉质料之间的区别做出充分的解释”(《全集》1卷405页)。也就是说,如果范畴自身就是先验逻辑认知的“质料”,那么拉斯克对范畴如何能被给予(就如可感觉地存在的质料在知觉中如何被给予)这一问题的忽略就是不合适的。拉斯克关于意义的“真理论的(aletheiological)实在论”从而最终依然是非批判的,因为他把所有这样的问题都看作是心理主义的。通过将有效性奠基于意向性之中,海德格尔为这一问题指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他对胡塞尔的“范畴直观”的高度关注,显示了在其后来的作品中他是多么严肃地来对待它的。26然而,在这里海德格尔只是简单地评论说,如果不首先弄清“下判断的主体”,那么人们将“永远不能将所谓的‘有效性’的意义完全端呈出来”(《全集》1卷405页)。
关于范畴问题的第二个视域,海德格尔接着指出,必须将批判实在论和先验唯心主义的动机(motives)带入“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去”(《全集》1卷404页)。屈尔佩的实在论正确地保留了认知对象的先验性,但是它的自然主义没有公正地对待意义问题。马堡唯心主义正确地坚持了有效意义的逻辑首要性,但是和拉斯克一样,没有认识到“逻辑的最基本问题自身只显示给那些将‘前科学的’知识考虑在内的逻辑探究者们”(lp,185页),在这种“前科学的”认知中可觅得在质料上被决定的形式的起源。但是,即使说拉斯克把握了对形式的质料决定的话,那么他对判断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还是依然深陷于“真正的先验性”这一准教条主义泥潭之中,这种先验性关注的是“结构问题”,它脱离了在内在性中赢得或发现结构的问题。质料决定的问题并没引导他走向对形式/质料二元分立的“价值和局限进行不可规避的有原则的探究”(《全集》1卷405页),从而它的“极富成果的”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对象的意义概念,驱使他来到了“他也许从没充分意识到过的形而上学问题”面前(《全集》1卷406页)。27但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又是什么样的“更高的统一体”呢?这就是范畴问题的第三个视域。
5.形而上学问题
前两个问题域属于逻辑自身,包含其客体和主体方面的协调。然而,第三个问题则要求超出逻辑的范围,从而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在此所谓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前行论述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一超出之举的成问题的特征说些什么了。
如果第一个问题(在范畴上划定意义的逻辑领域)不诉诸第二个问题(主体和判断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那么海德格尔是通过诉诸胡塞尔的内在性观念而开始走向这一目标的。胡塞尔的《观念ⅰ》已提供了“对‘意识’的丰富性的决定性洞见,并摧毁了关于意识一般的空洞性的通常看法”(《全集》1卷405页),但最终说来这还是不够的:“人们根本就不能如实地看到逻辑和它的问题,除非它们由之而被解释的背景成了超逻辑的”(《全集》1卷405页)。尤其是,为主观的(现象的)逻辑问题提供背景的内在性概念,不能以任何传统的或当代的唯心主义或实在论的模式来理解。显然,能澄清这种内在性自身的范畴不能通过对认知的意蕴关联,也即对逻辑的“认识论主体”的反思而被赢得。必须超越逻辑,超越“理论态度”,这种态度“只是活生生的精神(living spirit)的诸多形成方向之一”。这样,范畴问题的第三个视域就显示为,依据“活生生的精神”观念“对意识进行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解释这样的任务”(《全集》1卷406页)。由于这“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精神”(《全集》1卷407页),所以“历史和它的文化-哲学的、宇宙目的论的解释”就必须成为“在范畴问题范围内决定意义的因素”(《全集》1卷408页),也就是说,在一种范畴形式理论中,历史属于决定着意义的质料。
这些观念引出了诸多问题,它们对充分阐释海德格尔的早期逻辑著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虽然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吁求反映了他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是他自己的话语则远非一种盖泽尔( geyser )或者森特罗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它们来自黑格尔,或者更精确地说,来自狄尔泰的后黑格尔主义的生命哲学。但在此我们将仅仅指出,海德格尔诉诸形而上学的方式与真理的逻辑有关。海德格尔说,正是“真理问题”要求一种“对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宇宙目的论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哲学离开了逻辑“结构研究”而“突入到真正的实在和真实的真理(ture reality and real truth)”(《全集》1卷406页)。即使逻辑意义(真理)既非心理的又非形而上学的,但海德格尔依然要求以某种方式对其所谓的“存在论”地位予以具体阐明。形式/质料的结构统一体在逻辑的范围内也许够用了,但是如果人们要为逻辑学“保证给我们真正的实在和客观性”的能力奠定根基,那么“逻辑的意义就必须被带入到与其存在的意义(ontic significance)也有关的问题中去”(《全集》1卷406页)。
这些有所节略的评论等于宣称先验逻辑没能回答问题:何为意义?“形而上学”应当提供通达“存在的意义”的途径,但清楚的是,海德格尔在“结论”中的用法并不与那个主要文本[《教职论文》——译者注]中被发现的形而上学(一门关于超感觉实体的科学)的意义一致。何为存在的意义?当海德格尔暗示说这将是一种“对对象概念的先验的-存在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在“存在的意义”这个词中听到他后来作为存在论而加以展开的东西,也即对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的(先验)研究,这是承继作为真理基础的原型意义的先验逻辑研究的学说。
一种源自先验逻辑学的“意义的形而上学”最终要求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一点昭然地显示这样一个问题之中,即如何用那个主要文本中的系统术语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协调起来这样一个问题之中。考虑到逻辑学作为理论的理论的绝对优先性,它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作为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理论的形而上学。又考虑到对象、形式和质料是全部的逻辑原则,那么对于对象的一种存在的解释,只能是一种(对形式和质料的原事态的)“存在的”意义的把握。例如,说质料“决定”形式,或者说形式“澄明”质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形而上学是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科学,那么关于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它又能告诉我们哪些逻辑学所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呢,既然它已经预设了逻辑?它的“超逻辑”原则从何而来?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但两则评注已指出了困难之所在。28第一,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在中世纪哲学中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是“共属一体”的,“脱离了生活,作为一种理性主义构造的哲学是无力的,而作为非理性主义体验的神秘主义则是盲目的”,因此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必须在某种更高的统一体中被审视(《全集》1卷410页)。第二,与质料决定问题相联,他承诺要揭示艾克哈特(eckhart)的神秘主义对于“真理问题”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全集》1卷402页)。29因此,似乎决定形式的质料并不要求作为一种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反之,对逻辑意义的“真正的实在和实在的真理”,及对它的“存在的意义”的突破,似乎蕴涵着与神秘主义的结合。然而它也将有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解释”的特征,我认为这意味着它依然关注着批判的、在现象学上被理解的“独一无二的意识关联”(《全集》1卷277页)。
因此,范畴问题的形而上学视域也要求一种对主体的先验的存在解释。主体的“真正的实在”是历史的,在其内在性中真理问题逻辑地被构建并被解决。范畴既然是质料自身的意蕴关联,那么它就不能从一种无时间性的意识一般中推演出来。因此范畴的出现——“对可经验者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资源”的出现——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了对范畴的本质进行“存在的”解释,这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如果并非首先是在科学中,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前理论的可理解性中、在其“在有效性中的生存”中,质料的意蕴关联原初地显示自身,那么把范畴理论限定于科学的可理解性原则就是人为的做作。可理解性、范畴体系并非仅仅在理论生活中才被发现。因此,逻辑学必须认识到,意义(和范畴)的根源存在于活生生精神的所有富有意义的形成方向中。只有通过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活生生精神的“基本形而上学结构”,“及其与形而上学的‘起源’的关系”,人们才能理解如何能将“行为的独一无二性和个体性与意义的普遍性和持存性本身一起融入活生生的统一体中”(《全集》1卷410页)。30
这就是意义的形而上学,也即“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的终极视域。意义(逻辑对象)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之间的差别被设定了,虽然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表明这种意义与一种对行为的非心理学的、逻辑的研究并非水火不容。但是,在形而上学的或“存在的”层次上,依然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活生生精神的基本形而上学结构,来理解个体性和普遍性、行为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要求对内在性和意识的现象学领域进行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解释。认识论的内在性必须被提交到历史的活生生精神的超逻辑背景中去,这种背景是意义的原初所在(虽然显然不是根源)。海德格尔没有说人们怎样做到这一点,也没有说这种解释的逻辑地位会如何。
可以表明这一要求很快就把海德格尔引向了他的核心发现之一,也即抛弃意义与“对象”的先验逻辑的同一性,转而采用(作为“世界”的)意义的先验存在论概念。但是这将需要考虑他早期的弗莱堡讲座课程,同样也要求对他如何和为何逐渐抛弃了1916年的“哲学的更深层的、本质上的世界观特征”这一思想(《全集》1卷410页)进行充分的解释,这一思想是掩藏在他那有点神秘主义气息的形而上学背后的。我们在此只是提请人们注意:对范畴理论、对哲学化的科学的要求,继续在他那些研究缘在(dasein)的生存状态(existentials)的文本中发挥着影响。尽管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存在与时间》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在逻辑真理问题中被摆明的挑战,也就是去说明不同的(包括它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式中真正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种说明并不意味着为知识问题提供某种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而是对它的一种先验存在论的再阐释。 [1]本文依据了海德格尔的下列早期著述,它们是与当时的逻辑学有着重要关联的:“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das realit?tsproblem in der modern philosophie”)(1912),“逻辑新探”(“neuere forschungen über logic”)(1912),《对查理斯·森特罗尔的的评论》(review of ‘charles sentroul’s kant und aristoteles’)(1914),《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us)(1914)和《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1915, 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最后这本著作附有1916年的一个结论《范畴问题》(“das kategorienproblem”)。在文中我是依据《早期著作》(frühe schriften)(《[海德格尔]全集》1卷)中的页码来引用这些作品的。所有的引文都是我翻译的,但参考了先前已有的译文。
[2]这是“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争论系统地进行之处,而且对于新经院主义的这样一个策略,即表明“现代”思想家及其争论的问题(包括现代科学)都能被纳入经院主义的框架中去的策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策略被教皇通谕aeterni patris(1879)官方化。因此,沃尔夫-迪特尔·古道普(wolf-dieter gudopp)在其《青年海德格尔》(frankfurt: verlag marxistische bl?tter, 1983,21)中,看到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有一种关键性的新经院主义式的“反现代主义”。但是在对海德格尔早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审查后,胡戈·奥特(hugo ott)在《马丁·海德格尔:正在形成之中的传记》(frankfurt:campus verlag,1988)的第74页以下,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曾深深地被“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所吸引。
[3]由于我没有篇幅在此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所以我只是简单地指出,我将把“bedeutung”及其同族词译作“意义”(signification),而将sinn及其同族词译为“含义”(meaning)。海德格尔在所引段落中提及的“准备性的工作”与将自然语言转译为逻辑形式(如表征符号)的任务有密切关联。这就出现了海德格尔与符号逻辑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我在此不讨论它。在1912年的逻辑评论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了罗素和怀特海,他要争论的只是这种“逻辑斯谛”并不能通达“真正的逻辑问题”,即“[‘对逻辑问题进行数学处理’的]可能性条件何在”的问题(《全集》1卷42-43页)。
[4]海德格尔的重构部分地奠基于[《理论语法》一书中的]“意义的形态”(de modis significandi)这一章,后来这本书的作者被证明是埃尔富特(erfurt)的一名司各脱主义者托马斯,而非司各脱本人。由于考虑到它的问题历史的方式(《全集》1卷196、399页),这一出入对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影响甚微,所以我将继续在文章中将它指涉为“司各脱”。
[5]于是,正如曼弗雷德·布莱拉克(manfred brelage)在其“先验哲学和具体的主体性”[载《先验哲学研究》(berlin:de gruyter, 1965, 72-230)]中已表明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计划可被看作他完善或超越一种形式的“客体逻辑”(这种逻辑是关于有效知识的原则的)几次努力中的一次,它们具有晚期新康德主义特征。在为批判的认识论寻求背景的这些努力中,除了海德格尔的努力以外,布莱拉克还探讨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晚期那托普的《思维心理学》、r·赫尼希斯瓦尔德(r. h?nigswald)的《单子论》和n·哈特曼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论”。
[6]伊曼努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 kemp ith)译(london:macmillan,1968),98(a59/b84), 100(a62-63/b87)。
7同上,97(a58/b82)。
8“wirklichkeitereich”(实在性领域)是海德格尔指称范畴 “种类”(sort)的常用词语,不同对象和对象领域(gegenstandsgebiete)都归属于这种范畴种类,当然他有时也使用诸如“缘在的形式”(daseinsform)、“实在性的形式”(wirklichkeitsform)、“实在性的方式”(wirklichkeitsweise)等相关词语来表达这个意思。考虑到这些概念和接下来的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区分之间的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在此“存在”(being)只是意味着实在的单个领域的范畴,也就是只意味着可知觉的现成存在者。在1925-26年的冬季学期的讲稿中,海德格尔明确否认这种 “来自洛采”的用法(《全集》21卷64页)。
9诸如“存在者”、“因果性”、“事件”(occurrence)等等。经验科学家不关心这样的范畴,而是关心科学的对象之中及其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海德格尔正是这样理解科学的“理性”维度的。但显然,在来自范畴维度的抽象中,正如下面将被探讨的一样,科学家通达对象的“理论”方式失却了它的意义。
10对较布莱拉克,前面所引书的第103页。
11表明如下一点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这些(无可疑义的)早期著述中,不是海德格尔的那研究方式,而是他对现象学的那种吁求是现象学的。关于狄尔泰,我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出色探讨,参见弗瑞特尤夫·罗迪(frithjof rodi)编著的《狄尔泰年鉴》4卷(1968-87)中的文章。
12在逻辑评论中,而后又一字不差地在其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赞许胡塞尔已经“打破了心理主义的进路”,然而同时他也赞同那托普的如下论断:新康德主义者从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论证中“学不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全集》1卷19、64页)。
13埃米尔·拉斯克,《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die logik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kategorienlehre),载《作品集ⅱ》(gesammelte schriften ⅱ),欧根·赫里格尔(eugen herrigel)编著(tübingen:j.c.b. mohr, 1923, 6)。当下文中引用这本1911年的作品时,其出处会在文章中给出,此书名被缩写为“lp”。根据上面我对“存在论差异”一词的用法,比较一下拉斯克早已使用了的而海德格尔将会使用的明确表述(如lp 21, 46, 117, 121页)。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和逻辑学的无家可归性”(lask, heidegger, and the homelessness of logic), 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3/3(1992) 卷222-39页。
14当然,新康德主义者并没有把范畴看作思维的心理形式,但是他们的确是将范畴理解成了有效知识的形式原则。然而,拉斯克拒绝承认这种关于知识的提法,对他来说 “认知”蕴含着一个认知主体。被称为“有效性”的实在样式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拉斯克试图界定的,而非定义式地设定的,虽然如下文所论,恰是在此海德格尔发现他失败了。也参见前面所引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一文。
15要对拉斯克心中所想进行充分的解释需要进入他对体验(erleben)和认识(erkennen)的区分,并对他的“功能形式/质料”的区分进行阐释。本文的当前目标更为有限,但可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和先验逻辑观念”,载罗伯特·苏克罗维斯基(robert sokolowski)编著的《胡塞尔和现象学传统》(washington,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88, 63-85)。
16虽然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证明,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心理主义的还是先验的这个问题早已被解决了,“先验的-逻辑的解释受到了偏爱”(《全集》1卷19页),但是心理主义解释的依然存在正显示了康德思想(如“综合”思想)的一种不清晰性。拉斯克无论如何也没完全解除康德的心理主义(lp,243-262页)。人们知道,大约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海德格尔已对康德发生了一种新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一条对康德进行现象学解释的道路(《全集》25卷6页)。参见丹尼尔·达尔斯托姆(daniel dahlstrom)的“海德格尔的康德式转折:对他《纯粹理性批判》的评论的注释”,载《形而上学评论》45卷(1991)329-361页。达尔斯托姆没有涉及海德格尔在早期作品中对康德的解释,在那儿海德格尔似乎感到,像那时的胡塞尔一样对康德有所保留是合适的。
17这个词——对《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被马克奎利(macquarrie)和罗宾逊(robinson)译为involvement(“意蕴关联”),虽然如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在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berlin:de gruyter, 1970, 290)中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这个词所包含的“两个含义也许没有任何语言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一问题值得另行对待,但现在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如果逻辑空间的“关联整体”(beziehungsganzes)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联统一体”(bewandtnisganzheit)的先兆的话,那么海德格尔采用拉斯克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一词来解释逻辑形式就是这一过渡中的重要一环。在我的文章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对它留而不译,以此来突出这个词的成问题的新奇之处。
18这形成了拉斯克的第二篇重要论文《判断理论》(1912)(载《作品集》,前面所引的书,尤其是413页及以下)的主题。当本文在下面引用《判断理论》时,它被缩写为“lu”。
19用拉斯克的话说,这是一个已内在于逻各斯的原型意义对主体来说“成了内在的”的过程(lu,414页)。虽然海德格尔称赞拉斯克关于判断的书“对范畴理论而言甚至比他的《哲学的逻辑》的意义更为重大。”(《全集》1卷407页),虽然在其博士论文中他使用了拉斯克的“元语法的主谓理论”(《全集》1卷177-181页;以及1912年的《全集》1卷32页以下),但是与“成为内在的”这种观念相对的“先验性”观念,使得拉斯克不可能对对象和判断之间的关联进行意向行为的探讨。而且,如下面的第4节所要讲的,正是从这里海德格尔转向了现象学。
20所引段落是拉斯克的(lu, 425页),而且他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意义概念明显相对地引入它们的。对拉斯克的先验性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参见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前面所引书的第73-78页。对拉斯克来说,先验逻辑是一种关于“未被任何主体性触及过的”对象的逻辑,然而由于认知“原罪”,这种对象是一个“失乐园”(lu, 426页)。
21这一短语预示着作为“形式显示”概念的范畴观念,这些概念“以一种特殊方式来解释现象”(《全集》61卷86页),它们是海德格尔在1921/22年的冬季学期引入的。在此,范畴“在生活自身中生活”,是“生活在其中通达自身的”突出方式(《全集》61卷88页)。
22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r·m·斯特瓦尔特(roderick m. stewart)的“海德格尔《教职论文》中的意义和激进的主体性”,载《人与世界》12期(1979)360-386页;及约翰·卡普托(john kaputo)的“现象学、神秘主义和思辩语法: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研究”,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5期(1974)101-107页。在即将出版的论文“1919年战争应急时期讲课: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突破”中,西奥多·克兹尔对斯特瓦尔特和卡普托对样式(modi)所做的处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校正。也可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的的起源》(berkeley/losangele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的第31页及第515页以下。
23这与海德格尔如下的论断有关:在对其“作为问题的问题”,及对“解决它们的方式和可能性”的“反思”这种“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思想“显示出缺少方的自我意识”。一句话,“在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的人不是凭其自身的(bei sich selbst)”(《全集》1卷199页)。据海德格尔说,这并非毫无益处,因为它排除了心理主义的错误,但是它也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精确的[即逻辑上充分的]主体概念”的缺乏。
24海德格尔在1912年的论实在性问题的文章中研究过这些问题(《全集》1卷1-15页,尤其是13-15页),这也是他在“结论”中所做的简短注解的背景。
25最后,海德格尔抛弃了批判的——或“科学的”——实在论,因为它摧毁了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区分。根据屈尔佩“自然主义的”观点(如在其1902年的《今日德国哲学》中),最终只有通过一种“归纳的形而上学”知识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种形而上学将关于主体的科学(心理学)和关于客体的科学(物理学)的成就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发现,这种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假设的”特征是要不得的(《全集》1卷15页)。
26例如,在1925年的夏季学期,海德格尔将范畴直观视为现象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全集》20卷63页以下)。而且在1973年的查林根(z?hrigen)研讨班上的报告表明,海德格尔把范畴直观概念看作“胡塞尔思想的闪光点”。参见《四个研讨班》,由库尔得·奥克瓦特(curd ochwadt)译自法国研讨班的草稿(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7, 111)。
27在1921-22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自己研究了形式/质料二元分立的“价值和局限性”,最后告诫说:“最好是把形式概念与范畴概念分开”(《全集》1卷86页)。这一结论是已蕴含在作为“质料”的意蕴关联的范畴形式这一观念之中。
28这一问题最终在海德格尔的“事实性的解释学”中得以阐明。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的‘实际性’概念领域的起源”,载《狄尔泰年鉴》,前面所引书的第91-120页。我只想补充说,这种解释学依然明显地被理解作先验哲学。以此观点对《存在与时间》的一种解释,可以在卡尔-弗里德里希·格特曼(carl-friederich gethmann)的《理解与解释》(bonn:bouvier verlag, 1974)一书中找到。
29参见约翰·卡普托的《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秘因素》(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8),尤其是第145-152页。卡普托正确地把海德格尔转向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看作是受“为真理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愿望所驱动的。这种解决办法将真理视为思想和存在的相互关系或共属(151页)。并且他推测到——又一次以充分的理由——这一解决办法的目标是一种“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式的实在论”(152页),尽管这种实在论远非经院主义的实在论,而是非常接近于先验唯心论,但是由于海德格尔特别提到的“对形式的质料决定原则”问题,这样的神秘主义成了一种选择(《全集》1卷402页)。在此拉斯克再次提供了部分背景:他把最终非逻辑的质料的被给予性描述为一种神秘主义的声音,“对于劫夺含义与意义的感受的沉思”(lu, 84页)。
30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海德格尔。在1912年他提出了如下怀疑:“逻辑学同心理学的严格分立也许是不可赢得的”,而且“逻辑的东西蕴涵于心理的东西之中的事实”是一个“特殊的并也许永远得不到阐明的问题”(《全集》1卷29-30页)。在1914年他又注意到如下问题:“心理实在和判断的有效持存(subsistence)之间的关联应如何界定”,并且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更深层的解决办法甚至是否能称为一个目标”都感到疑惑(《全集》1卷176页)。在目前我们的讨论涉及的背景中,即在海德格尔1916年的作品中,他主张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种活生生精神的形而上学而得以解决。然而,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暗示“判断的真实完成和理想内容的分立”是完全未被证明的,而“心理主义”也许实际上“有权坚持反对这种分立”,即使它没有澄清那(本体论的)关联(《全集》2卷287页)。这当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接受了心理主义,虽然图根哈特提出论证说他还是成了它的一个翻版的受害者。参见《真理观念》,前面所引书的第331页以下、第340页以下。
第十四篇 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_西方哲学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分引论、通论、分论和结论四部分。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但作者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问题,就是康德把哲学史看得太轻闲。而黑格尔则把哲学史订得太封闭。在“通论”中,为了探讨哲学史撰作的意义根本,作者列举了一些要目,作为反省的据点,其中包括:康德就“学院意义的哲学”与“世界意义的哲学”的区别、哲学活动的“处境”问题、哲学史撰作涉及的处境差距、哲学史的过去与未来导向、哲学史的主动性和进步问题、哲学史的分期和标名及种种有关的复杂性、哲学史的发展与脉络问题等等。在“分论”中,为了说明上述要目对哲学史的撰作和理解的深远影响,作者列举了西方哲学史各种最具代表性的分期和标名,以显出其中所可能涉及的种种复杂性,并作出初步的批判的反思。在“结论”中,作者带出“实质”和“虚灵”两种哲学史撰作风格的区别(前者为史实导向而后者为意义导向),并指出必须能于前者之上进一步发展后者,哲学史家才能于哲学史的撰作中取得方法上的主动和让哲学史的意义空间得到有创意的开拓。
【英文摘要】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sections.in section one,it starts with a critici of the kantian and hegelian view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which the author considers both problematic,as they rend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an intellectual undertaking which is either too trivial or too rigid.in section two,in order to secure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a more meaningful basis,a number of features pertinent to the issue were outlined,such as:kant’s own distin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in scholastic sense and in coic sense,the problem of“situation”,the discrepancies of situation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past and future orientations,the question of activeness and progress,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in periodization and nomenclature,the notion of development and of context,etc.in the third section,to exemplify how these features merit our serious attention,the various phases or periods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re discussed so that the complexities of their possible reinterpretation are exposed for critical reflection.in the last section,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brief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historiography of fact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meaning,and suggests that only by developing the latter on top of and beyond the former can a more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be attempted,so that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can become methodologically activ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matically open to innovative reflections and reinterpretations on the other.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撰作|分期|标名 the historiography of western philosophy/periodization/nomenclature
一、引论:康德与黑格尔——对哲学史的两种看法
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哲学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元素。wWW.meiword.cOm然而,哲学史到底是什么?哲学史与哲学本身有什么关系?学哲学之余为什么要学哲学史?这一连串问题是亟需回答的。要考虑这一组问题,我们可以康德和黑格尔二人的态度作为引子。查康德和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有天壤之别,但可能各有某些偏见,对他们的态度稍加分说,对我们今日考虑应如何对待哲学史,或有一定启发。
康德没有直接讨论哲学史的专著,不过在《纯粹理性批判》方篇“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一章中的立场还是非常清楚的。[1]康德基本上会把哲学史视为关于哲学的历史性知识,又认为历史知识是出于资料之给予(ex datis)而非出自理性之原则(ex principiis),是“外铄”而非“内发”,是被动而非主动。这样的知识,并不能造就一真正的哲学家(philosoph),而只可成就“学者”(gelehrte[r])[2]、“爱意见者”(philodox)[3],或康德所说的“活人石膏压模”(gipsabdruck von einem lebenden menschen)[4]。在prolegomena书中首页,康德更以讽刺的口吻说:“有些学者,以为哲学史(无论旧的或新的)本身即已是哲学了,我今天这部prolegomena并不是写给他们看的。”[5]
至于黑格尔,他对哲学史显然采一完全不同的态度。他留有三大卷的《哲学史讲演录》,对哲学史的重视,固不待言。在演讲录中,黑格尔不知是有心抑无意,竟然冲着康德讲了如下一番话:“哲学史的学习即就是哲学本身”。[6]这番话可以朝许多不同的方向诠释,不过有一点最清楚不过的,是黑格尔对哲学史的价值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应马上指出,黑格尔这番肯定并非毫无条件的,事实上,黑格尔很清楚表明,历史上的哲学理论由于受到其时代的限制,都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不过是“一些哲学意见的贮存”,或甚至是“一些愚昧见解的展列”(galerie der narrheiten)[7]。然而,黑格尔并不因此认为哲学史没有意义,相反地,黑格尔从一辩证的历史观点设想这些“意见”都是有关哲学家在他们的时代中所能察见到的“真相”,这一代一代的意见虽然都终将显出其片面性而难逃被否定的命运,但其构思与超克却扮演了精神于历史洪流中自我教育的角色……。如果我们熟习黑格尔的哲学路数,当会明白,此中所谓“精神”的“自我教育”,并非就你、或我的个人而言,而是就“绝对精神”这“大我”为了贯彻其既定的“内在目的”的自我教育而言。而同样地,“哲学史的学习即就是哲学本身”一句话所指的“哲学本身”其实是“绝对精神”本身。因此,这一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指哲学史的内在发展和绝对精神所内涵的观念世界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同意黑格尔这种想法,则我们面对着哲学史诸人物时,我们的理解、诠释乃至判断,除了由“理性的狡诈”逐步透露的识见外,在黑格尔罗列森严的系统思维下,便根本再无弹性可言了。对于不一定愿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我们,这种情况可接受吗?
总而言之,康德不大重视哲学史,是因为认为哲学史的学习过于被动,如今我们便应问,哲学史的学习真的如康德估计一般地被动吗?其次,黑格尔特别钟情于哲学史,是因为他认为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展示了绝对精神的进展的历程,则我们亦可问,哲学史各阶段的理解与评价,真的如黑格尔设想那样封闭吗?
二、通论:哲学史的撰作与哲学史家的角色
以下先就哲学及哲学史的问题作一进一步的理论,以响应上述疑问。在过程中,我将渐渐引入哲学史撰述不能避免的“分期”和“标名”问题,务求对上述疑难的解决,提供一有利的概念条件。
1.哲学的本质问题:谈哲学史当然要从哲学谈起。关于哲学这回事,康德曾作过一些很深刻的反省,其中有两项关于哲学的区分很值得注意,这两项区分着眼点不同,但却互为表里地把哲学这门“学问”的精神说得淋漓尽致。第一项区分是把哲学分为“哲学学说”(philosophem)与“哲学思虑”(philosophieren)[8]。此中,后者指的是哲学作为面对世界时种种藉以解惑的思虑活动,而前者指的则是这些思虑最终被宣之于语言文字的学说或著作。二者中,康德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活动”为主为本,而“学说”则是从是末;学习哲学若只知学说,而不解其背后的思虑活动及其处境,则很容易令学说与提出学说的活动者的生命割裂,变成舍本逐末。康德的第二项区分是把哲学大分为“学院意义的哲学”(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世界意义的哲学”(philosophia in sensu coico)。此中,前者指的哲学是于学院中被研习的一门学问,包括对既往学说的研究。康德认为这一种研习哲学的方式有助于吾人掌握哲学的概念技术,其好处就是训练吾人心智的“机巧”(geschick-lichkeit)。但是康德认为单单从事学院意义的哲学是不足够的。康德认为学哲学必须能掌握“世界意义的哲学”才算得完满。一言以蔽之,康德的意思是说哲学不应只是概念和文字游戏,而必须能响应世界,和响应吾人的存在处境中的疑惑,才会显得尊贵(in sensu eminenti);治哲学必须碰到这一层面的思虑活动,哲学才能为吾人“解惑”和教吾人“受用”(nützlichkeit)。[9]
2.“处境”作为哲学问题最基本的考虑:康德以上的分野于当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回响就是“处境”(situation)的考虑。处境就是“存在处境”(existential situation)的意思,指的正是吾人生命实践中所遭逢的,并且要面对的事态,包括个人于生活和于世界中要面对的困惑及由此而涉及的种种抉择。当代哲学对处境问题说得最透彻的,莫若海德格。他除重点讨论“处境”问题外[10],其它诸如生命的“被投掷性”(geworfenheit)等讨论都与处境的考虑息息相关。而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即触及同一问题。换言之,我们一般所谓“哲学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些verbal questions,而实乃一些real problems;因为problem一词的希腊文语根(πρóβλημα,προβλλειυ)本来就可解作“被投掷于吾人之前者”[11],故归根到底,其实也包涵了“处境”的意思。海德格于早年著作中曾说:“形而上学〔哲学〕如只被了解为一些与生命割断了的纯智的构作的话,则这意义的哲学是无力的”[12]。这番话,既上契康德精神,也下开其后的哲学基调。[13]
3.哲学史必涉及处境的差距:哲学史顾名思义地以哲学为历史描述之对象。一般历史以事实为描述对象,但哲学史描述的却非一般意义的“事实”,而是哲学家们于其独特的处境中带着一定意向性的“哲学思虑”。因此,哲学史家和其观察的对象之间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处境上的差距,这些差距可以是时代、社会、、文化上的、甚至是性别上的距离。所以,哲学史家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处境与古人的处境之间这些差距,并尽量尝试跨过此差距步步逼近其对象人物的处境以揣度其思虑中的种种意向。后世哲学家谈论先代人物时,尽量“代入”其处境,以显示其原本面目是首先要完成的使命。在这意义下,从发生的观点系统地治理前人的哲学永远有某一定的首要性,而且这一种工件是一切进一步的哲学史工夫的基础。
4.“回到处境本身”:要代入哲学史对象人物的存在处境并不容易,但绝非不可能。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家的存在处境于细节上固肯定有分歧,但大关键处却可以雷同。事实上,历来最真确的哲学问题都离不开生死爱欲等最普遍的存在处境。当代的现象学提到的“回到事物本身”,放之于哲学史的研究,可表述为“回到处境本身”。存在处境的回溯,是一切跨世代跨文化的哲学史理解与比较(乃至人际沟通和体谅一般)的最有效保证。所谓“最有效”的保证,当然并非指“绝对”的保证,因为历史资料永远无法穷尽,而观察者的偏见亦永远不能完全排除。“最有效的保证”是说在面对着无法逾越的种种处境差距的条件下就历史上的人物的哲学思虑作最大可能的逼近。
5.哲学史可以过去为导向,也可以未来为导向:要尽量客观展示前人的学问和思虑,焦点固然在于过去。但另一方面,正如一切历史撰述都不只是纯为了过去,而都可有志于未来一般,哲学史史家于追求逼近历史人物的心境之余,同样地而且同时地有权利把古代任何哲学理论置于自己的或上下古今种种不同时空的、甚至跨越文化的存在处境中反复衡量,以便从中取得教益。这一种向古人“借鉴”的哲学史工作,焦点显然在于史家观点下的未来。换言之,哲学史同时是从后世的眼光去了解前代,和是以前代的智能去启迪后世。这一两面性柏林(isaiah berlin)有一很精警的,就是“to see the past in the future and the future in the past.”[14]
6.治哲学史如何取得主动性:康德对哲学史知识的保留,是因为怕吾人只知浸淫于哲学历史事实中而失去了哲学思想应有的主动性,而沦为哲学史的“活人石膏压模”。不过康德顾虑的这种情形其实只会在吾人脱离了处境去治哲学史时才会出现。治哲学史如能做到“回到处境本身”,便已经体现了康德所谓的“世界意义的哲学”,而且使一己的处境与古人的处境乃至生命连上了关系,并从而取得了思想上的主动性。[15]正如黑格尔指出,哲学永远都是在针对当下的挑战的。透过处境的媒介,今人治古人的哲学理论时,便再不只在翻历史的故纸堆,而是在就问题和就处境与古人神交,用黑格尔的,“真正意义的哲学史,并不处理过去,而是在处理一永恒的和真确的现在”[16]。
7.哲学史是否不断在进步?黑格尔说哲学史是“蒙昧的展列”,是因为假定了世上有一绝对的真理。而他认为哲学史的发展代表了层层的进步,亦因为他以为可以用此一绝对真理作为衡量的尺度。但如果我们无法像黑格尔一般相信世上有他所指的绝对真理的话,则哲学史是否不断在进步这一讨论,便失去了其强制性。在一个“后黑格尔”的观点下,在雷同的存在处境跟前,哲学理论的价值端在乎有关理论能否对治处境中的困惑。此中,辈份高的不一定有更高的“智能”,相反地,较晚的历史阶段亦不一定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为“进步”。对哲学史稍加认识,当知后人不一定真的可从古人的智能获取教益。但无论如何,只要能对一些实在的存在处境的反省有助益者,哲学史任何方式的对比与参照都是值得的。
8.哲学史的分期与标名——“简约”原则及其利弊:一切哲学史之区分均脱不了区分者(本身往往即晚生的哲学史史家)的观点。因此,一切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和种种关于分期本身和当中各派别的标名(nomenclature)亦带有区分者视野下的色彩,包括其理论重点和价值赋给。其可能有洞见之余,亦可有偏见。[17]由于观点可以不同,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或同一位哲学家的学说可以从属于不同的分期、可以被纳入不同的派系、甚至可有不同的标名。哲学史撰作中每一个标名都甚有一种参考价值,但都可能有一定的限制。每一个标名都只能从大处点出某观察角度下的特点,都只是一些“简约”(simplification)的结果。哲学史标名的“简约”原则的最大优点是能提纲挈领、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地点明大关键的所在。哲学史的标名,就有如吾人练武或学艺时的口诀与心法一样,能以最精简的方法,传达最精要的义理。例如说,吾人把洛克的哲学标名为“表象实在论”,把巴门尼底斯标名为“逻辑一元论”,又或把黑格尔标名为“绝对观念论”亦是以最少的语言道出了颇复杂费解的道理,初学者对这些标名尽管未能实时领会,但只要据理揣摩,最终必有所得。然而,简约的代价就是必须承认其有某些限制,例如一些标名也许只反映某一种“观点”(perspectivity),和只是“相对”(relativity)于某一问题才提出。因此,在哲学史中遇到或使用一些简约的标名时,必须同时意识到此一“简约”背后涉及的种种限制。怀海特(whitehead)有一番名言:“当寻求简约,并置以怀疑”(seek simplicity and distrust it)。[18]所谓对简约置以怀疑,就是应了解简约背后覆盖了无尽的“复杂性”(complexities),而这些“复杂性”在不同观点下随时可揭示出新的面貌。
9.“简约性”背后的“复杂性”:哲学史的“复杂性”可涉及许多不同的情况:a)哲学史中标名不同的名家或传统就其理论元素而言,往往“交互渗透”(mutually diffused),因为每一位重要哲学家所受的传统冲激,都可能是多元和复杂的;b)被纳入同一分期阶段(如大陆理性主义)中的不同哲学家可以表现迥殊的形态,他们之所以被归于同一个标名之下,是相对于某一问题而已(如理性主义是相对于知识的“根源”问题);c)一旦换了另一个角度,本属“同一”标名下的各个名家随时可“各奔前程”地归入不同的“阵营”中;d)同一个历史阶段的哲学,除却标名所大致指谓的理论风格外,往往同时可包藏各种“暗涌”(undercurrents)、“逆流”(anticurrents),甚至种种边缘人物。
10.“发展”与“脉络”:黑格尔哲学带有浓厚的“思辩性”,连带地,其构思中的哲学史发展亦沾染了浓厚的内在目的性(innere zweckmssigkeit)和终极目的色彩。在今日的我们,当然很难,而且不必像他一样应允历史有任何终极目的,或坚持历史按某一内在目的在不断进步。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很有意义地运用“发展”的概念去处理哲学史问题。因为,即使撇开有没有终极目的不谈,历史还是可显出一定的“脉络”(zusammenhang,context)的。德国哲学传统所谓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与问题史(problemgeschichte)研究,[19]就是朝向哲学观念的发展脉络去设想的。正如上述,problem一词的希腊文字根πρóβλημα本解作“投掷于前”,而可引申出“当前的处境”的意思;而所谓conceptus或begriff亦可意谓吾人对处境的一些“掌握”。由此观之,概念史和问题史的作用正正是要显出不同时代哲学家在遇到同样或相类似的处境时如何运用相关的概念活动作出响应。这一种观察方式所带来的教益,正是哲学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事实上,近世许多哲学史名著,都奉此一原则为圭臬。文德尔斑的《哲学史》[20]、海姆塞特(heinz heimsoeth)的《西方形上学的六大问题》[21]等都是这一类哲学史撰作的经典例子。
11.哲学史发展脉络的实质性与虚灵性:哲学史的“发展”可以涉及跨世代甚至隔世代历史人物之间实质的传承和影响关系。这些关系如真的存在,固值得追溯和予以说明。但如果考虑到哲学史其实可以是晚生代哲学家从历史中取得教益的工具的话,则哲学史“发展”脉络之成立,根本上不须以历史人物实质的传承和影响关系为必要条件。正如说“六经皆我注脚”,在治哲学史时,一旦撇开了实质历史传承的限制,则只要有处境、问题和概念作为“绳墨”,哲学史(特别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哲学史)的所谓脉络便有了无限灵活重塑之可能,而哲学史研究的创意空间和意义深度也得以大大开拓。
三、分论: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各种分期与标名
以上的一些反省是从道理上说明哲学史作为一和哲学有关的学问于学理上的梗概。但一切学理都必须在实践中去验证,才知其是否真有效用。笔者限于识见,以下能做到的,是就西方哲学史惯用的一些分期,举其纲目,并分别就这些分期的准则和由此而订定的标名作一些反省。由于此中,每一分期下所涉及的哲学问题都可能是千头万绪,因此,笔者的“反省”也不求作一系统之处理,而只求胪列“简约”背后的“复杂”,如能因此唤起学者就问题的注意,目的便已具足。
1.古代哲学:natural philosophy?primitive science?tragic wisdom?
(1)希腊哲学乃整个西方传统的精神泉源,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古代希腊哲学”只是一笼统的称谓,希腊哲学包涵了许多不同的元素,是我们在谈论希腊哲学时必须清楚辨别的。如以学派论列,古希腊自miletus以还,前后出现过不少重要思想家,但历来许多学者(包括尼采和黑格尔)都认为在芸芸学派中,主要以“埃奥尼”(ionian)和“伊利亚”(eleatic)两股精神最有代表性。此二者就标名而言,由于基本上只是“以地为名”,表面上看本无甚么哲学意味可言。但这两个名称背后其实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取向。简约言之,埃奥尼重视世界(κóσμοs),因而力求以种种途径(包括感官掌握、理性推求等)揣度世界之秩序。而伊利亚重视的却是“存在”(ευαι),其所以如此,是因其对感官不信任,进而对充满殊相和运动的花花世界亦不信任,因此,其学说不从世界入手,而从不待于感官,和可藉纯粹思维设想的“存在”开始。这两个传统中,严格言,埃奥尼可谓代表了希腊哲学的“主轴”,因为许多就地域而言本已逾出了埃奥尼范围的学说(如毕达哥拉斯的数字学说和晚后的原子论),只要其关怀的焦点是“世界”,亦可纳入广义的埃奥尼传统之中。
(2)谈及希腊哲学一般,或代表其主轴的埃奥尼传统,学者最容易因为其重视世界、自然(φσιδ)等问题便片面地把它定性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22]。就以最早期的miletus学派为例。一般初学者往往粗略地以为学派的中心思想不外提出如“水”、(πειρου、气等“原质”(ρχ,urstoff),因此不外是一些自然哲学云云。殊不知古希腊之所谓κóσμοδ或φσιδ,其实根本不等如今日吾人熟习的和经过了“解魅”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希腊传统虽亦有把哲学家称为φυσιολóyοι的[23],但希腊人谈的“自然”是保有一定神秘性而又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然。希腊人对自然的秩序有兴趣的同时,是希望于其中同时找到人如何自处的秩序。windelband论希腊哲学史时,说sophist运动代表了希腊“人事论阶段”(anthropological period)的开始,又把希腊哲学的所谓“伦理阶段”往后推到亚里士多德,这是大大地低估了较早的所谓“宇宙论阶段”中诸位哲人对“人事”的热切关怀和其对“伦理”问题的响应。[24]
(3)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指出,miletus学派的anaximander和后来以弗所的heraclitus与其只思考“世界原质”的问题,还特别关心自然秩序问题。只不过其构思中的秩序并不只是现代科学寻求的那一中性的“律则”,而是一从果报观念(retribution,lex talionis)引生出来的宇宙公义原则。[25]而此公义原则之建立,与其只让吾人得以“认识”世界,不如说是为吾人提供了于悠悠天地之间应如何“自处”的道理——就是训勉吾人要离开对一己利害得失荣辱的执着,把自己放诸天地之间,并与天道合一。这一种理论明显地并非单纯地为认知性(cognitive)的,而更带有浓厚的规范性(normative)和指引性(prescriptive)的,而此中传达的高度的生命智能,又岂是所谓“自然哲学”一语所能表述?事实上,anaximander和heraclitus后来先后得到黑格尔、尼采、海德格等哲学家特别重视,都和这些生命智能脱不了关系。[26]
(4)要说明广义的埃奥尼传统不只是自然哲学,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可数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由于democritus首先提出了“原子”(τομοδ)一概念,一向多被标名为“原子论”(atomi)的创始人或早期的唯物论者(materialist),这些说法就方向而言当然错不了。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近代道尔顿(john dalton)提出的原子理论和继后的有关研究为准则回头去了解democritus的历史地位的话,我们很容易把 democritus的学说解释为(甚至限定为)某一意义的“原始科学”(primitive science)。这样的话,democritus哲学的真貌便会被曲解。因为,democritus提出原子学说,目的绝不只在乎“科学地”研究世界的结构。他其实是在“设想”世界万物尽管不断变化崩解,但无论怎样崩解,到了最后总有个尽头——大不了就是成为“原子”这一“不可分”((-τομοδ的字源理解)的极限,而在原子的层面,一切新的秩序乃至新的生命乃重新成为可能。从democritus留世的残篇所见,他提出原子论学说后,最主要的应用场域并不在于解释物质自然,而在于进一步以原子学说说明“心灵”,和说明心灵的种种活动,如认知、感情,乃至最重要的伦理生活。democritus哲学最终的归趋,并不在于自然世界,反在于道破生死的疑惑[27],和为吾人处事处世订定一些生活原则,如心灵的喜乐(εδαιμουη)、愉悦(εθυμα)、节制(σοφροσυη)、优雅(εκαριδ)和宽大(μεyαλοψυχη)等。[28]当然,一个像democritus一般带“唯物”色彩的理论到底是否真的能充分解释和确保以上的心灵素质或许令人生疑,但这些素质的谈论,已很清楚的说明了democritus提出原子论绝不只有志于成就所谓“自然哲学”或一些不成熟的“原始的科学”。[29]由是观之,西方出了道尔顿后,democritus的原子论并不因此而过时。
(5)至于eleatic传统,就整体影响而言,并不能和广义的ionian传统相比,但就哲学问题而言,可谓另辟蹊径。伊利亚传统由于不信任感官,只有“倚赖”纯思维,该传统最主要代表的巴门尼底斯(parmenides)就是因为在纯思考“存有”一概念时,为了避免思想矛盾(不许违背同一律),乃坚信“非有”不能存在,并进而设想“存有”不能涉及过去、未来、运动、殊多等性相(因皆涉及“非有”故),而终于逼出几近匪夷所思的那“不来、不去、不动、不多”的“太一”学说。[30]伊利亚学说于哲学史上的影响大致有两点:a)伊利亚传统极端的主张后世全然采纳者虽然罕有,但其不信任感官而侧重纯思维这一点,影响还是极为深远的,我们只消看柏拉图和后来的大陆理性主义便知此言不虚。b)由于舍“世界”而谈“存有”,伊利亚学派可视为“存有论”(ontology)的奠基者,但也正由于其存有论的建立只透过种种性质(运动、殊多等)的否定而达成,正面内容根本缺如,所以同时也是“虚无主义”(nihili)的鼻祖。[31]这一种哲学进路一方面成为后来主张要正面立说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32])首要攻伐的焦点,另一面却间接启发了求反面立说的一些理论(如negative theology),其影响绝不容低估
(6)上古希腊哲学的“断代”问题:最后要一提的是早期希腊哲学的断代与标名问题。这一时期的标名,一般多用pre-socratic一词。这个自从hermann diels的经典作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面世以来,几乎已成了典范。然而,论者多未留意,除了pre-socratic这个标名外,哲学史上还曾出现过pre-aristotelian和pre-platonic这两个用法,而这两种的倡议者,还分别是“黑格尔”和尼采二人。由于连pre-socratic在内的三种标名法都涉及一“断代”的问题,此中涉及的到底是什么准则是很耐人寻味的。首先,pre-socratic一词的断代准则可能比较“中性”和容易理解,而这一标名的订定主要的理由是以雅典的哲学为希腊哲学的大成,因而以雅典哲学的兴起为分界线。此外,由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三人有师承关系,把断代的分割线划在祖辈的苏格拉底,是最自然不过的。由此推论,pre-aristotelian和pre-platonic两种标名法的订定,内中便显然大有文章了。先说pre-aristotelian:按上述的理据,此一标名的用意很明显是要说希腊哲学的重心或高峰不单只是雅典传统一般,而直接地在于亚里斯多德个人。pre-aristotelian这一在谈论希腊科学的论述场合颇为通行,但用在哲学史讨论场合,以我所知,以阿奎那斯的一些疏解者开始[33],近世除杜威用过外[34],海德格也曾试过着墨。不过,海氏提出这一标名并不全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他因为认为黑格尔对亚里斯多德高度重视,因而说黑格尔暗地里其实在以亚里士多德为断代标准云云而已。[35]至于pre-platonic一词的标示,情况却又更不同。尼采用pre-platonic一词是因为其不忿plato曾表示要把tragic poets自城邦放逐[36]。尼采认为这是哲学坠落的开始,因此,他用pre-platonic去指谓希腊早期的哲学,就是要为这一阶段的哲学之意。[37]这一的意图,同时带出了对雅典传统的轻视和对希腊早期哲学重新评价的要求,而这一种态度,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继的学者,一如海德格,甚至其它如波柏等。[38]
(7)希腊哲学最终大成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位巨擘。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代表了希腊哲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的两次大的整合。换言之,柏氏和亚氏都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既往的传统,都几乎把发展到当时的所有哲学问题处理了一遍。在埃奥尼和伊利亚两个传统之间,总的而言,柏拉图对伊利亚传统较为同情。他虽因同时受到多种其它希腊哲学元素的均衡浸淫[39],而没有完全成为巴门尼底斯信徒,但其学说中的伊利亚色彩是无法掩饰的。相反地,亚里斯多德对伊利亚传统提出鲜明的对抗,因而可说是埃奥尼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二人基本趣向迥殊,柏氏向往一“他世界”(因而带出理想性),而亚氏则有志于“此世界”的安顿(因而显出务实性),因此二人虽然继承同一个文化传统,但取材、偏重都不同。但尽管如此,两人所用的哲学术语仍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如何厘定柏亚二人在不同问题上的真正关系乃哲学史家无止境的挑战。最后,由于柏亚两人都对继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40],如何在讨论后来哲学发展的场合里,随时适当地追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便更是哲学史家学养的最大考验。
2.中世纪哲学:medieval:scholastici?dark ages?under-currents?
(1)西方历史自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世纪这漫长的阶段[41]应如何分期和评价无论在社会史上和在哲学思想发展上都是争议极多的。这些争议导至这一时期无论于时代分割和标名上都存着多种立场和说法。其中最中性的一种标名就是“中世纪”(medieval,middle ages)。中世纪一词取意中立,是指夹在古代与后来如文艺复兴等世代中间的历史阶段,在这理解下,中世纪的最早阶段又往往与古代晚期首尾相接。[42]但是除了“中世纪”这一中性的标名外,欧洲过往曾流传过“黑暗年代”(dark ages)这一个。最早提出dark ages一标名的,正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佩克特拉(petrarch)。[43]影响所及,到了1883年出版的american cyclopedia还是把五至十五世纪千多年的历史标为“黑暗年代”,并视为可与“中世纪”等同。[44]今时今日,这个带有贬意的标名已没人敢随便使用。不过,“黑暗”这个意念,在哲学史的角度看,还是扮演着某些挥之不去的角色的。因为,尽管我们今天不再把中世纪视为“黑暗”,但只要我们对中世纪以后的历史阶段的标名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些标名潜在地和不自觉地还是在针对中世纪某一意义的“黑暗”而订立的。先说所谓“文艺复兴”,其除指失落了的古代文明的重新面世外,还带有和中古的“黑暗”告别的意味。[45]此外,再往后的“启蒙运动”(siècle de lumière,enlightenment,aufklrung)一标名中“光”(light)这一意念,明显地也是针对中世纪残余的“黑暗”(darkness,finsternis)而提出的。[46]
“光”、“暗”这对比喻,作为理论“判教”的手段,其实在古希腊时期早见端倪[47],而往后亦非只有近世的人文传统才会运用。欧洲的人文传统固常暗讽中世纪之“黑暗”,但从哲学史角度看,有一点我们不应忽略,就是自古代晚期到中纪的神学传统其实一直以“光”去指谓信仰和救赎,其目的正是要显出“尘世”和“世俗”(heiden,heathen)的“黑暗”。这一段历史,最远可追溯到奥古斯丁写“天主之城”和其后引入神学的“光启”理论(illuminatio)。由此可见,中世纪与后世孰“光”孰“暗”根本没有绝对标准可言,光、暗可说是“上帝”与“凯撒”的争持jiāo@①gé@②中双方共享的思想武器,作为今日的哲学史家,我认为还是以少用为妙。
(2)中世纪阶段,由于民族、和军事的原因,希腊罗马文明学统中断,加上宗教的禁锢,这时期的西方哲学几乎全然成了教神学的天下,这固人所共知。就内容而言,中世纪哲学包括了“教父哲学”(patristik)与“经院哲学”(scholastik)前后两个阶般。中世纪哲学整体的主要目的,就是一步一步建立教条(dogma)。单就此一目的而言,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斯二人先后为教神学奠下了重要基础。与希腊哲学的璀璨纷陈相比,中世纪哲学单就思想题材便已明显地较为逊色。不过撇开教教条的建立不谈,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酝酿或激化:如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共相论争、个体化原则、理智与意志孰为优先之争论、意义理论、自然法与制定法之争论等。而这些问题就本身而言都是意义深远的。
(3)修会传统:教文明就建制而言,长久地存在着教庭与修会的对立。所谓教庭,是指教皇、大主教、主教等权力架构,及直属这架构下的僧侣。而修会则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宗教团体。这一区分流传直到今日,仍有secular priest和regular priest的二分。中世纪最早期曾出现过许多“沙漠隐者”(desert hermits)以苦行忏悔修炼灵性,其偶有者,可说是修会的滥觞。遗风所及,到了中世纪中后期,民间不少富宗教情操者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往往主动放弃物质,以亦贫修行,由此而组成的团体最有名的是“道明会”(dominicans)和“方济会”(franciscans)。这些赤贫修会的僧人最初行动较为自由,后来才改为集中于修道院修行,不过,其坚持俭朴如一,这一种生活方式,和教庭僧众大体上的尊荣显赫,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修会传统在中世纪以后还一直在蜕变和发展,为新一代的文明带来了新的力量。总言之,中世纪的民间修会由于并不直接受命于教庭,可与宗教权力中心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相对于直属教会的僧侣而言,往往有较大的性,于思想和生活等各方面亦较为富于创意。因此修会传统往往成为中世纪和往后许多苦行者、大学问家(如abelard,duns scotus)、慈悲济世者(st.francis of assisi)、圣人(st.teresa of avila)、甚至异见者和殉道者(如giodano bruno)的温床,其对于西方文明整体的贡献是不容忽略的。[48]
(4)正统与异端:教哲学世界最饶富意味的课题,是正统与异端的对立。这课题比教庭与修会这对立鲜明得多和严峻得多。从一宗教的角度看,教所谓正统,是指一些非要捍卫不可的教义;但从一历史角度看,所谓正统教条ecclesiastical dogma,其实是不断在发展中的。教教庭建立正统的机制,主要是透过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的召开[49]。由于正统的界定不断在变,所以所谓异端,亦因时而异。例如在教早期希腊教会时期的俄利根(origen,185-254ad),其关于撒旦亦可得救赎的观念在几百年后肯定被视为异端,但当时连第一届大公会议还未召开,所以并未构成异端罪。但后他百几年的伯拉纠(pelagius,354-418?ad)便远远没有他那样幸运。查伯拉纠乃与奥古斯丁同代的一位不列巅籍,他虽只一介修士,却以虔敬自律而深具人望,甚至对教会中人亦起了影响。他提出一些神学思想,都是革命性的:如不相信原罪,认为救赎不应以受浸为条件,主张救赎可由人自身的向善达成,和甚至认为所谓救赎根本不是叫人从死里复活,而是让人的心灵提升到一更高的精神层次。伯拉纠的学说虽极具争议,但教会最初并不取全然反对的立场,但后来奥古斯丁插手予以大力挞伐,终导至其学说于几个地区会议中被定为异端,和于431ad于以弗所举行的第三届大公会议上被教会严厉谴责。试想伯拉纠的学说如果得以流传,教教义日后的发展肯定大大不同。伯拉纠被定性为异端,与后来“教会以外无救赎”(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一教条的订立大有关系。这条一直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准则,终于在二十世纪唯一的一次大公会议(vatican ⅱ)上被一定程度上放宽[50],委实令人既鼓舞又慨叹。
(5)不过,历史上教正统与异端对立最有趣和最讽刺的现象莫过于马丁?路德。出身自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马丁?路德其实的确是奥古斯丁彻底的信徒。路德正因为坚信“教会以外无救赎”、“因信称义”等“正统”教条而对当时教会颁行“赎罪券”(indulgences)不满,因而激发了宗教改革的滔天巨浪。但本来出师有名的路德却马上被评定为“异端”,并被逐出教会。
(6)总的而言,教世界的异端许多都是从内部酝酿的,根本上是教的一连串的内部反省,在一定限度内,这些异端都非常富于创意,都起着冲击基本教义的作用。教教庭仗着其无上权力(如逐出教会、收监、酷刑、异端审判、处决等),一般都可以轻易把这些异端铲除,但在岁月悠悠之下,过往的异端,未尝不会对后世的正统产生影响。[51]教的正统与异端的对立,可说是一场不平等的角力。
(7)中心与边沿: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欧洲古代文明失传,而此期间负起保持西方古文明血脉的,主要其实是诸国。在公元九至十二世纪之间,保存和论述西方古代文明(包括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三大重镇,都不在教世界,而是世界中的开罗(cairo)、哥多巴(cordoba)和今日饱受美国战火蹂躏的巴格达(baghdad)。在这一意义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哲学谁是中心,谁是边沿,有时真很难定夺。
(8)历史中的教与生命中的教: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曾指出说“哲学出了错误,大不了造成愚昧,但宗教一旦出错,却可以很危险”[52]。历史中的教曾犯过许多错误虽是事实,但这不能抹煞教(一如任何宗教)作为人类追求神圣、追求永恒慰藉所作的贡献。中古教撇开不断求建立教条和捍卫正统等活动外,还是存在着许多于追求灵性方面造诣非凡的人物的。哲学虽然重视理性而别于宗教的重视信仰,但只要我们不要闭塞至成为“唯理”主义者,和明白理性本身亦有其限制,则中世纪许多世外人物发自生命,出于至诚的思想,对更广义的哲学还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3.文艺复兴作为现代的前奏
(1)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基本上只是一比喻,取的是法文的“再生”的意思。它没有很确实的年代,严格而言,是中世纪向现代的一个过渡时期。今日一般史家和哲学史家谈到“文艺复兴”,指的都是十四、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而大成于十六世纪的一个文化运动。许多学者拘于以为文艺复兴的“再生”指的只不外是已湮没多年的希腊罗马学术的再现,这见解是颇为片面的。因为在严格的历史观点下,我们应指出其实早在italian renaissance好几百年以前的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欧洲各地其实早已经历了好几波的古希腊罗马学术“复兴”浪潮。[53]因此,单纯的古学振兴运动并不足以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本质揭示。除了继续发展学术外,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反面上代表了对中世纪神权的反抗,在正面则代表了对人自身的活动与价值的重新肯定[54],就这一带浓厚人文色彩的大取向而言,文艺复兴的精神其实直通到更后来的启蒙运动。当然地,启蒙运动比起文艺复兴更重视科学、进步和开明等理念。
(2)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由于涉及对中世纪神权的反抗,所以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时间上相距不远,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进行的。
(3)humani?传统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理解,认为除了一些外在的特质(如希罗学问的恢复、希腊艺术风格的重振等)外、在精神层面看,最主要的特点其实是其“人文主义”(humani)的色彩。“人文主义”一词,其实涉及许多可能意思。著名学者kristeller便常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humani其实只就当时研习humanities这一风尚而言,而与近世所谓人文主义有别。[55]不过,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说法,我们还是不能忽略,humanities这个概念本身除了本就从“人”导出外,当时的所谓humanities都是涉及如语言、历史和道德伦理等人类社群活动,而其传习亦以“人格”的培育为目的。此外,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经过神权漫长的压抑后对人自身地位的醒觉,和由这一种醒觉而带来的一股殷切的求变的意愿,毕竟是无法抹煞的。[56]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了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话,则其与“现代”的关系便更清楚了。因为所谓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也正好在于笛卡儿以降的“自我的发现”和由此而衍生的“主体性哲学”传统。由此可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理念下的人文主义还是一脉相承的。
(4)所谓人文主义,论者一向大多持一正面肯定的态度。不过这一情况自海德格以来便有了很大的改变。海德格的一篇极有名的文章标题正是《人文主义书简》。文中,他一反传统对humani无条件地肯定的态度,而认为humani潜在地其实是把人推到了万事万物的中心,换言之是某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57]
(5)海德格对humani的批评并非只冲着文艺复兴运动而提出,其实是同时针对了后来的启蒙运动和作为现代哲学主轴的“主体性哲学”,特别是沙特的“存在主义”,但考虑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现代文明潜在的关系,这些批评未尝不也令吾人对文艺复兴整个理念要加深反省。海德格毕生各种著作中,对主体性哲学传统可谓挞伐有加,他最主要的指责,就是主体性哲学传统要把人标榜为天地万法的“关系中心”(bezugitte),俨然要把人的地位“神化”。海德格的指责从文献上初步地观察,未尝没有道理。君不见被目为“first modern man”的笛卡儿岂不真的曾扬言要让人成为“自然的主宰与拥有者”吗?[58]
(6)海德格虽然对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能力过份高估存有很大的戒心,但这并不表示他不明白人在芸芸存在中确实有某一种独特地位。因此,如何能把人于存在中的独特性标明,而又避免把人的地位过分彰显,便成了海德格思想的一项主要课题。他在《存在与时间》书中谓人的特点在于“存在理解”,他在上述《人文主义书简》中他提出“人是存在的牧者”(der mensch ist der hirt des seins),提出“语言乃存在的屋宇,是世人之安宅”,和后来常谈及的“偏心圆”(ekzentrisch)概念等理论,都是对有关问题的响应。话说回头,文艺复兴于精神上与“现代”同气连枝固如上述。从哲学史的观点看,我们对与其直接相关的人文主义应作如何评价便成了一个极度重要的问题了。海德格固看到自文艺复兴到现代这大传统的某一些历史症结,并提出了某一些响应,但是否必须如他建议一般处理,是大有商榷余地的。总的而言,我认为海德格认为主体性哲学对现代危机要负上责任一议虽有一定道理,但批评却到了过当的地步。因为海德格的批评实低估了主体的许多正面功能(认知的和非认知的)。主体的过度“自我膨胀”固然不当,但主体的全然退隐同样会带来文明的另一些危机。[59]
(7)“东方文艺复兴”问题:最广义的“文艺复兴”,最远除了可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数百年如carolingian renaissance等时代外,最晚还引出一项鲜为人知的“余韵”,就是所谓的“东方文艺复兴”(oriental renaissance)的问题。查oriental renaissance一概念,最早乃于十九世纪初由德国浪漫派文人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提出,其所指的是古代东方(特别指古印度)文明于欧洲的“再生”。而friedrich von schlegel与乃兄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正都是把梵文和古印度文明引入德国的主要代表。就时代而言,oriental renaissance其实是欧洲文化经历了以理性为主导的“启蒙运动”阶段之后的一股“逆流”[60],因为就理路而言,其所指的乃是西方“理性”高度膨胀后以古代东方智能的发现作为一种抗衡,而这与中世纪神权禁锢一切后西方人以古代希腊文明的再造作为一种抗衡可谓如出一辙。平心而论,所谓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其在欧洲发展之初,本来只代表欧洲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运动。而自省的契机就是透过东方远古不同的价值观和另类的生命态度的对比,以便对西方当时经过了启蒙运动以后日益注重理性和追求进步的文化作出重审与重估。在这一意义下,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和下文将会提及的“反启蒙”实在极有渊源。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东方文艺复兴本来是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一步。不过,自1979年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一书[61]面世后,欧洲人这一本是文化反省性的运动完全被“化”地了解,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兴趣被诠释的西方对东方“权力化”和“对象化”的一些针对性行为,换言之,东方的理念反而被诠释为西方中心论世界观下的“他者”。said的学说面世至今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其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毁誉两方,可谓旗鼓相当。我们在这一篇文章虽然无法深入评论,但“东方主义”的评价的论争,起码再一次清楚地印证了哲学史问题的复杂。
4.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reformation vs.counter-reformation
(1)宗教改革是教经千年以来的教条化以后自内部产生的一些反抗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在十六世纪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wittenberg教堂门外钉上批评教会时弊的95条开始,后来很快漫延至法国的喀尔文(jean calvin,1509-1546),和瑞士的兹文力(zwingli)[67条]他们除对各种“圣事”(sacraments)重新解释外,更勇敢地起来另行建立教会。
(2)所谓counter-reformation,一般直译作“反宗教改革”,这严格而言实有一点语病。因为其所指的,是天主教受到了新教于各地兴起的严峻挑战后,认识到教内的确长久存在着弊端,因而求自行改革整顿的运动。所以这一股“逆流”亦可称为“天主教改革运动”(catholic reformation)。而承担此重任的,除了教宗自身(自保禄三世pope paul ⅲ起)外,最主要的便是由伊纳爵罗约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创办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包括立志到异邦传教的耶稣会修士圣方济各(st.francis xavier,1506-1552)〕,还有由圣德勒撒重振的迦密会(carmelites)等推动。他们对教会的主要贡献除了努力传教外,就是以身作则留下了极富于宗教情操的言行。
(3)counter-reformation作为几乎与reformation同步进行的运动,固乃为势所逼。但其影响却如细水长流般从十五、六世纪一直伸延到当代。近世最开明的一位教宗约望二十三世(john xxⅲ)便是这运动近世的一位健者。而他于一九六二年举办梵蒂冈第二号大公会议的基本目的,亦正是要对天主教仍存在争议的一些教义寻求修正或合理折衷之可能。约望二十三世为vatican ⅱ指派了当年才三十四岁,进铎才不过七年的hans küng为大会官方顾问,可说把counter-reformation推向了新的高峰。不过küng后来和karl rahner同被现任的教宗约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ⅱ)严词谴责并公开褫夺其代表教会向公众的权利(missio canonica),俨如被驱逐出教,这又一次印证了counter-reformation运动的反复[62]。
5.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rationali-empirici:
(1)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就地域上被英伦海峡截然二分,哲学史一般为双方各列出人物:分别是理性主义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和经验主义的洛克、柏克莱和休谟。就时序而言,双方的代表人物此起彼落,其于派内固有一定传承关系,而跨派之间亦有交互冲激,如笛卡儿之影响洛克,和洛克之影响莱布尼兹。
(2)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标名骤看之下,似乎没甚么关连,但这只是错觉。事实上虽然理性和经验表面上是两个概念,但其实都是“相对”于同一个哲学问题而表现的两种立场——即人类真确知识最原初的根据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在对这一涉及认识基础的主导问题作响应时,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即分道扬镳,前者主张知识的基础在纯粹的概念思维,而后者则主张在感官的给予。这一区分准则间接地反映了一项事实,就是“知识”或更严格言的“认知”问题乃是这一个时期欧洲哲学整体而言的主干线。
(3)离开知识问题的场合,“理性”与“经验”两个标名便再不一定适用了。例如理性主义者的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其实参与了许多经验科学的研究,而洛克谈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休谟在谈有如同情等人类情感(passions)时都渗入了许多经验主义原则并不容许的理论元素。由此可见,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标名的确只在知识论的场合适用,一旦离开这一主线,其理论意义立即变得模糊。这正是上述所谓“简约”必有其限制的最好例子。
(4)由于两派六位哲学家其实并非只在处理知识论问题,所以除了就认知问题他们分别体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代表性的立场外,六位哲学家个别而言的哲学兴趣其实各有各的姿彩,连带其表现的哲学风格亦属迥殊。如洛克和莱布尼兹之同热心于,笛卡儿和莱布尼兹之精于数学与科研,柏克莱之献身于宗教、经济和教育,休谟之兼爱治史与宗教批判等。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宾诺莎。对像他一般的智者(sage)而言[63],认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才是哲学最为吃紧之处,而一般意义的知识论问题对他来说根本只属末节!总的而言,这六位哲学家撇开作为二派的主要代表之余,基于其个别风格,每一位都另有其足以传世的特点。对他们作研究时,都不应被“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等简约的标名限囿。
(5)康德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吸取了一定养分,但对孤立而言的二者都不同意。其对二者的批评可谓“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理性主义失诸独断(dogmatius),经验主义却失诸怀疑(skeptizius)。康德最精警的批评,是指莱布尼兹把世界“理智化”(intellektualisiert)的同时经验主义者则把世界“感官化”(sensualisert)。[64]对康德来说,独断主义的毛病在于过于漠视世界的感性面相,只一厢情愿以为只要努力去一些概念的内容(如上帝的完美性)即可对世界的真相作出明确的断定;而怀疑主义的毛病则在于一方面以为人类本颇为复杂的知识可尽数由最简单的感官材料构成,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无法据经验原则充分解释复杂的知识如何可自简单的感官与料导出,因而陷入对世界整体的意义的理解危机。康德这一种“平议”各家学说的识见,终于促使他对人类知识得以构成的各种成素(elemente)作全面的重审或“批判”,并因而成为开创一的思想家。
(6)尽管就关键的知识论问题而言,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似乎被康德学说完全超越了,但哲学史里似乎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因为在全幅的考虑下,理性、经验两传统各家对哲学不同方面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如笛卡儿对人的主体自我的重新发现,斯宾诺莎跨越世代的生命智能,莱布尼兹对整个观念论传统后续发展的启发[65],洛克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的巨大影响,柏克莱对英国常识哲学的建立,和休谟一方面的经验立场对康德的冲击,和其另一方面的情感学说对德国神秘浪漫传统的影响等。[66]
6.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vs.counter-enlightenment
(1)启蒙运动是现代欧洲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学科的,而且发展悠长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欧洲各民族的步履不一。一般而言,可以追溯到笛卡儿。但作为一有力的文化运动而言首先可数十七世纪英国洛克(john locke)及他的上的伙伴lord shaftury等,然后十八世纪由法国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接力,在德国则有莱布尼兹、吴尔夫,甚至是康德(虽然存在着争议)等追随。
(2)启蒙的基本理念:由于牵涉太广,启蒙运动各家理论重点并不全一致,不过大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一些方向:如对宗教的排拒、理智力量的强调、对科学的重视、对知识客观性的信念,对开明的诉求(enlightened despoti)、个体自由成了不可侵犯,个人和社群幸福的追求成了天经地义,和对上述种种新秩序之将为人类带来进步的向往〔甚至必须时要透过革命去达成〕。如此澎湃的新秩序观念,成为一代一代欧洲人努力的方向,其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缔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反启蒙之暗涌:谈现代哲学史,乃至谈一般思想史时,启蒙运动固然是一重要焦点,然而学者认识启蒙者多,但至于所谓“反启蒙运动”,谈论者却甚少。其实,正如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几乎像一对兄弟一般,启蒙运动萌生未几,一股反启蒙的“暗涌”便如影随形般接踵而至。而前者不断扩展的同时,后者也亦步亦趋地发展。如果我们把理性主义的笛卡儿算作启蒙运动的“远祖”的话,则后笛卡儿不过几十年的巴斯噶(blaise pascal)便可说是反启蒙的尖兵。巴斯噶很清楚看到人的理性虽然重要,但却非一切。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话分别是:“心灵自有其理路,是理性所不知晓”[67],和“我们认识真理,并不只靠理性,还有赖心灵”[68]。为了要与笛卡儿的理性逻辑相对扬,更提出了有名的“心的逻辑”(logique du coeur)。在与权力向现代性的发展方面,edmund burke经过对法国革命的反省,提出了有名的伤感与怀古的论调:“骑士精神的世代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而欧洲的光辉将从此湮灭。”[69]。反启蒙阵营中后来出了意大利的维柯(g.vico),德国的哈曼(j.g.hamann)和赫尔德(j.g.herder),乃至于后来十九世纪的浪漫派思想家,都加入这一反对阵营。这些反启蒙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包括“理性”之普遍)作出正面的挑战,他们重申感情之重要,并认为诗的想象语言比理性的哲学语言更能逼近自然的奥秘。如此的一个强大的与哲学理性抗争的传统,尼采首先提出“反启蒙运动”(gegen-aufkrung,counter-enlightenment)此一标名[70],以志其梗概。后来名思想史家柏林即据此一标名写了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并作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结集成《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一书[71]。到了今日,counter-enlightenment已成为哲学界所不能不正视的课题。柏林的研究最有趣之处,是在《反潮流》书中除了重点讨论如vico,herder等公认的反对派之外,还把好几位一般人认为应纳入启蒙阵营的人物,都就其某些较为被人忽视的理论元素而认为对“反启蒙”思想有贡献——包括尊重多元主义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强调passion而甚至影响了哈曼的休谟等。至于卢梭(j.j.rousseau),柏林虽未有于书中专章处理,但言下亦有此意,此一论断在晚近的研究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认可。[72]
(4)但启蒙运动是否真有如反启蒙浪潮所指一般只知强调理性而把人类其它素质(如感情、信仰等)完全忽略和轻视,给人“cold rational enlightenment”[73]的印象呢?就这一问题卡西勒著《启蒙运动哲学》(philosophie der aufklrung)一书即力图为启蒙运动作全面的。他基本的想法是认为后世对启蒙运动构成“浮浅的理性主义”的印象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启蒙主义阵营中有像霍尔(d’holbach)和拉密特(la mettrie)等过于极端的份子,的确会带来这一负面的印象,另一原因他认为是十九世纪的浪漫派等反对者对启蒙理念的肆意曲解。卡西勒因此力图指出大多数出色的启蒙主义者(包括鲍加登、莱辛、康德等)并不如浪漫派所指一般忽视理性以外的元素。卡西勒为启蒙主义的意图和今日哈贝玛斯(habermas)的哲学纲领显然有很深的渊源。
(5)总的来说,卡西勒为启蒙运动的虽有一点道理,但如因此以为可以完全开脱历来对启蒙理性的批评,又似乎过于乐观。例如柏林(isaiah berlin)为卡西勒《启蒙运动哲学》一书写书评时,即以如下一语相讽:“对卡西勒教授而言,人类思想的历史几乎快乐得不带半点阴霾,特别自文艺复兴以还者……”。柏林对所谓启蒙理性“不乐观”的态度,可谓溢于言表。[74]
(6)从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而产生的最“复杂”的哲学问题,就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哈贝玛斯提出的所谓“未完成方案”(unvollendetes projekt,incomplete project)的讨论。[75]哈贝玛斯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要在当代对启蒙理性普遍表示失望的氛围下,挺身指出尽管启蒙时代理性确曾有“主体中心”和“过份乐观”的毛病,但与其因此而只知缅怀前现代的美好日子(old conservatives),或只知推崇一与人文割裂的科技文化(neo-conservatives),又或干脆全面否定理性和全面现代或启蒙的理念和以种种其它理念(如权力意志、存在、带狂醉意味的诗意)(young conservatives)作为取代,倒不如设想启蒙乃一仍未完成和乃有待改善的文化方案。哈贝玛斯后来提出的沟通理性理论,就是循这一方向继续发展出来的。无论我们同意哈贝玛斯的方案与否,“未完成方案”的讨论起码可在当代哲学种种对理性和对哲学不信任的迷思之中指出了一些解惑之途。
(7)循着同一方向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十九世纪的意志学说、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和今日对整个西方学界影响至巨的后现代思潮,都未尝不是“反启蒙运动”的延续。而作为与“启蒙”孪生的“反启蒙”,与其真的是启蒙的全面否定,不如说是对启蒙理性的修正,而修正的主要渠道,就是对理性的效力的批判和对理性与人类其它能力的关系的重新界定。事实上,哈贝玛斯所谓的“未完成方案”,与其是十八世纪较狭隘的理性(如condorcet所持者)的全面,又何尝不是对理性问题的一批判性的重估。[76]
(8)回到哲学史的向度观察,哈贝玛斯提出启蒙理性涉及“未完成”一面的议题,其实在康德哲学中早已种有根苗。首先,康德虽然强调理性,但却绝非一只知宣扬“启蒙理性”底光明面的理性主义者,相反地,他是一理性对其自身效力的“批判主义”者。此外,在〈何谓启蒙?〉一短论中,康德即清楚地指出,“启蒙世代”(zeitalter der aufklrung)恰好并非一“已启蒙的世代”(aufgeklrtes zeitalter)[77];当然,康德作这区别的目的是要点出启蒙的主要精神在于人类理性摆脱种种如宗教、等蒙昧枷锁所表现的自由,但就历史发展中人类理性还要面对种种说不尽的挑战这一点而言,启蒙说不定只能以一“未完成”的身份才可体现其内在价值。
7.康德的批判主义的历史定位(the kantian doctrine)
(1)康德哲学的标名:从哲学史的观点看,谈康德哲学最棘手的问题,是其同时拥有许多不同的标名。是知识论?超验哲学?批判哲学?还是哲学人类学。这些标名都可从康德的学说中找到一定根据,其中的超验哲学和批判哲学甚至是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在诸帆并举的情况下,哪一个称谓才最能代表康德,委实费煞思量。首先,康德最重要的经典作《纯粹理性批判》(特别前半部)的确涉及某一意义下的知识论问题,后来新康德学派中的马堡学派由于重点主要放在这一部份的论述,所以较倾向于把康德视为“知识论者”,但西南学派和后来如海德格等学者大力反对这种看法,就是怕这样会把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理解得太狭隘。事实上,即使把康德哲学视为“知识论”,我们亦似应辨别我们是以完全对象意义的“知识”(erkenntnis),还是其实是以人的“认知”(erkennen)为圭臬。如果我们懂得这样考虑,便能领略康德所谓“超验哲学”的意义了。因为超验哲学的许多解释中,最重要的一点正是就人类认知“能力”中的一些对感性杂多有塑造功能的成素(elemente)而言的。[78]这意义的超验哲学康德有时干脆唤作“对理解能力的解剖”[79]。至于“批判哲学”,康德很清楚地指出“并非为了建立或一些系统……而乃在乎人类理性能力的探讨”[80]。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人类理性对自身的反省的“批判哲学”,其与“超验哲学”在学理上互为表里,都是某一意义地以人的活动为本。至于“哲学人类学”一标名,从康德在《逻辑学讲义》及予书信中特别列出其哲学的第四条问题“人是什么?”一点而言,委实是出师有由的一种。[81]总而言之,把康德界定为“知识论者”可谓最无新意,也最为片面;而“哲学人类学”一说涵义最广,也存在着最阔的诠释空间,但由于内中涉及的复杂性委实太多,如不加以限定,又很易与其它以“人”为对象的学问混淆,所以就算使用,也必须步步为营。
(2)康德哲学的断代性格及其历史地位:康德以一人之寡,竟然独领,奠定了一个时代。不过,更应注意的,是康德哲学自面世之后,慢慢更成为了断代的标准,而康德所谓“断代”,还包涵了两重意义:首先是康德本人成为了西方哲学的分水岭,即有所谓pre-kantian和post-kantian的区别;其次,就康德哲学发展而言,人们已习惯了把“第一批判”的出版视为康德哲学内部的分水岭,即所谓pre-critical与post-critical的分别(康德全集首二卷即命名为vorkritische schriften)。这现象在哲学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显示了康德哲学在西方整体而言不可取代的地位,也显出了“批判哲学”作为康德哲学的标名,在康德哲学的整体发展中,可能还是最关键的。
(3)康德哲学在现代哲学史中的“特殊地位”(sonderstellung)。从哲学史分期的角度看,康德既是现代哲学的佼佼者,又可算是启蒙运动的殿军,复是所谓主体性哲学传统最主要的代表。然而,我一向认为,康德哲学在西方现代哲学整个发展中保有一很特殊的地位。此中所谓“特殊地位”(sonderstellung),并不指康德哲学有甚么特别尊贵或了不起的地方,而是指其能“不落俗套”地超越了时代重重的樊篱。具体地说,康德虽厕身于现代,但其“现代性格”却不太浓厚;其虽然深受启蒙运动影响,但对启蒙的精神却已能保持一定距离地作极深刻的反省;他虽然也谈论主体,但对主体的地位却不至于像主体性这一大传统的其它人物一样估计过高。其所以如此,全因为康德对人底有限性深深契认,并予以严格恪守。因此,在“反启蒙”、“后现代”、乃至“反主体”(海德格)相继盛行的今天,康德哲学仍保留其某一种“超然”的地位。
8.“德意志观念论”分期的多种可能:versions of“german ideali”:
(1)运动的多种界说。在现代哲学史中,德意志观念论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页。不过,作为一哲学运动而言,德意志观念论的范围向来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设想。最窄的一种理解是指自费希特、经谢林到黑格尔三人在短短几十年内的哲学发展,这一种主要把德意志观念论了解为“后康德”的一些“绝对观念(唯心)论”[82]。但这种今日已较少采纳,取而代之是以较为宽松的尺度,把康德也算作德意志观念论其中一员。这一种看法主要的用心是认识到费、谢、黑三人的哲学和康德渊源太深,不从康德说起难以窥运动之全豹。不过,学者尽管把康德纳入德意志观念之中,但一般对康德与后来三位哲学家的基本分别(如其超验观念论之异于绝对观念论)仍抱持高度戒心。[83]除了上述两种了解外,亦有论者把歌德和novalis,schelgel等德国浪漫主义者(特别是贺德林)也算到运动之列,为的当然是要把德意志观念论的复杂性尽量显出。
(2)mahnke的理解:从“分期”和“标名”的角度看,我认为关于德意志观念论最与众不同,而且最意义深远的,要首推dietrich mahnke[84]。mahnke独排众议,认为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才是德意志观念论的三位巨人[85]。mahnke显然认为莱布尼兹于哲学史上的地位被过于低估。他的主要着眼点是要说明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是德国系统哲学从萌芽定向,经自我检讨,到克服困难和全面开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从系统综合的兴趣上看,mahnke认为莱布尼兹接近黑格尔远多于康德,只不过其综合的方式不同而已。mahnke把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的综合比况为“和声的统一”和“旋律的统一”,并指前者为一些静态的调和之时,后者为一动力的辩证云云。
(3)“力”与“观点”:透过mahnke的启发,我们不难发见,即使我们不全跟随他的路数,莱布尼兹作为最广义而言的德意志观念论者,甚至是其奠基者这一构思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86]从这一角度切入,我们不难发现莱布尼兹除了作为“理性主义”者外的许多重要哲学贡献(philosophical legacy)。如要举例子,只须看“力”和“观点”二概念的提出,即足以见其后果之巨。查“力”(la force,conatus,kraft)一概念,是莱布尼兹用以说明substance〔或“单子”〕而提出的[87]。透过力的设想,莱布尼兹不单解析了物理世界,还为后来强调spontaneity原则的主体性哲学留下火种。后来康德的“能力”(vermgen)学说,以至胡塞尔的主体理论都和莱布尼兹的“力”脱不了关系。至于“观点”(point de vue)一概念,更开启了德国哲学关于认知涉及观察角度的反省[88]。“观点”概念是莱布尼兹用以说明心灵实体作为一“形而上的点”(metaphysical point)或作为一观察者时必须自一独一的角度去表象世界。[89],莱布尼兹的“观点”概念是“界域”概念(horizont)的滥觞,因为界域的界定正有赖观点。界域概念经过了康德的酝酿,终于在胡塞尔、海德格和葛德玛的哲学中大放异彩。[90]这么算起来,莱布尼兹的“观点”连同日后的“界域”甚至可以说是德国哲学的第一号“运作概念”(operational concept)。[91]
(4)一般理解下的德意志观念论(fichte-schelling-hegel)与mahnke理解下的德意志观念论比较之下,便有如几着招式刁钻的散手和一套大开大阖的拳套的分别。就“德意志观念论”这一标名而言,愈是狭窄的分期愈是把焦点集中于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之上,愈宽松的分期则愈能带出德国哲学传统整体的关怀——人类心灵的自觉活动及由此活动所缔建的层层界域。我们似不能忽略,“德意志观念”归根到底而言其实是“德国”的“观念论”的意思。总的来说,莱布尼兹除了总结了理性主义这一“跨民族”的“小传统”外,其实还下开了整个德国哲学的“大传统”其影响不单贯串了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甚至直通于二十世纪的现象学。难怪胡塞尔给mahnke写信时,竟曾说其现象学乃“德国哲学乃至德意志观念论的真正终极目的所在”。[92]作为当代“界域”理论的代言人,胡塞尔这番话可谓意义深重。
(5)humboldt作为德意志观念论的别支:一向讨论德意志观念论的,尽管就其起源问题可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其终结于黑格尔,从来很少异议。但我近年渐有一种想法,就是德意志观念论自莱布尼兹、康德发展下来,可以于黑格尔高度思辩性的哲学以外找到很不同的归结,而洪堡特的语言哲学就是最好的例子。洪堡特哲学与黑格尔几乎是同期,因此也继承了同一个德意志传统[93],但洪堡特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不采纳思辩性的进路,而是纯然从表面看来最简单、最“物质性”的基础入手,即可说明“精神”如何发挥其内在的活力,以“有限资源,作无穷运用”(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ans),一步一步地缔建出最丰富的意义世界[94]。而这个“物质”基础,就是[95]。透过乔姆斯基(chomsky)这一桥梁,洪堡特这一种“非黑格尔”的“德意志观念论”结果成为了二十世纪英美与欧陆哲学的一个极重要的接合点。 四、结论:实质和虚灵之间
总的说,哲学史的分期及与其有关的标名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史各重要阶段和各焦点人物的理论特征。但一切分期与标名都只可以“权宜”地采用,因为,愈是通行、愈是普及的分期与标别,愈可能是吾人思想的障碍物与陷阱。哲学史撰作,就客观的任务而言,除了要逼近历史人物哲学思虑的实况外,还应包括历史脉络的建立。但脉络除了可从实质一面去揣度外,还可以从虚灵处着笔。实质的哲学史和虚灵的哲学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虚灵”一词是很容易令人误解的,而一个最大可能的误解,就是以为“虚灵”就是“虚构”。此中,“虚构”之所以是一种误解,主要因为我们潜意识地以为有一“实在”的哲学史脉络作为一绝对标准,而大凡不符这标准的便是不同程度的虚构云云。中外学界,向来关于哲学史分期等问题多有争议,其中泰半是“实在”和“虚构”之争。然而,在经过康德思想洗礼后,我们对哲学史的脉络问题,和由此引申出的分期和标名问题,其实可以有一新的判断——正如康德以后吾人再不能妄谈“物自身”一样,今日我们谈哲学史时亦不能先认定有所谓绝对的“哲学史自身”(philosophiegeschichte an sich)可供吾人用作绳墨;因为说到底,哲学史永远是吾人自某一晚生世代,据某一观点,和循某一兴趣理解下的哲学史而已。在这一种理解下,本文一直沿用的“实质”和“虚灵”二词的准确意义便脱颖而出。
所谓“实质”哲学史,指的是循一些可经验地追溯的历史自然顺序(如师承、友侪、学派等影响)而建立的思想脉络。这一“实质”的哲学史在建立之际,便必已涉及分期和标名等问题,而为求“提纲挈领”和眉目清楚,吾人固可提出一些足以表征时代的术语,作为历史作“断代”的说明,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实质”并不能绝对化成为“实在”,我们要有接受不同程度的挑战的准备。如只知墨守于某一种自以为绝对的说法,则自己要承受“理执”之苦之余,只会堵塞了自己和他人对哲学史脉络加深体会的机缘。
同样地,“虚灵”并不能曲解为“虚构的实在”。因为虚灵并非无中生有的杜撰,而是哲学史种种实质的元素之间的一些自由而灵动的关联与组合,此中,虚灵的关联与组合虽有高度的自由,但并不是任意和无章法的。在没有实质历史脉络的直接支持下,虚灵的哲学史的脉络关系必须以观察者生命处境为经纬,和以问题概念为绳墨,其意义才不会落空。虚灵哲学史最引人入胜的,是其可随机而发,和有无穷的重塑可能。虚灵的哲学史再没有对错的问题,而只有有意义抑无意义的问题。虚灵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定非要违背实质哲学史不可的。实质哲学史是学习哲学之必备,但其只能算是哲学底不可缺少的“初阶”。真正有深度的哲学史,必须要或多或少涉足于“虚灵”的领域,因为只有这样,哲学史才能真正摆脱单纯的“历史学”的窠臼,让“哲学史”真的成为“哲学的”历史。
康德本人过于轻视哲学史是以为哲学史工作过于被动,黑格尔高度重视哲学史是以为哲学史印证了绝对精神的轨迹。从我们上面的,哲学史未必像康德设想一般被动,也未必像黑格尔设想那样封闭。我们的显出,只要扣紧存在处境,哲学史便可取得主动性,只要不妄言哲学有甚么绝对真理,哲学史便可以享有高度的开放性。而所谓的虚灵哲学史,无疑是哲学史家乃至哲学家争取主动与开放的最好出路。
【参考文献】
[1]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kdrv),a835-837/b863-865.
[2]kant,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kgs),band ⅶ,p.138,280.
[3]kant,logik,kgs,band ⅸ,p.24-25;kdrv,bxxxvii.
[4]kant,kdrv,a836/b864.
[5]kant,prolegomena…,kgs,band iv,p.255.
[6]hegel,vorlesungen ue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uhrkamp-werke,band 18,p.49.
[7]hegel,ibid.,p.29.
[8]康德的区分主要是标示哲学除一般当作一学习对象的哲学(名词),更有作为活动义的一面。此中,重点当然放在philosophieren这一动名词之上,philosophieren(philosophiren)一词康德使用得极为广泛(主要著作中凡43起),后来黑格尔用得更多,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德国学界灵活运用。至于philosophem一词固然是指哲学活动的果实解(一若自theorize一动词可引出theorem一名词),就使用而言,康德只用过一次,但其所指极为明确,至于后来黑格尔则用得多许多。
[9]有关这问题的讨论,详见拙文:〈康德论哲学的本质〉,《从哲学的观点看》。(台北:东大,1994),页1-21。
[10]heidegger,sein und zeit,12.unvernderte auflage(tübingen:niemeyer,1972),p.299ff.
[11]有关讨论,参见关子尹;《从哲学的观点看》,页58-59。
[12]heidegger,die kategorien-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in frühe schriften,(frankfurt/main:klostermann,1972),p.352.
[13]哲学探究不可离开“处境”(situation)这一点,几乎是今日哲学的共法。就这一问题曾作标题化讨论的,较重要的代表是karl jaspers,见jaspers,philosophy,vol.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p.43ff.
[14]参见isaiah berlin,review of cassirer’s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transl.by koelnn and pettegrove(princeton/lond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269,(1953),pp.617-619.
[15]今人robert piercey便提出哲学史对古人的理解可以是一些他所谓的“主动的模仿”(active mimesis),他并以此一观念去克服康德对哲学史的挑战。参见piercey,“active mimesis and art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43,no.1(20xx),pp.29-43.
[16]参见hegel,lesser logic,§86n2 wallace’s translation,2[nd]edition,p.160.
[17]法国年鉴学派史家便曾儆惕吾人种种分期卷标可能会是一些“wrong labels which eventually deceive us about the contents”(bloch),和可能“ending up by giving the signs authority over their contents”(braudel)。引见dietrich gerhard,“periodization in history”,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p.58;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网络版,url:]。便另一方面许多著名哲学史家还是把“中世纪”的年代订得很前。例如emile bréhier著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一书便把moyer age的开始订于公元五世纪;而karl vorlnder著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则把古代之“终了”订于boethius(480-525a.d.)之余,还把mittelalter之起点上推至公元首几个世纪的教父哲学;其它如windelband,alfred weber,等亦同样把最早的教父哲学都列入中世纪哲学。
[43]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theodor e[rnst]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new york,1959),or in speculum,vol.ⅹⅷ(1942),pp.226-242.
[44]american cyclopedia(1883),i,p186。引见mommsen,ibid.,p226.
[45]就这一问题,见上引mommsen一文p242,另外,参见本文下面有关“文艺复兴”一概念的。
[46]上引mommsen一文(p227)即引用lucie varga的研究[das schlagwort vom‘finsteren mittelalter’(vienna-leipzig,1932)],指出把中世纪视为“黑暗”直到启蒙时期还是欧洲人针对中古教文化的一“作战呐喊口号”(battle cry)。
[47]毕达哥拉斯学派曾提出十对对反原则,光、暗之对反即属其中之一。见aristotle,metaphysica,book a,986a22-28.
[48]当然地,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地大学的建立,对于中世纪哲学传统的传承亦绝不能忽视。
[49]教的大公会议是指由教宗召开的主教会议。罗马天主教认可的大公会议自最早的尼西亚一号会议(325 ad)到最晚近的梵蒂冈二号大公会议(1962-65 ad)已召共二十一次。
[50]vatican ⅱ,lumen gentium(ad 1964)§16.
[51]例如1962-65年梵蒂冈二号大公会议的讨论结果,便把十九世纪教皇pope pius ix的许多条(连“教会以外无救赎”)训谕了。见网页:http:///china/">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四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pp.141-184。此外参见tze-wan kwan,“subject and person as two selfimages of western man:som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dicated to jan patocka(1907-1977)on the occas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organizations(opo).held november 6-10,20xx,at charles university and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czech republic,prague.now available at url:http:///essays/kwanarticle.pdf.
[60]参见raymond schwab,the oriental renaissance.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1680-188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从书名可见,schwab理解中的“东方复兴”,直到从莱布尼兹对“中国”的发现,追zōng@④到浪漫运动的终了。
[61]参见edward w.said,orientali,1st edi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62]hermann haring and hans-josef kuschel(edited),hans küng:his work and his way,translated[from the german]by robert nowell,london:fount paperbacks,1979.
[63]黑格尔曾说“要读哲学,首先要成为斯宾诺莎的信徒”〔werke,suhrkamp,band 20,p165〕;尼采曾把spinoza称为“最纯粹的智者”(den reinsten weisen),〔见nietzsche,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475,tliche werke(dtv-de gruyter),band 2,p.310〕;此外,罗素则是视spinoza为“大哲学家中最高贵和最可亲者”(the noblest and most lovable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s),[russell.op.cit.,p.552].
[64]见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a271/b327.
[65]见本文后面有关德意志观念论的讨论。
[66]休谟对康德的影响世人谈论已有许多,但关于休谟情感学说这另一面的影响可参见isaiah berlin,“hume and the sources of german anti-rationali”,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oxford:oup,1981),pp.162-187.
[67]见pascal,pensées,§227.(paris:garnier,1964),p.146.原文“le coe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it pas.”
[68]见pascal,pensées,§282.ibid.,p.147.原文“nous connaissons la vérité,non seulment par la raison,mais encore par le coeur.”
[69]edmund burke,“the death of marie antoinett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原文为“but the age of chivalry is gone;that of sophisters,economists,and calculators has succeeded,and the glory of europe is extinguished forever.”
[70]friedrich 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77)22[10],tliche werke,band 8,(berlin:dtv/de gruyter,1980),p.382.
[71]isaiah berlin,“the counter-enlightenment”,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ibid.pp.1-24.除了这篇文章标题化地探讨“反启蒙运动”问题外,柏林许多其它论著(如论hamann,vico,herder等的文章都和这一主题有关。
[72]参见柏林上引书中有关rousseau讨论多起。此外,近年就卢梭与反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可参见arthur m.melzer,“the origin of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rousseau and the new religion of sincerit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2 1996,pp.344-360。另外,牛津四卷本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主编alan charles kors曾于一篇访问中对卢梭作了如下评语:“but in the final ysis rousseau’s anti-intellectuali and his contempt for natural knowledge,especially for applied knowledge,set him very much against the deepest currents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in that sense,he was the precursor of the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参见kors,“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navigator 11/1997.web url:http:///articles/interriewalan-charles-kors.asp(retrieved jan.10,20xx).此外,kors编的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volume 1(oxford oup,20xx),pp.307-311中“counter-enlightenment”一条(作者:sylvaine albertan-coppola)亦有同样论断。
[73]法国启蒙主义者condorcet便常给人此一印象。近年好几本书都谈到这问题;参见emma rothschild,economic sentiments:adam 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xx)。此外,尼采提出joyous or gay science(frhliche wissenschaft)明显地是要针对descartes代表的cold,rational science而言的。
[74]见isaiah berlin,review of cassirer’s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刊于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269(1953),pp.617-619.柏林原文为“for professor cassirer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at any rate since the renaissance,is almost cloudlessly happy…”
[75]见jürg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postmodern culture,ed.hal foster(london & sydney:pluto press,1983,1985),pp.3-15.se also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eds.)maurizo passerin d’entreves and seyla benhabib(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
[76]在几年前一篇文章里,笔者曾借乌纳穆诺(unamuno)及佩里斯纳(plessner)等理论提出:在情感的挑战下,吾人只有透过对理性底限制的深层的和最彻底的确认,才能重新确定其于限制下所仍保有的功能与地位。参见关子尹著:〈说悲剧情怀—从情感先验性看哲学的悲剧性〉,《无涯理境—劳思光先生的学问与思想》,刘国英、张灿辉合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xx),pp.177-217。
[77]见kant,“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rung?”,kgs,band ⅷ,p.40.
[78]这一点从《纯粹理性批判》书中所有涉及“能力”的论述的术语之前都冠以“超验”一点可见,如“超验感性论”、“超验逻辑”、“超验图式论”、“超验想象力”等。
[79]见康德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ft,a64-66/b89-91.
[80]见康德kant,verkündigung des nahen abschlusses eines tractats zum ewigen frieden in der philosophie.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ⅷ,p.416.
[81]见kant,logik.ein handbuch zu vorlesungen,kgs,band ⅸ,p.25;另参见康德1793年5月4日致c.f.studlin信札,kgs,band 11,p.429。信中,康德甚至把anthropologie一字置于括号中直接用以说明列出的第四条问题。
[82]这种最主要的代表是法国哲学家威柏尔(alfred weber)。见weber,history of philosophy,tranl.by frank thilly(new york:scribners & sons,1908),§ 64,参见网版:http://www.class.uidaho.edu/mickelsen/toc/weber%20toc.htm(12 june 20xx).
[83]rüdiger bubner很清楚指出康德作为德意志观念论者“只能于设有保留下生效”(nur mit einschrnkung geltung verdient)。见bubner(hrsg.),deutscher idealius,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text und darstellung,band 6,(stuttgart:reclam,1994),p.7。此外,karl ameriks亦表示了类似的态度,见 ameriks, “introduction:interpreting german ideali”,the cambriddge companion to german ideal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
[84]dietrich mahnke乃胡塞尔早期的学生和助理,曾于胡塞尔编的jahrbuch里发表了关于莱布尼兹的重要著作leibnizens synthese von universalmathematik und individualmetaphysik.(halle a.d.s.:niemeyer,1925),jahrbuch…,7.band.。除此之外,并先后发表过有关莱布尼兹的论着多种,主要有:leibniz als gegner der gelehrteneinseitigkeit,(stadde:pockwitz,1912);eine neue monadologie,published as kant-studien ergnzungshefte 39(berlin:1917);unsichtbares knigreich des deutschen idealiws(halle:niemeyer,1920);“die neubelebung der leibnizschen weltanschauung”,logos,band ⅸ,1920-21,pp.363-379;leibniz und goethe.die harmonie ihrer weltanscichten.(erfurt:stenger,1924);unendliche sphre und allmittelpunkt(halle:niemeyer,1937)等。
[85]见mahnke,leibnizens synthese…,ibid.,p.305.
[86]除了mahnke外,另外三位学者也很强调莱布尼兹与德意志观念论的紧密关连:a.heidegger,参见identitt und differenz(pfullingen:neske,1957),pp.15-16,also beitrge zur philosophie(frankfurt-main:klostermann,1989),pp.202-204;b.nicolai hartmann,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dealius;c.michael inwood(hegel dictionary的作者)曾把莱布尼兹形容为“the first great german philosopher is leibniz,who[…]decisively shaped the future course of.philosophy in germany and was in a sense the founder of german ideali.”见ted honderich(e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german philosophy”条目,(oxford:oup,1995),p.311.
[87]莱布尼兹1694年首先于“on the correction of metaphysics and the concept of substance”(acta euruditorium)一文中提出“力”的概念;其后于1695年“specimen dynamicum”一文中提出了各种力的分野和说明。以上两篇文章均参见leibniz,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transl.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roy e.loemker(dordrecht:reidel,1976),pp.432f;435ff.
[88]最近便再有学者着文申明这一点,见paul redding,“what is an epistemic perspective?”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vol.28.20xx,p.371ff.
[89]参见leibniz,“a new system of the natur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substances,as well as the union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body(1695)”,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ibid.,pp.454-461.
[90]关于界域问题,参见拙著,“husserl’s concept of horizon:an attempt at reappraisal”,ecta husserliana,vol.31,(dordrecht:reidel/kluwer,1990),pp.361-398.
[91]“运作概念”的意念,可参见eugen fink,“operative begriffe in husserls phnomenologie,”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11,(1957),pp.321-337.
[92]胡塞尔的原文是“echte entelechie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der des‘deutschen ideali.’”.参见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band ⅲ,hrsg,von karl schuhmann,(dorderecht:kluwer,1994),p.432.引见rudolf haller’s review of husserls briefwechsel[…],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volume 52,1996-97,pp.227-236.
[93]参见拙著,“wilhelm von humbold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29,number 2,berkeley,june 20xx,pp.169-242.在该文的引言中,作者尝试指出洪堡特语言理论中涉及的一些莱布尼兹、康德甚至黑格尔等哲学中的元素,并说明其与洪堡特语言学的关系。此外,卡西勒亦曾著有〈洪堡特语言哲学中的康德元素〉一文,cassirer,“die kantischen elemente in wilhelm von humboldts sprachphilosophie”,in:binder,j.(ed.):festschrift für paul hensel.ohag,greiz.i.v.,pp.105-127.
[94]就洪堡特对人文科学整体而言的贡献,参见ernst cassirer,“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1935)”,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goteborg,symbol,myth,and culture,essays and lectures of ernst cassirer,edited by donald phillip veren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56.卡西勒原文为:“this expression of wilhelm von humboldt does not simply apply to language alone;it applies,with the same right and ground,to all productions of our spiritual culture,to all that i have tried to bring together under the general concept of‘symbolic formation’.”
[95]除洪堡特外,语言学家如jakobson也常把设想为sound matter。就此问题,参见关子尹:〈洪堡特《人类语言结构》中的意义理论——与意义建构〉,《从哲学的观点看》,台北:东大,1994,页219-267。
第十五篇 柏拉图人生哲学之初探_西方哲学论文
至于这个架构究竟是怎样的?亦要在此作一简单的交代。首先,「人生」究竟是指甚么呢?一般来说,人生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段生命历程,而在这段生命历程之人人总会有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吉凶祸福,当中如何处理?如何面对?如何活出人的意义?如何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些全是人生哲学所要面对及处理的问题。既然说是人生哲学,当然以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作为问题讨论的中心,以人作为问题的起点。于是我们便会先问「我是谁?」的问题,要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及地位作出界定。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必定会涉及到前世问题,正如佛家所提出的疑问:「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3]既然问及前生,亦必会再追问来世的问题,于是乎便会出现人生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前世、现世、来世。关于人生存在时间三向度的问题,科学不能够回答,因为科学建基于经验,对三世问题无法肯定,当然亦没法否定,那么只有哲学中的道德进路及宗教进路可以处理。针对人生存在三向度的问题,引发出三大问题,就是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今生当若何?第一个问题是问「生」的问题?第二问题是问「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问如何在现世活出生命意义及价值追求的问题,这涉及爱、欲的问题。基本上,人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就是本论文的主要架构。只要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界定清楚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自己死后的去向之后,就可以为现世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确立安身立命之所,然后突破人生的局限,展现生命存在的价值。
二)柏拉图对「生」、「死」问题的看法
1.有关「生」问题的探讨
在人生哲学中,有关「生」问题的讨论亦即是处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了人的结构是怎样及构成人的元素是甚么这两个问题。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借蒂迈欧之口,十分详尽及有系统地论述了整个宇宙(包括人在内)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的问题。柏拉图指出整个宇宙是由宇宙创造者德谟革(demiurgos)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创造神依照永恒不变、自我同一的模型,配合水、火、气、土这四种元素(材料)及场所(空间)创造出整个宇宙。基本上,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作为推动宇宙运作的力量,再按几何结构来创造出天体,然后再创造时间,使可感世界的一切都能发生在时间之中。可以说,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然后再创造出世界的形体。[4]接着,创造神又创造了各种动物,包括天上诸神的族类,飞翔在天上的鸟类、水族类及陆地上行走的生物。[5]创造神在最后阶段才创造出人。在造人的过程之中,亦是先做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出人的肉体。可以说,人跟宇宙的构造一样,是由灵魂与肉体这两部分构成,而在构造的过程中,神是先创造精神性的灵魂,然后再创造物质性的肉体。至于构成人的元素,亦是水、火、气、土这四大元素。[6]谈到这里,我们已处理了人的结构(灵魂与肉体的组合)及构成人的元素(肉体由火、水、气、土四大元素组成,灵魂是诸神摹仿创造者制造的,当中有不朽的理性及可朽的情绪、欲望和感觉)是甚么的问题。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生从何而来」的答案已不言而喻:人就是由神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有一点要交代清楚的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讲的创世纪并不是宗教所讲的那一套,当然其中有些观点是宗教继承柏拉图的。再者,柏拉图所讲的创造神亦非宗教所讲的上帝,因为柏拉图所讲的神是哲学上、逻辑学上的神而非人格神,况且柏拉图的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它亦需要借助永恒的理念、模型及四大元素及空间才能创造宇宙。
2.有关「死」问题的探讨
a.死后往何处去
有生必有死,柏拉图处理了「生从何处来」的问题之后,接着就要处理「死往何处去」的问题。「死」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避免,故此有「生」是否一定会「死」这个问题是没有讨论意义的;但是人死之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却不同,不同的哲学家及宗教都会提供不同的答案,甚至有人更会认为人死如灯灭,「人」一死甚么都没有,又何需处理死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呢?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就够面对死亡问题,柏拉图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上文曾提及人是由灵魂及肉体这两部份组合而成的,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人的肉体,所以灵魂的存在是先于肉体的,而且柏拉图更认为灵魂与肉体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存在的东西,灵魂先验地是理型界的存在,肉体是现象界的存在,所以人死后灵魂未必一定会落入轮回之中,如果能够行善积福,遏制欲望、净化灵魂的话,灵魂就可以永远脱离肉体的束缚,再返超越的理型界之中,可以说,在柏拉图的思想之中,理型才是永恒存在的世界。所以,柏拉图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并非一件苦事反而是一件乐事,因为死亡正是代表灵魂可以从肉体的枷锁之中释放出来,虽然灵魂的可朽部份会跟肉体一同死亡,但是不朽的、纯洁的部份却会重获自由。柏拉图在《斐多篇》(phaedo)中说:「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以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对吗?除此之外,死亡还能是别的甚么吗?」[7]虽柏拉图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的分离状态,但是灵魂解放出来之后是否一定会返回永恒的理型世界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时已被肉体的欲望(如情欲、物欲、性生活享受)、仇视、畏惧等不良因素所污染了的话,灵魂不会超升而返回理型界,反而要落入不断的生死轮回之中。[8]有关灵魂如何轮回的情况,留待下文详作论述。相反地,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它造成的污垢的话,灵魂就可以不需接受轮回之苦,返到理型界或比这个世界可能更加美好、更加昌盛的世界。[9]
至于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呢?柏拉图说要训练自己从容面对死亡,训练的工具就是追求哲学,透过哲学的追求就可净化灵魂。可以说,实践哲学可以令我们禁止一切身体的欲望,不受欲望操控,这样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10]至于如何实践哲学,如何净化灵魂,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中有详尽的论述,故不在此赘述。
b.灵魂不朽的论证
由于人的死亡只代表灵魂与肉身的分离,并不代表灵魂必定是从肉体的牢狱中获得释放,重新进入永恒的理型世界。柏拉图为了令灵魂重返理型界有可能及使人的行为必定具有善恶因果的价值一致性,所以一定要说灵魂不朽,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提出了六个论证。
一)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11]
柏拉图说:「凡有对立而存在之处,对立的事物产生对立的事物,例如美是丑的对立面,正确是错误的对立面,还有无数其它事例。……这是否为一条必然的法则,凡有对立面的事物必定从其对立面中产生,而不会从其它来源中产。」既然生与死是对立的事物,所以两者理应交互生成,从生有死,从死有生,生生死死,不断循环。由于生死交互生成,不断循环,所以灵魂再生,不朽存在就成为可能。
二)从知识的回忆说来推论出灵魂不朽[12]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于理型界的知识客观而真确,而这些知识的获得与感性经验及现象界无关,而现在寄寓于肉体之中的灵魂绝不可能认到这些真确而具客观性的真理。故此,这些关于理型界的知识必定是灵魂在前世已经有,只是现世通过回忆作用把这些前世已有的知识重新召回来。故此,有关理型界知识的成立就足以证明灵魂曾于前世存在,甚至之前几世存在过。根据此理,现在世亦将会成为未来的过去世,现在的知识将来亦会成为来世回忆的对象,由此可以明灵魂是不朽的。
三)从灵魂的神性导出灵魂不朽[13]
柏拉图将存在的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的;另一类是凡人的、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灵魂与肉体相比起来,柏拉图认为灵魂与前一类事物最为相似,肉体却与后一类事物相似。既然现在灵魂跟第一类事物同样具有不朽的、统一的、单一的、不可分解的属性,故此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也不可能被毁灭,所以它必然是不死和永恒的存在。
四)从语意证明灵魂不朽[14]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生命原理,生命既然是灵魂的生命原理(本质属性),故此应该是不朽的,否则生命原理与灵魂在语意上会出现矛盾,因为如果灵魂是可朽、是死灭的话,就会与生命构成矛盾。
五)从道德伦理角度证明灵魂不朽[15]
柏拉图认为任何存在物的坏灭衰亡,必定由内在而固有的恶因所造成。灵魂之中虽有恶的成份,如无知、怯懦、放纵等,但是灵魂却不会被这些恶的成份影响而灭亡。可以说,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于灵魂的恶都不能使灵魂坏灭衰亡,灵魂仍是永恒地存在着。故此,灵魂一定是不朽的。
六)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16]
柏拉图说:「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的。那些要由其它事物来推动的事物会停止运动,因此也会停止生命;而只有那些自身运动的事物只要不放弃自身的性质就绝不会停止运动。还有,这个自动者是其它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第一原则。」由于灵魂是一种自动的存在,亦是推动其它事物的源泉及第一原则,故它无生灭可言,一定是不朽的。
c.对灵魂不死论证的批评
柏拉图要设证灵魂不死,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透过理性的方法去证立灵魂不死呢?。如果以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来看的话,灵魂根本是超越经验范畴的形上存在,我们对它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性经验,如果我们强行以理性范畴去证立超验的灵魂存在的话,这就是理论理性的误用,最后只会变成独断论(dogmatists)。柏拉图对灵魂的论证亦一样,因为我们对灵魂缺乏经验,所以同样地可以其它理由来证立「灵魂可朽」的命题。事实上,柏拉图这六个论证亦存在着缺失的。例如第一个论证: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是互相相对地交互生成,如有「生」的概念时就预设了有「灭」的概念,有「灭」的概念时亦预设了有生与之相对,这只是概念上的相对互生,但是在经验上是否真的有生就一定有灭,有灭就一定有生呢?这是存疑的,生死问题亦是同一情况。再者,生死是互相交互生成,亦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生证明了死,死再证明生,然后生又再反过来证明死。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又如第六个论证: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虽然柏拉图说「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并以此作为论证灵魂不朽的大前提,但是我们如何建立「灵魂是自动的」这个小前提呢?所以最后亦是推不出灵魂不朽的必然结论。其它的论证亦存在着不同的缺失,但我们没有必要将之逐一指出。
另一方面,柏拉图虽然要证立灵魂不朽,但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朽却并非指所有的灵魂,而只是指灵魂的理性部分。基本上,柏拉图将人存在的灵魂区分为三类,分别为理性、及欲望。其实,如果柏拉图将灵魂不朽作为宗教上的信仰或道德上的设准来看待的话,就可避免以理性范畴去论证灵魂不朽而引致的缺失。但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说为现实人生的生命超升及道德行为的因果价值统一性提供了必然的保证。
三)柏拉图对「爱」、「欲」问题的看法
当我们处理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之后,就要处理「今生当若何」的问题,究竟在现世存在,我的责任和使命是甚么?我完成了这些责任没有?如何生活才可以提升生命的质素活出生命的意义?
1.爱欲与生死轮回的关系
柏拉图要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提升生命的质素,否则就会沉沦下堕。而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真、善、美。真与美、与善是有等同的价值,但只存在于理型界之中,人生追求的过程就是哲学。那么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是甚么呢?就是爱(eros),爱的本质就是要追求美、善,而智慧是最美的东西,所以追求美、善亦即追求。可以说,对的追求亦是欲望(desire)的一种,不过这种向着美、善进发的欲求是正面的,层层超升的,是由最低层次的肉体上的「爱」超升到追求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绝对统一。这样,透过哲学对的追求,人的灵魂就可以净化,死亡时就可以摆脱肉体的束缚,直接到理型世界之中。相反地,如果人只沉沦于肉体上的爱物质生活的享受及过着不正义的生活的话,欲望只会使人不断向外索求,最终只会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亦需要在生死之间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得到净化为止。
2.贯通三世的生死轮回观
柏拉图虽然说「死亡」是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状态,但是灵魂从肉体解放出来时未必一定是完全纯净的,不是纯净的灵魂是不可以立即重返永恒存在的理型界,反而要在生死之中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完全净化为止。以下将对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的轮回情况作一介绍。
a.轮回的原因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讲了一个神话,他说:「纯洁的灵魂若不能跟随神,甚么真理都看不见,而只是碰到不幸,受到健忘和罪恶的拖累,并由于重负损伤了它的羽翼而堕落地面,那么它就会遵循这样一种法则沉沦。」可见,如果人不追求真理、追求智慧,最后只会受到罪恶的拖累,沉沦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生命质素不断地下降。[17]柏拉图亦说如果人「转向一种比较卑贱的、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那么当灵魂不谨慎或醉酒之时,两颗灵魂中的劣马(及欲望)就很有可能乘其不备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做那些大多数凡人以为是快乐的事来充分满足欲望。做了一回,他们以后就不断地做。」[18]可见当人追求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及耽于逸乐时,就会失去智慧,并会为满足欲望而要于生与死之间不断轮回。
b.不同形态的轮回
柏拉图指出人依据自己所做的不同行为而投生到不同的肉体。「那些不去努力避免而是已经养成贪吃、自私、酗酒习惯的人,极有可能会投胎成为驴子或其它堕落的动物。」至于「那些自愿过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无法无天、使用的人,会变成狼、鹰、鸢。」而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的善的人……通过习惯和实践来获得,而无需哲学和理性的帮助,……可能会进入某种过着社会生活,受纪律约束的动物体内,比如蜜蜂、黄蜂、蚂蚁,甚至可能再次投胎于人。」[19]而那些第一次再生的灵魂,柏拉图说他们不会投生于任何兽类之中而只会投生为人,不过他们会因应自己看见真实存在的程度多少而投胎成九类不同的人。看到大多数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智慧或美的追求者,看到最少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僭主。现将这九类灵魂投生为人的情况表列如下:[20]
类别 灵魂所投胎成的人 对真实存在的认识
第一类 智慧或美的追求者 最多
第二类 守法的国王或勇士和统治者 少些
第三类 家、商人或生意人 少些
第四类 运动员、教练或医生 少些
第五类 预言家或秘仪祭司 少些
第六类 诗人或其它模仿性的艺术家 少些
第七类 匠人或农人 少些
第八类 蛊惑民众的政客 少些
第九类 僭主 最少
柏拉图又在《斐德罗篇》249a中指出,所有投生于肉体的灵魂,如果是依照正义而生活的话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命运,若不依正义而生活的话,命运就会较差。换言之,人若依正义而行事的话,生命质素必定可以得以超升。那么要多久才可以脱离生死轮回呢?柏拉图说是要一万年,不过如果人能用爱欲来追求智慧的话,只要三千年就能得到解脱(恢复羽翼、高飞而去)而返理型界中。
3.如何透过爱来净化灵魂
其实,柏拉图探讨「生从何而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确立现世的意义,要为现实人生找寻安身立命之归宿。正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及来世的生命走向,亦意识到自己灵魂的不死,于是人生就有希望,人才能够有意义地生活下去,才能够选择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去做,逃避自己认为不应该的事情,逐步逐步提升自己生命存在的质素及价值。
对于现世(生),柏拉图提出了「爱」(eros)的学说,「爱」的问题在《会饮篇》中讨论的最多。基本上,人是有追求美善的天性,于是乎便产生了「爱」。「爱」是生命的动力,亦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力。有了「爱」,人可以依恃着它去过合乎正义的生活,去认识真理,去追求人生的美善。「爱」作为一种欲求(desire),可有两方面的发展方向,如果追求美善的话生命就会超升,灵魂就会得到净化,如果追求逸乐、沉迷于逸乐的话,生命必定会向下堕,当中的关键全在人自己自由意志的抉择。
《会饮篇》中所提及的爱可有精神上及肉体上的分别。精神上的爱是指对真、善、美的渴求。肉体上的爱亦即是,之中又有男女之间的异及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同。其中同比异更为高尚,因为异只是为了性的满足及繁殖下一代,但是同却以精神上的智慧和美德作为自己渴求的目标。当然,柏拉图并非只停留在同之上就满足,还要再作突破,从肉体上的追求层层突破至精神上的追求,即从肉体上的生育求不朽,升华至精神上的生育,追求智慧和美德的不朽,直接把握真、善、美的理型。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种名为「向上引导」(epagoge)的方法来认识「理型」,即从具体事物开始,层层向上转化,最后达到「理型界」。这个对「理型」的认识及转化过程,可表述如下:
步骤 层层超升、突破的情况
第五步 突然跳跃而到达最后的目的,直接把握美善的理型。(absolute beauty and the good)
第四步 再由对美的灵魂的追求,进一步转向追求美的制度和学问(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第三步 突破对某一殊别的美的形体的追求,认识到掌握灵魂的美是高于肉体的美。
(from the physical body to the spiritual)
第二步 从美的形体认识了美的道理,认识到各个美的形体都共有的美的形式。
(general beautiful body)
第一步 人开始爱一个殊别的、具体的美的形体。
(particular beautiful, physical body)
总之,最初我们是认识美的形体,然后是美的灵魂、美的制度、美的学问、美的智慧,最后直接把握美的自身,即美的理型。透过这种层层超升的方法,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就可以突破生命之中的种种局限。直接达到理型界的存在。而这种净化灵魂的过程,亦是哲学的学习过程。可以说,透过哲学的训练就可以将生命转向,获取真实的知识、智能,直达理型界。因此,柏拉图认为人应该学习哲学,社会亦应以「哲学王」来统治,提升自己及别人的灵魂,发挥其中的圣洁本质。这亦即是柏拉图所讲「洞窟之喻」的精神。[21]
四)柏拉图人生哲学与佛家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从「生」、「死」这两方面确定了生死轮回是人存在无可避免的必然处境,而人之所以要堕入生死轮回之中完全是基于自己对欲望的渴求及沉沦,不愿过合乎正义的道德生活,故此现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哲学、追求、由肉体上的「爱」开始层层超升突破,转化为对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理型。这样去作哲学的实践,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话,死后必定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返回理型的真实世界之中,获得最终的解脱。这种由现实人生要面对生死轮回的处境而追求生死解脱,超越生死轮回的思想跟佛教同出一辙。以下尝试以表列的方式将佛教的轮回思想跟柏拉图的思想作一简单的比较。
佛教(原始佛教) 柏拉图 备注
1.「人」作为存在主体的构造 人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及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当中有物质性的元素(四大及色蕴),亦有精神性的元素(受想行识四蕴) 人由灵魂及肉身这两部份组成,灵魂是精神性,肉身是物质性的。而人的肉身是由火、水、气、土这四大元素所组合而成。 两者均认为人是由精神性及物质性的元素组合而成,佛教的四大跟柏拉图的四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人之所以
要轮回的原因 被贪、嗔、痴等无明烦恼障蔽,不断起惑造业,这便要偿付错误行为的代价:生死轮回。 被欲望、罪恶拖累、渴慕虚荣、耽于逸乐,甘于过比较卑贱及非哲学的生活方式。 两者都是以自己生命中的不良因素作为轮回原因,大家都是自作自受的。
3.贯通三世
的轮回主
体 原始佛教说无我,只是以业作为贯通三世的媒介,后来瑜伽行派吸收部派的思想而安立阿赖耶识(ālaya vijñāna)作为轮回主体。 以精神性的灵魂作为贯通三世的轮回主体。 佛教是无我的轮回思想,柏拉图是有我(灵魂实我)的轮回思想。
4.轮回的界
域 佛教认为众生是在三界(欲界、、无)、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之中轮回转生的。 认为人会在畜生、昆虫及人这几类个体生命存在的形态中投胎,在人这界域中分为九等高低不同的投胎。 在轮回的界域上,佛教比较丰富,基本上,柏拉图只划分出人及畜生二趣。
5.超越生死
轮回的方
法 消极方面:受持五戒、十善。不犯错,不作恶因。
积极方面:修八正道、积习善因、以求解脱。 学习哲学、以「爱」去追求真、善、美藉以净化灵魂。
两者的方法虽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6.解脱的境
界 超出六道、断除生死,证入涅盘境界。 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进入理型界的真实存在。 彼此的目的地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有超越生死轮回的要求。
从上表的比较可见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所讲的十分相似,尤其是在精神上大家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认为人自己行为上(生命中的恶及烦恼影响)的偏失引至到生死轮回,最终的理想都是要在现实人生上好好修行,突破自己生命的局限,最终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不过,在某些地方,如轮回的原因、轮回主体的具体运作及轮回的界域这几方面,佛教的论述是较柏拉图的要精密。佛陀所处的年代比柏拉图要早二、三百年,当时柏拉图有否机会吸收到佛教的轮回思想呢?[22]这有待历史学家去作进一步的考证。虽然,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的相比是较为逊色,但是柏拉图不竟是哲学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柏拉图能够以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前世今生的问题,并为现实人生确立方向、价值和意义,这已是柏拉图哲学的一大成就,这亦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价值所在───起了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确立人生超升方向的宗教意义。
五)结论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可以放在过、现、未三世的时间框架中以生死爱欲作为切入点来加以讨论。三世其实是处理三个主要的问题,在生死的交互循环之中引发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前者是生命的起源问题,后者是终极归向,终极关怀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柏拉图提出了创造神创造之说,指出神不单创造人的肉体,还创造了人不朽的灵魂,亦对人的结构加以。对于生命的终极归向问题,柏拉图提出了灵魂脱离肉体束缚而重返理型界永久实存的主张。在处理了生死及轮回的问题之后,便可安立现实的人生,突破生命的局限而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现实人生中,柏提图提出「爱」与「欲」这一对概念,提出人人皆有欲望,如果沉沦于物质享受及欲望之中,生命必定会下堕并沉沦于生死轮回之中,相反地,如果人能够遏制肉体上的欲望、突破肉体的爱而将之升华为精神上的爱,透过哲学的追寻而获得智慧,把握真、善、美的埋型的话,生命必定能突破局限,层层升进,待灵魂完全得到净化后便可摆脱肉体的束缚而与永恒真实存在的理型界相契相入,进入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虽然柏拉图有关生死轮及超越解脱的思想没有佛家那么精密,但柏拉图不竟是一位哲学家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学说较佛教逊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柏拉图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考而能起着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的宗教功能,这是柏拉图人生哲学成功及值得被肯定的地方。 参考书目
1.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一、二 左岸文化 20xx年4月初版
2.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三 左岸文化 20xx年7月初版
3.柏拉图着、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 商务印书馆 20xx年1月初版
4.柏拉图等着、刘小枫等译《柏拉图的会饮》 华夏出版社 20xx年8月第一版
5.程石泉着《柏拉图三论》 东大图书公司 1992年6月版
6.曾仰如着《柏拉图的哲学》 商务印书馆 1998年4月2版2次印刷
7.汪子嵩等着《希腊哲学史》 第二册 出版社 1997年5月1版第2次印刷
8.傅伟勋着《西洋哲学史》 三民书局 20xx年3月二版
9.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 中国大学出版社 20xx年6月版
10.邬昆如着《西洋哲学史话》 三民书局 20xx年1月增订二版
11.段德智着《死亡哲学》 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4年8月初版一刷
12.冯沪祥着《中西生死哲学》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xx年2月初版
13.杨绍南着《人生哲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1996年3月初版第七次印刷
14.alexander nehamas & paul woodruff, “plato’s symposium”,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15.brian proffitt, “plato within your grasp”, wiley publishing, inc, 20xx.
注释:
[1]转引自段德智着《死亡哲学》,页70。
[2]这五篇对话录分别为:《斐多篇》(phaedo)、《斐德罗篇》(phaedrus)、《会饮篇》(symposium)、《国家篇》(republic)及《蒂迈欧篇》(timaeus)。
[3]见《顺治皇帝归出词》。
[4]参阅《蒂迈欧篇》,27c-36d。
[5]参阅《蒂迈欧篇》,40a。
[6]有关神造人的具体过程,可参阅《蒂迈欧篇》,44d-46c。
[7]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64c。
[8]详见《斐多篇》,81b。
[9]详见《斐多篇》,80e-81a。
[10]详见《斐多篇》,82c。
[11]详见《斐多篇》,70e-72d。
[12]详见《斐多篇》,72e-77d。
[13]详见《斐多篇》,78c-80c。
[14]详见《斐多篇》,102a-107b。
[15]详见《国家篇》,611a-611c。
[16]详见《斐德罗篇》,245c-d。
[17]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
[18]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56c。
[19]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82a-b。
[20]详见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e。
[21]即突破自己的局限,从感觉经验开始层层突破,最后直接把握理型的真实。并且当自己的生命超升了之后,还返回洞窟救度其它人,教他们认识理型的真实世界。
[22]一般认为柏拉图的轮回思想是学习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
copyright (c) hong kong society of humanistic philosophy. all rights reserved.
第十六篇 卢梭的法律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_西方哲学论文
在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家中,卢梭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别声誉,那就是他的名字紧紧与“第一次建立在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法国大革命连接在一起。“这场革命,导师是卢梭”。(注:转引自李凤鸣、姚介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卢梭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原则奠定了主要基础,并通过信徒罗伯斯比尔等人(注:“罗伯斯比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法]巴奈尔:《法国革命中的卢梭》,巴黎1977年版,第602页。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9页。马拉赞扬卢梭是“真理和自由的倡导者,恶劣习俗的者,人道主义的保卫者和神圣权利的复兴者。”他多次上街宣读卢梭的著作。勃·姆·列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哲学》,第163页。 转引自阎海云:《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4期。)在革 命过程中加以实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已达成的共识。研究卢梭的法律思想对大革命的 影响,既有利于把握这位著名启蒙大师的历史地位,又可以解读法国革命的特色。
一、卢梭的平等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自由是卢梭思想的名义目标,但实际上他所重视的、他甚至牺牲自由以力求的是平等。”(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7页。wWW.meiword.cOM)恩格斯指出,在“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注:《马恩全集》第20卷,第699页。)
(一)法律平等思想与贵族制的废除
平等对于卢梭来说,有切肤的感受。卢梭是当时惟一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受到富贵人家的欺凌与侮辱,也得到了穷人真诚的帮助。卢梭宣扬“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要知道一位贵族跟一个牧人都有两条腿,也都只有一个肚子。而且那些所谓必需的东西实际上对于他的身份并不是必需的。”(注:[法]卢梭:《论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4页。)他十分厌恶那些上流社会的权贵,指责贵族在法国坐享有害而无益的特权,是法律与自由的死敌,“在它大放光彩的那些国家的大多数,除了专制的势力和对的外,还能产生什么呢?”(注:[法]卢梭:《新爱洛伊丝》第1卷(第62封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7页。)所以,他坚持法律平等,即“法律的条件下对人人都是同等的,因此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注。)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全体公民都有责任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来为国效劳,每个公民也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受到提拔和优待。
法国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不久制宪会议就通过第一个法令即“八月法令”(8月4—11日),取消了封建贵族的司法、养鸽、狩猎、免税等特权。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著名的《宣言》,明确承认“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1790年3月15日,议会宣布“一切特权,一切财产的封建性质和贵族性质一律废除。”6月19日,议会进一步作出决议:“永远废除世代相承的贵族阶层”,“任何人不得再保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贵族头衔”。1791年9月3日,革命颁布了冠以《宣言》的宪法,从此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终于完全代替了封建等级特权的原则。与此同时,卢梭提出的平等思想也在1791年宪法中得到了落实:“一切公民,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都得无差别地担任各种职位和职务。”的确,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靠出身、权贵,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和才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登上了舞台并担当了重任。(注:参见尹虹:《论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二)经济平等思想与雅各宾的社会分配方案
在所有的平等要求中,卢梭把经济平等的原则放在首位,因为“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注:[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要实现人的平等权利,首先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做到“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足的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可以穷的不得不自身”。(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注:[法]卢梭:《论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每一个公民只准有一个作坊,一个商店。”无套裤汉党人的这一主张是卢梭论述的 雄浑回声。1792年12月2日,在向国民公会所作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著名演说中, 罗伯斯比尔提出“一切权利之中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利”,“社会生活的首要法律是保 证一切社会成员都有生活资料”;(注:[法]波普朗编:《罗伯斯比尔选集》第2卷,巴 黎1973年版,第85页。转引自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 于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臧妫?4页。 )他同时还强调“一切损害生命的投机活动都不能算是贸易,而是抢劫。”(注:[ 苏]沃尔金、塔尔列:《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苏联科学院1941年版,第2 97页。转引自刘宗绪:《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革命的上升路线》,世界历史1981年 第2期。)1793年4月24日,在《关于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著名演说中,罗伯斯比尔 又根据卢梭的学说提出了关于所有权的四点著名建议:“所有权是每个公民使用和支配 法律保障他享有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也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尊重他利的 义务的限制;所有权不能损害我们周围人们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违反这个原则 的占有,任何交易,都是不合法和不道德的。”(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 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7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法的全新解释,按 照这种解释,所有权已经受到了法律、公民责任心、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已经不是绝 对“神圣不可侵犯了”。这就为从法律上限制私有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此,罗伯斯 比尔强调“给予贫困者以必要的帮助,是富人对于穷人的神圣义务;履行这一义务的方 法由法律规定。”(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37页。)圣鞠斯特也是卢梭思想的忠实信徒,认为“富有是不名誉的事”,“应该 是既不富也不贫”。他计划,凡死后无直接亲属者产业应由国家继承;禁止有自立 遗嘱权,公民每年必须报告其财产的使用情形。(注:[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81页。)
“他们(雅各宾派)从卢梭关于国家对公民财产拥有无上权力的学说中,为自己的社会 措施找到了理论根据,这些社会措施是:反对投机倒把,国家调整物价,强制推销公债 ,等等。”(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 版,第263页。)为缓和财产不均的现象,1793年国民公会废除立遗嘱赠与的自由,法令 规定:“在直系亲属之间的财产处分权,不论是基于死因、生前赠与或通过契约赠与, 一概予以禁止。”“其结果是,所有卑亲属继承其尊亲属财产的平均份额。”(注:[德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27页。)有关法令还规 定,遗产必须由死者的子女平分,死者赠送给外人的遗产部分不得超过财产的1/10,赠 款的限额不得超过20万利维尔;凡已经拥有20万利维尔财产的公民根本无权接受赠款。 否则,就会破坏有继承权的亲属之间的“神圣平等”。(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8—119页。)1793年5月4日,粮食法令(第一“限价法令 ”)公布,规定“所有商人、农民或谷物和面粉的任何所有人,均应立即向其住所地的 市乡申报其所占有的谷物或面粉数量和性质。市乡人员根据市乡议会决议,有 权到拥有谷物或面粉而未依规定办理申报的、有申报不实嫌疑的公民家中进行搜索。” 1793年6月23日,国民公会颁布“强迫公债”法令,规定已婚者年收入1万利维尔、未婚 者在6千以上的,须征累进公债;收入在9千利维尔者应纳重税。(注:[苏]卢金:《罗 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8页。)圣鞠斯特还曾下令向富人强迫借款,交 款如迟1天处以1个月的监禁。1793年9月3日的法令规定统一全国粮食价格,禁止私人买 卖粮食;9月29日,著名的全面限价法颁布,规定了全国粮食、日用品和原料等39种商 品的最高限价。1794年7月27日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责令商人出售库存商品,违者 处以死刑。1794年11月15日的法令规定,对面包、肉实行定量供应,对面包质量作了统 一要求,这种面包被称为“平等面包”,凡违反者以“违反全体公民平等精神”论处。 (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3页。)
二、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指出:“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重要的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想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57页。)
“雅各宾专政时期是卢梭思想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时期。卢梭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是 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派不能不被卢梭学说的激进主义所 鼓舞,——在他的学说中,的原则得到了极为彻底的发展。”(注:[苏]沃尔 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
(一)不可分论与法国权力机关的设计、运作
卢梭认为,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由代表的意志是一个整体所决定的。“由于是不可能转让的,同理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37页。)基于此,他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的分 权论,认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 体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7页。)且看他 最尖刻的一段:“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 :他们把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与行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 ,分为内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开。他们把主 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权威的正确概 念,出自把仅仅是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认为是权威的构成部分。”(注:[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正是 不可分割的信念,这使得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除了以最刻板的权力分立形式 外,无法被接受。”(注:[英]m.j.c.维尔:《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 66页。)卢梭的不可分割的“理论是对混合和均衡思想的一种直接的抨击 ,在法国大革命对贵族权力以及后来对君的抨击中,这种理论达到了其最高峰,卢 梭的理论在当时至高无上就意味着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宪制的观点不大可能为人们所接受 。”(注:[英]m.j.c.维尔:《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0页。)
卢梭的不可分理论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了具体验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抛弃英美的两院制,实行一元制。在法国应建立一院制的议会还是两院制的议会?当时代表王政派的议员们主张实行美国式的两院制以代替富于贵族式的英国两院制;革命派主张建立一院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卢梭的论。他们坚持认为,立法权应由代表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来行使,一院制符合在民原则,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 的表达,而公意只能有一个,代议机关又是代表公意的,因此议会应取一院制,两院制 违反不可分割的原则。1789年9月10日的表决中,以849票对89票(122票缺席)的压 倒多数否决了两院制,通过了实行一院制的决议。(注:参见洪波:《法国制度变 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高毅:《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文化》,浙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5页。)但随着革命的结束和卢梭主 义影响的消失,法国人为了消除“一院制的恶果”和“过去的不幸”,在经过多年的争 论和实践之后,1875年宪法使两院制在法国最终确立,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是反对分权,导致“立法中心主义”。如果说1791年宪法是崇尚权力分立的孟德斯鸠主义的试验场,1793年宪法就是孟德斯鸠主义的火葬场。1793年5月10日,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宪法》的演说中,谈到分权原则时说:“权力均衡,在当时的风气似乎要求我们这样对各邻国表示尊敬的时候,在我们过分的自卑感使我们赞美外国一切稍微有点像自由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醉心于这种制度。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察觉,这种均衡只可能是幻想或灾难,它会使毫无作用,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使相互竞争的 各种权力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同这种平衡暴君权力的安排有什么相干呢?需要 彻底铲除;不应该在领主间的争论中寻找喘息的机会,权利的保障应当是 自己的力量。”(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45页。)1793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卢梭式宪法,主要体现在坚持,摈弃三权分立,庄严地宣布:“属于。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动摇的和不可让与的 。”(宣言第二十五条)这无疑是卢梭的不可分割思想成分在宪法中的沉淀。革 命过程中,在为挽救社会事业所必须的名义下,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被赋予无限制的 权力(全部权力),“为了捍卫自由事业,国民公会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合理的或强力 的手段”。(注:转引自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载楼均信 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这种“ 立法中心主义”势必导致孟德斯鸠所崇尚的“公民自由”的毁灭。对此,当代新自 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哈耶克作过精辟的:“法国大革命曾经试图为增进个人的权 利而树立法治,但其目标并未实现,原因在于大革命的一种致命信念,即既然所有的权 力都已置于手中,一切用以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措施也就不再必要了。”(注:转 引自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页 。)
(二)不可代表论与直接制的建立
卢梭明确指出:“正如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也是不能被代表的;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 个意志,而绝不可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的代 表,他们只不过是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 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自以为是自由的;他 们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 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25页。)“立法权力是属于的,而且只能属于。”(注:[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只有在全体都参加立法的国家 里,人们的自由、平等才能得到保证。“雅各宾派从卢梭那里吸取了有利于由投票 批准法律和选举公职人员的论据”(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卢梭的忠实学生的马拉, 认为必须规定,代表们通过的法律只有在拥有的民族批准以后才能生效。由于提出 了这一全民批准法律的要求,因此马拉远在革命前就已经事先想到了1793年的革命宪法 的一个条文。”(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 3年版,第288页。)这就是后来宪法规定的第十条“议定法律”。1793年的雅各宾 宪法在交全民投票时,获180多万人拥护,反对者只11万人。在选举公职人员方面,179 3年宪法规定,的包括法国公民的全体(第七条),直接选任代表(第八条) ,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公共仲裁人、刑事审判官和大理院的审判官(第九条)。
“如果当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 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 而只有一个惟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 意见。因此,为了很好的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并且每个 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版,第39—40页。)在卢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公开性”不仅被视作大众行使自 身权利的依据,而且被看成是杜绝政界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本手段。具体表现在:(1)反 对程序中的无记名投票,复归古代的唱名、鼓掌表决,1793年宪法甚至要求民事仲 裁人“进行判决的评议是公开的,他们应高声发表意见”(第九十四条)。(2)国民议会的会议应当是公开的(1793年宪法第四十五、四十六条),允许民众旁听,导致实践中旁听者通过鼓掌或呐喊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允许群众举着武器在议会大厅内列队,直接左右了议员们的意志。(3)1793年宪法还废除了议员的“立法豁免权”,将民众对代表的监督扩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总之,卢梭的原则,这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拉卡纳尔写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革命替我们阐明了《社会契约论》。”(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6页。)
(三)革命权论与起义权的宪法确认
卢梭十分重视对暴君的革命权,强调这是社会契约赋予的权利。他认为,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树立”,当君主而用个人意志代替公意、篡夺国家侵害的生存要素(财产、自由和生命)而出现暴君时,完全违背了的目的,为维护社会契约、和其他权利有权用暴君。“从篡夺了的那个时候起,社会之约就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当然地又恢复了他们天然的自由,这 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根据义务的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当被迫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一旦公民可以打 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 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他们的自由的,所以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 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 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9页。)从而表明,通过暴 力革命恢复自己的社会秩序,这是的神圣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
在卢梭伟大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自此以后民众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5—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公然侵入王宫,试图通过把“面包坊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即国王、王后和王子)带回巴黎置于直接监督之下,以使困扰百姓多年的“面包问题”得到永久性的解决。“起义权”的概念由此在群众心目中被具体形象化 了。它将推动群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1792年8月10日,起 义者冲进立法议会所在地——“马奈兹”大厅,抓住路易十六、解散议会,废黜君王, 诞生了法兰西共和国。巴黎人把这一天的革命叫做“无套裤汉的革命”。
在讨论1793年《宣言》的过程中,罗伯斯比尔等人不满足于只承认“以合法手段反抗的权利”,也反对把反抗说成是“自然权利”,力图赋予反抗以一种合法形式,强调“把反抗权套上合法的形式是专制的最后表现”。(注:[法]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其结果是,1793年宪法前的《宣言》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强化了群众的革命起义传统:“反抗乃是另一些的当然结果”。“当社会成员之一受到时,即是对社会的。当 社会受到时,即是对其各个成员的。”“当违反的权利时,对于 及一部分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从此,法国难有小,要有就是大了,表现在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经常会出现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纷纷在各区聚集”。也许看到“革命”具有导致政局不稳的后遗症,1795年的《宣言》对“起义权”只字未提。但从法国革命到后来的“巴黎公社”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交接,和却演化成了交替拉锯的“习俗”。
三、卢梭的爱国教育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与卢梭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王朝国家时,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这一口号。卢梭一方面赞同和继续着这种批判,同时又更加深化了这一理论主题。在他心目中,祖国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他给祖国这样定义: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司法、、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为了加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证明,卢梭的这一教诲在大革命中为革命者所遵从。
(一)公民宗教理论与法国的“最高主宰崇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章中说,为了国家的巩固,增加一些宗教的动机是必要的。法律除了本身产生的那种力量以外,还应有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宗教给它的。国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要使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可以促使他热爱自己责任的宗教。天主教不能成为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精神只有利于暴君制。对于国家来说,宗教的教条只有涉及到公民的道德和责任时才是有意义的。“最高权力应当规定一些决定公共行为的教条,如果没有这些教条就不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它们的总和构成‘公民宗教’。这些教条非常简单,这就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和关怀备至的神明的存在,未来的 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在其他方面每个人都可 以持不同的见解。但是国家有权驱逐不信仰公民宗教教条的人,——这不是因为他没有 信仰,而是因为他反对社会。同样地,如果有人已经公开声称信仰这些教条,而他的行 为却如同不信仰这些教条的人一样,那么国家就应当处以死刑,因为他在法律面前说了 谎。”(注:《卢梭全集》法文版,第7卷,第258—259页。转引自[苏]沃尔金:《十八 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1页。)在卢梭看来,公民宗教 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敬拜仪式,它是一种没有教堂和教士的宗教,其惟一的教职人员 就是行政官,公民向行政官公开表明他遵守《信仰宣言》忠于国家和个人道德有关的条 款。公民信仰宣言的条款“应由者规定”。(注: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5—186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罗伯斯比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在宗教思想 方面也步他的后尘。”(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第233页。)“卢梭学说中的‘宗教认可的合法性’,曾明显而又令人信服地被罗伯斯比 尔的公安委员会的宗教政策证实了。”(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 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页。)这就是“最高主宰崇拜”(注:1789年的《 宣言》中就有“最高主宰”的提法。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仍处于宗教不可缺少的 时代,起草者还不可能提出废除宗教的口号。从理论上说,“最高主宰”不是天主教中的上帝,而是出自卢梭的自然神论和人格化的神。从策略上看,当时法国大多数人仍然是天主教的虔诚信仰者,这种提法既照顾到信奉天主教人们的宗教感情,又同时满足了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教人们的要求。不过,“最高主宰”是什么,只能处在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而随着天主教的摧毁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让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样 子出现在法国人面前。)的确立。
1794年花月18日(5月7日),罗伯斯比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报告,并附《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历史学家将其总称为“花月法令”。这是罗伯斯比尔一生中的代表作品。在报告中,他凭个人的信念并从出发,希望由此树立一种能淳化风俗、强固道德信仰的宗教:“在立法者眼里,凡是对人有用,对实践有益的就是真理……对最高主宰的存想意味着对正义的不断存想;因此,最高主宰的观念是社会的,又是共和主义的。”(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7页。)“神的存在,来世之说,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4页。)在罗伯斯比尔的建议下,《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获得通过。该法令共15条,最能说明最高主宰崇拜的性质、目的的有:“法国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第一条)“法国认为,完成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是崇拜最高主宰的最好的方法。”(第二条)“法国认为,在那些应尽的责任中,最重要的是痛恨背信弃义和专制统治,惩罚暴君和叛徒,帮助不幸者,尊重弱者,保护被者,为自己的邻人尽力做好事,并以正直态度对待所有的人。”(第 三条)“择定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为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第十五条)(注:参 见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 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此法令颁布后被制成大 标语、大幅宣传画,覆盖所有的大街小巷。在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这一天,法兰西共 和国举行了隆重的开教大典、和。全国的共和国庙门额上刻着“法国承认 主宰及灵魂不死”。最高主宰的崇拜产生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武装的力 量,相当数量的农民天主参与了叛乱。
(二)重视教育的思想与宣言的传播
卢梭认为,国家依赖着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对此,必须要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共和紧密联系起来。而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从儿童时代开始,教育他们爱自由、爱法律、爱祖国。(注:参见[法]卢梭:《论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他还列举了具体的内容,如要让孩子10岁时知道祖国所有的物产,13岁知道祖国各个省份、道路和城市,15岁时通晓祖国的整个历史,17岁时知道所有的法律。
1793年12月1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公共教育法》。其基本原则是教育免费并且公办。不满6周岁的儿童不得入学,儿童在8岁前即应入学,家长、监护人或保护人不得在儿童于学校至少连续读满3年之前让其退学。家长、监护人或保护人应将儿童或受保护的未成年人送入初等学校。如有不遵守规定者,应受警事管教法庭的检举。如其不遵守的法令的动机被认为并非正当时,对初犯者处以相当于其所纳税款的1/4的罚金;如属再犯其罚金加倍,违法者将被视为平等的敌人,并被剥夺公民权10年。国民公会责成教育委员会提出公民教育中绝对必需的知识的基础书籍,并宣布此类书籍首要的几种为《宣言》、《宪法》和《英勇善行一览》。(注:转引自《关于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文教政策》,杨子竞译,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在革命过程中,人们教孩子们学习《宣言》和宪法,孩子们登上讲坛宣读宪法。(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三)大众节日思想与国家激发的理想精神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卢梭还提出要通过节日、公共庆典等方式来培养所有公民的爱国热情。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起被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注: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3页。)
罗伯斯比尔把规定国家节日作为公共教育的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说:“应该有整个共和国的普遍和隆重的节日;每一个地区,也有特殊的节日,它们可以是一些休息日,也可以代替那些由于紧张而取消了的原来的节日。”“所有的节日都以唤醒使人类生活具有美丽和光彩的普遍感情,唤醒对自由的热忱、对祖国的爱和对法律的尊重为目的。”(注:波普朗编:《罗伯斯比尔选集》,巴黎1973年版,第176页。转引自陈崇 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 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他的建议下,1794年5月7日国民 公会通过法令,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每年都将庆祝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793 年1月21日、1793年5月31日这些节日。(注:这些日子分别为攻陷巴士底狱日,巴黎人 民起义、废除国王日,处死路易十六日,雅各宾派开始执政日。)法兰西共和国将每十 天分别纪念36个全国性节日。(注:这些节日包括:最高主宰和自然节,人类节,法国 节,世界自由节,热爱祖国节,憎恨暴君和叛徒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光 荣和不朽节,友爱节,艰苦朴素节,勇敢节,诚实节,英雄主义节,大公无私节,禁欲 主义节,爱神节,夫妇挚爱节,父爱节,母爱节,孝顺节,儿童节,青年节,成年节, 老年节,灾祸节,农业节,工业节,祖先节,后裔节,幸福节。)可以说,几乎达到了 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比尔都亲自过问,节庆活 动通常都设计成大,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 ,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
结语
1789年巴黎攻克巴士底狱后,举国欢腾,取得革命胜利的为此特制了一种扑克牌。在扑克牌的梅花k上画的是卢梭立姿全身像:身着红色长袍,手执一本《社会契约论》,面部表情作沉思状。像的两旁,一边写的是“让-雅克·卢梭”,另一边写的是“智者”两个字。
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为卢梭立一座雕像。
1793年春天,国民公会决定把卢梭尊为先贤。
1794年10月15日,卢梭的遗棺从落葬地起柩。次日,国民公会的一个代表前去接收卢 梭遗骸,仪式在《乡村牧师》的音乐中进行。17日,卢梭落葬于先贤祠,国民公会主席 坎巴塞雷斯宣读葬词:“我们向卢梭致敬,我们的再生——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 观念、习俗所发生的一切幸运变化,都归功于他。”
卢梭的特殊人格已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卢梭的名字永远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第十七篇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_西方哲学论文
(一)学问的生、死、原、伪与“交配”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WwW.meiword.COm到了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古希伯来人的原始神学又如何呢?耶稣之死(公元三十年)象征着原始神学的第一次死亡;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犹太教的神学经过了一次再生,变成了伪人学的教神学;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中世纪后期,由阿奎那出面使神学又一次再生,变成了伪哲学的经院派神学;再经过新教改革运动,伪哲学的神学也终于走到了垂死的尽头。
古希腊人的原始(自然)哲学又如何呢?古希腊人的城邦社会帮助产生了哲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城邦社会完结了,自然哲学的时代也跟着完结了;从希腊化时代到古罗马帝国,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学人的手中,原始的哲学变成了伪人学的道德哲学;到了西方中世纪时代,经院派哲学其实是打着哲学招牌的伪神学;直到十六世纪由笛卡儿创生了西方近代新的(自然)哲学的时代。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笔者本人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 (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中国古代人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它们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发生了时间性的历史演变。这种合流的历史演变的结果,就像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变迁,不仅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在它们的交配和互补中产生了全人类历史的大质变,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交和起始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均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等。其中尤其必须提到笛卡儿,他被人们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开启了对人性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学、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的大发明和大创造的时代,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学与,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共同产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方面,只具备孤立的原始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与西方人相抗衡的,仅仅靠单一的原始人学以及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中国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近现代人类理性的工具——科学与。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神学(但不缺乏迷信),更缺乏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又自行死亡了呢?
(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文本的自由想象去动摇社会不可或缺的理性基础,以“反人道主义”的名义抹杀个人价值和人的尊严。所有这些,都是用现代艺术的价值观来否认或削弱其他两个领域的价值观的做法,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说一千,道一万,西方哲学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确已经彻底地死了。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有什么疑义呢?
问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将应该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是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破坏呢,还是在种种危机面前,通过思维方法的创新,通过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踏着哲学的遗体推出人学的逻辑,以解决新世纪人学的问题!
笔者自然认为应该是后者,而且还坚信,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思想者也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利奥塔:《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参阅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26页。
〔2〕转引自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182页。
第十八篇 内容“ 述”形式 (上)——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_西方哲学论文
从来的哲学家总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重要的却是改变世界。
——
摘要:本文从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全方位阐述了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它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关键词:内容|形式|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
美学,乃艺术之哲理,基于艺术本身,并非哲学之机械成分。www.meiword.com所谓艺术,这里取其广义,容纳音乐、诗词、绘画、小说、戏剧电影等。这些艺术门类使人们感受到“美”,究其原因,并非在于创造某种艺术效果之前,艺术家持有某某“正确”的理论,恰恰相反,艺术是“不讲道理”的。艺术的美在于依照其不同门类的特点,使人们的耳朵和眼睛等感觉器官获得不同性质的“物质”享受。所谓“讲道理”的艺术,这里特指欧洲艺术哲学“观念在先”的传统,它的要害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模仿”说。“观念在先”与“模仿”的一致性乃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并不单纯局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换句话说,这里的“一致性”既包括唯心论,也包括唯物论和其他哲学派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无论就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来说,音乐表达了人的某种感情,诗歌也是这样,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音乐通过旋律的变化、诗歌借助于词语制造的类比隐喻,但两者都表述心声;至于绘画、小说、戏剧的传统也是一致的,即通常一定要有一个“原型”或者“模特”(无论是逼真的还是传说中的),绘画、小说、戏剧语言的任务是与“艺术语言”自身之外的因素相一致。以上“一致性”的艺术情趣与欧洲历史上制度乃至各种思潮的变迁无关,其中也不乏近代以来个别有胆量艺术家的异端“邪说”,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欧洲传统的艺术情趣。欧洲艺术情趣的真正变化酝酿于19世纪中叶,蔓延于整个20世纪,时至今日,其花样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追根寻源,探讨不同艺术门类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尝试的性质仍旧是哲学的,它立足于“理解”,但却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一 耳朵的物质趣味:音乐
奥地利音乐学家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于1854年出版了极具现代艺术色彩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这本小册子预见了20世纪欧洲音乐的走向。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立场简明扼要::"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这句简单的表白背叛了欧洲传统音乐美学的总体倾向——这种倾向强调乐音在情感中制造的效果。对旋律的解释总要依附于表达感情,否则,好像音乐家就会无所适从.这个道理不仅涉及到音乐创作和欣赏,而且事关各种艺术本身。
在审美艺术中,传统的观点把诉诸于纯粹感官的要素称为"形式",比如,音乐中(乐音,等)的音响,绘画的线条轮廓色彩,诗歌小说戏剧中各种可听(说话)和可视(文字)的语言或相当于语言的因素(肢体语言之类)本身。让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这里所谓的"形式",其实统统是纯粹物质性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是艺术中"唯一真实"存在的要素。我们不知道音乐表达了怎样的感情,只是听见了乐音;不知道图画描的是什么"东西",只是看见了线条色彩和轮廓;同样道理但需要认真思索才能澄清的是语言的艺术----这里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而且是语言自身(语言自身也是物质的各种要素)。无论是逻辑的语言、说话、文字还是肢体语言,语言自身就是一种艺术。这是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使然,语言自以为表达了某种意义(所指,真理,观念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表达,没有通达,语言并没有能力指称超越自身之外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传统哲学或艺术中所谓"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似乎被以上各种"物质形式"所代表或表现的"事物",比如,乐音表达了某种情感,线条色彩轮廓描绘了画布外的事物或模特,各种语言的技艺表达了某些观念等等。我们注意到,以上一切"形式"的要素都是具体的,有诉诸感官的形状或音响之类,而"内容"的要素往往是“抽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传统的说法,"形式"要服从"内容"(西方哲学史中"形式"与"内容"的用法在很多情况下非常混乱,比如柏拉图的说法与我们正相反,他的“理念”或事物的"形式"乃是我们所谓"内容")、表达者要服从被表达者、"物"("唯物")要服从"心"(唯心,其性质是观念的)。显而易见,按照我们的标准,传统的"唯物主义"其实不过是"唯心主义"。现在,汉斯里克要扯断形式与内容的传统关系,他说得非常简单,音乐的美就在于乐音本身,乐音不表达感情,不依附乐音之外的任何因素,乐音就是音的前后,升降,协调,对抗,追逐,飞跃,消失——这些不但是音乐的形式,也是音乐的内容,因为除了音响之外,音乐再无其他内容。汉斯里克这样说:“玫瑰发出芳香,但它不是以‘芳香的表现’为它的内容的;森林散布阴凉,但它并不‘表现阴凉’。我特别反对‘表现’这概念。”为什么呢?因为“表现”把事物本身人为地一分为二,把本来并没有联系的因素统一起来,构造幻象。音乐是不可说的,音乐不但摈弃感情,也鄙弃形象和思想。天才作曲家对声音有敏锐的幻想力,这就是他的“直觉”或倾听能力,这是对乐音的“直觉”,与依附于“看”的感觉情感理智没有关系,乐音没有任何目的,也不是教育人鼓舞人的手段,目的和手段的说法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其他的目的给音乐戴的“高帽”,使善良的人们信以为真。事实上,怀有不同目的的人,经常把同一段优美的乐音,应用在不同的场合和画面,但这与乐音本身没有关系。由于千百次的虚假宣传,汉斯里克不得不以极大的耐心才能让读者相信,听众只是听到了乐音,而没有“听”到任何感情,虽然音乐可以唤起情感,但是音乐的科学性却只在于“耳朵的物质性情趣”。汉斯立克写道,“窃窃私语?这是有的:——但不是‘爱慕’的窃窃私语;风暴,的确有的,但不是‘战斗豪情’的风暴。音乐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它能窃窃私语,也能作出暴风雨或沙沙的声音,——但只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把爱憎带了进去。”‚乐音给听众造成表达了某种感情的错觉,乃在于音乐奏出了”力度”——快、慢、强、弱、升、降——这就是“耳朵的物质性情趣”,用哲学语言,它们是声音在时间中不同方向的运动。这与任何艺术企图无关。把不同力度的旋律解释成欢快或者悲伤,就像服装和绘画中总用红色表示快乐,白色表示纯洁一样,只是一些心理习惯的约定,并非有真理可言。“表达”或“表现”的音乐美学是人们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心理习惯。相比之下,汉斯里克用“象征”一词代替“表达”:“表达”给人的印象是“必定如此的联系”,“象征”则在艺术和人的感受之间建立偶然的关系,具有神秘色彩的、没有联系的联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黄色体味嫉妒和色情、从g大调听出忧伤,或者由青松油然滋生哀悼之心。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知识分子的“解释”功劳,与乐音、色彩、静物无关。音乐家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不会“解释”,只会作曲,作曲的过程是解释不清的,平庸与天才作曲家的区别在于把乐音或旋律化作丰富多彩的能力,处理乐音高低长短无数中断与连接的能力,听出声音最微妙的差异之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感情丰富之能力,因为正如汉斯里克所说,天性富有感情的女人,在作曲方面却远不如男性——作曲过程中的主观性,比如情绪激昂之类,恰恰是“科学”的作曲应该排除的因素。同样的道理,汉斯里克提出,真正的音乐欣赏不是以事先的“解释”心情“有选择”地听,而是静观(静听,这样的态度像是现象学的)—— 冷静,没有感情(无我境界),从而像变化声音要素的魔术,拆解和变化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训练出一双最微妙和发达的、具有“物质”情趣的专业耳朵——它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因为乐音或和声并非自然声音的模仿,单纯的自然声音像是“同声齐唱”,而和声是不同音调(像是有不同源泉的语言)的混合,它来自异域。
我们进一步从列维-斯特劳斯(以下简称“列氏”))佐证汉斯里克的态度,因为列氏从结构主义立场19世纪以来欧洲音乐,它们之间有相似性。汉斯里克的音乐立场有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立场:语言和乐音一样具有约定的性质,声音与其代表的对象之间(就像音乐旋律与某种抽象的感情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声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约定的习惯(尽管语言约定的习惯更为持久和牢固)。俄裔语言学家雅克布逊进而用音位学音乐的“约定俗成”性,音位学不包括词汇,音符的结合不同于语言,就像节拍和旋律不属于语词(因为相比之下,词语是套语)。换句话说,与语言对比,音乐更加排斥表达、模仿(就像我们以下将要的福柯的立场,福柯认为可述的与可见的之间从来就不一致,人们从来没有真正画出所见到的东西,也见不到说出的东西。展开将,福柯的议论也适合音乐的“听”和“想”之间,音乐没有模仿任何感情却能使我们喜欢)。这样的立场之所以困难,乃在于人的精神总是自发地从音乐中寻求解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情趣,但“形而上学的情趣”与现代欧洲艺术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后者的态度只是排斥艺术“解释”的“唯一性”而诉诸于任意性。列氏在其美学著作《看·听·读》第四章“话语与音乐”中甚至追溯到法国18世纪音乐家夏巴农(chabanon 1730-1792)。夏巴农与写了《达朗贝尔之梦》的狄德罗一样,都对蜘蛛和蜘蛛网发生浓厚兴趣,他说“蜘蛛就这样位于它自己网的,同各条线路保持沟通,因而生活在每条线路之中并能(如果这些线路像我们的感官那样受激励)把其他线路可能给它的感受传给其中之一。”这是对欧洲现代音乐等艺术情趣的绝妙阐述:音乐并不一定与一种感情联系,就像汉斯里克说过的,乐音可能像窃窃私语或暴风,但并非一定表达情人的悄悄话或战斗豪情。于是汉斯里克干脆说,乐音与感情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们这里也可以换个角度说:乐音可以与感情有任意的关系,就像蜘蛛对蜘蛛网的感觉是四通八达的,永远还有料想不到的线路。我把这称为微妙精神或情感的延伸,它在下述波德莱尔式的“通感”中得到了验证(把从不同的感官得到的不相像的感受体味成相像的,列氏说这样的“感受沟通”要有理智的参与。这也打破了福柯所限定的界限,比如虽然在听音乐,却好像“看”,但这种联系是任意的,并非真的看见了什么)。列氏指出,不同感觉通路(像蜘蛛的线路)之间的关系是形式的关系,不是内容。换句话说,从听到看或想,只是开创新的通路关系,关系就是形式。
雅克布逊的音位学之所以是结构主义的,乃在于与词语比较,音乐更符合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在音乐中就是乐音)的任意性与差异性原则,列氏这样说:“音乐给人的乐趣有赖于——尽管每个音在本质上毫无价值——这个音前面的各个音和它之后的各个音。”‚音乐比语言更能说明语言的特点,而音乐自身却不是语言。列氏引用了夏巴农一句尖锐的话表明他自己的态度:乐音并不是事物的表现,而是事物本身。换成结构主义语言,语言和乐音一样都是任意的,都不来自对自然的模仿。夏巴农对纯器乐的描述也同样使用于语言,它们都使听者和读者的精神无着落,处于摸不透意思的忐忑不安之中,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耳朵和头脑,才能摆脱习惯的束缚,得到特殊的乐趣。音乐与语言的主要差别,在于语言有音乐所不具备的约定俗成性质。
二 诗句与通感:打通不同感官之间的线路
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开创的象征主义诗歌对现代法国及欧洲文学艺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们的创新也是形式上的,即诗“句”或诗“词”的连接出乎读者的预料。诗人下笔时,诗“词”决无事先想好的寓意,比如读者读到“头发”,万不可与头发的习惯所指或寓意联系起来,绝对猜不出诗中与“头发”连接的词语。波德莱尔在“头发”一诗中把清香、乌木色的海浪、风帆连在一起。好像诗人来到“一个喧闹的港湾,可以让我的灵魂,大量地酣饮芳香、色彩和音响。”此刻的感受叫做“通感”(correspendances)‚,波德莱尔称这样的写诗技巧为“奇袭”(coup de main)。在欣赏效果上,读者的“精神”在前一个词上还没有着落,就已经接上一个不搭配的词变形为另一个形象,依此类推。在技巧上,变换词义的速度奇快(有时则巧妙利用一词多义)。所有这些,在形状上构成一幅超现实主义绘画,就像啤酒瓶的一半变成了胡萝卜。波德莱尔大量的利用这样的手法,描写绝望(恶)中的美丽(花)、的爱情,其感受令人震惊(这些诗作“经验”并非真的经验,它在柏格森与普鲁斯特的“绵延体验”中有回应,其写诗技巧犹如狄德罗认为演员在表演时应该“不动心”),像是“鬼鬼祟祟的快乐”,又像被意外的词绊倒。波德莱尔的创新在“形式”,即词与物之间的断裂,他的诗句在这种断裂的缝隙处最激动人心,它们是以“危机“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经验”——普鲁斯特称这种经验具有宗教仪式气氛的“气息力”(表现在非自主记忆中),它能穿越距离和不透明性体察某种似乎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瓦莱里称这样的“气息”混淆感觉和梦,梦中的“我”与所看见的东西之间是平等关系,就好像“我”所看见的东西像“我”看见他们一样看见“我”,这创作手法同样来自波德莱尔(诗句“人穿行于象征之林,那些熟悉的眼光注视着他”ƒ)。换句话,象征主义的“象征”与“通感”是同义词。我们在波德莱尔诗作中涉及“看”的语境中,总与这样的象征相遇(人眼的延伸,看见本来看不见的东西)。除了世俗的眼睛,人还有一双全然不知道距离的眼睛,荒漠冷淡的眼睛,就像镜子里正在盯着我的眼睛“看”的“我的眼睛”。
浪漫的卢梭曾经感受“瞬间”的幸福状态,痴迷的灵感状态,“无心”的状态,没有词语可以到达的状态,这时的词轻飘飘,它不代表一个对象,因为词只是唤醒“启示”的“物质”要素。卢梭对笔下的“词”能唤醒“什么”根本无法把握,那写字的手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同样,“波德莱尔肯定有某种指向外部自然的超然意向性,不是把自然当作以自在和自为方式存在的实在,而是作为类比的巨大贮藏器和激发想象的物。”„打开世界的另一窗口,顺着诱惑走,在不同的可能性中抉择,一个词生育另一个词,词序新的排列不断生出未知的意义。诗“词”的选择是任意的、无法预见的、仅存于瞬间(故好像不是人手的能力),滋生一个未曾污染的境界——这是启蒙时代精神自由的延伸,读象征主义诗歌犹如中了魔法。不知它在黑暗,抑或在光明。
诗的功能在于暗示,也是上述的“象征”。“暗示”是难以言传的,故“象征”具有神秘性(这与中国古诗词的“比”“兴”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法文“poesie”词源学的含义是“创造”(creation)。诗比其他文学类型更能创造未曾有过的内心状态(境界),更能透过“微光”窥见新的情感世界——借助于通感,不相关联的词相互替换,它是语词不合常理的增补——波德莱尔借用这种手法写下他最有名的诗篇“parfum exotique”(异国的清香),他献给与色情的化身、他最挚爱的混血姑娘让娜·迪瓦尔。波德莱尔沉浸于就像在桃花梦中游荡:“当我闭上双眼,在暖秋的晚上/闻着你那温暖的的香气/我就看到有幸福的海岸浮起/------而那绿油油的---清香/在大气中荡漾,塞满我的鼻孔/在我心中混进水手们的歌唱”…的香气飘向异国海盗港湾,在接下的“头发”一诗中(咏娜·迪瓦尔的头发)有把诗人带回充满阴暗的卧房。清香--海岸-阳光-女人的眼睛天真-男人们身体瘦长/头发-沉睡-卧房异邦-丛林-发辫-海浪——接二连三的“隐喻”让读者应接不暇(在这些语境中,隐喻也是通感的同义词),又不同于一般的隐喻,因为其中哪个词也不是“词源”,词的不同形状(比如发辩-海浪)叠加一起,相互滋生高难度的象征,不是命名,也不是解释,读不出准确的含义。另一个象征派著名诗人魏尔兰(verlaine)以另种方式发展波德莱尔的手法,他的一首《秋歌》只顾及音韵朗朗上口:”les sanglots longs/des violins/de l’automne/blessent mon coeur/d’une langueur/monotone”(抽泣慢/小提琴/金秋/伤我心/倦怠/真乏味)。这几乎不是诗,因为词之间不但不搭配,其相互连接也不像“发辩-海浪”那样能相互唤醒,选择某词的唯一理由就是有开口元音o或鼻元音on,对这首诗的所有其他提问都没有答案。‚这又有些像小时候听女孩子跳皮筋唱的儿歌:“小土豆/西瓜皮/马莲开花二十一”这样的语词连接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它破坏了旧的用词习惯:因为这里的词被念叨时并不是垂直指向词的含义(并不代表一个对象或观念),而是从横向不相关的词中获得“尖锐”却不清晰的异象(“武,舞也”参见页下注释),其中的和谐是在声音的运动中获得的,流矢的时间由于其因素的变幻(武-舞)而成为空间的(或立体的)象征图画,这是另一种心理习惯,却也是自然发生的(详见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寻找失去的时间》)。
三 绘画:“这个不是烟斗”
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有一幅名画《这个不是烟斗》,它的画面再简单不过了:黑板上的线条组成了一个逼真的烟斗模样,黑板下方的小字却是“这个不是烟斗”。此举决非画家恶作剧,其深刻的艺术哲理让福柯折服并写了画评《这个不是烟斗》。福柯的道理简单:可见的(物)与可述的(词)之间从来就不是一致的。福柯这番话正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哲理,比福柯早半个多世纪,法国诗画家兼剧作家阿波利奈尔一句看似玩笑话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们不满意用双脚走路,于是发明了轮子,但轮子和脚一点儿也不像。又比阿波利奈尔早不到半个世纪,法国诞生了惊世骇俗的印象主义画派——所有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印象派画家马奈、塞尚、莫奈等人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与马拉美属同时代人,他们之间有超出人们意料的相互影响。马拉美这样回答一位蹩脚诗人(这人试图写14行诗,他向马拉美抱怨说他有好的念头,却总写不好):“你不该用观念写诗,而要用词------(又从词过渡到绘画——引者)肯定有某种物质事实落在视觉上(词与绘画的色彩都是物质——引者),绘画的技术(它的基本原罪就在于伪装了这门艺术的起源,绘画是由油布和颜色组成的艺术——原注)诱惑这些傻瓜相信外表的相像,这样的看见过分简单化了。”„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指明了马奈作品的创新之处,就像《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一书作者所言:“白色在它成为一块白颜色的布之前就已经是白色。绘画的快乐远大于模仿的快乐”…这也是莫奈、梵高和整个印象派遵循的原则,它让画笔从模仿中逐渐解放出来。像马拉美的象征派诗句一样,印象派绘画也离开了模特或透视的“科学唯物主义”,认为绘画的起源不是“模特”,而是色彩本身,色彩是画家的眼睛真正看见的东西。色彩不是连接画家与模特的桥梁而是屏障。
印象派绘画之后,20世纪初始,相继有阿波利奈尔的“画诗”,从中并列走出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欧洲绘画流派。其中阿波利奈尔的“画诗”功劳极大。“画诗”乃阿波利奈尔所谓“美丽的象形文字”(galligrammes)之简称,这是他的作诗方法,他把诗句“我抽烟斗”用同样的拼音字母排列成烟斗形状,就好像一幅由美丽的象形文字构成的图画,一反欧洲人阅读拼音文字时只考虑字义,因为文字变成了形状,可“述”的变形为可“见”的,而“可见的”(画)可以与“可述的”(字)所指对象(一个模特)无关——这正是现代欧洲绘画的基本原则,画布上的构造与画布外的世界决不一样。达达主义的“达达”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意味的“名字”,它认为绘画艺术是“伪造”(伪造就是创造)的代名词,所以透视画是最糟的画,就像日常用语是最糟的言语,因为它不如照片,因为它是套话。真正的画与真正的语言与自然和自然语言一点儿也不像(这又与弗洛伊德立场并行不悖,因为弗氏诉诸的潜意识等于说,意识的本色就是“伪造”,也就是不一致,不可认真)。现代欧洲画家辩解说,绘画并非自然物的解说词,无需讲理,就像聪明的作家挑选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词,而毕加索作品中最多的裸女画则像是出自一个瞎眼的“老色鬼”之手,这些立体且变了形状的和,与裸女们身体的其他部位绝对不成比例(因为前者大,印象深),这些画不是“看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是“心灵”消遣性质的冒险,画得美丑或相像并不重要,画家梦幻中的那些形状更重要,它带给人浑浊且没有逻辑的快乐(像《恶之花》),逃离了人们早已习惯的万有引力。所有这些艺术企图,乃是有意的制造晦涩。作为对毕加索有意制造晦涩的解释,他的立体画中那些变了形状的和象征着一股“看不见的力”,这也是梵高的名画《向日葵》的魅力所在。画家和欣赏者的眼睛只看见感受的形状,至于这些形状是否代表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则是无关紧要的。
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家布勒东“篡改”了的名言,声称对(艺术)世界的解释远不如对它的改造更重要。布勒东是正确的,艺术的本质是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哲学解释都永远落后于艺术,除非哲学自身演变为艺术。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汉斯立克著:《论音乐的美》,音乐出版社,1982
2, 列维-斯特劳斯:《看·听·读》,顾嘉琛 译,三联书店(),1996
3, (法国)波德莱尔 著《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 译,文学出版社,1991
4, 本雅明 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 魏文生 译,三联书店(),1992
5, marcel raymond,from baudelaire to surreali, wittenborn,1950
6, deborah a k aish , la metaphore dans l’oeure de stephant mallarme , slatine reprints , 1981
爱德华 ·汉斯立克著:《论音乐的美》,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 同上书,第28页。
转引自列维-斯特劳斯:《看·听·读》,顾嘉琛 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87页。
‚ 同上书,第89页。
(法国)波德莱尔 著《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 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9-60页。
‚ correspendances,这个词在法语中的含义是对应、相称等,《恶之花》中译本把这个词翻译为“感应”,也比较符合波德莱尔的原义,“感应”是在本来没有关系的两个事物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比如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
ƒ 本雅明 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 魏文生 译,三联书店(),1992,第162页。
„ marcel raymond,from baudelaire to surreali, wittenborn,1950,p15。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普鲁斯特的巨作《寻找失去的时间》,主人公从马塞尔从小甜点的香味联想到教堂的种声。从可见的到不可见的,又参见相面术和现象学。
… (法国)波德莱尔 著《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 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deborah a k aish , la metaphore dans l’oeure de stephant mallarme , slatine reprints , 1981 p 4.
‚ 这并非玩笑,我在学友李河处得知,远在西方象征派诗人之前的中国汉代学者刘熙所作《释名》中用大量例子描述了汉字中“音谐义近”的释义方法:“道者,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得也,得事宜也;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义,宜也------智,知也------经,径也-----。”参见《释名》卷四、卷六。这里,中国古代智慧的关键词“道、德、武、仁、义------”等等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生义。
„ marcel raymond,from baudelaire to surreali, wittenborn,1950,p 360。
… 同上书,第360页。
第十九篇 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_西方哲学论文
哈伯馬斯(j. habermas 1929- )是當代哲學大師、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哈伯馬斯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並在靠近科隆的古倫梅巴斯(grummerach)地區的一個小鎮裡長大,1949年進哥廷根(gottingen)大學學習,1954年在波恩大學完成博士論文,1956年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思想家阿多諾(t. adorno)相遇,成為哈伯馬斯一生的轉捩點,他在學術上的多才多藝使他有資格成為阿多諾的助手,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接棒人[1]。1961年應伽達默爾(h. gadamer)的邀請,到海德堡大學擔任哲學教授,1964年回到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擔任社會學教授,1971年前往施坦恩堡(starnberg)的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擔任所長,哈伯馬斯著名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就是在這裡開始萌芽的,1983年重返法蘭克福大學執教直至退休,20xx年4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到及上海作學術演講。哈伯馬斯是一個多產的思想家,重要著作包括《知識與興趣》、《溝通與社會進化》、《溝通行動理論》等。[2]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通常被稱為「社會批判理論」,這個學派積極關心社會理論問題和從事社會改造活動,特別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ideology)進行批判。wWw.meiword.cOm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哈伯馬斯經歷到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衰落與困境,這與它理論本身存在的弱點密切相關,首先,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對社會科學的理論成果和哲學一直沒有認真看待,亦未與它們作系統性的對話,否則便可藉此來顯示自己的意義;其次,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從黑格爾那裡繼承的理性概念是一種過時的哲學的理性概念,對要求根據經驗實證的社會理論來說,是一筆過於沉重的遺產。[3]對60年代末舊批判理論陷入危機的反思,以及當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哲學的轉向的影響,促使哈伯馬斯將批判理論由意識哲學向語言哲學的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的「革命」,即「溝通行動理論」的建立。[4]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哈伯馬斯致力於意識形態(例如資本主義或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哈伯馬斯把意識形態視為一套因不勻稱的權力關係(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所導致的「系統扭曲的溝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一套有關社會的系統地歪曲了的觀念。哈伯馬斯認為「系統扭曲的溝通」的存在與社會宰制及社會壓抑是一體的兩面;他這種看法基本上是沿襲馬克思(k. marx),突顯出社會對人宰制和壓抑的一面。[5]哈伯馬斯認為意識形態的社會宰制現象是透過語言而形成的,當語言淪為人們藉以「偏頗」地表達個人或某集團的意見(如透過宣傳、大眾傳播媒介、文化產業等),從而成為壓抑別人或其他集團的意見的工具,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境況就是一種「系統扭曲的溝通」,它對個人的需求和欲望會造成壓抑、甚至形成精神病,若表現在整個社會層面而言,便是意識形態的社會宰制現象。[6]對於意識形態的批判與消解,我們並不是以一套新的意識形態來取代舊的、被視為虛偽的意識形態,而是要從肯定人具有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和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可以進行自我反省、並能與別人形成自主、和諧且毫無宰制的溝通情境,在這種「理想的言語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s)下,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與消解。[7]於是哈伯馬斯致力於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
哈伯馬斯認為,語言溝通的基本單位不是語句,而是「言語行動」(speech act)[8],這是語言(language)與行動(action)的統一,「言語行動」包含「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和「非語言力量或部分」(illocutionary force or component),它亦是一種提出「有效性聲稱」(validity claim)的行動,在言語行動中,說話者不但講出命題內容,他還提出「有效性聲稱」,聲稱這句話的有效性,並願意為這個「有效性聲稱」提供所須的理由,這就是言語行動的「非語言部分」。哈伯馬斯認為,「非言語力量」是一種激發(motivate)聽者依說話者的言語來行動的能力[9],因此,言語行動具有作用與功能。言語行動首先要符合文法規則,因而可被理解(comprehensible),然後哈伯馬斯區分三種言語行動,它們有不同的有效性聲稱,屬於不同的溝通模式,對應不同的實在領域,並具有不同的功能:(1)真理性聲稱,說話者聲稱(assert)命題內容是真的(true),這屬於一種認知的溝通模式,對應於客觀世界,具有認知事實的功能;(2)真誠性聲稱,說話者保證(promise)其表達的感情和意向是真誠的(truthful),這屬於一種表意(expressive)的溝通模式,對應於主觀的內心世界,具有表意的功能;(3)正當性聲稱,說話者聲稱言語行動是正當的(right),這屬於一種互動(interactive)的溝通模式,對應於社會世界,它有調節行為、建立合法人際關係的功能。[10]
在溝通行動中,對話者必須預設以上三種有效性條件,即真理性、真誠性及正當性。溝通行動是指「兩個或以上的主體通過語言協調的互動而達成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和一致」這種行動;[11]溝通行動是「主體間通過語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動。[12]溝通行動是使參與者能毫無保留地在溝通後達成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使個人行動計劃合作化的一切內在活動。[13]溝通行動還是通過相互理解、達成意見一致,從而構成他們所從屬的社會集團的社會化的統一的過程,也是行動者在溝通過程中構成他們自己的同一性,證實和更新他們的同一性的過程。[14]當然,溝通行動是一個「理性」的溝通過程,哈伯馬斯承認「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 or rationality),這基本上指通過關於事實、規範及經驗的言語溝通達到相互理解後,必能確立行動主體所共同遵循的行動或價值規範;[15]因此,這是一種真理的共識理論(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事實上,必須在溝動行動中,特別在一個「理想的言語情境」中才能達成共識;這裡「理想的言語情境」指所有參與者都有相等的機會,參與陳述的、表意的和規約(regulative)的言語行動,在沒有任何不公平或強制的條件下,進行平等真誠的溝通與對話,並排除只對單方面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和特權。[16]
哈伯馬斯提出溝通行動理論,除了實現社會批判理論由意識哲學到語言哲學的範式轉換外,以消解意識形態的社會宰制現象和建立合理化的社會,他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透過溝通行動來建立普遍的社會倫理規範,即商談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雖然產生很大的影響,但亦受到其他哲學家的批評,例如美國的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r. rorty)就批評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批評他自以為找到終極真理,其實這純屬「絕對主義」,當然實用主義者是不會贊同任何絕對普遍的道德法則。[17] 註釋:
[1]高宣揚《哈伯瑪斯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頁20。
[2]大陸學者一般將「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譯作「交往行為」,有時則譯作「交往行動」,請讀者注意。
[3]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xx,頁46-47。
[4]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頁53;請讀者注意,這裡用了庫恩(t. kuhn)關於科學革命的述語:範式轉換。
[5]李英明《哈伯馬斯》,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頁80,96。
[6]李英明《哈伯馬斯》,頁96。
[7]李英明《哈伯馬斯》,頁101-102。
[8]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曾受到奧斯汀(j. l. austin)和塞爾(j. searle)的言語行動理論(theory of speech acts)的影響。
[9]j. habermas,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maeve cooke,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p.8.
[10]j. habermas, "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collected in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maeve cooke, p.92;哈貝馬斯著、張博樹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70。
[11]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頁72。
[12]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頁73。
[13]哈貝馬斯著、洪佩郁等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頁142,386。
[14]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頁77。
[15]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頁80-81。
[16]李英明《哈伯馬斯》,頁119。
[17]中岡成文著、王屏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xx,頁110。
第二十篇 走近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_西方哲学论文
以国人对于西学的重视,言必称希腊似属当然,《柏拉图全集》和《亚里斯多德全集》率先出版便是一个明证。然而在所谓的轴心期之后,国人对于西方文明重要整合期的希腊化-罗马哲学却知之甚少。面对一系列庞杂的流派和人物,国人难免一头雾水。国内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零散翻译,如四十年前商务馆的《物性论》,开放以后“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中的《西塞罗文集》、《塞涅卡道德书简》、《皮浪主义文集》,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的普卢塔克《名人传》等,然而毕竟失之于零碎而不成系统。究其原因也许是在世人眼中,希腊化时期,古典哲学的高峰已过,开始凋零。殊不知,这一时期跨度大、流派多、人物繁,恰是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张力有着非凡的意义。相形之下,国内的研究太少,译介太少,重视远远不够。令人欣喜的是,《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已经摆上了学人的书桌,这套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包利民、章雪富先生编译的丛书,很好地弥补了国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缺门。该《译丛》选编视角独到,涉猎内容广泛,值得学人瞩目。
将西方文明喻之为“两希”由来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说,“两希”如西方文明之“两翼”,“两轮”助其前行。然细查国内研究的现状,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却每每只言希腊,当然对于希腊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论对希伯来的研究,这犹如独轮车行路,走起来未免不稳。然而“雅典”还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话题,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君不见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主宰;斯宾诺莎则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欧洲诸多思潮的兴起。wwW.meiword.COm马丁·布伯、罗森茨维格更无疑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此“希”对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编者并不是单纯从希腊或希伯来的经典来编纂译丛,而是从“两希文明”融合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涵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他们独到的学术视野。
整套丛书共选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341-271bc)和卢克莱修(94-44bc)、晚期斯多亚主义的塞涅卡(4bc-ad65)和爱比克泰德(ad55-135)、怀疑主义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ad204-270)、犹太-希腊哲学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106b.c.-43b.c.)和普鲁塔克(ad46-120),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希腊教父哲学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d354-430)。《译丛》涵盖了后亚里斯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流派,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从历史上来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直到公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覆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古典哲学终结。这一段时期被可以看作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中去,事实上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复合文化,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泽普,罗马军团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两希”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译丛》所选取的哲学家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选择面的广泛,很好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侧面,以及教在希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质。就《译丛》选取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后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其二是教神学形成的主流从斐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奥古斯丁,其三是当时重要的哲学家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然而除了从斐洛到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和教的关系外,其他流派与教的密切关系亦是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所谓“两希文明”融合的背后,体现的恰是教神学的产生。这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视角。
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城邦,在城邦丧失性之后,对城邦的虔诚不复存在,个体问题因而彰显。个人开始反省自我,从自身寻找幸福,个人主义开始形成。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转而更为关注伦理和心灵问题,即便是伦理学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社会伦理转变成个体伦理学。哲学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走向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伦理化的哲学最终为宗教的兴起所吞没,哲学家的沉思终不及宗教教义的影响。这似乎是那个时期哲学的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译丛》的编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学的这一走向。
在后亚里斯多德经典的三大流派中,伊壁鸠鲁派认为,灵魂的安宁具有最高价值。所以,研究哲学,通晓自然,就能达于精神的健康,这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享受。对此,《译丛》选取了伊壁鸠鲁的书信、概要和残篇,以及卢克来修的《万物本性论》予以表达。斯多亚派秉承犬儒的倾向,坚持德性人乃是自我克制的人,后受亚里斯多德影响,强调按自然生活。《译丛》选取晚期斯多亚派塞涅卡的《伦理文选》和爱比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而怀疑派则认为文明不足认识事物,对于事物我们一无所知,所以要克制自己,悬置判断,不采取行动,从而摆脱尘世。《译丛》则选取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皮罗学说概要》及其他一些作品。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些思潮作为人类主观的“自由意识”发展而保留在它的精神发展的历程中。但最终还是要走向“苦恼意识”,这就体现在哲学向宗教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斐洛的犹太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在《译丛》中则体现为斐洛的伦理神学文章,以及普洛提诺《九章集》的选本。当理论不再给自己的发展提供动力,哲学就必然在另一种中寻求保存自身,那便是教哲学的诞生,《译丛》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论灵魂的作品则在此列。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不仅有教的形成,世界主义、平等主义、个体主义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思想也初现端倪。教既是彻底的希腊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最能体现“两希”融合世界思潮。
除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体现“两希”融合的当属斐洛、普洛提诺、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希伯来文化以信仰为主,而希腊文化讲究哲学理性。“两希”的融合,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这方面教教父哲学是一个极大的代表。当然就教父哲学而言,无论是希腊教父还是拉丁教父,人物众多,特色鲜明,单单教父哲学就可以编纂几十卷的文集,在《译丛》中则选取了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以作代表。
在“两希”融合这条线索中,首先是斐洛,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首先将宗教信仰和哲学理性结合起来的犹太哲学家;而在宗教史上,他主张逻各斯是上帝和人的中介,被认为是教的神学先驱,教神学之父。就斐洛的方来说,他用喻意解经法来沟通哲学和圣经。正如编者章雪富先生所言:寓意解经法“体现了希腊化犹太人看待自身传统和希腊传统的方式。”那就是把希腊主义和犹太文化结合起来。斐洛认为在希伯来的经典中摩西使用神话、历史叙述、祭仪律法等外在形式表述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是和希腊哲学完全一致的。通过斐洛的喻意解经法,把摩西五经中的神秘含义翻译成希腊哲学的用语,把其中的道德法律内容翻译成了希腊人的哲学语汇。这样,宗教性的事件就开始进入了伦理和知识的领域。斐洛的解经法,开创了犹太教,尤其是教解经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用宗教神学来替代哲学打下了基础。斐洛的喻意解经法坦然面对文化因素的差异性,并把这种差异性表达为跨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固守各自的传统。尽管《译丛》中的这个选本关注的是希腊化犹太伦理的神学本质,但还是深切体现了斐洛对于摩西五经的哲学解释。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而且这个进程还在继续。
其次是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竭力从超感觉世界中引伸出感觉世界。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不仅有哲学的论证,亦有宗教的神秘体验。这样,新柏拉图主义以对启示的需要来代替的哲学研究。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有很强的东方色彩,以至于有人认为普洛提诺首先是埃及的宗教人士,是通过哲学来表达其宗教经验,否则就无法解释普罗提诺的观点。在普洛提诺的学说中三个神圣实体的学说对教的影响最大,他通过重新解读柏拉图,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解决了从终极第一实体“至善/太一”流溢,并逐步下降,经由神圣的第二实体理智到第三实体灵魂,最后进入最低的可感现象世界的世界图像。从而与教圣经中创世纪的教诲相应合。在《译丛》中《九章集》的选本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普洛提诺对于自然、凝思和太一的看法。
其三是代表教父哲学的尼撒的格列高利。在整个2世纪到5世纪的三百多年中教父哲学是“两希”融合的中坚,其坚实的理论后果就是教哲学的产生。教父哲学是在针对犹太教和希腊哲学来为教辩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历史的诡吊在于它恰恰体现的是希伯来和希腊的一种碰撞和融合。在教父哲学中,与拉丁教父较为排斥希腊色彩相比较,希腊教父融合了希腊与教的色彩更浓厚些。《译丛》选取了尼撒的格列高利作为代表,与同是希腊教父的奥利金过分浓厚的希腊色彩相比,尼撒的格列高利所走的道路更中和,在新柏拉图主义和教圣经之间保持了中间道路。在《剑桥晚期希腊和早期中世纪哲学》中他甚至被誉为“第一位教哲学家”。《译丛》中选取了他哲学类、修道类和教义类的代表作中有关人论的问题,体现了从哲学的人论向圣经中“人是神的形象”这个观点的转变。
最后自然是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虽然位列拉丁教父四大博士之一,但是真正说来,他才是整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两希”思想融合的真正代表。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他清楚地梳理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从而在哲学的高度厘清了希伯来和希腊关系的实质。在奥古斯丁看来,信仰与思想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他的名言是“一切信仰都是思想”,并且信仰是以“赞成的态度思想”。思想的前提是信仰,神圣的启示是教神学的必要条件。奥古斯丁坚持“相信,然后理解”,强调信仰的优先地位,但并不排斥理性。理性为信仰作好准备,信仰为理性开辟道路。这样奥古斯丁就可以很好地把教学说奠基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上,并利用古代哲学的前提、原则和方法来阐述解释圣经。在《译丛》所选的《论教教义》体现的就是奥古斯丁的这些基本原则,而《论灵魂及其起源》一书则基于教的立场对灵魂这一希腊哲学的古老问题进行了探讨。
《译丛》还选取了希腊化-罗马时期的重要哲学家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其有关共和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现代,只是他们的译作在《译丛》中还尚未出版,未知其内容如何,一时还无从置喙,期待着它们能尽快和读者见面。
最终而言,“两希”的融合是现代西方文明基因的合成期,它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大。斯多亚主义表现了对于的适应,其普世主义的思想及自然法的理论对中世纪以及现代哲学影响甚广;伊壁鸠鲁主义乃是现代唯物主义和原子主义的滥觞,一直支配着现代人的思路;而怀疑主义为现代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前提;菲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利高利、奥古斯丁等人促成的教哲学在更大范围对世界的影响。在这些貌似凌乱的人物中,勾勒的却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基础。因此,“两希文明的哲学经典”有待国人的进一步重视。笔者希望《译丛》能在目前十本著作的基础上,编纂更多的文集以飨读者。
从体例上来看,《译丛》非常地道的作法是请专家撰写中译本导言,在这个领域浸淫已久的包利民老师和章雪富老师不仅自己亲自作有关内容的导言,还根据不同的作品请港台乃至海外的专家学者撰写导言,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作法。若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译丛》的容量还偏小,希望看到这个时期更多的著作的出版,并以更加完整的版本面世,正如编者章雪富先生和译者石敏敏女士的心愿,希望看到的是完整《九章集》的出版。
本文地址:www.wordls.cn/zuowen/27495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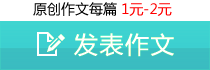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