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性——一个关于规范与事实紧张的宪法例证_宪法论文十篇
论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性——一个关于规范与事实紧张的宪法例证_宪法论文十篇
【法学论文】导语,眼前欣赏的这篇共有132399文字,由姜小明经心修改,发布到美文档!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法律作为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其核心就在对于秩序与公正的研究,是秩序与公正之学论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性——一个关于规范与事实紧张的宪法例证_宪法论文十篇如果你对此篇文章感觉哪里不好,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论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性——一个关于规范与事实紧张的宪法例证_宪xx文 第一篇
内容摘要:我国农民宪法地位具有双重属性,即性和法律性,且两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规范因素是因为宪法兼具性和法律性决定了和“公民”两个宪法概念的不一致;事实原因是我国长期革命史和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这一状况结揭示出理想与现实、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有必要通过解释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并通过完善公民基本权保障体系缓解紧张。
关键词:农民、地位、法律地位、宪法概念、规范变迁
从法律逻辑上来看,农民的宪法地位似乎应毋庸议。一则,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关于国体、统一战线和建设事业主体的内容暗含了农民的地位;二则,体现农民法律地位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诸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20xx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农民是人,是公民,自然是基本权利主体。两者结合,似乎农民的地位与法律地位具有统一性。实则不然。一方面与法律、规范与事实的互为纠结使问题并非如法律逻辑那样清晰、明朗,他方面比较宪法史也不乏关于一部分自然人长期没有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平等保护的例证。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我国文本载明的宪法概念进行规范阅读,结合理论、比较法和现实,获致对农民宪法地位的整体认识。
一、双重属性与不对称
在我国,农民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属性,且两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所谓双重属性,是指农民既具有地位,也具有法律地位。所谓不对称,是指农民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间具有落差。Www.meiword.cOm造成这一状况的既有规范因素,也有事实原因。规范因素是因为宪法具有双重性,即性和法律性,意义上概念和法律意义上“公民”概念并非总是重叠;事实原因是我国长期的革命史和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农民宪法地位的双重属性与落差也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
在宪法史上,并非所有社会群体的宪法地位都具有一致性。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地位而无法律地位,或者享有不完全的法律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只有法律地位而无地位;有时一部分社会群体既无地位,也无法律地位。这是因为,宪法兼具性和法律性,与法律的不一致性决定了和“公民”两个宪法概念在规范内涵上的差异。当今社会,不管一国实行何种制度,宪法的性使各国宪法都将“在民”或者“权力属于”作为宪法原则,宪法也被视为全志或者意志的产物。借助“在民”理念催生的现代宪法,无人敢于公然宣称将一部分社会群体排斥在之外,宪法须依赖“我们”这样堂而皇之的宣示奠定其合法性。但是,上的宣示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宪法上的并不必然就是法律上的公民。由是之故,某种意义上,一部宪法史也是逐渐缩小社会排斥范围的历史,而部分社会群体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错落的种种形态,也构成了宪法社会排斥史的规范写照。
历史上,最为明显地只有地位而不具有法律地位或者不完全法律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黑人和妇女。[②]其中黑人宪法地位的变迁史既对美国宪法序言所宣称的、且被美国人长久引以为傲的“we the people”形成巨大讽刺,也折射出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美国宪法通篇甚至对黑人未置一词,但宪法直接涉及奴隶制的条款有五条,间接涉及的有十多项条款,其中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关于奴隶制的妥协条款有三条。这就是五分之三条款(the three-fifths clause)、奴隶贸易条款(the slave trade clause)和逃奴条款(the fugitive slave clause)。五分之三条款出现在美国宪法第1条。该条规定国会的权力,其中第2款(3)规定:“众议院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合众国所辖各州人口之多寡,分配于各州,此项人口数目(包括所有自由人及五分之三非自由人并包括服役期内之人,但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算。)人口统计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及此后每十年,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实行之。”其中的“五分之三非自由人”指的就是黑人。奴隶贸易条款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9款,该款(1)规定:“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应当准予入境之人,其迁徙或入境时,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禁止之。但对于其入境,得课以每人不超过10元的税金。”如果仅从字面来看,这里并无任何黑人或者奴隶之字眼,不了解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的人甚至不能从中看出这是一条关于黑奴买卖的规定。实际的情形是,该条的“准予入境之人”指的是黑人,“准予入境”是指奴隶贸易。翻译成白话,该条可表述为:现有任何一州可以自由从事奴隶贸易。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制止奴隶贸易。但对于奴隶贸易,每人须收取低于10元的税金。逃奴条款出现在第4条。该条是关于州与州及联邦之间关系的内容。第4条第2款(3)规定:“凡根据一州的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因该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结束其该项兵役和劳役,而应因服役州的要求将其人交还。”此处也没有出现任何黑人或者奴隶制字眼,而是“服兵役”或“劳役者”,其中“劳役者”就是奴隶。用直白的语言叙述,该条的意思是这样的:一州逃往他州的奴隶,他州必须负责交还。从五分之三、奴隶贸易和逃奴条款的内容来看,制宪之时的美国黑人不具备完整法律人格,只相当于五分之三的人,他们是奴隶,也是财产。
美国宪法之所以措辞如此含蓄隐晦却又选择默许奴隶制度的存在,实乃是理想让位于现实、法律让位于的结果,既是出于迫不得已,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性,还是一种妥协。一方面,蓄奴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1789年制宪之时,13州中有7个州是蓄奴州;[③]出席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中,有9人是种植园主,有15人是奴隶主;[④]作为制宪者之一、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就是蓄奴者;另一个虽然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但却是《宣言》的起草者,也是美国开国之父的杰弗逊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蓄奴者。另一方面,制宪者熟悉自然权利理论,深知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意味着什么,让《宣言》中“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庄严文字依然激荡于胸的他们在宪法中公然写出“奴隶”或者“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制宪者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对现实予以默认,但又心存不甘。他们既要默认这一与自己理想相悖的制度,又不愿直陈其事,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春秋笔法。制宪者面对现实的无力、尴尬乃至虚伪还充分表现在对宪法原文是否应包含《权利法案》,以及对1787年宪法原文的批准上。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之一的平克尼将军就曾道出了其中的隐衷。他在1787说服南卡罗来纳州宪法批准会议上的辩论道:“对于本州的成员而言,另外一个反对插入权利法案的理由极为重要。这样的权利法案通常以宣称人人生而自由为开始。现在,我们(固然)应以极糟糕的恩惠宣称这一点,(但)当我们财产的大部分是由人组成的时候,谁实际上生而为奴呢?”[⑤]这里既表现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紧张,也显示出宪法的性和受历史条件决定的特点,即宪法本身并不能抵御那些明显具有违宪内容的条款,作为决断,宪法内容受制于事实,是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产物,也是妥协的结果。
更有甚者,如果按照美国最高的解释,美国黑人既无地位,也无法律地位。在1857年的德雷特·斯格特诉桑弗特一案中,美国最高通过否认美国宪法中与“公民”的区别,来拒绝给予斯格特以自由人和美国公民的身份。首席法官塔尼在阐释裁决理由时指出了“公民”与之间的关系。他说,美国和美国公民两者是同义词,两者皆指“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有权通过代议的方式参与的”。宪法制定时,联邦没有公民,宪法批准后,联邦内各州的公民在宪法生效时转化为联邦公民,但在宪法批准时黑人不是各州的公民,因而他们也没有能够转化为联邦公民。州可以在联邦成立后,将本州的黑人变成本州的公民,但不能将黑人变成联邦公民。所以,黑人不是美国联邦公民,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也无权到联邦告状。塔尼还特别认为,殖民地的领袖在起草《宣言》时,并没有将作为财产的黑人包括在他们所指的“所有人”的概念中,黑人的公民地位和权利问题,“根本就没有被制宪者们放在心上”[⑥]。他认为,制宪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意义,也清楚其他人会怎样理解他们使用的语言的涵义;他们知道任何文明社会都不会将黑人种族包括在内,也知道黑人种族将根据公意总是被排除在文明和文明国家之外而注定要成为奴隶的”[⑦]既然黑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公民,那么黑人的宪法地位是什么呢?塔尼认为黑人应定为介于外国人和公民的地位。所谓公民,他们必须效忠美国;所谓外国人,他们不能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这就是说,美国黑人既不属于的范围,也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法律地位。
另外一个地位与法律地位不完全对称的例子是美国妇女。妇女在美国属于自然人,理论上属于,具有公民资格;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条文和字面含义上,也看不出有关美国妇女身份和法律身份差异的内容。但在实际上生活中,美国妇女长期只享有宪法规定的私利,不享有权利。所谓私利,是指妇女可以与成年自由人一样签署契约、买卖房屋等;她们也有人身安全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享有宪法规定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是,妇女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享有权,即没有投票权,不得参加陪审团,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服兵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参加陪审团和服兵役不仅仅是公民义务,而是公民权利,即具备公民身份资格的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只享有完全公民资格的人才享有的权利,而非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妇女是自然人,但她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陪审团和服兵役是公民权利,也是权利,妇女自然不享有这些只有公民才享有的权利。这一状况直到1920年美国宪法通过第19条修正案之后才予以改善。[⑧]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自然人在社会里具有双重身份,私身份和公身份。私身份有权从事私人行为免于国家干预,公身份则以公民资格参与公共生活。只有具有完整的公民资格的人才同时具有两种权利。正因为此,美国学家阿克曼提出了“私人公民”这一概念,[⑨]其意在于把自然人的“私”的一面与“公”的一面统合起来。严格而言,这一概念只存在于一个实质上教育和财富基本同质,形式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妇女之间在实质和形式上不存在任何差别,或者差别不大,个人既享有私人意义上的宪法基本权,也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私人公民”的概念才能成立,个人的地位与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完全统一。
只有法律地位而无地位的典型例证是外国人。宪法在宣称是国家主人,宪法是意志之时,并没有将外国人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国家概念所包含的、领土(疆域)和中的是指国家疆域之内的,国家概念将外国人排斥在范围之外,宪法宣示的不包括外国人。因而,不管是在一国旅游、短期居留还是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只要不具有住在国的国籍,就不是本国人,不是公民。除此之外,外国人不具有地位还表现在他们不享有选举权、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等问题上。虽然外国人在居住国没有地位,但他们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而不是全部,如人身自由、财产保护等,因为外国人是自然人,很多国家宪法基本权利的主体是“人”,“人”既包括本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目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外国人在居住国享有的权利范围呈逐渐扩大之势,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如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等。但是,总体上,外国人不享有地位,只享有法律地位。
我国时期的宪法现实提供了一部分人不具有地位但却享有不完全法律地位的例证。那时,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在上被称为“反动派”或“反动分子”,被排斥在的范围之外。他们是公民,但被剥夺权利,不享有宪法基本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导我国现实的是的敌友区分理论。在此概念之下,和公民的概念不一,范围不同。早在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一文中开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⑩]所谓朋友,在国内指的是;所谓敌人,指包括国内外的“反动派”和“坏分子”。属于朋友范围内的,是,也是公民;国内的“反动派”和“坏分子”的,不属于的范围,虽然他们是公民。敌友区分处于宪法理论中决断论的核心。斗争中区分敌友并非独此一家,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的决断论中就包含了行为和动机中敌友的基本划分。因极端依赖事实,决断理论被批评为是不受自身之外任何事情束缚的结果,也是观念中的虚无主义。[11]但是,与任何宪法理论家相比,施密特都显示出他对权力真实运行状态的非凡洞察力,因而决断理论恰恰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清晰认知之上。虽然这种宪法理论因极端依赖事实而缺少一种评价和规范的尺度,决断论被批评者认为缺乏关于决断的形而上学,即关于决断的正当性基础,然而很多情况下,的强权事实状态使规范显得卑微,评价因此变得无力。上的敌友区分论与其宪法观显示出内在一致性,即强调宪法对事实的承认。他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的《新主义的》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历来的,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公民成功有了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12]可见,的宪法理论。所谓法律地位,指农民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具体法律关系是指宪法关系,农民在宪法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其法律地位的表现。宪法关系中的农民不再作为阶级而存在,而是一个个体,即公民。理论和法律上,只有当一个人被视为具有人格的个体时,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如果只是作为某一群体的组成成分,则属于被社会排斥的对象,意味着他们远非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个体。这就需要考察农民在我国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具体包括基本权主体和基本权内容。
在探讨农民是否作为基本权利主体时,首要的问题是定义农民的概念。谁是农民?农民的标准如何界定?是按户籍?还是按其所从事的职业?如果按户籍,则一部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公民可算作是农民;如果按职业,则既有一部分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具有农业户口的公民不能算做农民,也有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公民可算做农民。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农民的统计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根据户籍制度,我国现有农民约九亿人。这九亿人中有一部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的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4]有的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为私营企业主,有的是村镇的管理者,有的是村镇的教育工作者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国有农场直接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劳动的公民,他们是工人而非户籍意义上的农民;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转而去农村或者农场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两部分人都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在此,本文将前述两种标准结合起来定义农民,农民是指那些拥有农村户口并直接从事与土地有关的农业生产劳动以及以农业生产劳动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此外,农民还包括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属于农业户口的牧民、渔民等。
从基本权利的主体来看,按照标题,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所标明的基本权利主体是公民,但各条款的主体不尽相同,除“公民”外,还有人、劳动者,以及妇女、儿童、母亲、华侨等。这里忽略后几种不计,主要前三种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看农民是否包括在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内。就第一种情况而言,20xx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制“人”的权利,农民是人,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除少数几个条款外,大部分主语是“公民”,农民是公民,具有中华共和国国籍,属于基本权利主体。就第三种情况而言,宪法第43条休息权的主体是劳动者,但此处的“劳动者”是否包括农民并不确定。如果按照文意即字面解释方法,“劳动者”包含农民;如果按照目的论即制宪者的立法目的解释,结合城乡分立及“劳动”和“休息”的规范含义,“劳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参加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而是获得有报酬的工作,“休息”也非一般意义上的闲暇,而是享受国家法定假日、最低工时和带薪假期,则此处的“劳动者”就不包括农民。
从基本权利的内容来看,农民并非不享有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全部,而只是部分,其中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权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保护,出现较大缺失的是社会权。包括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住宅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监督权,科研和文学艺术创作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排斥农民。将农民排斥在外的主要是一些社会权条款,包括第42条的劳动权,第43条的休息权,第44条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3条规定:“中华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无论此处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还是“劳动者”,从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的权利内容来看,农民不享有这些基本权。
劳动权是指有权利取得有保障的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质量发给之报酬,具体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劳动结社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该条的主体虽然是“公民”,但根据劳动权的规范内容,农民显然不享有劳动权。休息权指享有最低工时、给薪休假和带薪公共假日。[15]该条规定的主体是“劳动者”,农民虽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但并不包含在宪法规范含义上的劳动者之列,因而并不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休息权。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权的主体是“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农民既不属于这一范围,自然不享有其权利内容。物质帮助权指公民在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社会扶养和救济的权利、在失业之时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具体包括住房权、食物权、衣着权、健康和医疗权、受教育权。该条的主体虽然也是“公民”,但根据物质帮助权的规范内容,农民显然也不享有这一意义上的物质帮助权。
农民虽然享有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权,但由于诸基本权利之间的竞合,对农民一项基本权的贬损也会影响另一基本权的享有。例如,自由权中的平等作为一项原则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予以贯彻,由于城乡差别待遇,平等原则并未及于一切领域,农民在前述社会权方面的缺失即为不平等原则没有完全落实所致,因而农民并不享有普遍和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权。又如,权利既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也包括担任公职,农民报考公务员受到限制,也是权利和平等权位完全落实的表现。结社自由也如此,结社不仅包括性结社,还包括经济性结社,农民无法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联合,也意味着不享有结社自由和平等权。人格尊严权体现在许多领域,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待遇,既违反宪法平等原则,也侵犯农民的人格尊严权。受教育权的实现经常与生活状况有关,由于贫困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农民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难以实现。此外,农民的一些基本权往往因公共利益,诸如社会稳定、城市化、工业化等受到侵犯和限制。例如,监督权中的提出意见权即因社会稳定而受到限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经常以公共利益之名被征收或者征用,不给予公平补偿或者延迟补偿。环境权虽然没有写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不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而是规定在总纲第26条,[16]作为国家的政策指导原则,但环境关涉个体的生命安全、健康、居住和生存条件、农业生产利益等,现实生活中因片面追求工业化损害环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农村和农民是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受害者。这些都在实际上侵害了农民基本权。
我国不同时期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表明,农民的宪法地位具有双重性,且双重属性之间呈不对称状态:作为阶级的农民的地位高,作为个体和公民的农民的法律地位低。宪法的这一规范事实揭示出三方面问题:一是暴露出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说明不等于法律,规范不等于实存;二是提供了宪法依赖于客观事实的例证,证明宪法的性不容忽视,诚如所言,宪法只是对事实的承认和肯定,而非创制规范;三是与世界上其他宪法一样,我国宪法同样具有社会排斥性的一面。
三、变迁规范缓合紧张
与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并非完全不可以缓和,宪法的社会排斥性也不必然具有规范正当性,因而有必要在法规范层面,通过解释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并完善农民基本权保障,提升农民的法律地位,一定程度上缩小双重属性之间的距离。
赋予相关宪法概念以新的规范内涵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我国社会现实变化为规范变迁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取消城乡二元体制、与该体制相适应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差别待遇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取消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方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目前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也将改变为农业工人。在此情形下,那种将“劳动者”区分为从事产业化劳动的工人和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民失去其必要。另一方面,具有历史正当性的宪法内容并不必然具有规范正当性,一如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美国宪法关于黑人法律地位的修正案条款也证明了这一点。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和各州于1865年和1868年分别通过和批准了第13条和14条修正案。第13条修正案规定取消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第14条修正案确立了黑人的联邦公民和州公民的身份资格,以及平等保护原则。饶有趣味的是,在取消奴隶制和劳役的第13条修正案中,修宪者不再效仿制宪者顾左右而言他,而是直接使用了“奴隶制”(slavery)一词,这与制宪之时措辞的含蓄隐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从侧面说明宪法原文保留奴隶制是制宪者对事实的默认,也说明历史合理性不能成为规范合理性的借口和理由,当历史和事实发生变化之时,需要通过一定方式进行规范变迁。一定方式既可以是修宪,也可以是宪法解释。美国选择修改宪法赋予黑人新的宪法地位,包括获得完整的宪法人格、取得公民权、不得作为奴隶、享有选举权、获得平等保护等。根据我国的情况,因宪法中“人”、“公民”和“劳动者”含义较为明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赋予这些宪法概念以新的内涵,完成规范变迁。
首要的问题是确立宪法中“劳动者”以新的规范内涵,应抛弃那种不将农民纳入“劳动者”范围的目的论解释方法,而选择体系解释方法和文意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蕴涵着统一农民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契机。既然序言和总纲中的、“专政”、“统一战线”、”“劳动者”都包含农民阶级,“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人”和“公民”也包含了农民,因而将三部分内容联系起来解释,可以赋予“劳动者”以新的规范内涵,将农民纳入“劳动者”的范围,使享有基本权利的农民个体的法律地位与序言和总纲叙明的农民阶级的地位一致起来。文意解释更为便捷。按照文意解释方法,我国现行宪法中“人”、“公民”和“劳动者”等宪法概念的内涵无不包括农民。20xx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其中中的“人”是指一切人,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农民是中国公民,在“人”的概念之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的主体是“公民”,“公民”是指具有中华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农民具有中华共和国国籍,也是中国公民,应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第43条“劳动者”的字面含义包括一切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中国公民,农民从事体力劳动,属于“劳动者”。此外,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农民是中国公民,应受平等法律保护,在一切领域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或者有合理根据的差别待遇。国际文件也提供了将农民纳入“劳动者”之列的规范依据。《世界宣言》第23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分别用“everyone who works”和“workers”来表示“劳动者”,“workers”的文意同时包含着“工作着的人”和“工人”两层意思,包括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产业工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工人。虽然《世界宣言》不是国际条约,但是,作为普遍宣言,其条款具有宣示意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条约,我国已批准了该条约,其条款和内容对我国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尽管由于各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不相同,各国户籍制度也不一致,该词的规范内涵与我国宪法“劳动者”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文意义上,此处的“劳动者”无法将从事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农民排除在外。
在将农民纳入“劳动者”规范内涵的过程中,还须明确“劳动者”中“劳动”一词的“工作”含义,从而确立农民是劳动者一部分,享有劳动者享有的一切基本权的法律观点。这是因为,宪法和法律的所有语言有特指,“劳动者”中的“劳动”也有特定的规范含义。英文的劳动一词是work,劳动者一词为worker,work和worker即为工作和工人,说明劳动者就是工作着的人。所谓工作,并非仅仅指在工人在企业从事的劳动,农业生产劳动和城镇职工所从事的劳动一样属于“工作”。与“工作”相关的还有报酬,即工资。“工资”并非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农民的劳动报酬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所得进入市场交换而获得。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除一些国有大型农场之外,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大部分农业生产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劳动报酬也非以工资方式支付,目前部分农村地区的产业化经营占总体比例并不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使农民的收入直接与其劳动情况挂钩,收入形式并非像城镇职工那样以“工资”形式获得。“工资”是直接对应“工作”而言的,农民收入和所得不以工资报酬形式出现,并不能说明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不是工作;相反,农业生产劳动是全社会所有工种中的一种,农民收入不以“工资”形式出现不能作为否认农民生产劳动工作性质的理由。
这样,除序言和总纲中“劳动者”的含义不予改变之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劳动者”这一宪法概念应将农民包括在内。因为序言因带有性,其宣示品格涉及国家性质和基础,“劳动者”一词的规范内涵既不应予改变,也无改变的必要。总纲属于政策条款,“劳动者”的含义在上下文中较为明确,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待立法明确,亦无改变之必要。这就是说,农民是人,是公民,是劳动者,属于基本权利主体,享有宪法规定的所有基本权。
除了明确“劳动者”这一宪法概念的规范内涵之外,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还须完善基本权保障体系,使农民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由于农民基本权保护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社会基本权方面,社会权属于立法裁量,其规范内容需立法进一步明确,以为实践中的权利实施提供具体标准,因而既需要修改旧法,也需要制定新法。目前,一方面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劳动法规旨在保护城镇职工劳动者的劳动权[17],农民作为劳动者并未包括在其中,另一方面,国家也无专门针对保护农民劳动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劳动法》第3条在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的权利的同时,第2条规定适用对象是中华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这一限定将本文所指的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农民排除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外,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或者制定关于农民劳动权保护的专门法律,或者扩充现有劳动法律体系的适用范围。前一种立法例可选择在我国目前正在起草的《农民权益保》中纳入相关内容,后一种立法例可选择修改《劳动法》,将农民列入保护范围。虽然在表面上农民劳动没有与任何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但是农民和国家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是农民与国家之间劳动关系的真实反映,“剩余全是自己的”是作为劳动报酬给予农民的。所以,国家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用人单位”,农民是与国家这个“用人单位”形成一定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该受到《中华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
从这些权利的规范内涵来看,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产业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物质保障权相比,农民社会权保障有其特殊性,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全部属于立法问题,行政机关亦须制定相关的农业政策,以为农民基本权实现确立具体的实施标准。就劳动权而言,农民取得报酬的权利与粮食价格有关,国家根据情况采取价格补贴的方式提高粮食价格可保证农民收入;[18]国家也可以采取降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用产品价格来保证农民收入。这就需要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和有效措施予以保证。依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方式,农民劳动权应重点保障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和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等。从长远来看,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产业化经营管理,是谋取农民获致普遍意义上的劳动权的长久之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国家的“建设新农村”政策以及农业科技化与工业化等的支持。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为农民生活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农业生产对气候和自然环境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自然灾害和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高于工业企业,因而对比城市居民,农民的物质帮助权尤其重要。鉴于我国目前农民工作的特点,农民休息权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休息权有区别,但国家也应完善各种休息设施,帮助农民实现休息权。就农民的社会保障权而言,农民虽然不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也应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因而立法应该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应对疾病、伤残、生育、年老、死亡、失业、灾害和其它风险的能力。社会保障权事关农民生存,是农民的基本权利,只有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开展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计划,才能真正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实现宪法中人、公民与劳动者三个宪法概念之间的统一。
此外,立法应力争在一切领域贯彻平等原则,实现平等保护。农民报考公务员应根据情况逐渐放宽乃至取消限制,开通管道方便农民提出建议和意见,实现农民作为公民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参与。为保证农民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志,争取利益,应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条件促成农民结社权的实现。[19]实践中土地征收、征用应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和生活,在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国家也应加强环境保护以利于农业生产,提升而非破坏农村生态和农民的生活环境,保障农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事关人格尊严、国民素质与民族未来,实现义务教育免费也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结语
理想与现实、法律与、规范与事实之间有一种永恒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不能作为让理想永远臣服于现实、法律永远依附于、规范永远让位于事实的借口。理想固然与现实有距离,但可以努力使现实接近理想;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但可以形成法律;规范固然有其滞后性,但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贴近事实。在此,惟愿“建设新农村”政策敲响农民身份与命运的希望之钟,也祈祷宪法不仅是理想,也是现实;不仅是宣示,也是法律文件;不仅是规范,也能成为事实,以赋予农民完整的宪法人格,落实平等保护,缩小社会排斥,实现农民宪法地位性和法律性之统一。
--------------------------------------------------------------------------------
[①]或者“在民”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构成深刻理解宪法理论、宪法实施和司法裁判的基础。该原则既奠定了的合法性,也为各种权力设立了界限,以防止权力滥用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宣言》承认这一原则,在第3条规定:“全部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者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地来自国民的权力。”美国宪法在序言中以“我们美国”这一宣称提供制宪的正当性基础。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作为宪法原则还是司法裁判的法理和宪法依据,美国法官在多个判例中阐述这一原理,并将之作为裁决的根据。实际上,我国宪法理论对这一宪法原则及其价值挖掘得不是太深,而是太不够了。只是宪法学者在阐述该原则时,应注意与学原理作出区别,着重其在构成国家基础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权力界限、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价值,并且尤其需要注意司法裁决过程中法官对这一原则的司法阐释。作者注。
[②]1787年美国宪法以“我们”开头,宣告共和国的诞生。只是,这些神圣的字眼很难与具体的现实划上严格的等号。1787年宪法中宣告的“我们”能够代表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皮鞭下的黑人奴隶吗?它能够代表那些“活该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吗?它能够代表作为美国人口另一半的女性吗?汪庆华:《宪法与: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理论》,中国网,20xx年9月16日。
[③]这七个州是: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尔、纽约和罗得岛。这些州已经宣布废除或即将宣布废除本州的奴隶制。另外六个州则拒绝取消奴隶制。这六个州是特拉华、佐治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④]参见任东来等著:《美国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第88页。
[⑤] another reason weighted particularly,with the members from this state,against the insertion of a bill of rights。such bills generally begin with declaration that all men are by nature born free。now,we should make that declaration with a very bad grace,when a large part of our property consists in men who are actually born slaves?see the bill of rights,p294.
[⑥]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⑦]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⑧]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各州不得因性别关系取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其实,新泽西州早在1776年宣告美国从英王统治下出的前两天就通过了一部授予所有合格居民,包括男人、女人和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并规定了一个适度的财产资格要求。妇女在1776年至1797年间偶尔有权投票,直到1807年之前,她们都有相当多的投票次数。此后,一些妇女选民被指控在选举中就一个的任职问题弄虚作假,导致1807年两院立法机构又通过了一个法令,取消了妇女和黑人的投票权,只允许“自由白种男性公民”投票。参见[美]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⑨] 参见汪庆华:《宪法与: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理论》,中国网,20xx年9月16日。作者认为,阿克曼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区分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个人主义的公民和古典共和主义眼中的完全献身于的公民。
[⑩]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11]参见洛维特:《施米特的决断论》,载刘小枫选编:《施密特与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xx年,第34、42页。
[12]《选集》一卷本,第693页。
[13]劳动者的条件是:①在劳动年龄范围(中国劳动年龄男子一般为16—60周岁,女子为16—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的工人,最高年龄男子为55周岁,女子为45周岁)之内,具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人。②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③具有劳动权的公民。④有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未达劳动年龄已经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仍然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均被统计为劳动者。参见贾湛:《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第529页。
[14] 20xx年1号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目前,官方统计的农民工有1亿,占全国工人总数3.5亿不到三分之一。民间统计的农民工为2.5亿。参见何海宁:《2.5亿农民工养老保险应立法》,载《南方周末》20xx年2月24日第22版。
[15] 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的休息权的保证是:“工人及职员工作时间规定为八小时,从事劳动条件困难之职业者工作时间缩减为七小时至六小时,劳动条件特别困难车间中工作时间缩减为四小时;规定工人及职员每年保留原薪之休假;广泛设立疗养所,休养所及俱乐部提供劳动者享用”。波兰1952宪法给予休息权的保证是第59条(二):“对于工人、职员休息权的保证是:根据法律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方法缩短工作时间;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大量缩短工作时间,以法律规定休假日;一年一度地保留原薪的休假。”第59条(三)规定休息的组织、旅行、疗养所、体育设备、文化宫、俱乐部、阅览室、公园及其他供休息处所的发展,造成城乡日益广大的劳动健康和文化娱乐的可能条件。
[16]我国宪法总纲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17]这些法规包括:《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失业保险条例》,《中华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8号)》等。
[18]20xx年初,发布以增加农民收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一号文件,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294亿元;对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达到120亿元,对部分地区的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和良种也予以补助。同时,为了抑制化肥价格上升,国际还对化肥企业进行补贴——各项补贴累计140多亿元。参见余力:《零农赋时代的“三农”问题》,载《南方周末》20xx年3月10日第19版。
[19]关于成立农民组织及农民的结社自由问题,《南方周末》20xx年10月19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秦晖访谈录》一文。文中对农民组织和结社自由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明确的探讨和论证。
论我国代理制度的完善_宪xx文 第二篇
关键词: 代理法/直接代理/间接代理/民法典/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代理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代理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另外,在我国代理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为完善我国代理立法,应确立和贯彻两系兼收并蓄的原则,民商合一的原则,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等原则。当前,应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完善我国代理立法,尤其是间接代理制度。《民法典》中的代理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代理,第三部分是间接代理。应当将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共同适用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而在规范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时,应以代理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民事责任为框架进行系统的立法。
一、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格局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格局
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此外,还包括有关代理制度的行政规章,如《关于外贸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的司法解释《最高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
《民法通则》第4章第63条规定了代理的法律效果和代理的范围,该条继受大陆法系的传统,未规定间接代理,仅对直接代理做了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wWW.meiword.Com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规定了代理的三种形式: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第65条规定了委托代理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以及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第66条规定了无权代理。第67条规定了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时,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连带责任。第68条规定了复代理。第69条规定了委托代理终止的事由。第70条规定了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终止的事由。
《最高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对于《民法通则》中的比较原则、模糊的代理制度条款又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其中,第79条补充规定了委托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为数人时,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第80条对《民法通则》第68条中的“紧急情况”做了解释。第81条规定了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办理转托手续的要求,以及委托代理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民事责任的承担。第82条补充规定了被代理人死亡后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依然有效的四种情况。
《合同法》在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对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问题做了规定,并在第21章“委托合同”中导入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代理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代理(第402条和第403条)。其中,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只有经法定代理人追认,该合同方为有效的要求,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第48条规定了无权代理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第50条规定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虽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未规定间接代理,但我国的一些行政规章肯定了间接代理。例如,外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代理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代理人)代理进出口业务。如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第1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合同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第15条)。所以,我国的外贸代理既可以是直接代理,也可以是间接代理。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外贸代理制的一大问题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代理制,从而造成了概念和理解上的不统一。[1]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代理制,不如说是我国民法学没有严格区分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行纪关系作为间接代理,是代理的一种形式,把行纪关系与代理制对立起来,似有不妥。
另外,在中国银行银条法(1992)13号《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代理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的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代理。
此外,在我国商事生活中代客户买卖证券的证券商,代客户买卖期货的期货商,都是间接代理人。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把期货经纪公司界定为依法“设立的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这与间接代理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2.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存在的问题
总体说来,我国的代理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代理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例如,根据《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度的暂行规定》,外贸代理既可以是直接代理,也可以是间接代理,但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外贸代理只能采取直接代理的形式。由于《民法通则》的效力要高于《暂行规定》的效力,因此,外贸代理在法律适用上就产生了困难。
另外,我国代理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虽然对委托代理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等问题做了规定,但关于代理限的证明、第三人对代理限的质疑、委托代理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代理权、授权委托书的交还、代理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等问题,我国的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复代理问题而言,我国仅在《民法通则》第68条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关于委托代理人选任复代理人的责任、法定代理人选任复代理人的责任以及复代理人的权限则未做规定。就狭义无权代理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对狭义无权代理的规定过于简略,有必要借鉴英美代理法,健全我国的狭义无权代理制度,特别是就狭义无权代理的主体要件、客体范围及例外情形、追认的方式、追认的时间限制、追认行为的代理、追认的法律效果做出规定。为适度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应当承认对追认的时间限制,并应明确规定被代理人追认的两种具体方式(包括明示追认和默示追认),并对积极的默示追认与消极的默示追认做出列举。
当然,在起草《民法典》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国际先进的代理立法经验、判例和学说,也要尽可能地把现行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代理制度的合理部分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二、完善我国代理立法应该贯彻的原则
1.两系兼收并蓄的原则
我国现行代理立法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较大。例如,就立法体系而言,《民法通则》把代理与民事法律行为共同置于总则中的第4章,这与《日本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风格一脉相承。《日本民法典》在总则中的第4章规定了“法律行为”,“代理”乃为该章的第三节。《德国民法典》也在总则中的第3章“法律行为”中设专节规定了“代理和代理权”。将“代理”置于“法律行为”的名下予以规定,更可见代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密切联系。虽然《合同法》导入了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与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代理,但将这两种代理形式放入第21章“委托合同”予以规定,这种立法技术又与《法国民法典》第3编第13章“委托”把委托合同与代理混为一体予以规定的思路相吻合。虽然有许多学者批评《法国民法典》没有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委任合同)和代理权限,肯定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在拉邦德理论的指导下,严格区别代理权限与委托合同的做法,但我国《合同法》还是选择了委托合同作为导入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与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代理的载体。至于我国代理法的基本理论,也基本上源于大陆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民法典》。在继承大陆法系代理法传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移植英美代理法的先进经验,并使之融入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说,是我国立法者面临的历史挑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英美代理法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成长为私法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推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代理法的先进理论和制度,一些国际代理公约也导入了英美代理法的合理成份。《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明确规定了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国民法学界有必要倾力研究英美代理法,我国立法者应当把进一步移植英美代理法作为法律移植的重要一环,真正把英美代理法与大陆法系代理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的立法镜鉴。当然,鉴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长期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而对英美代理法学说与制度的继受相对薄弱,因此,努力使英美代理法的消化吸收与我国固有的民法理论相契合、相协调,就成为民法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民商合一的原则
除民事代理外,民商法学界尚有“商事代理”的提法。所谓商事代理,是指商人之间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代理关系。我国坚持民商合一主义,即在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特别法。这些单行的商事立法为特别民事立法。除非商事立法有特别规定,商事关系应当补充适用民法中的一般规定,对于代理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鉴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笔者建议《民法典》系统、全面地规定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代理人与第三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为各类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这样,《民法典》的代理制度不仅是调整一般代理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也是调整商事代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鉴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商事代理关系纷繁复杂,《民法典》不可能,也不宜对其一一做出规定,而是通过诸单行的商事立法予以调整,为适应变动不居的代理实践对立法调整的要求,包括《票据法》、《保险法》在内的商事立法可以对《民法典》无法覆盖的特定代理事项做出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立法对代理事项未做规定时,仍应补充适用《民法典》中的代理规定。
3.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的原则
代理立法的实质在于协调代理关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对交易风险的分配做出制度安排。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使各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尤其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立法者有必要在代理立法中规定诸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包括命令型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增强代理法规范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但是,代理关系毕竟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受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因此,立法者应当允许代理关系各方当事人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约定。立法者的这一容忍态度主要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设计来实现。当然,强制性法律规范和任意性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所占的比例,应当由立法者在参酌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代理立法实践,慎重做出决定。
三、在《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我国代理制度总体框架及若干问题的建议
我国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将会更加广泛地借助代理制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无论是直接代理制度,还是间接代理制度,都将有着巨大地生存空间。为使我国的民商法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有必要在总结我国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民法典》中的代理立法,尤其是间接代理制度。
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的代理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代理,第三部分是间接代理。
1.关于一般规定的完善
鉴于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笔者认为应当将不仅适用于直接代理,而且适用于间接代理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这种具有一般性的代理法律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代理的范围、代理的效力、不同种类代理的法律适用原则、代理权的产生、委托代理权的授予、委托代理权授予不明时的民事责任、代理限证明、第三人对代理限的质疑、委托代理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代理权、代理人意思表示的瑕疵、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的禁止、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情形中被代理人的撤销权、委托代理权的终止事由、法定代理权或者指定代理权的终止事由、授权委托书的交还、代理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委托代理情形下的复代理人、委托代理人选任复代理人的责任、法定代理人选任复代理人的责任、复代理人的权限、数名代理人代理权的行使、代理人不履行职责时对被代理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对被代理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代理事项违法时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所负的民事责任等。
上述具有一般性的代理法律规则有些体现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有些体现在《最高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之中,但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代理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除了对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还有必要弥补目前的立法漏洞,在《民法典》“代理”一章中增加规定有关一般代理规则的新制度,如代理限证明、第三人对代理限的质疑、委托代理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代理权、代理人意思表示的瑕疵、委托代理人选任复代理人的责任、法定代理人选任复代理人的责任、复代理人的权限等条文。其中,默示代理权限是英美法系的代理制度,而其他的一些制度则在《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民法典》、《澳门民法典》中都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却未予规定,实为一种遗憾。因此,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弥补法律漏洞。
2.关于直接代理制度的完善
“直接代理”中应当就直接代理的效力、狭义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的追认权、相对人的催告权、相对人的撤销权、狭义无权代理人的责任、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的连带责任、表见代理,隐名代理等问题做出规定。此处仅就隐名代理制度做一探讨。所谓隐名代理(unnamedagency),指代理人不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但明示为被代理人利益而为意思表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的代理关系。在商业实践中,有些代理商为了不使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直接建立联系,经常采取隐名代理做法。我国一些进出口公司在代理被代理人和外商做贸易时也经常为回避作为合同直接当事人的风险,而采取隐名代理形式。其中,为提醒相对人注意到隐名代理的情况,代理人往往需要在合同中注明“代表被代理人”、“买方代理人”或“卖方代理人”的字样。如此一来,对方即可知其处于代理人的地位,但尚不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究竟是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信息就是财富。商业机会不断涌现,但若不及时把握,便稍纵即逝。隐名代理制度对于被代理人、第三人把握商业机遇都大有好处。对于被代理人而言,即使自己的知名度或者信用度不高或者不愿意很快将自己的确切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第三人,也不妨碍代理人代表自己同第三人订立合同;对于第三人而言,只要代理人明示为被代理人签约即可,而不必在缔约时立即究明被代理人姓甚名谁。因此,隐名代理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英美法系以代理人的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被代理人身份的公开状况为准,将代理划分为显名代理(公开被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的代理或者被代理人身份公开的代理)、隐名代理(被代理人身份部分公开的代理)和不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因此,隐名代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代理类型。
对于隐名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责任问题,在英美法系也有不同的态度。《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了这样一条普通规则:除非代理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代理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在披露了被代理人身份之后也是如此。[2]美国纽约在“阿格斯格诉麦克纳特”一案[3]中指出,为公正起见,第三人有权要求代理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因为,“允许代理人把一个隐而不露、第三人根本不认识的被代理人推到第三人面前,将会剥夺第三人根据合同所享有的一切可行、负责任的补救措施”。
但是,英国法对于隐名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责任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且没有采纳《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的普通规则。英国有判例认为,在隐名代理情形下,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仍是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应由被代理人对合同负责,而代理人对该合同不承担个人责任。[4]但一般说来,只要代理人在隐名被代理人授权范围内缔约,隐名被代理人就有权取得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参加有关合同的诉讼活动。可见,隐名被代理人和显名被代理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严格区别。
按照英国的判例法,代理人在同第三人缔约时,仅在信封抬头或在签名后加列“经纪人”(broker)或“经理人”(manager)字样是不足以排除其个人责任的,而必须清楚地表明他是代理人,如写明“买方代理人”(asagentforbuyer)或“卖方代理人”(asagentforseller)等字样。至于他所代理的买方或卖方的姓名或公司的名称则可以不在合同中载明。
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代理与不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所具有的功能与大陆法系中间接代理的功能基本相当。但严格说来,大陆法系缺乏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代理制度。
有人认为,《德国商法典》第383条至第406条规定的行纪是一种隐名代理。[5]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大陆法系中的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不仅委托人的名义被隐去,而且委托人的抽象身份也可以被隐去。可见,除非法律要求行纪人与他人开展的每个商事活动都属于为委托人办理的行纪业务,作为间接代理的行纪既可相当于隐名代理,也可以相当于不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另外,《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条规定的无代理权的委任、间接代理或者行纪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名代理。
但在英美法系的影响下,某些大陆法系国家也承认代理人为隐名被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的可能性。如根据《荷兰民法典》第3:67条之规定,代理人可以为隐名被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但代理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确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的期限内(缺乏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时),披露被代理人的身份,否则,除非代理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代理人被视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缔约,并亲自对其缔结的合同负责。我国民法学者胡长清先生认为,《日本民法典》第266条、《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项但书、《德国商法典》第344条、《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瑞士债务法典》第32条第2项,均规定了隐名代理。他还认为,旧中国民法典“既采民商合一主义,犹对隐名代理未设明文,似有缺憾”[6]。
《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2条明确规定了隐名代理,并规定代理人的行为直接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产生约束力,但代理人实施该行为只对自己发生约束力时,例如,涉及的是行纪合同,则不在此限。该条的立法态度非常接近于英国法的立场。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首次规定了隐名代理。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而最终源于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与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例如,该条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但忽略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有鉴于此,建议新民法典中增列这类情形,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为求得严谨起见,也为进一步扩张隐名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将隐名代理制度脱离《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从而将其与显名代理一同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代理制度中予以规定。
针对代理人不向第三人披露被代理人身份的问题,建议新民法典借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3条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第三人请求代理人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人应当公开被代理人身份;代理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公开被代理人的身份的,代理人自己应当接受合同的约束。
建议《合同法》第402条条文修改如下:“1)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代理人和第三人的除外。2)第三人请求代理人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人应当公开被代理人身份。代理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之所以将隐名代理制度置于直接代理,而非间接代理一节,是因为隐名代理人虽不直接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但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买方代理人”或“卖方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3.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完善
就间接代理制度而言,我国代理立法首先应当明确间接代理的定义及其效力。在此基础上,应当就代理人的通知义务、被代理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第三人和被代理人的抗辩权等具体制度做出规定。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间接代理与行纪合同的关系
行纪,在我国古代称牙行。传统的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委托人给付行纪费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行纪人可以是办理营业登记的委托行、商店、经纪人等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今的行纪合同与传统的行纪合同相比,扩大了适用范围。第一,传统的行纪人限于以行纪为业或者其他可以从事行纪活动的经营者,现今的行纪人可以是经过营业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未经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传统的行纪活动限于动产买卖和其他财产交易,现今的行纪活动包括不动产买卖在内的财产交易,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活动。第三,传统的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现今的行纪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7]
尽管有学者提出间接代理与行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从以上可以看出,现今的行纪合同与间接代理几无区别。二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即委托人(被代理人)、行纪人(代理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代理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二者都有两个合同,即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内部授权行为),行纪人(代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代理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由委托人(被代理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考虑到代理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民法典》代理章规定间接代理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等有关内容,在间接代理中规定被代理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代理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2)间接代理中代理人的披露义务
由于在间接代理中与第三人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代理人,而非被代理人,因此从保护第三人或被代理人的利益出发,有必要规定代理人的披露义务。关于间接代理中代理人的披露义务,建议做如下规定:“1)如果代理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代理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代理人将会违约,被代理人有权要求代理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2)如果代理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代理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代理人披露被代理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8]
该条文参考了英美代理法的有关判例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第3:303条、第3:304条的规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规定的被代理人的介入权和第3:303条规定的第三人的选择权,只有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意向通知分别送达中介人和第三人或者被代理人时,才能行使。因此,《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4条规定了披露的要求。
(3)间接代理中被代理人的介入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导入了英美代理法中的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可见,该条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有关抗辩权的限制性作用。但是,该条对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存在着不足。该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行使受托利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显然过于苛刻,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其他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就不能行使介入权了。而根据英美代理法,只要受托人不对委托人履行义务,委托人就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前提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开身份的被代理人以及合同不仅仅因代理人的人身因素而签订。[9]此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代理人无论是因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对被代理人的义务,被代理人都可行使介入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把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界定为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代理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欧洲合同法原则》同样没有把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局限到中介人因为第三人原因对被代理人不履行义务。为充分保护被代理人的介入权,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修改为:“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该条对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内容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当之处。根据该条规定,被代理人可以行使代理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根据英美代理法,身份不公开的被代理人所享有的介入权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介入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并直接对第三人行使请求权,在必要时还有权对第三人起诉。可见,被代理人介入的对象仅仅是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被代理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仅仅限于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取得的,以第三人为债务人的请求权。另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被代理人仅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所取得的权利。《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规定,被代理人仅有权对第三人行使中介人代表被代理人取得的权利,而不包括中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为了避免被代理人滥用介入权,损害代理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应当严格限制被代理人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被代理人只能行使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应当修改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的规定也有欠周延。根据该条规定,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根据英美代理法,除了上述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代理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7项之规定,代理人可以按照被代理人明示或者默示的指示与第三人约定,排除被代理人的介入权。为预防被代理人介入权的滥用,兼顾第三人的利益,保持代理人与第三人所缔结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建议增加规定被代理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代理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应当修改为:“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被代理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
根据以上,建议将间接代理中的被代理人的介入权规定如下:“1)代理人向被代理人披露第三人后,被代理人可以行使代理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代理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被代理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或者被代理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的,不在此限。2)被代理人应当将其行使介入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代理人和第三人。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三人不得再向代理人履行给付义务。”
(4)间接代理中第三人的选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才能行使选择权。但是,根据英美代理法,只要代理人没有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请求被代理人履行义务。[10][2](p395)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只要代理人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3条规定,如果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为充分保护第三人的选择权,确保第三人的债权得到充分实现,建议放宽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与之相应,《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应当修改为:“代理人因被代理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为预防第三人在行使选择权时由于随意变更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而给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造成损害,并使被选择的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对其履行提前有所准备,建议对第三人的选择权行使规定如下约束条件:“1)代理人向第三人披露被代理人后,第三人可以选择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2)第三人应当将其行使选择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在接到通知之后,被代理人不得再向代理人履行给付义务。”
(5)间接代理中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还规定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即“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该规定也存在着不足。例如该规定中的“其”指代不明,极易使人理解为第三人,因为,根据语义学,指称代词一般应当指向语句中距离指称代词最近的中心词。但是,如果把“其”理解为“第三人”就会导致一种非常荒谬的解释:委托人居然可以向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对受托人的抗辩。为避免产生歧义,并与英美代理法和《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中的“其”明确为“委托人”,而在《民法典》“代理”一章中则明确规定为:“1)被代理人行使代理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其对代理人的抗辩。2)第三人选定被代理人作为其相对人的,被代理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代理人的抗辩以及代理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注释:
[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324.
[2]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xx.p179.
[3] agersingerv.mac naughton,(1889)114n.y.535,21n.e.1022,11am.st.rep.687.
[4] the santa carina(1977)1lloyd’slr478.
[5]董碧仙.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比较探析[j].中外法学,1997(4).
[6]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297.
[7]河山,肖水.合同法概要[m].: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p230.
[8]有关该条文的立法说明及理由,请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xx年12月版,第233页。
[9] g.h.l.fridman.supranote24.p230-235.
[10]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xx.p395.
普通法传统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_宪xx文 第三篇
违宪审查制度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出现,是由美国的法律传统决定的。美国作为普通法国家接受自然法学说,而按照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的判断,依据宪法审查人定法不过是对自然法与人定法关系原理的扩大使用。普通法法律至上学说的自然延伸是宪法至上,其间接的结果就是以司法权审查违宪的立法。权力制衡的原则在美国宪法缔造者们的笔下早就推演出司法机关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的结论,马歇尔的创造不过是对制宪者们的逻辑结论的实践。普通法传统赋予法官的特殊地位,也使法官有条件创立新的制度。而以普通法的传统为构成要素的美国民族精神,则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创立提供了文化基础。
[关键词]违宪审查;普通法;法律传统
违宪审查,已经不是个新问题了。1803年马歇尔在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创立了这个制度,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1]471违宪审查制度是美国法制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美国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违宪审查制度会在美国出现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当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该原则的时候,人们接受的如此坦然,而不是在社会中掀起轩然?它是官出于偶然的发现,还是历史中早已注定的必然?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美国的法制传统谈起。美国是一个普通法的国家,它在保持普通法传统方面甚至比英国还要彻底[2]28,而正是这一点注定了违宪审查与美国的姻缘。
一、 自然法的理性追求及其之于人定法的地位
自然法,人们将其定义为一种超越于人类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WWW.meiword.CoM接受自然法的人们信奉这种权威,遵从这种权威。自然法学说本质上是对“理性”和“正义”的追求,接受自然法就是寻求一种高于人、高于现实生活的真理。这样的认识中隐含了对人类判断力的怀疑。自然法所营造的即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世界上存在一种高于人类判断力的“理性”和“正义”,人类自身行为的真理性要接受自然法也就是这种“理性”和“正义”的检验。当西塞罗说“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的时候,他强调了法律的行为准则地位,而真正的法律之所以应当被普遍遵守,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他符合理性。按照这样的判断,人们遵守法律实际上就是服从理性。
既然自然法的理性追求本身包含着对人类判断力和人类行为的怀疑,那也就自然包含了对人定法的怀疑。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符合理性和正义的要求才具有法律的效力,不“正义”、不“理性”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自然法在其效力上具有高于一切人定法的权威,人定法要根据自然法的原则而制定。自然法是判定人定法好坏的唯一标准。正如西塞罗所言:“实际上,只有根据自然法而无其他标准,我们才能够辨认好的法律和坏的法律之间的区别。”[3]66格老秀斯的看法更为典型:“有人性然后有自然法,有自然法然后有民法”。[3]76这里的“民法”指人定法,而“人性”是对理性的追求。先有理性,再有自然法,自然法反映的是对理性的追求;有了自然法,才有民法即人定法,人定法的产生以自然法为依据,接受自然法的检查。自然法理论中的这些观点暗含了这样一个判断:一切法律都是值得怀疑的。正是这种“怀疑精神”,给以后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空间和依据。
自然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人们无法用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正当利益的时候,就会把希望寄托于一种超然的形态,一种“高级法”的权威。这个时候自然法就是超验正义的高级法。在文明时代,美国认为美国的宪法是“最高理性”的体现,与自然法具有类似的地位,广为所认可和推崇,宪法就是在文明时代体现正义与理性的“高级法”。自然法与高级法思想的联通实现了理性与权威的结合。根据自然法的规定,不理性的、与自然法相矛盾的人定法是可以审查并裁定其无效的,在这里,人定法作为与自然法相对应的对象,是可以被审查的。同理,延伸到时代,制定法作为与宪法相对应的对象,亦是可以被审查的。于是,自然法的理性追求及其高于人定法的地位,使得依据宪法审查人定法犹如人定法接受自然法审查一样顺理成章。
二、法律至上的观念
罗斯科&xx8226;庞德曾断言,“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普通法的法律至上学说在美国发展的产物。”[2]8这话说出了违宪审查制度与法律至上学说的关系,也反映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创立与美国这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美国是一个由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多个州组合成的国家,它的形成靠的不是事先存在的某种强大的国家统治力,比如来自英国的君王的控制力,而是十三州的契约。合众国的建立没有改变十三州作为组成国家的主体的地位,从而在这个“联合”而成的国家中,使十三州协调一致地运行起来的力量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国家权力核心的统治力,而是这十三州(后来是五十多个州)共同接受的宪法。对十三州或者后来的五十几个州来说,真正有说服力的是这些州共同接受的契约或宪法。这样的国家结构和美国国家建立的这样的历史过程,决定了法律,具体说就是宪法,在美国国家生活甚至一般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在权力和法律的关系上来看,也就是法律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宪法的至上地位。
法律至上在法治理论中揭示的是关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的道理。[4]86它的基本要求是权力服从法律。这样看来,法律至上似乎与违宪审查制度无关。但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却为依据宪法审查法律铺平了道路。柯克在处理“博纳姆医生案”中议论(“附论”)道:“在很多情况下,普通审查议会的法令,有时会裁定这些法令完全无效,因为当一项议会的法令有悖于共同权利和理性或自相矛盾,或不能实施时,普通法将其予以审查并裁定该法令无效。”[5]45在这段论述中,我们虽然看不到法律至上的文字,但它却充满了权力服从法律的精神。法令,直接权力的一种表达,当下掌权者提出的要求;普通法,一种说不清出自何人、来自何时的既定的法律,在这两者之间,不是法令决定普通法,而是相反,法令要服从普通法。普通法对法令的裁定实际上就是对权力的意志的裁定,对行使权力的机关的行为的裁定,因为法令就是具体的“议会”或其他有权的机关发出的命令。柯克的这段话所遵循的逻辑说明,只要人们坚持权力应当服从法律,也就同意法律至上的口号,就自然可以接受依据一种更有权威的法律(在柯克的案子中就是普通法)对出自具体立法者或掌权者的法律进行的要求和主张。
柯克的主张虽然没能在英国变成稳定的制度,但他的观点却揭示了法律至上学说所蕴含着的制度创建的能力。美国接受了法律至上学说,美国中贯彻了法律至上的原则,美国也就获得了创建违宪审查制度的机会。按照庞德的理解,正是在对英国殖民地的法律,特许令状制度,成文宪法以及宣言等的遵循、反思等,把美国引向了法律至上的境界,并在这里让柯克以和理性约束议会的理想得以实现。[2]52美国人接受了“普通法的法律至上学说”,造就了他们自己认为“必须执行”的“成文的联邦宪法”,他们“接受”“以司法权审查违宪的立法”[2]51的制度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点在违宪审查制度的创立者马歇尔的判词中即可窥见一斑。马歇尔说:“立法机关的权力是限定的和有限制的,并且这些限制不得被误解或者忘却。宪法是成文的。出于什么目的对权力加以限制,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对这些限制要予以明文规定?假如这些限制随时有可能被所限制者超越,假如这些限制没有约束所限制的人,假如所禁止的行为和允许的行为同样被遵守,则有限和无限权力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要么宪法制约任何与之相抵触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么立法机关可以以普通法律改变宪法……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要么是优先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不得以普通立法改变;要么与普通立法法案处于相同的地位,像其他法律一样,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修改。” [6]6-8无限权力是什么?就是不承认法律至上的权力。有限又是什么?在马歇尔看来,就是其权力被宪法“限定”的,就是根据宪法来看其权力 “有限制”的。宪法是否可以被立法机关的立法修改,不是这个法与那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立法机关所掌握的权力是否可以改变那创设立法机关的宪法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宪法应当具有“优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马歇尔让他的当事人,同时也是它的反对党,接受他的判决的基本理由。
三、 权力制衡的原则
所谓权力制衡原则,即"三权分立、相互制衡"[7]23,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应相互制约,保持平衡。权力制衡带来的不仅仅是“行政效果”,更是“效果”[8]105。
对权力制衡的思考由来已久。当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对外权的时候,他不只是注意到了权力划分,因为分配本身就意味着设定界限,而被界限分开的权力以及掌握这些权力的机关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之间的限定。事实上的权力划分是由行使权力的机关之间的相互限定造成的。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划分以及划分开的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的观点发展为系统的“三权分立”学说,实现了国家权力理论发展历史上的飞跃。而美国人率先在国家建设上应用了这一理论。
联邦党人在他们的理论设计中,从而也就是在权力制衡理论所应有的延展中,包含了司法权这个在孟德斯鸠看来最弱小的权力对立法权这个在时代看来决策权最突出的权力的制约地位。联邦党人认为,“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他们所说的“一定限制”包括 “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这样的限制“在实际执行中”就是“通过执行”。他们提出,“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并强调,“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9]392。他们指出了制约立法权的必要性,同时也设计好了制约立法权的办法。这个办法与后来马歇尔所做的完全一样。当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中宣布“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机关法案”“无效”[6]6的时候,他不过是美国制宪者预想到的以司法权制约立法权的权力。
不仅孟德斯鸠的理论在美国可以转化为联邦党人的国家建设方案,美国在建设邦联时的经验或者说是教训也足以教会美国制宪者提高司法权的地位,赋予司法机关限制其他两种国家权力的权力。在合众国成立之前,北美邦联机构曾经发挥了国家机关的作用。但邦联后来的发展证明邦联体制是不成功的,而邦联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司法权的欠缺和软弱。它“致使邦联条例或邦联国会制定的法律无法有效的约束各州,而仅仅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劝告。”[10]263既然原因出在司法权不够有力上,解决的办法当然是加强这项权力。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上,崇尚国家整体权力的当事者们或许只是为摆脱邦联法律所处的无能的法律劝告的窘境,但他们选定的加强司法权的解决办法却足以使美国走上运用司法权扩张联邦权力,以宪法确定的塑造实际的国家的独特的发展道路。[11]如果说在这样的思考中包含着权力制衡的智慧的话,那么,美国人的这样的经历和经验的积累,为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也为美国制度中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降生奠定了经验基础。
四、 法官的创造性作用
梅利曼曾说:“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和建立起来的……在美国,法官还有权决定立法是否违宪,是否有效,并享有广泛的解释法律的权利,甚至可以适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尚具法律效力时,法官也可对它作出解释”。[12]34 梅利曼的话反映了法官在普通法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普通法传统的国家中的法官与中国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法制中的作用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主要担当执行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或其他某种有权的主体发布的法律的任务,而普通法传统的国家的法官除了适用已然存在的法律之外,还不断地创造新的法律,而那由他们适用的法律也多出自他们或他们的前辈之手。普通法传统国家的法官的这种特殊地位,不仅使他们在法律面前往往可以表现出某种主动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有机会决定法律制度甚至制度的进程。他们可以创造,决定法律制度和制度的新的进程也是创造。
柯克在与王权作斗争时说:“除了法律与国家认可的特权外,国王没有特权。而且,国王自己不能解释这种特权,只有法官才是权威的解释者。”[5]42在柯克的时代,是谁赋予了柯克所坚信的只属于法官的这种解释特权的权力?是宪法吗?不是。决定法官这种权力的不是别的,而是普通法的传统,或者说是普通法的力量。普通法是一种深刻的力量,它总是成功地捍卫自己的原则,并因为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才形成了所谓普通法的传统,积聚了它自身的力量。实际上完成“捍卫”职能的主体是法官。法官们的努力使普通法的原则得以捍卫,使普通法变得坚强有力;反过来,强有力的普通法又给了法官独特的地位。柯克所说的对国王特权的解释权,实际上就是强大的普通法给予法官的法律解释权。马歇尔在创造性地使用了违宪审查权时,他的权力从哪里来?马歇尔和今天的人们都可以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或者宪法的其他规定或原理中找到根据,但实际使用这种权力的冲动却可以在普通法的传统中找到缘由。普通法可以给他这样的力量。普通法创造过无数捍卫普通法的法官勇士,[2]23他们一代又一代地把普通法固有的原则、制度贯彻下去,一代又一代地对试图破坏或可能破坏普通法的固有甚至应有原则、制度的行为做斗争。马歇尔当然也可以做这样的勇士,为维护他所信奉的充溢着普通法精神的法律或者就是美国宪法而有所作为。
美国继承了普通法传统,在法制发展中赋予法官特殊的地位;同时,美国又树立了法律至上这一存在于普通法的精神之中的信念,这便给了美国的法官们依据法律、运用普通法所赋予的力量,创设依法评判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可能性。没有马歇尔的智慧和努力,违宪审查制度也许还要等很久很久才会诞生,因为说到底,没有法官的努力,由法官操作的违宪审查制度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柯克也好,马歇尔也罢,都是在普通法的大熔炉的背景下造就出来的英雄,是他们的英雄壮举缔造了最先出现在美国中的违宪审查制度。但同时人们也应相信,即使没有马歇尔,历史会造就另外的“英雄”,因为普通法还在前进,普通法所塑造的一代又一代的法官们还在捍卫着那已经形成悠久传统、积聚了强大力量的普通法。
五、民族精神的支撑
德国历史法学家萨维尼说:“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3]122违宪审查制度之在美国产生并得到健康发展,可以说是以普通法的传统为构成要素的美国民族精神、法律文化的体现。
某种制度在特定国家的长期存在甚至被加工到完美的程度,不能从个别领导人的性格中找答案。一种新的制度在一定国家的产生,有时仅仅用时事变迁也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一些并非普遍存在的制度在某个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往往与一定民族的深层次的文化特点有关。科举制度尽管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但这种形式却只在中国得以发展为稳定的制度,其深厚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埃及法老制度是古代国家君主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种形式与古埃及人特有的崇拜习惯、对天人关系的特殊认识等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古埃及特有的信仰,便没有它的特殊的君主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是取得了民族精神或民族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存活的。
1803年,当马歇尔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树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旗帜的时候,美国社会上下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极大的波澜,就是马歇尔的反对党,他们反对的理由也显得有气无力。人们对马歇尔的做法虽然觉得多少有些突然,但对他的创举总的感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顺理成章。在普通法的传统与文化的背景下,当违宪审查还只是表现为一种观念形态时,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法律观念和意识的有机成分,不仅在法官们的司法活动中时而显现其指导作用,而且获得民众的价值观念的支持。美国的普通法的法律传统、传统,营造了支持司法权制约立法权和行的文化环境,也耕耘了培植违宪审查制度的土壤。
[参考文献]
[1] 郑贤君.宪法学[m].:大学出版社,20xx.
[2] 罗斯科&xx8226;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法律出版社,20xx.
[3] 王明辉.何谓法学[m].:中国戏剧出版社,20xx.
[4] 徐祥民.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m].:法律出版社,20xx.
[5] 爱德华&xx8226;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三联书店,1996.
[6] 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 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制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xx.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上卷[m].:商务印书馆,20xx.
[9]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商务印书馆,1980.
[10]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m].济南:山东出版社,1998.
[11] 焦诠.司法审查制度溯源[j].南京社会科学,20xx(1).
[12] 约翰&xx8226;亨利&xx8226;梅利曼.大陆法系[m].:法律出版社,20xx.
abstract: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which is not appear in other national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ecided by legal tra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common law country accepts the natural law theory, however ,on the judgment of the natural law method, the natural law overtops the statue law.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at the constitution examines the statue law is the expanded use of the relational principle between the natural law and the statue law. the supremacy of constitution is the nature extends of the supremacy of law in common law, its indirect result is that we should examination un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by the judicial power.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of the check and balance has already deduce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judicial office have power to announce the legislation which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 regulations is invalid in the writing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 founders. marshall's creation is the practice to the constitution founders’s logic conclusion. the traditions of common law entrusts with judge's special status, also enable judge to have the condition to establish the new system.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pirit which takes the tradition of common law as it’s integrant part, has provided the cultur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key words: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the common law legal tradition
普通法传统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tradition of the common law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review
论国家财产的物权法地位_宪xx文 第四篇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写入物权法的法理依据
内容提要:国家财产包括不能进入或者尚未进入民事领域的财产(包括为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与进入民事领域的财产两部分。国家通过投资或者拨款而进入国有企业或其他企业以及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财产,除公有物及公用物之外,国家即丧失其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归国有企业等私法人或者行政机关等公法人享有,国家享有投资人或者设立人的权益。国家所有权或者由宪法或其他公法直接创设,或者关涉公共利益,故其性质为公权而非私权,不具备私权特征且基本不适用物权法的具体规则。民法为私法,重在保护私的利益,公法领域的国家财产应由公法加以规定和保护,“国家财产神圣”不应成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国家财产 国家所有权 公权 私权 物权法
中国社会的和谐,必须建立于各种利益冲突的平衡基础之上,其中,各种财产利益的平衡,是建立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本条件。物权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宪法原则的指导之下,确认和保护民事领域中的合法财产权利,通过建立一整套有关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确认和保护的具体规则,使民事主体的合法财产能够获得法律上的稳定和安全,使财产的交易安全能够获得保障,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协调、巩固和发展。为此,正在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实行了对各种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受到某种尖锐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一原则违反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论据和思路是:我国宪法第12条和民法通则第74条均规定了“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物权法草案“删除”了这一规定,主张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实行同等保护,由此否定和破坏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WWw.meiword.Com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否写入物权法并作为其基本原则?国家财产与集体财产及个人财产在物权法上是否具有平等地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对物权法乃至民法的基本性质的认识。
一、国家财产及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及其法律特征
(一)国家财产的含义及其存在形态
首先必须明确“国家财产”、“全民所有的财产”以及“国家所有权”几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国家财产即全民所有的财产,国家所有权即国家对于动产和不动产享有的直接支配权利。在此,“全民所有”的财产不等同于“国家所有权”。所谓“全民所有”,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公有制的高级形态(集体所有为低级形态),但全民所有的财产包括国家直接享有的一切财产权利(包括所有权、知识产权、股权等等),国家所有权仅为其中的一种。物权法仅对所有权及其他物权进行规定,并不涉及物权之外的财产权利,所以,物权法中所指的“国家财产”,仅是国家财产中的一部分,即国家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财产。
国家财产可分为国家专属财产与国家非专属财产,前者指其所有权只能由国家享有的财产,包括国家对城镇土地、河流、矿藏、海域、军事设施等享有的所有权;后者指其所有权亦可为国家之外的主体所享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财产还可分为进入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与不能进入或者尚未进入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所谓“进入民事生活领域”,是指国家通过投资、拨款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将其享有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授予或者出让给国家之外的第三人所涉及的财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通过投资设立国有独资企业或者与他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行为,将其货币或者其他资产的所有权以注册资金的方式转让给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通过丧失其对财产的所有权而获得其投资益(即股权)。此时,国家投资所涉及的国家财产,即属进入民事领域的财产。此外,国家通过行政拨款或者其他方式交给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的资产,除公有物(为公众服务的目的而由机构使用的物,如机关的建筑物、军事设施等),以及公用物(为一般公众所使用的物,如公共道路、桥梁、公园等)之外,即被视为这些“公法人”的财产,为其进行民事活动的物质基础。
在此,有以下三个误区需要澄清:
1.“全民所有的财产是全体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全民所有”与“全民共有”不同,前者是所有制意义上的概念,后者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全民所有的财产,其所有人只有一个,即国家。此为物权法知识的abc。因此,认为代表国家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的无权处分国有资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2. “全民所有的财产为公有制财产,永远只能属于全民所有,不能转让给个人,否则,公有制就变成了私有制”。在此,“全民所有制”所描述的是一种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非具体财产归属之一成不变的状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果国家财产完全不进入交换领域,则其无法实现任何保值、增值,公有制所担负的经济职能将无从实现。前述观点根本不懂得国家财产存在的根本意义和运用的基本手段。
3. “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民法上的企业法人制度,要求法人组织必须具备财产,而国有企业要获得民事权利主体资格,就必须拥有其财产的所有权,否则,国有企业无法成为的权利义务载体,无法参与商品交换活动。因此,国家在投资设立国有企业时,即丧失其对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取得其投资利。对此,尽管物权立法中存在极大争议,物权法草案也尚未明确承认企业法人的财产所有权,但如果承认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则等同于承认任何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均享有所有权,其错误性显而易见。因此,将国有企业的财产认定为国家财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应归属于国有企业法人,国家对国有企业享有的股权,才是国家财产。
如上所述,国家财产一旦进入民事领域,则转化为国有企业等民事主体的财产,国家丧失其所有权,该部分财产本身在法律上即不再成为国家财产,也不再代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而被视为一种私的利益。
(二)国家所有权的性质
法律部门的划分有其特有的历史沿革和科学依据。根据法律主要保护公权还是私权、法律关系是否为公权力所约束以及法律关系主体是否表现其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身份为依据,法律被分为公法与私法。依据历史传统,用于主要调整民事生活领域的民法,属于私法。而权利的性质也因其所依据创设的法律(公法或者私法)不同以及表现的利益性质不同(公的利益或者私的利益)而被分为“公权”与“私权”。民事权利属于私权。
诚然,公权与私权的界分仍为学界存疑的基本问题之一,但依据主流学说(法律根据说),“凡根据公法规定的权利为公权,凡根据私法规定的权利为私权”。[1]换言之,公权与私权的界分标志之一,为权利创设所直接依据的法律的性质,虽然此一问题又关涉公法与私法的分界争议,但其大致界限仍然是可以判明的。与此同时,另一种学说即“利益说”则认为,凡关涉私人利益者为私权,关涉公共利益者则为公权。
很显然,公权与私权的划分,与权利本身的内容(是否为财产权利)是毫无关系的,关键在于其权利创设所依据的法律性质以及其表现的利益性质如何。
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如何?其究竟为公权亦或私权?
1.权利创设之依据
国家所有权中,首先包含国家专属财产所有权。可以发现,在我国,这些权利是由宪法直接创设的。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9条第1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依上列规定,国家对于城市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系直接依据宪法(公法)取得,亦即宪法规定本身,即使国家直接成为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无需其他任何法律加以确定或者承认。由此可见,前述国家财产所有权性质上应属公权而非私权。据此,那种批评物权法草案有关国有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之国家所有权的规定纯系毫无意义地重复宪法规定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事实就是,物权法并非前述国家财产所有权的创设依据。
2.权利所表现利益之性质
除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等重要财产之外,其他尚有未被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所有的财产,包括公有物和公用物等。这些财产由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予以具体规定。但是,无论公有物或者公用物由民法或其他法律加以规定,因其权利所涉并非个人利益而系社会公共利益,其权利具有与一般私权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性质。故依照公权与私权划分的另一种学说即“利益说”,此等所有权仍应定性为公权而非私权。
由上可见,所谓国家财产应分为公法领域的财产与私法领域的财产两部分。凡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因其处于国家之静态支配状态或者处于公法关系之领域,其所有权不能进入或者尚未进入民事流转,故其权利性质应属公权。凡进入民事领域即私法领域的财产,即成为机关等公法人或者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法人等私法人的财产,由经济学或者所有制的角度观之,这些财产不妨称为“国有资产”,但从民法的角度观之,这些财产为民事主体享有所有权的财产,非为“国家所有”的财产。国家机关在运用这些财产参加民事活动时,不得依据其公权力载体的身份,只能依据其私法上主体的身份;而国有企业本身即非为公权力的载体,故其财产更不能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三)国家所有权的特征
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质,亦可通过其权利特征加以说明。
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因其关涉公共利益,故因之而发生的法律关系应属公法调整。就其所有权的特性而言,可以发现:
1.国家专属财产所有权不具民事上的可让与性。
2.国家所有的财产不得被强制执行。例如,公有物以及公用物一律不得被纳入破产财产。
3.国家所有权原则上不适用物权法的具体规则。例如,国家所有的土地等不动产所有权不适用物权变动的公示规则;国家所有权不适用共有、善意取得、取得时效以及占有保护规则,等等。
4.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不处于同一法律关系领域(一为公法领域,一为私法领域),故其相互之间不可能居于完全平等的相互地位。其表现为,国家所有权是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载体,此种利益当然高于私人利益。据此,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得强行将他人之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如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私人财产),或者基于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使需要而强制消灭他人之所有权(如强行拆迁私人房屋),或者基于公有物使用的需要而限制他人所有权的行使,即使他人之权利的行使完全符合通常的准则(如基于军事设施使用的需要,限制其周边的居民以正常的方式使用土地或者建筑物)。
很显然,如果将国家所有权定性为“私权之一种”,则其在权利设定变动以及权利行使等诸方面即应与私人所有权适用相同的法律准则,但整部物权法所规定的有关物权设定变动以及物权行使的基本规则,几乎均不适用于国家所有权,此足以表明国家所有权应属公权无疑。
二、物权法与国家所有权
(一)物权法应否规定国家所有权
如前所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法律部门设置的基本方法。依照一种并不绝对的划分界限,公的利益主要由公法保护,私的利益主要由私法保护;公法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个人对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侵害;私法的任务,则主要是防止国家公权力对私的利益的侵害。因此,作为私法的物权法,应当对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权利(物权)之得失变更及其法律保护做出规定,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对一切财产利益的保护任务。公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主要由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加以规定和保护。据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家所有权的法律确认,应由宪法规定;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和保护,应当由行政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规予以规定。简言之,物权法应主要确认和保护私的利益。
但是,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来都仅具相对性,亦即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的区分,只是对某类法律或者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之基本属性的揭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不能用刀子把它们精确无误地切割开”,[2] 即在公法中有可能包括私权的规则,在私法中亦不妨包括公权的规则。而各国法律何以“将各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关系归属于这个法律领域或那个法律领域”,依据德国学者的观察,“历史原因的影响”发生了重要作用。[3]这就是说,各国的立法政策、立法传统,均有可能是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发生某种程度的模糊。而现代社会发生的所谓“公法私法化”(如在宪法或者行政法中更多地规定私权规则)以及“私法公法化”(在民法中更多地注入公权力的约束和影响),则是此种交叉和模糊因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
纵观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可以发现,各国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模式并不相同:德国民法及其强调其民法的私法性质,未对公有物或者公用物作出规定,亦未对国家强制征收私人财产做出规定(此种规定交由德国基本法作出[4])。但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士、泰国、伊朗、墨西哥、智利、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大陆法国家,则普遍在其民法典中对于公用物或者国家所有权作出某些基本规定乃至具体规定,不过,对于国家征收私人财产问题做出规定的,仅只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民法典。[5]
为此,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物权法上可以规定公有物和公有物以及国家征收、征用的一般规则,其中,有关国家征收、征用的规定,应从限制公权力滥用的角度着手。但对于国家就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的创设,我国宪法已经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故物权法不应予以规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如何模糊,“民法与私法概念的合二为一”,[6]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民法中注入某些公法规则,并不影响其私法性质;物权法对于国家财产做出某些规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其变成了公法。换言之,如果物权法不规定国家所有权,只能说明民法的私法性质被立法者予以强调,但如其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只不过说明了立法者基于其立法政策,在民法中更多地注入了公法的因素,但物权法对于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并不能表明此种所有权即当然具有私权的性质,更不能表明物权法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二)物权法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我国宪法有关“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毫无疑问表达了国家对公有财产的侧重保护,但这一原则,却不应写进物权法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作为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平衡器,法律的作用是确认不同利益的边界,协调其利益冲突而非加剧其冲突。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其主要目的有三:
首先,从立法技术来看,公权与私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公法关系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系以公权主体的身份参加,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其基本特征是主体间存在隶属关系;而私法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系以私权主体(民事主体)身份参加,涉及到的私的利益,其基本特征是主体间地位平等。这种根本差异,决定了公法与私法之完全不同的调整方法与基本观念。如果诸法混杂,公私不分,则法律规则的设计和适用,将成一团乱麻,难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其次,从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来看,公权与私权分别代表了彼此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利益。划分公法与私法,不仅可以正确界定公权与私权之准确范围,明确其权限边界,而且可以确定公权与私权有可能发生冲突与碰撞的临界点并予以整合,以此防止冲突的发生以及确定解决冲突的准据。
第三,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公权以国家为主体,私权以个人为主体;公权为强者,私权为弱者。为此,为防私权遭受公权之侵犯,须将私的生活(市民社会)与公的生活(国家)相分离,以民法规定私人生活的基本准则,奉行私权神圣、私法自治之原则,排除国家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以此达成公的利益与私的利益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的目的。
上述表明,公法与私法各有其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价值追求目标。公法重在保护公的利益,私法重在保护私的利益。就财产权利而言,宪法和其他公法重在保护国家财产权利,而民法则重在保护私人财产权利。两相分解,两相配合,两相抗衡,利益平衡方可获得。与此相反,如果把国家财产的确认、管理和保护作为物权法的主要内容,无异于让物权法代替了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的职能。而大量公权力规范的进入,则会使物权法成为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相互交错混杂的大杂烩,使物权法乃至民法丧失其排除公权力非法干预和介入的特定功能。
质言之,法律的原则和基本理念依法律的目的和功能而定,由此产生不同法律部门所遵循的不同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方式,如果公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权(公的利益),私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保护公权及公的利益;公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私权即成为公权的奴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即被打破。如果私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的利益,其结果便是私法被公法所吞没,由此,私法不复存在,私权保护亦不复存在。
为此,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能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乃至民法的基本原则只能是“私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和理念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3条关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明文规定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1]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79年第11版,第45页。
[2] 引自[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7页。
[3]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页。
[4] 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xx年12月版,第53页。
[5]参见《法国民法典》第531-541条;《比利时民法典》第538-541条;《瑞士民法典》第664条;《泰国民法典》第1304-1306条;《伊朗民法典》第24-26条;《墨西哥民法典》第764-770条;《智利民法典》第589-598条、第600条、第602-603条、第605条;《意大利民法典》第822条。
[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第16页。
中国传统的司法与法学 修订版_宪xx文 第五篇
摘要:原刊摘要:“近来国内法学界流行着两个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其一指责中国传统司法者不遵循法律和先例,仅仅就事论事,凭天理人情作成判决;其二声称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没有法学可言。二者都与事实不符。第一,中国自秦汉时起,法律已极繁多,在有明文可以适用或有成案可以比照的情形,司法者都乐于遵循,不会自找麻烦另寻判决的依据。如果没有法律或成案可用,任何法制里的司法者都该先仔细案情"就事论事",然后探索法的精义"天理人情"而作成一个合乎公平正义的判决;中国传统司法者的做法并非例外。第二,中国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不仅以纯理性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的法律加以注释、批详,并且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经验中去深究其渊源、目的、效能,以及法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系、法的正当性,法律条文不足时应该如何补救等等法学上的重要问题,留下许多著作,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只因他们的观点、方法和所用的语言及陈述方式与近人习见的不同,所以被忽略了。”
这是经过作者修改,已经在学术刊物发表的最终稿。原先网络散布的同题演讲记录稿中的一些错误,曾经引起争论。如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此版为最终发表版本。--人文与社会编后语
关键词: 传统 司法 法律 法学 韦伯 卡迪司法
中国传统法制自成一系,与世界另几个重要法系并立,各有短长。如要加以检讨,应该先对它作一番整体的、深入的研究;如果想用另一法系的某些规定作为他山之石以改善中国法制,则更须对那些规定甚至整个法系作一番同样的研究,看清了二者的优劣,慎为取舍,不可以轻易地将中国目前的问题一概归咎于传统,更不该盲目地仿效他人。WWw.meiword.COm
前言
20xx年春我应邀到西南政法大学访问,和一些师生们谈起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听到的大多是负面的评述;此外我也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刊,很多也有类似的论调。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大意谓:中国传统的纠纷处理犹如 “卡迪司法”,其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而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天理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判决者可以翻云覆雨;无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伸张正义。除了这种论断之外,又提到日本滋贺秀三的话,说中国几乎找不到与国家权力分离而具有地位的法界精英,从理性的探索中产生学说、判例,以创造并支持 “法”,所以他在畅论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各国的法学之后,谈到中国法学时“几乎有点无话可说的感觉” 。
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国内的法学前辈十分感慨地说,他们对中国传统司法和法学的看法与时下流行的不同,但是因为在过去数十年受过许多挫折,不能甚至不敢将他们的看法说出来;而目前六十多岁的学者则大多只完成了一部分大学教育,然后中辍了十年左右;四五十岁的学者求学的过程虽然比较平顺,但是因为在小学、中学时,社会上普遍地强调中国传统的劣点,进入高校后当然很少有人乐意去探究中国的传统,而且自民初五四以来一般人已不能阅读文言文,因而无法接触中国经典,只好看一些外文著作的白话中译本,学得了一些外国的东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所知极少。
我远离家乡将近六十年,对国内情形自多隔阂,有了这些见闻之后,才领悟到为什么目前国内法学界强调“法律职业”、“法律人之治”等等话题,以及为什么国内一般法学著作所称道、引述的,大多是些外国的学说。虽然有了此领悟,我仍然不免为之惊讶困惑,一则因为在那些外国学说之中,许多是很有争议的,有的甚至已被证明有误,而引述之人似乎并不清楚;[①] 二则因为国内的那些著作,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绝少深入的探究,仅仅用外国的观点和语言,去审视和讨论中国的司法和法学,泛泛地,但是很武断地加以批评。这两点在治学方法上都是很不妥当的。
由于自己的这些感受和若干师生们的鼓励,我决定将一些想法写出来。因为身在旅次,可以查考的资料有限,只好谈谈大意,凭记忆所及略作征引,欠缺不妥之处,待以后补正。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虽然对于此文有兴趣的大约都是法学界的人士,但是我希望一般人也能容易地阅读它。时下的法学写作往往用了很多外来的、生涩的语汇和非同寻常的陈述方式,不仅读来诘屈聱牙,而且因为那些语汇的内涵及外延往往很复杂,容易引起不当的联想,怪异的陈述又往往扭曲了理路,结果使得作品冗长枝蔓,只在那些语汇里反复回绕,却说不清楚作者的真意。其实法学应该讨论的都是社会中的基本问题,每个社会都自古至今继续在探讨它们,并且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语汇,将探讨所得的成果陈述出来,所以学者在讨论本国法制之时,无须借用外来语汇;如须论述他国的意念,必先深究其义,然后以本国语文中易解之辞加以翻译,不要滥创新词,使读者莫明其妙。总之,法学的写作与文学的不同,应该平易地、通顺地将事理铺陈在读者眼前,任他依据常理去了解评断,才是佳作。
中国传统司法和「卡廸司法」
现在来谈中国传统的司法。首先必须对“卡迪司法”(khadi justice)略作说明。依据伯地区的传说,卡迪是当地若干部族里处理族人纠纷的长老。 max weber称他们所做的工作为卡廸司法。至于他们是否仅仅就事论事,然后依据个人的观点作判,weber并无确据。近来学者们比较共同的看法是:卡廸之所以能处理纠纷是因为他们熟悉族中的习惯准则,那些准则对他是有拘束力的,如果他的裁决与之冲突,很难为当事者和族人们接受。无论如何,在十七、八世纪之时伯及其它地区的法律(sharia law)已甚严密,不仅有许多实体法条文,其程序法更是详细。从那时代起,卡廸已不可能凭一己之意处理纠纷了 [2]。
在中国古代的部族社会里可能有过类似伯部族的“卡迪司法”。《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话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3],或许可以为证。大约因为部族社会人数不多,关系密切,又长期聚居在一起,自然地形成了许多利于共处的习惯准则。古代文字的使用不普遍,那些准则大多没有记录成文, 但因他们出于习惯,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里都自然地遵行不违,偶尔有些纠纷皆由长老们依据这些准则加以处理。所以即使在古代社会里的司法,也不是全无准则可循,只是其准则没有成文化而已。
到了部族逐渐聚合成为较大的地域团体时,各部族的习惯未必尽合,所以渐渐有了由地域性权威制定的法令。《尚书》和《周礼》里曾提到夏、殷、周的若干例子,其中有涉及人际关系的,也有涉及财产交易的。[②] 春秋之时各国的法令更多了,但是大约仍未公诸于众。到了鲁昭公六年和二十九年,郑国、晋国先后将其主要的法令铸于刑鼎,表示将要永久、普遍地遵行[4]。秦代的法令“繁于秋荼”。汉代以后,法令之多更是汗牛充栋。近年出土的器物铭文及简牍中可以看出,那些先秦和秦汉的法令不只是刑法,许多与解决民事纠纷有关。此后历代的法典中除了惩处叛逆、命盗等等“重情”的条文之外,也有不少关于户婚田土等等“细事”的规定,所以我国传统法制对于民、刑事件的处理是有一系列规则的[③]。
当然,有规则与是否遵循规则是两回事。大致而言,中国传统的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遇到法有明文规定的事件都依法办理;在没有法或法的规定不很明确的情形,便寻找成案,如有成案,便依照它来处理同类案件。许多地方档案及地方官的审判记录都可证实此点,极少见到弃置可以遵循的规则不用,而任意翻云覆雨的现象。理由很简单:司法者和任何公职人员一样,乐于使用最方便的程序处理事务。在有法条或成例可循的情形下,故意别寻蹊径为其判决另找依据,不仅自找麻烦,而且可能导致上控,使自己受到责难甚至参劾,在正常情形下,一般司法者绝不会这么做。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司法者不遵循规则,不将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是与事实不符的。
将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固然是一个妥当而且可以树立判决稳定性的办法,但是并不容易做到,因为人情万变,法条有穷,而成案的适用有许多限制,一个成案即使和待理之案似属同类,但因情事不可能完全相同,两案是否可以视为“同样的事情”,必须慎重考虑。所以在以成案为重要法源的英美等国,也是每逢一案都必须仔细检查其案情,然后探究是否有完全符合的成案可引。如有相似之案但情事稍有不合,即应指明其异处而加以区别, 不予引用,另依法理寻找一个更切合的处理办法[④]。这种做法便是“就事论事”,“议事以制”。它并不是“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而正是在仔细考虑之后,有意地将不妥的规则搁置而适用更恰当的合乎法理的规则,以寻求公平正义。寻求此一目的与维持判决的确定性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法和法理
什么是“法理”?为什么可以在法理里找到判案的准则?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知道什么是“法”。简单地说,“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犹如一种游戏的规则,规定人们在某类情况之下应该或不应该如何作为或不作为。它和一般游戏的规则一样,先要有一个目的,由参与者去争取;其次要有一套“内在的理则(逻辑)”,使得为了各种不同的情况而设定的细部规则能互相契合,让参与者易于了解并遵行。但是法有一些特质使它有别于一般游戏规则:(一)法所适用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人数较一般游戏的参与者多出千万倍;法所应付的情况也较一般游戏里的复杂出千万倍。(二)法的目的不是一些简单的胜负,而是极为高妙远大的人际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繁荣。(三)法的内容不是一些技术性的细则,而是一套具有价值导向的规范。
了解了法的特质之后可以来谈“法理”了。简单地说“法理”是法之所以为法的理由或依据,也可以说是法的基础和必备的要素。由于上述法的特质,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要素:一个妥善的目的和一套周密的理则。后者很容易了解:一个法律的理则不周密,包含了缺陷和矛盾,当然不能成立;如果它与其它的法有冲突,也必须加以修正[⑤]。 前者需要一些说明,因为法所寻求的“公平正义”是什么?它来自何处?众说纷纭。大致而言, 它是由人们比较普遍、持久的是非善恶观念衍生出来的,是法的最深的基础,也是判定法之正当性、可行性的最重要的标准。这种观念又是怎样产生的?最早思考此一问题的是宗教家,他们大多推说这种观念是由神订立的。其它的思想家则从人们的心理倾向、生理需要和人际互动关系中去找答案,结果有的认为可以由个人探索内心去领悟它,无须外求;有的认为有赖特别聪慧的人(圣贤)去厘定;中国的法家和西方的实定法学派(legal positivists)[⑥]则认为是由掌握了权威的人树立的[⑦]。前几个说法各有若干信奉者;支持最后这个说法的人比较少,因为掌握了权威的人所立之法未必尽善,所以法的基础不应该只是他们的好恶,而应该是社会大众公认的一套是非,这种准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被称为“天理人情”,用现代的话来说便是“法理”。
天理和人情的应用
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是否必然会导致裁决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都知道,倘若裁决者不以寻求公平正义为目的,任何的规则都可能被他滥用。国法被滥用的可能尤其大,因为它是掌握权力者所制定的,并不一定有充分、完善的法理基础;它的内在理则可能不很妥当,因而它的各部分之间或许会有间隙、矛盾;它也可能和外在目的——公平正义——不符,因而被认为是恶法。滥用可能有这些缺点的“国法”是很容易的;相对的,某种准则既被认为合乎“天理”、“人情”,可见必定是为多数人公同认可的,可以由一般有常识、理智的人加以验证确认的(所以常言道“天理自在人心”)。当然它也可能被滥用,但滥用的过程和结果都可以很容易地被一般人看出来,所以其滥用反而比较困难。因此泛泛地说天理人情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而必然会导致裁决者翻云覆雨是不确当的。
就事论事的必要
至于是否可以通过就事论事不完全遵循现有国法的司法制度而伸张正义这一问题,答案已在前文之中。现在再简单地申述一遍:任何一国的法律都不是充分的(不能周密无失)也不是自足的(不能自证其是),在许多情形下司法者必须探索法理才能解决问题。司法制度不能伸张正义的原因极为复杂,而“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对待”、“就事论事”、“不严格遵守规则及判决的确定性”、“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天理人情有高度不确定性”等点,都不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不易伸张正义的主要原因。要检讨此一制度的优劣,必需深入中国以前的社会、、经济、立法、司法多种制度和实践以及传统的观念、习惯等等层次里去仔细审察,严格才行,不可轻易地指陈少数几个现象,便加论断[⑧]。
法学的基本问题和中国的传统法学
第二点要谈中国的法学是否不足道。我们知道法是一种社会规范,法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规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道、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等。既然已有这些规范,为什么还需要法?法与其它规范有怎样的关系,什么差异?法是哪里来的?若是由人制定的,什么人,以什么资格,用什么方法可以正当地取得立法权?掌有此权之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立法吗?或者应该遵守某些程序,寻求某些目的?如果是,那程序和目的是什么?由谁决定?依据那些程序,合乎那些目的而立的法有位阶和优劣吗?如果有,应该如何厘定?发生了疑问应该由什么人,遵循什么程序加以鉴别?鉴别所据的准则是什么?是一种高阶的法,或者是法之外、之上的另一种规范?如是后者,它是什么,怎么来的?除了这一高阶规范外,法与其它规范之间是否也有位阶关系?如果有,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处理?法可以超越甚至取代那些规范吗?或者法的内容应该甚至必然有若干限制,让某些社会问题和人们的行为听由其它的规范去处理、厘定?法应该如何施行?司法权由何而来?司法者应具备什么资格?司法权与立法权及行之间有什么关系,什么区别?这些关系和区别需要怎样的制度和规则来维持?法之施行须靠什么力量,是国家的权力吗?如果是,这种权力应该如何使用?它是否有内在的限制,因而只能在某一范围内生效?如何防止其滥用?如被滥用,以致遭受的抗拒,应如何处置?谁可以请求司法者执行法律?司法者在调查、审理、复核、裁判及执行最终判决时,应遵守什么原则,什么程序?如果在此程序中发生非常的状况,没有法律可循,应怎么处理?例如实体法对于某一事件没有明文规定作如何裁决,司法官可以将此事置之不理吗?或者可以引用其它规范来弥补法律之不足?如果这么做,他是否侵犯了立法权?如果不可以这么做,的权利义务无法厘定,个人和社会都受到损害,立法、司法制度的功能受到怀疑,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以上提到的是法学,尤其是法史学和法理学,所研讨的一些最为明显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更细的,无法在此列举。如果在这些问题之上再升高一层,则须探究法制与、经济、社会等其它制度的互动,以及法制与法理的演变和导向等等更为深奥的问题。每一个文化体系里都有人研讨这两个阶层的问题,中华文化应该也不例外。为什么滋贺先生讲到中国法学“几乎无话可说呢”?因为他未曾深入地探究吗?还是中国的法学确实不够发达?他自己的解释是“中国几乎找不到与国家权力分离而具有性地位的法律界精英,从理性的探索中产生学说、判例,以创造并支持法”。这句话显然有两个含义:第一,凡是与权力有关的人都不能客观地思考法学的问题。这种想法是与事实不合的,中国历来有许多知识分子曾经或多或少地参与过的工作,但并没有变成的喉舌,反而因为得知其弊,而加以深入的批判,对法学作出许多贡献,例如先秦的孔、老、墨、庄、孟、荀、商、韩对法的起源、基础、功能和限制,法的正当性,法与其它规范的位阶,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资格,司法权与行的调适,与之间的关系,个人与权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各项权力被滥用时个人及民众可作怎样的反应等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看法。我在《先秦政法理论》一书内依据上述诸点分类编集了这些看法的原文,可作参考[5]。
秦代开始将多项权力集中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以后以科举取士,这些措施压制了一般人的言论自由,因而学术上不再有先秦那种百花齐放的盛况。但是知识分子对法学的研究并没有断绝,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资料记载着许多法学家的言行和著述,例如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恒宽的盐铁论,刘歆的周礼,路温舒的论刑讯之非;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王充的论衡,应邵的风俗通,班固的白虎通;魏代陈群等人关于肉刑的辩论;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南北朝时期南宋王弘等与八座丞郎之间的德法之辩;南陈沈侏等论测囚之法;唐代长孙无忌等的唐律疏义,柳宗元的封建论和断刑论,白居易的论刑法之弊,沈毅和牛希济的论感化,吕温的论上下一遵于法;宋代王安石等的论自首,宋慈的论检验,杨万里的论法之效力,欧阳修的论纵囚;明代方孝孺和黄宗羲的论法从,马文升的论司法专业化,刘球的论司法不受皇命干预,顾炎武的论人治,苏伯衡的论德刑之别;清代崔述的驳无讼论,李绂的论折居,钱大昕的论婚姻,孙颐臣的论法律教育,郭鸣鹤的论法律演进,吴铤的论刑罚之功能,王明德和薛允升对清律的诠释,沈家本对历代法制的考述和评论等等。这些资料散见在他们的传记和著作里,有许多又被分类纂集在艺文类聚、玉海、十通、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之中。我为了准备做中国传统法制及法理的研究,在公私图书馆查阅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后来选出2352种,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书目》三册 [6]。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也纂集了有关的资料出版为《中国法制史料》八巨册[7]。此外中国历代都有些审判案件的“公牍”(如棠荫比事、名公书判清明录、刑案汇览、府判录存、鹿洲公案、抚吴公牍、樊山公牍、吴中判牍、宛陵判事日记、郑板桥判牍、秀山公牍、卢乡公牍)及档案(如宝坻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淡新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宫中档、军机处文件),其中纪录了许多司法者竭尽心力去探求事实,辨析条例和法理而作成公平判决的实例。这些判决大多是由司法官司的幕友及属员所撰的。我曾写《清代的法律教育》一文,说明他们曾受特殊的法律教育及在职训练,往往终生从事司法工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约二、三万人)的法律专业群,对于全国的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合理化、制式化[8]。他们也留下不少著作(如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续佐治药言、万维翰的幕学举要、 王又槐的办案要略、张廷骧的入幕须知五种、宗稷辰的幕学说、胡志伊的幕职问答、 陈天锡的迟庄回忆录), 详细叙述司法实务及许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行注意之点。任何人对于以上种种资料稍有所知,便不会说中国没有人从事法学的研究了。我相信滋贺先生不会不知道上述的那些资料。他在谈到中国法学时之所以“无话可说”另有原因:他认为中国关于法的研究不是经由“理性探索而得的学问”。
法并非单纯的理性的规则
将“法”看作是一种纯理性的产物(一套从某些前题出发,循着严密的逻辑规则演绎出的原理和准则)是西方受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生的一种法学理论。近代奥国的hans kelsen 对此阐述甚详,但是他也承认法律行为并非全由法律决定[9]。美国的oliver w. holmes在讨论法的本质时有一名言,“法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10]。roscoe pound, ronald dworkin 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11]。本文后段提到美国最高的几个判例, 便是为了证明法不是一套单纯的、由理性和逻辑所能建立起来的规则。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摹仿西方法制,学者们也尽量以西方的观点和思考方法来研究法学问题,以西方的词汇和推理模式来陈述其研究的结果。滋贺先生常以西文发表其著作并曾在西方讲学,更是不得不如此。因为人是用语言来思想的,不同的语言往往会导致不同的想法。当然,形成不同想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观点。绝大多数的事物都有许多层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而看到不同的现象。用了不同的语言将这些现象描述出来,自然会显出很大的差异。但是因为若干重大的基本课题是古今中外的人们都在追究并试图答复的,如果能对各时各地人们所提出的问答,将其因时因地而异的语言外壳剥去,直视这些课题本体,便可以发现它们是可以由人们用共识的理则来了解,并以一套共通的语言去改述的。法学的基本课题便是前文提到的人类为什么需要法,法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系,等等。现在且以涉及规范的类别、位阶及适用次序三方面的问题为例,略为说明如下:
中西法学的异同
西方将多种社会规范笼统地称之为法,但细分起来则有“自然法”、“人为法”、“宗教法”、“国家法”、“习惯法”、“国内法”、“国际法”、“普通法”、“衡平法”、“成文法”、“案例法”等等。其中有许多实在应该称为道德、伦理。它们之所以被杂入“法”内,原因在西文里“法”可以指无价值意义的“实然”(actually be)的规则(rule),也可以指有价值意义的“应然”(ought to be) 的规范(norm),二者常被混淆。但是这些“法”虽在西方社会里并存,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是有高低位阶的——在古代及中世纪,自然法和宗教法处于优势,与之不合的人为法可能被判为无效或被撤销;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人为的国家法位阶上升,实定法学派甚至认为只有经过一定的程序,由一国的统治者所颁布的才是“法”,是一国国内的最高规范,可以由国家以其公权力加以施行,而其它各种的“法”都被视为只是人们可以用作参考的行为准则,未必受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但是在一般西方人的观念中,“法”仍具有广泛的意义,他们的日常行为也都遵循着许多不同的“法”。西方的司法者在作判决之时,所依据也并不只是国家颁布的和成案树立的“法”,而常常引用许多其它规范。 英国的衡平法(equity)便是为了弥补普通法(common law)的缺陷而形成的,其原则大多以情理为据。美国的判决也常常深入探究案件所涉的社会背景以及现有成文法和成案所据的法理及相关的规范,然后决定某些法条或成案是否可以适用。如果认为不适用,便将法条判为违宪不予遵循,或者将成案另作新判。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例如其最高在1954年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决若干州规定黑白分校的法律违宪[12],并否定了1896年该院所作plessy v. ferguson 一案所立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在教育领域的效力[13];在 1973年roe v. wade一案中判决若干州限制堕胎的法律违宪[14];在1989年的texas v. johnson一案中判决德州禁止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违宪[15]。因为当时美国联邦没有关于这些民刑事件该如何处理的法律和完全可用的成案,所以法官们花了许多笔墨,作了许多情势的及法理的申述,然后援引了宪法内有关公平保障(equal protection)、正当程序(due process)及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等高度原则性的规定作成了上述三则判决。
中国的法理思想与此大同小异。如前所述,长久以来国人认为社会里有许多规范并存着,大体而言有道、德、礼、习惯、乡约、家乘、行规和法。“道”出于人们共识的理则和共有的情感,人们可以很自然地了解并接受,因而可以适用于人们的一切行为,人们也心悦诚服,所以被称为“天道”或“大道”。“德”是人们从道中体悟所得的比较具体的修身处世的准则,因为各人的注意点可能有异,这种准则也多少因人而稍有出入,所以其适用范围较窄,效力也较小。“礼”是人们基于道德和习俗而订立,用来美化行为的准则,其适用范围及效力视其合理性和实用性而定,但必然较道德为窄、为弱。“习俗”是一个地区的人们长久遵循的行为模式,未必合于普遍认可的准则,其适用范围及效力当然有限。比这准则更窄更弱的是“乡约”、“家乘”、“行规”等。它们是少数人为一些小团体而订立的,但因为其目的在于保障全体成员的利益,其内容也大多合乎情理或经成员共同认可,所以在施行时困难不大。最有问题的是“法”,它的基础未必是道、德,甚至也不是常人熟悉的情理和习惯,而只是少数人的特殊想法,其目的往往只在保护某些特殊的利益或排除某些特殊的障碍,其合理、正当的适用的范围当然较窄,虽然因为有权力的支持可以强迫人们遵行,但未必能使他们由衷地信服;如果它过于不近情理,人们会想出种种办法逃避甚至公然反抗它,所以它的效力也相对的比较小。
基于这种看法,多种规范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形成了上下的阶层: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窄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看起来像个倒立的金字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受到各层规范的拘束,但在决定是否遵循某一规范之时往往会考虑较高的规范才采取行动;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则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当地适用于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范以谋求解决,如荀子所说:“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16]。传统的“比附援引”和“经义决狱”都是因为现有法条不当或不适用而作的补救办法,实例繁多,不必枚举。我曾写过《良幕循吏汪辉祖》文,他在清代乾隆年间用这些方法处理案件而得到了合乎公平正义的结果,可以作为参考[17]。
以上的可以显示,对于一些基本的课题,中西的看法并无大异,但是因为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语言,将某些观点稍强或稍弱地陈述出来,在一个不明底细的、粗略的观察者的眼里,便显得南辕北辙差距很大了。滋贺先生用了西方人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畅论西方法学之后,如果接着以同样的语言和方式来谈中国法学,自然觉得“无话可说”了。
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学
近来国内有许多人像滋贺先生一样,用西方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在中国的资料里去找寻类似西方对那些问题所作的答案。因为找不到,失望之余,得到了和他相同的结论。有的声称他们能欣赏、甚至详论中国文化中“法以外的东西”,如诗词、伦理等等,但对于中国文化中“法以内的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说法有三个缺点,一是方法上的——如上所述他们不应该以一种法系惯用的观点和语言,去看和讨论另一法系;二是功力上的——从他们的论着中可以看出,大多对中西法学的了解都很有限; 三是认知上的 ——如上所述,在许多情形下,司法者需要在“法以外”的文化里去寻找更高一层的准则,以弥补法之不足或判断法的正当与否。初步学法之人固然必须究其文义,一个研究法学的人如果仍将研究对象局限于狭义的法——条文及判决——而不能进而究其精义,他的格局就太小,所见也太肤浅,对于上述许多法学上的问题都无法了解,更无法解决了。荀子说“不知法之义而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18] 便是此理。
在回应了国内常见的对传统司法和法学的评断之后,我想再简单地强调两点:第一,中国传统的司法固然有许多缺点,但不在滋贺先生和时下国内若干学者指出的地方。我正在写的struggle for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里,评论了了传统法制本身的设计上及外在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里的许多问题,指出许多实例显示在传统社会里仍有很多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力以赴,争取立法和司法上的公平正义,而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不该笼统地, 轻易地将中国传统法制说得一无是处。第二,中国传统法学自成一个体系,有无数知识分子自古至今在探讨着各种基本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的理论。只因他们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对现代人说比较艰深难懂。我们应努力去学习、了解,不可因为它与常见的西方翻译过来的语言不同,而将那些理论弃置不顾,甚至否定其存在。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于清季迭次被东西者所败,侵略者勾结汉奸在中国强行推销和教,犯下了许多罪行,反而指责中国法制野蛮,胁廹清廷给以治外法权[⑨], 因而启动了中国近代的法制改革。其实在明代及清初欧洲耶稣教会教士 (jesuits) 到达东方之后,曾经将其本国与中国相比,盛赞中国许多制度的优点,其中也包括法制在内。十八世纪后欧陆的法制逐渐改良,到了清季才显得比中国的刑法和程序法宽恕慎密。所以法制的优劣是相对的,因时因地而异。从现在的标准看,中国的传统法制的确有许多缺点,应该改革。改革应该先对已有的东西去芜存菁,然后斟酌时势,决定取舍。这是清季和期间有识之士的做法。此外有一些丧失了自尊和自信的人,认为只须引进西方的法制即可。此说的问题是:西方的法制是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的产物[⑩],中国没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虽然可以抄袭西方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但在付诸实施之时,便会遭遇到许多西方没有的问题,无法取得同样的成果,所谓橘逾淮成枳是也。有人因而主张“全盘西化”,但此说必须假设人有无限的可塑性,这一假设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不幸的是现在似乎还有人同意此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学一概否定,盲目地赞扬西方的法制和法学, 不知道西方人已看出他们自已的法制里有许多缺点,例如成案法 (case law) 的不确定性[11],社会里缺乏诉讼以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12],许多律师不顾公平正义,唯利是图,被称为被雇的鎗手 (“hired guns”) [13] 或救护车的追逐者 (ambulance chaser) [14],立法及司法被特殊利益团体 (special-interest groups, 如教会、工会、企业、财团、民间团体、种族集团) 所控制 [15] 等等;西方许多法学家则对目前仍在流行的实定法学 (legal positivi) 不满,而很欣赏中国传统法学将各种规范看成一个整体的观点 (holistic view) [16]。所以我要强调:西方的法制和法学虽有其长处,但并非没有缺点。我们在改进中国法制的时候,不能、也不该跟随西方人曲曲折折地走他们已经走过的路,犯同样的错误,寻求同样的补救办法,而应该深切地审视中外文化的优劣,取长舍短,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走的路;在研究法学的时候不可以为了一时的需要,鼓吹短视的做法,而应该看得高远一些,认清法学的基本问题, 先切实地去了解我国的传统,然后参考其它法系 (西方、、印度等) 的理论,综合中外的智慧, 盈漥而后进, 建立起一种更好的学说。这番话不是虚夸之言,我们读别人的著作,无论它多么博洽深奥,不要奉为圭臬,拾其唾余,而应该自行去思考基本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们也要自信并自勉: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而且要做得更好。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risprudence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taipei, china)
abstrac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raditional china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disregarding established rules and precedents and thus likened to “khadi justice.”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since the qin and the han periods when laws proliferated and decided cases recorded, traditional chinese judges, as civil servants elsewhere, took the easy route of applying existing rules and precedents. in the absence of such guidelines they had to find other ways to solve problems brought to them, particularly civil disputes. in doing so, they would carefully examine the facts and resort to norms above the law (e.g.,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general precepts of justice), a practice shared by judges in all jurisdic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jurisprudence is said to be underdeveloped. this only demonstrates how ignorant the critics are. even before the qin, legal theories flourished. through the later periods many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annotating the statutory laws and studying basic jurisprudential subjects such as the origin, objectives and functions of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other social norms, and left enormous amount of works of great profoundness.
the criticis are apparently prompted by a now prevalent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present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 sweeping denial of the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is not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improvement, especially if the critique is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 and ignorance.
key words: traditi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参考文献:
[1] 贺卫方.法律人丛书总序[a].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xx.1-2.
[2] coulson, noel j., 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4; conflicts and tensions in islamic jurisprud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turner, stephen p., weber,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marsh’s critique, newsletter, comparative & historical sociology, winter 20xx; marsh, robert m., weber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 reply to stephen p. turner (ibid); 林端 .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 – 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 [m]. 台北: 三民书局, 20xx
[3] 左传•鲁昭公六年[m]
[4] 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m]
[5] 张伟仁辑.陈金全注.先秦政法理论[m].:出版社,20xx.
[6] 张伟仁.中国法制史书目[m].台北:研究院出版社,1976.
[7] 岛田正郎.中国法制史料[m].台北:鼎文书局,1982.
[8] 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a].中国法律教育之路[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45-247.
[9]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0] oliver w. holmes, the commo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edition.
[11] roscoe pound, the formative era of america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1939); law finding through experience and reason (harvard, 1960);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1986);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1978).
[12] 347 us 483 (1954).
[13] 163 us 537 (1896)
[14] 410 us 113 (1973).
[15] 491 us 397 (1989).
[16] 荀子•王制[m].
[17] 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j].大学法学论丛,19.(1):1-50,19.(2):19-50.
[18] 荀子•君道[m]
--------------------------------------------------------------------------------
[①] 近来西方学术的发展异常蓬勃、快速,对于以往的经典和当前的问题,都有许多和评论性的著作,而且在一本新书或文章出版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又有许多评论在学刊、 newsletters甚至网络上发表出来。国内学者如果不能看到这些新的著作和评论,或须等待其中译,当然就无法及时知道西方学者对某一本书或文章的反应,因而对于此一书文的引述就可能不很妥当了。
[②] 参见《尚书》“吕刑”、“盘庚”、“牧誓”、“费誓”、“康诰”、“酒诰”、“大诰”、“多士”、“多方”、“尧典”、“立政” 诸篇。《周礼》虽系后人所作,大致仍有所据。其中关于民刑的实体法及程序法叙述颇多。见唐贾公彦等撰《周礼正义》,集于艺文本《十三经注疏》。
[③] 杨鸿烈在其《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对中国历代法令有简要的介绍,可以参看。
[④] 英美法系虽然重视 stare decisis (stand by the decided matter),但此仅系原则,事实上常因情势变迁而改变先例 (precedents)。本文稍后要提到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一案便是一个显着的例子。
[⑤] 关于此点,《韩非子》内 “五蠧”、“解老”、“亡征”、“饰邪”、“饰令”、“南面”诸章有精辟的见解。 lon l. fuller 在其 the morality of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一书中也有详细的。
[⑥] positive 一字源於 posit (手制),引伸而成制定的(prescribed),所以西方将人制定的(尤其是权威者所制定的)法称为positive law.今从林端教授译为“实定法”。
[⑦] 关于西方各派法学,下列著作内有简要的叙述和批评: clarence morris, ed., the great legal philosophe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9; george sabine, thomas thors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 illinois, dryden press, 1973; leo strauss, joseph cropsey,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howard davies and david holdcroft, jurisprudence, texts and commentary, london, butterworths, 1991; m.d.a. freeman, 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6.
[⑧] 这一点我曾在1987年写的“传统观念与现行法制”一文内提出,参见张伟仁.传统观念与现行法制[j]. 大学法学论丛.17.(1):1-64。即将交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struggle for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⑨] 西人对此有其一面之辞,参看 g. w. keeton,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9)
[⑩] 例如英国法制中的若干细节,包括陪审制度 (jury trial),訟務律师 (barristers) 和事務律师 (solicitors) 的分工,以及许多证据法的准则,大多是在英格兰被诺曼底人征服 (the norman conquest) 之后为了保护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欧陆诸国禁止刑讯及强调证据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宗教审判 (inquisition) 的反动。
[11] 关于此点除上述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例外,可参看john h. baker, english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20xx); thomas g hansford, james f. spriggs, the politics of precedent on the us supreme cou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xx); robert f. nagel, “bowing to precedent”, (the weekly standard 011:29, 20xx); nicola gennaioli, andrei shleifer, “the evolution of precedent” (nber working paper 11265, april 20xx)
[12] 这种机制,色括由家族、邻佑、乡里、行业内的长老出面调解或仲裁在西方社会里很少见到。美国的情形特别坏,一有纠纷,双方便说“在见”(“see you in court.”),伤害了人际关系,浪费了许多社会资源。
[13] 1995年轰动世界的o.j. simpson trial(黑人足球明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其妻及友二命)一案的辩护律师johnnie cochran 便是一例。虽然有极强力的证据可以推断 simpson为真凶,但是cochran竟能鼓其如簧之舌,攻击检方办案技术上的疏失,因而廹使陪审团判他无罪开释,因而获得惊人数字的律师费。有关此案的资料极多,兹举两则和评论如下:douglas linder, the o.j. simpson trial, in the jurist, october 2000; martin mclaughlin and david north, the simpson trial: some ugly truths, in the iwb 20xx.
[14] 此类小律师专门趁人急难(如车祸以致死伤),促其起诉,以求巨额补偿,或在其它案件以仅收“胜诉费”(contingency fee)为条件,诱人兴讼。
[15] 这些团体,甚至许多外国,都雇佣了与单位或执政党有良好关系的人 (特别是卸任的高级官员或议员) 为说客 (lobbyists) 去为其雇主的利益关说,影响立法或行政。
[16] 西方近代的法律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w),法律人类学 (legal anthropology),法律与社会 (law and society),批判法学 (critical legal studies) 等都有类似的看法。
论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_宪xx文 第六篇
摘要:历史方法在宪法学的方体系中正日益被边缘化。与理论上的这一发展方向不同,历史方法在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却是一种正在被过度使用的方法。全面反思历史方法在宪法学中的运用,对于宪法学的实践与规范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历史方法在宪法学的运用中主要有四种面相,即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人们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的取舍不同,对宪法学保持的学科地位的意义也不同。历史方法在运用中存在许多缺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于历史合理性,从而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内在逻辑和价值目标的关注以及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历史方法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宪法学研究中更好地引入社会方法,而且对于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以及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宪法学;历史;方法
当今中国各类法学教科书对于历史方法的说明,基本上都运用在《论国家》一文中的一段话来阐述,写道:“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由于主义哲学强调世界观、认识论、方的统一,因此这里所谓的历史方法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法学研究中的全面贯彻。wWw.meiword.COM从法学方体系的结构层次出发,它更多的属于法学方体系中作为根本方法的主义哲学方法,因此也有人将之概括为法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2],当然历史方法还可以细分为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手段,如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不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有历史的方法,事实上历史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这是因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关注的是特定的历史事实,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事实只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的工具性资料,至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运用何种原则,则由使用者决定。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历史学提供资料,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的结构和原则。[3]
从历史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来说,历史方法几乎是“中立”的弥漫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方法,至于这个根据是“民族精神”、“社会习俗”还是“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影响历史方法的运用。历史方法的这种中立性和普适性,使得法学家确信这一方法尽管十分重要,但并非法学(当然也包括宪法学)所“专有”,在谋求学科独特性的学术努力中,历史方法不论是在整个法学领域还是在作为其分支的宪法学领域,都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整个法学方体系中所占有的比重也日益缩小。如果从方的结构层次出发,这一方法一般被归入到法学的一般方法或基本方法中,如果从同一方法序列的不同类型的角度出发,这一方法往往又被归入实证方法特别是社会实证方法之中。人们有时泛泛地谈法学研究中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有时又将历史方法仅仅归结为“文献方法”[4]。在将法的方体系分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律方法的情况下,法律方法基本上忽略了对历史方法的说明,历史解释基本上是唯一的存在形态。
在宪法的方体系中,历史方法的境遇也基本如此,如有宪法学者指出包括历史方法在内的“传统社会科学的老方法”“只能算是宪法学在蒙昧时期所采用的‘青铜铁石器’”,是“宪法学方法的无特定性状况”的表现[5],在人们看来只有发掘和强调宪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研究对象多有竟合的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中保持宪法学的学科地位。近来关于宪法解释和宪法规范研究的升温,说明了人们在认识上的转变。
本文认为,历史方法尽管缺乏个性,却与阶级方法一样,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仅仅将其在方结构中边缘化或弱化,而不对其进行全面的反思,对宪法学的发展有害无益。此其一。其二,历史方法在宪法学领域的运用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有一部分缺陷并非由历史方法本身引起,而是由具体的技术性手段使用不足引起的,因此,历史方法不应泛泛的为“宪法学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负方上的责任。其三,宪法学的知识体系庞杂,既有面向理论的又有面向实践的,在理论上的哲学立场不同就会导致实践上不同的利益取舍和衡量,因此,历史方法在不同的领域面相不同。有必要深入历史方法在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中不同的特征和作用,以达致对于这一方法的深入而客观地认识。其四,历史方法具有恒久的价值,在当今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更有其独特的理论功能,全面揭示这一点,是宪法理论研究深化的需要。
一、历史方法的面相
探寻历史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制度的现实或冲突的解决如果具有“历史根据”并表现出来“历史的合理性”,也就具有了巨大的说服力。对于宪法学来讲,不论是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制度操作层面,人们都不拒绝“向后看”的办法,但表现形式不同。
人们通常会在如下情况下采用历史的方法:
(一)对宪法学的概念、范畴或原则作语源学的。要理解和阐明宪法学中特定的概念、范畴和原则的内涵,人们往往需要到历史中寻找它们的思想来源。除了专门意义上的学术史的探究之外,人们经常采用的是语源的,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对于“宪法”这一概念的语源,[6]语源是对具体词语的来源、本义、引申义的考证和研究,是一种历史流变的,自然可以归结为历史。其他的如“国家”、、“民族”、“自由”、等等,都可见语源学的。
(二)宪法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各种社会变量长期累积的结果,既不会骤然发生也不会骤然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主观目的如何,制度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轨道。我们往往会在制度的“断裂”中看到“自然成长”的因素,后者的“自然”要比前者的“建构”更有生命力。这促使人们对制度的结构和制度的事实作全面的历史。法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史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洞察力,他说,“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7]“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8]中国比法国的历史更悠久、更复杂,因此现代性制度的建构就有着更明显的历史重负。
对宪法制度作历史有三种基本形态,其一,中国近现代的制度具有明显的移植色彩,因此对某一制度在西方的代表性形态作历史的梳理,成为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其二,有许多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本土化”的,此时人们所作的就基本表现为对制度的实践的较短时段的梳理;其三,有一些制度问题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有关,这时对制度的历史就可能追溯到中国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由于制度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所采用的历史有时只有一种形态,有时则三种形态并存。
中国的制度、保障制度、地方制度、司法制度等重要宪法制度的形成与现状都有人积极地进行历史的探究。[9]
(三)宪法的观念与文化。与对制度的历史不同,观念与文化的,是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出发的。近现代的历史学研究有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家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不仅有历史学家指出:“历史学只能在社会学的浸润中进展,反之亦然。”[10]而且,人类学取向则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即历史学家开始“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和信仰。”[11]人们希望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史学的转向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宪法的历史探究,人们几乎是毫不怀疑的认为人的观念与文化传统,是潜在的决定状况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不仅应该研究制度的发展史、制宪者的思想史,而且也应该探究普通人的观念史,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史
(四)宪法条文的历史解释。
在宪法的操作层面,永远无法回避条文的解释问题,解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法律活动。不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不论解释体制如何,宪法适用者在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宪法规范与个案事实合理结合起来问题,宪法规范总是抽象的,个案则具体而实在,解释因此成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桥梁。解释的方法多种多样,詹姆斯·安修在《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一书中列举了多达48条的宪法解释的准则,[12]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历史问题的,詹姆斯·安修到:“在宪法解释中,美国最高经常受到历史教训的极大影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事实”[13],就历史资料来看,“最高利用的历史大致有两类:(1)宪法产生前的,颁布宪法和修正时的历史,借以理解制宪者的意图。(2)能说明在宪法判决中值得考虑的社会利益的历史和能对这些利益的冲突作出公众所接受的调节的历史。”[14]从我们的视角来的话,前者主要指的是发现反映立法原意的“历史资料”,后者主要指的是协调社会冲突的历史惯例。
尽管人们对追究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有各种批评与责难,[15]但对制宪者的制宪原意作历史的,显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正像主张追究历史原意的学者所认为的,探寻立法原意不能局限于法律语词本身,而必须借助各种立法史资料,尤其是立法准备资料。通过对立法史材料的研究,解释者就能了解法律制定时的一般情况,了解释法律得以通过的一般社会状况(如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与权衡),以及立法者意图通过法律予以救济的对象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把握存在于法律背后的、社会和经济的目的。因此,立法史材料对于确定立法原意具有重要意义。[16]
上述历史方法的四种面相,可以概括为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前三种基本上属于理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形而上的学术研究方法,最后一种则是属于实用宪法学的操作方法,主要是形而下的宪法推理与宪法解释技术。由于人们在方的研究中正在努力区分“法学方”与“法律方”,并将后者视为方的核心,[17]历史方法的不同面向,从不同的法学领域来看,意义自然也会不同。
二、材料的取舍:“历史”的不同内容与意义
历史方法的不同面相使我们发现,人们几乎是轻率的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方法,至于“向后”的限度以及所搜寻的资料的取舍,大多因具体问题需要而定。这里面隐含着对于“历史”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的不同理解,如果不对“历史”本身做细致的话,就可能使本来具有经验性与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因为人的取舍而模糊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就出现了人们表面上是在做“历史”,而实际上不过是在为某种既定的目标寻找片面的资料,因此也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由“发现”历史事实的经验研究变为“解释”历史事实的价值探寻了。
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有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和艾希洪,他们在1815年创立了《历史的法学杂志》,成为历史法学派的喉舌。但是人们却发现,所谓“历史的”研究,“对萨维尼而言,其内容与对象不言自明地指涉罗马法;对艾希洪而言,毋宁是指涉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这种差异,也是导致日后历史法学派成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法学派的原因之一。”[18]引用这一事例是想说明,在不同的语境下、基于不同的目的,“历史”一词指涉的实体内容可以有巨大的差异。历史法学派的发展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历史方法在不同理论层面地运用也表现出来这样的特点。如果不对“历史”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作细致,历史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就有可能被“偷梁换柱”,从而降低了这一方法在法学方体系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古代史与不到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两相对比使得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方法,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历史不仅仅是向后看的问题,还有一个看得远与近的问题。
(一)有年轻的宪法学者在他的关于宪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在“宪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犹豫的列举了“历史方法”,“既然宪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积淀和蒸馏的结晶,而人类文化是连续不断的,那么,要了解当前的宪法制度,就必须寻本溯源,探索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后对于宪法制度的含义,方可以有较清澈的认识,这是把握宪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一步审省宪法得失和促进宪法发展的基础性条件。”[19]这里的历史显然是“大历史”,中西古今囊括无遗,他所使用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化”几乎是同义词。“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重大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20]这样的“历史”事实上只是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这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层面的历史体现出来的是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对宪法问题作宏大叙事的历史,是当前我国理论宪法学领域“历史方法”的一般性特点。[21]不仅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实证主义法学特征的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语源学探讨,也往往会陷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以对“宪法”的语义为例,[22]首先人们指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有‘宪法’这一词语,但他们的涵义却与现代的‘宪法’迥然不同”,接着人们就分别介绍宪法在中国和西方的词义演变,最后作为结论人们会指出“古代西方的宪法往往侧重于组织方面的意义,而古代中国的宪法却没有此意。”如果仅仅是为了说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宪法”都没有现代的根本法的含义,人们就没有必要作这种包含古今与中西的对比。结合教课书知识体系中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宪法的历史发展部分”,这样的知识内容显然是为“宪法产生的条件”这样的问题,提供历史的铺垫。“宪法何以产生于西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法?”“为什么在19世纪末宪法被引进到了中国?”“宪法在中国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历史境遇?”等问题是这一进路所隐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识。
这是一种宏观的、可以依研究者的兴趣无限向后追述的、跨文化的历史观。就历史资料而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经济、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资料[23],这部分资料并非宪法学的专业性资料,宪法学者只需要借用历史学的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显的“拿来主义”色彩。这部分资料使用的越多,宪法学的学科地位的表现就越差。
(二)当今中国宪法对于制度的历史,可以算是一种“中观的”的历史观。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纪为限,中国基本以19世纪中后期为限,由于涉及到制度的性质转变问题,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宪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是与特定制度形式直接相关的,较少的涉及到观念与文化问题。对于制度作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清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寻求现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为了发现用于处理宪法纠纷的制度惯例,即是以理论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实践为指向的。
认真当今主流宪法学对于宪法制度的可以发现,对于制度的研究在逻辑结构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制度概念、历史发展、制度内容、制度完善,这主要是教科书的制度模式,因为教科书与学术专著的目的不同,教科书主要致力于教给学生系统和完整的知识,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因此教科书的制度论证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识性的制度论证模式。我们以教科书对于制度的研究为例。许崇德教授主编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就对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来介绍,即“一、制度的概念”(概念);“二、制度的历史发展”(历史发展);“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内容);“四、加强和完善制”(完善)。[24]这四部分的内容分别承担了制度性质、历史合理性、合理性(其中包括规范性)、实效性的论证。其他如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这一逻辑顺序论述。对历史合理性的论证紧随制度的性质界定之后,表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具有统帅作用。宪法教科书之所以热衷于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在制度的研究中,人们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信:一个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至今,这个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合理性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思维定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对制度本身的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合理性探究。宪法学目前的知识体系对制度的规范和逻辑不足已证明了这一点。唯物史观虽然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显然不能取代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和逻辑。
对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脉络的,对于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种外在的,这种外在的所使用的材料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法学其他领域是开放的,宪法学既可以从其他领域中“拿来”,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简单的“拿去”。理论宪法学领域的历史尽管也可以是建立在严格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的,但资料的取舍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种形态的历史资料都有可能使用,观念的历史、制度的历史;古代史与近代史;整体的历史与专门的历史都可能交织在一起。历史的确定性有时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流变与文化的抽象。这样的历史正越来越转向历史社会学的。历史方法在这一层面的使用,仍然无功于宪法学的学科地位的形成。
对制度的历史还可以围绕特定制度的规范结构和内在运行方式来进行,这种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相比较而言无法直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因而有利于宪法学学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以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为例,对于我国为什么要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个,即“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历史传统”、“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状况”、“融洽的民族关系”[26],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外在于单一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实质涉及的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却没有真正的研究。
可见,对于制度的历史既有无法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历史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应用宪法学领域,“历史”的含义是基本上确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惯例、习惯性解释、确实可循的立法资料等。
宪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宪法中任何一个条文的解释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会利益,任何能够称之为宪法冲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应该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普遍性和稳定性。宪法的适用机关在运用宪法解决社会冲突时,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客观资料为基础。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过立法准备资料来加以,这里面的“历史”便是立法准备资料。有时它也指的是惯例或习惯性解释。[27]
在一般意义上,宪法的适用主要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一层面的历史方法乃是一种司法方法,在成熟的国家,这一方法的运用尽管还有争议,但已相当成熟。在美国有法官极力主张根据历史来理解宪法条文。宣称“其含义如此依赖于历史,以至定义反而成了累赘。法官适用宪法必须受制于这些历史。”[28]我国宪法缺乏司法适用性,宪法操作技术的发展缺乏强大的实践动力。历史目前所能见到的实践,基本上局限于立法机关对于制宪原意的,人们通常认为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应该是被参照的立法准备材料。
宪法操作层面的历史所奉行的是一种“微观”的历史观,强调资料本身的客观性。
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的历史方法被视为宪法学的特定方法,这时历史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的学科地位。但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历史解释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对于法官们来说,“虽然在宪法解释中参考的历史资料很丰富,但只要他有碍于保护现实的价值和利益,就几乎会被忽略或轻视。”[29]
三、历史方法的缺陷
罗斯科·庞德在全面批判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写道:“要理解19世纪历史学派的法理学教义,我们就必须牢记:就研究法律论题而言,历史法学派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且压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离了哲学时代那种积极且创造性的法理思想。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从更为直接的角度看,历史法学派在两个方面背离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离了自然法关于制定成文宪法的观念以及狂妄无视传统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特定时空下的条件的做法;二是背离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创造奇迹的思想。”[30]
他还转述了法官霍姆斯对历史法学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第二,它对法律的改进总是持否定态度;第三,它还根深蒂固地认为,一项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只要法律年鉴能够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为历史原则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项适当的甚或是必要的行为规则。”[31]
由于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发现而不是制定的,把历史作为“支撑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法律发展中的终极动因。”[32]也就是将历史方法作了极端化的运用,因此,历史法学派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终被其他学派所取代。
唯物史观与历史法学派的历史观在哲学立场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历史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被过度使用也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对于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历史合理性,客观上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帮助人们绕过了一些价值难题,但也因此使宪法学在价值问题上较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目标是近现代各国的制度共同关注的,但显而易见,人们对上述价值的理解不同,为实现上述价值而设计的各类制度的具体细节也不同。宪法规范内在地包含人们的价值选择,制度的发展应该以这些价值目标为标准并服务于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的建设而言,由于具有长期的借鉴与移植的历史,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和如何面对价值冲突,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价值难题。
历史方法强调资料的真实可靠,客观上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而实证的方法在价值问题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张价值多元的。运用实证方法对制度进行研究是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么,而不是制度应当是什么。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历史方法着重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从有关制度研究的客观结果上来看,就是通过对制度的外部条件的实证,取代对制度本身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适应国家性质的简单判断上,至于这一制度内的国家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与的关系、代表与选民的关系等具有较多价值内涵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辞便是根本没有。历史使人们摆脱了价值上的困扰,但也因此降低了宪法学的理论价值。
有学者在批判中国宪法学方的总体取向时指出:“在新中国的宪法学时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实证主义也好,虽然均受到我国主义法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在反对自然法、坚信规范可以创设权利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学其实恰恰与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脉相通。”不仅如此“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早已经再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得到极其重要的发展,而中国的宪法学迄今还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套‘纯粹’的规范科学,精微缜密的宪法解释学也尚未成就。”[33]
历史方法既是实证的,同时又是“非规范”的,无疑对上述缺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历史方法的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有关宪法制度的研究中阻碍了对规范与解释方法的运用。
宪法的方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人们除了有可能在哲学立场上根本对立之外,各种研究方法之间是可以共存和相通的,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由于目的不同则普遍存在以一种方法或几种方法为主导以其他方法为辅助的情况。如果在宪法学的整个研究领域都受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因此某一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研究方法是可能存在的。阶级方法在新中国早期的宪法学研究中就占有压倒的优势,并在客观上阻碍了其他方法的使用和发展。历史方法是否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有必要认真地。
在宪法学几乎所有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方法的身影。以宪法学对特别行政区问题的研究为例——问题被分成四部分:特别行政区是构想的产物;特别行政区的概念与特点;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法律制度。[34]抛开上述内容中对制度的规范性解说不谈,这一制度研究本身至少涉及到三个合理性问题:首先,在出现了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之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的界定的合理性;其次,为什么设立特别行政区而不是其他样式的地方,即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合理性;再次,特别行政区为什么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和法律制度,即特别行政区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合理性问题,宪法学教科书并没有基于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新变化,重新考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将其近乎武断地作为特例,认为特别行政区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被单一制吸收,即“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35]因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基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二个合理性问题,宪法教科书主要是通过对理论的合理性论证来进行的。“的伟大构想,是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提出来的。”“两部基本法的指导思想就是的方针”。[36]就论证的实质而言,使用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取代了对特别行政区这一地方性制度的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三个合理性问题,教科书中的论证一个是基于的原则,一个便是“从香港和澳门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37]所谓实际情况其实就是香港和澳门一百年来已经形成的和经济制度,仍然主要是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论证。
除了围绕着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的和法律制度作了简要的解说之外,即没有明显运用作为法学基本方法的价值方法,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没有运用精微缜密的法律解释方法,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以及在特别行政区运行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与其说历史方法阻碍了规范与解释方法的运用,毋宁说对历史合理性的重视减轻了人们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因此,霍姆斯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在历史方法的过度使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踪迹。但与阶级方法全面贯彻从而使得阶级性范畴成为宪法学的核心范畴不同,历史方法并不具有如此的特性,他对其他研究方法的限制是有限的。
其三,历史方法的过度使用,既有可能使人们忽视制度变革的实践,客观上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
历史方法强调对问题的研究“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这一研究方法的过度使用,将使人们主要关注制度在“过去”的发展历程,而不是制度在“现在”的展开。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空前激烈,现有制度如何完善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这是历史所无法做到的。制度的发展不仅有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作用,也有人的理性创造作用。历史方法使人们忽视对制度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从而不仅会忽视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也会忽视对人的权利实现的研究。
四、历史方法的价值
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看,特别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历史方法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就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而言,历史方法的价值也不必特别的考量,因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历史方法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是否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
当今中国的宪法学发展面临着两种深刻的危机:其一是面向实践的危机,宪法学现有的知识体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往往缺乏解决能力,无法快速应对社会新的发展需要,宪法学知识的社会价值相对其它部门法学较低;其二是面向理论领域的其他学科“攻城掠地”的危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经济学以及法理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竟合关系,一方面,这些学科不仅广泛地进行着“宪法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宪法学在同类问题的研究中又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这些学科所取代,也并非耸人听闻。
上述两种危机的形成,根本上都与宪法学在方方面的缺陷相关。其中第一类危机意味着宪法学在面向实践方面的研究方法不足,第二类危机则意味着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没有挖掘出来。如果要克服危机,实现方上的转换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历史方法有独到的价值。
(一)从历史到社会
对于的实际运行而言,历史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实际上,不论是远的或近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都是间接的。通过历史是否能够找到确定的规则,也被许多人怀疑[38]。但确定无疑的是历史的能使人们更好的关注制度的社会环境问题,从而将社会学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历史也可以弥补社会学的某些缺陷。有历史学家就了社会学家的缺陷,并提出了二者互动的可能性。他指出:“他们(社会学家)认为那些根据19及20时社会所建构出的理论模式,适用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社会学理论提供史家一个采用或舍弃的基础,然而如果这些理论无法符合历史学家发展理论叙述的需求,问题就相当麻烦。”“理论史家若想发展,就必须修正现存的理论,而不能只是把他们套用在史学主题上:同时必须以一种更具互动性的观念来替代社会学与历史学//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模式。”[39]从学术源流来看,历史法学派与社会法学派也有极深的渊源。[40]
当今在宪法学主流知识体系中被过度使用的历史方法,可以被利用来社会多元的利益格局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从而将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转移到制度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冲突,由此,可以使宪法学的研究更紧密地围绕制度本身并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指向。
(二)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
社会利益越来越具有多元性,无论是法官还是立法者都无法简单的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在利益衡量过程中,宪法以及宪法学都应该对利益的平衡发挥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推动了利益的多元化,特别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利益群体,原有利益群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所谓“共同利益”已经不存在。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状态,并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能人为的加以改变。如何认识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特别是在两种合法的利益需要之间进行协调,需要参考利益格局的发展流变。
宪法与其他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要以根本法的形式为国家设计一套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有限”,以最终保障的实现。对于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来说,要始终围绕着宪法规范,以社会发展为背景,对制度进行充分的逻辑。宪法学并不关心一种新的社会利益的出现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宪法学将全部的研究重心放在现有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为各种已出现的、未出现的利益冲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框架,特别是当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一套科学的权利救济机制。就这一研究重心而言,宪法学是不开放的,其他学科无法“攻城掠地”。历史方法的使用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研究重心的存在[41],并通过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宪法性解决机制的历时性研究,对现有的相关制度提出更客观的评价。对于其间所包含的价值评价因素,历史也有可能为某种价值目标提供经验性的客观标准。
(三)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
目前宪法解释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作为应用宪法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地位也正逐渐得到客观的定位。[42]有人诙谐地将宪法解释的方法称为宪法学的“独门暗器”[43],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学者的共识,“在实践不发达的国家里,宪法学通常就是某种道德理论或学说——某种。然而,一旦宪法形成了一部完备的文件,并在实际诉讼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素材,宪法学的研究重点就转移到宪法条款的意义本身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因此,宪法学主要就变成了案例研究。他更注重宪法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解释和澄清,而不是与评价规则的合理性。”[44]
历史方法在宪法学中的长期运用,已在宪法性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知识和成熟的技术,在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和规范转向,历史方法以其所奉行的实证主义精神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constitution
abstract: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is obviously marginalized in methodology system of constitution. contrary to this trend, this approach is overused in the mainstream knowledge system of constitu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reflect this approac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actices and norms of constitution. there are four main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in constitution, namely,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of etymology,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of institution,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of conception, and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of hermeneutic. the choice of historical data in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 affects whether constitution keep its independent status as a discipline. defective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not only hampers other approaches in some degree, but also overly depends on historical rationality for provi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nd hence lessens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paid on inherent logic and value goal of institution; make the scholars ignore hominine creativity of rationality in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still has its unique value. it can help scholars import social ysis approach into constitutional studies, reasonably set keynote of constitutional studies, and supply data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onstitution, historical ysis, approach
-------------------------------------------------------------------------------
[1] 《选集》第4卷,第26页,出版社1995年版。具体如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都采用了这一界定。
[2]如有法理教科书指出:“必须坚持法理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即是说,法的现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决不存在什么孤立自在的法的现象,而历史的联系是基本的联系形式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态度和眼光考察一切法的现象,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要有深厚的历史感,深入研究法的现象借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而作出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合理性评断。”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1页。
[3]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就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主动性。
[4]文献方法——“是从档案、报刊、杂志、官方文件历史记录等文字材料中收集情报和信息的方法,属于间接观察法。在法学的社会实证研究中,文献是十分重要的方法,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惟一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张文显主编:《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第78页。
[5]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29页。
[6] 我们可以在各类宪法学教科书中轻易得找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代表性的如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一章。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
[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32页。
[9] 王人博的《文化与近代中国》、季卫东的《法治秩序的建构》、蔡定剑的《历史与变革》《中国的制度》等等,都可见相关内容的论述。
[10] s·肯德里克 p·斯特劳 d·麦克龙 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王辛慧等译,上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1] s·肯德里克 p·斯特劳 d·麦克龙 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王辛慧等译,上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2]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13]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14]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5] 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2页。
[16]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7] 参阅林来梵、郑磊:《法律学方辩说》,《法学》20xx年第2期;张文显主编:《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将“法学方”与“法律方”分列第一和第二章
[18] 林端:《由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台北三民书局20xx年版。
[19] 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xx年版,第24页。
[20]萧箑父:《中国传统哲学概观(一个论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37页。
[21] 笔者曾经写作《中国的多元文化背景》、《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宪法典的文化意义》等文,现在想来,从方的角度看,几篇文章中对于历史的,无疑采用的都是大历史的观念。
[22] 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33-34页。
[23] 如关于近代宪法产生条件的研究、宪法观念与文化的研究等。
[24]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8页。吴家麟教授在1983年的国家统编教材《宪法学》中也基本上分成这样四部分来介绍,即“一、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概念);“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发展);“三、制实行集中制”“四、制的优越性”(内容);“五、坚持和完善制”(完善)。(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16页。)这说明长期以来对于宪法制度问题的研究,除了在内容上稍有变更外,在研究模式上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
[25] 《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26] 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27] 参阅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 历史对宪法解释的影响”部分。
[28]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9]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30] 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第18-19页。
[31] 【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第15页。
[32] 【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第29页。
[33]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20页。
[34]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44页
[35]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36]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
[37]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38] 一度在西方流行的相对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得先验的概念,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而已。否认历史可以被人是与理解曾经成为一种时尚。([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出版社20xx年版,中文版序。)
[39]s·肯德里克 p·斯特劳 d·麦克龙 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王辛慧等译,上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0] 参阅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从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20xx年10月版。
[41] 萨托利在《疏议》一文中对宪法与内涵的梳理就极具代表性。参阅萨托利《疏议》,载于刘军宁等遍:《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42] 如韩大元教授就曾指出:“宪法解释学的建立是现代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与基础,现代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完善。从宪法学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宪法学开始于宪法解释,终止于宪法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学反映了现代宪法学发展的基本去向。”(韩大元:《现代宪法解释学》,中国法学网。)
[4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39页。
[44]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45页。
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_宪xx文 第七篇
关键词: /法治/国家观念/国家权力
内容提要: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可以说明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理论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把事实有机地反映出来,但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法治思想不仅要被社会大众接受,而且也要被家接受。因此,本文以和法治的钟摆为题不过是要说明,如果法学家把法治思想运用于实践,那么,一个时代的法治思想必须同步于那个时代的信仰、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且必须给出一个有利的结果。换言之,形成民众和统治者对法治的信仰与接受法治的文化环境,对于现代和法治思想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其重要性往往大于理论自身的逻辑一致性。
从思想传统上看,人类法律的效力取决于稳定的权威。古希腊人的秩序观念承认了法律的重要性,罗马人通过确认公法和私法之分强调了对私法权利的保护。wWw.meiword.CoM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的学者和罗马法学家则通过论证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而强调限制权力,他们或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指出君主的权力必须受到教皇和上帝的制约;或者从世俗的角度出发,论证君主的权力不能侵犯人的若干固有的权利,必须符合某些普遍规则和道德等等。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行为的观念。这是因为,在制定法律时,立法机构不仅是立法的主体,而且也是家活动的舞台。法律制定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且被制定的法律也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因此,现代法治一般都强调国家的立法活动受到宪法的限制,然后,法律本身对整个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的首要性的支持。然而,用法律限制权力并不意味着法律应该取代,这既不符合法治的目标也不符合的目标,并将威胁到法律的可靠性、稳定性的职能,特别是其保持——至少是暂时地保持——尚未决定的产生于任何长远冲突的问题其现状的功能,还会使无法行使其正当职能之一,即公开讨论哪一项决策是正确的以及评估和加强利益。虽然已有学者指出,和法治本身不是本源性的,从基本方面来说,是决定法律,控制着法律。不是法治或创造了自由的社会,而是孕育了和法治。“法律的苍穹”不是的,它建立在的柱石之上,没有,法律的天空随时可能坍塌。[2]但笔者认为,法治作为现代国家基本原则的首要性意味着在问题上斗争的人应该支持法律,不应该干涉法律。法治一旦成为秩序的基础,就会指导人们通过法律规则而非诉诸来解决()价值观或者()利益的冲突。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这意味着要破除权威来源于的信条,赞成权威来源于全体的“同意”的观点(即治权民授)。当然,仅仅宣扬国家权威来源于这一信念对实践并无多大助益,除非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权责对应,控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事实上,法治的核心就是指在一种国家制度内,行为受到某些法律规范的限制。换言之,法治就是保护某些基本的个利不受制于武断行为的一种承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能随心所欲地创制法律,并决定它自己是否违反法律的内容的,绝不是一个法治之下的。以上我们也可以得知法治的关键问题是国家权力守法和社会权利保护问题。因此,本文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一)
公元前800年至500年,希腊人告别了部落社会的荷马时代,逐渐建立了城邦制度,而城邦制度是古希腊法律思想的温床。在柏拉图时代,希腊本地和各殖民地时常有互相争战的城邦,各城邦可以结成联盟,而且有不同的政体。有的是的,如雅典;有的是贵族统治,如斯巴达;有的是专政。这说明,希腊在古典时代就从未形成一个共同体。从各城邦多种多样的演进轨迹来看,大致经历了王政、贵族、僭主和几个时期。其中,雅典的是雅典发展的高峰。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也认为,雅典的确定,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当时,雅典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而是经过在概念上平等的公民们聚在集市广场(agora)上讨论后得出的。这广场往往也是,每个公民享有均等的发言机会。在雅典这样的大城邦,一次公民可能会有数千人参加,所以在会上发言的主要是研习过讲演技艺的贵族,或是拥有一群追随者的头面人物。在平民政体中,许多公共职务是由抓阄来决定的,但主要职位靠选举,一般也是由有权势的家族成员来担任。雅典的体制,就其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展而言,是由来统治的。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本质上是由下层阶级统治的。政体容许将真正的权力与责任赋予家人(虽然没有赋予奴隶或妇女),宪法保护并扩展他们的利益。富人与出身高贵的人在雅典比那些有着寡头体制的希腊城邦有更少排他性的权力控制。[3]
雅典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两位富于创新思想的立法者,梭伦和克利斯提尼的工作成果。他们抱着改变统治阶级与生活的本质的明确目标来改革政体。[4]梭伦推行的改革中有两个特点代表了希腊的基本特色。第一,梭伦谨慎地将地域单位作为活动的基础,这就使各个家族或部落的成员融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选区具有同样的功效:它将住在同一地域的各形各色的人们组合到一起,打破自然关系形成的界限,鼓励大家在整个居民区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参与活动;第二,完成改革之后,梭伦有意地离开雅典十年之久,让别人来管理这新的体制——这是分权原则的雏形。因为若要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设置一整套附有各种责任的抽象职位,而且从原则上说任何有能力的官员都可以担任这些职务。专制体制完全依靠专制者个人的品格秉性(他们往往是喜怒无常的),而体制的领导人则是按照职务所赋予的责任来行事。[5]
就我们所知,生活在雅典的柏拉图最先阐述了任何社会都要面临的中心问题:谁来裁定?柏拉图对统治者的信心建立在他自己关于至善的理念上,懂得至善就成为至善(to know good is to become good)。至善是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可以通过理性求得知晓。由此出发,柏拉图认为只有知识丰富、能把握理念的哲学王成为统治者才能避免国家陷入灾难。但在其晚年,特别是在参与实际斗争失败后,柏拉图认识到“理想国”真的只是“理想”,因而在《家》和《法律篇》等著作中强调,法律是维系社会生活的“金色的纽带”。与此相关,柏拉图开始关注法治问题,并首次提出第二等好的统治是“法律的统治”这个问题。统治者不再超越法律之上,而是“法律的仆人”。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由此看来,柏拉图眼中的法律是神圣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服从法律就是服从理性。但是,柏拉图的
法律思想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色彩,[6]他甚至还论证了一种等级制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国。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命运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制的疑虑。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指出,也会沦为专制主义。对古希腊人的体验来说,不受限制也会走向。这是因为多数派统治过于不稳定,公共福利会成为派别冲突的牺牲品,决策往往不是根据法律规定与少数派的权利作出,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处于支配地位的多数派的强大势力。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佳的体——他称作“波里体”(polity)——必须具有一定的成分。他研究了许多种体,对变革的机制尤其感兴趣,他认为:革命的起因总是某种对平等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本人既关心,又关心伦理,他提出了一个人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好公民能同时做一个好人吗?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会要求他的臣民采取错误的行动。[7]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会涉及到判断和法治理想的理论基础——人性论基础。从假设人类本性是固定不变的前提出发,亚里士多德推论出它的法治观的逻辑理由:良好的统治应当免除任意和不确定,但人的本性使任何人皆不能免除任意和不确定。因此,惟独法律的统治即法治可以免除人性的任意和不确定。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的,人类惟有作为共同体(国家)的成员才能追求“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只有在国家之中,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才能发展他的能力,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也同意柏拉图的下述观点,即如果国家中存在着品行和才能两方面都极为杰出的人物,那么这位优秀的人物就应当成为永久的统治者;但是,他又坚持认为,就是这种“如神”的人也必须是立法者,而且甚至在这样的人所治理的国家中也必须有法律制度。应当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中混入了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最优秀者。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8]这段话揭示了人类统治者的欲望与法律理性之间的对立,说明了法治具有一种人治做不到的公正特点。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后来凝结为哈林顿的名言:“要法治的,不要人治的。”也“构成了美国人对分权理论的解释和整个美国宪法体系的基石”。[9]
以上我们大致可以探知,古希腊人关于秩序的观念承认了法律的重要性。其中,最精华的观点在于断言法治应该阻止机构的退化。在亚历山大帝国的破灭与罗马帝国的巩固之间的三个世纪中,由于混乱而无序,公民们在城邦中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至善)的希望破灭了。这一期间,人们对国家普遍持有一种悲观、焦虑或冷漠的看法。斯多噶学派批评了古希腊城邦的狭隘地方主义,并坚持提出一种有关人类之城的思想,神和人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民,它还有一部宪法,即正当的理性,它教导人们必须做什么和回避什么。他们还认为在这个城市里所有个人都具有同等价值,并且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参与共同的伟大事业。这是一种由自然法和普遍理性推导出的世界主义观念和建立世界国家的想法。伊壁鸠鲁则进一步主张国家和法律不是什么神意的体现,也不是为了绝对正义而设立,它只是社会上一个个自私的个人为了防止彼此损害而达成的行之有效的妥协的产物,是作为有利于人们之间交往的一种契约而产生,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安全。这样,从亚里士多德到伊壁鸠鲁,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发生了翻转,亚里士多德强调国家大于、先于、重于个人,伊壁鸠鲁则认为国家的一切必须落实到个人的幸福上才有意义和价值。
(二)
罗马人把国家和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权力与义务。国家是社会性存在的一种必须和自然的框架,但个人才是罗马法律思想的中心。罗马人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并不必然是的动物。由此,罗马人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找到了一种在希腊城邦中不存在的空间,属于个人的空间。与此相应,对于个利的保护被视为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目标。国家也因此被视为一个法人,它在明确的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力。由于国家被视为区别于公民的一种集体的存在——这是古希腊思想中所缺乏的——因此,人们把它视为一种法律上的实体,它具有特定的功能并且其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公民同样也是一个法人,他拥有受到法律保护的而不受别人以及自身非法侵害的权利。
罗马的公法不发达,这是因为罗马是从王治走向共和国(执政官)再走向帝国。在王权发达的罗马,对公权的制约这个论调,思想家们没有力量质疑。而事实上,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甚至说,“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在这样一个大的帝国,让罗马去发展限制王权的公法理论以及宪法理论是不现实的。但是,罗马人提出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对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以及明确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罗马法学家在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最早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问题。乌尔比安说:“公法是与国家组织有关的法津”,“私法是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法律”。因此,凡保护国家利益的规范都属于“公法”,包括有关国家地位和利益,以及神职工作的法律规则、如宪法、刑法等。凡保护私人利益的规范都属于“私法”,如民法、商法等等。自古罗马法以来,公、私法的划分一直是法学中对法的基本分类。这种划分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为依据的,从而公法是国家的法,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由于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发源地,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公法一般是为市民社会服务的,公法绝对不能任意进入私法领域,干扰市民社会的生活。这反映出西方法律思想中重视保护,警惕国家权力的传统。近代早期西方法治思想不只是建立在关于个利的抽象原则之上,而且有着重要的法律文化根基,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对于私利、利益的系统规定正是这种根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原理上讲,罗马法律与希腊城邦法律的基础不同。古希腊始终是一个城邦社会,古希腊没有军事扩张,通过城邦的建设发展创造古典文明。后来希腊被罗马灭亡了,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斯多噶主义”等世俗化观点。从公元前6世纪末君主制解体到500年后渥太维成为奥古斯都大帝为止,罗马一直是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罗马人的确是创下了宏伟功业。他们创立了一直到现在仍为很多国家沿用的民法与刑法的基本框架。古希腊人认为法律的最后依据来自宗教、道德,柏拉图认为是理性,理性与道德有一致性。而罗马人则认为法律是享有特殊职位的个人所作出的、发布的符合习惯程序的命令。由此,我们可以引申为二者守法的理由是不同的,罗马人认为自己守法是因为它是共同体的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体现的意志,而不是因为这个法律符合正义或者体现了某种宗教与道德原则。古希腊和古罗马都经历过王治时代,人们对法律有原始的遵奉,这个法律是个习惯法。接下来在罗马出现了《十二铜表法》。罗马征服世界,不是通过信仰“神”来征服,而是靠它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过程中,罗马法得到完善,由《十二铜表法》又产生了“万民法”、“市民法”等等。
从王治到帝王,说明罗马并不是哲学王统治,它的智慧来自于。这告诉我们人人奉公守法所带来社会的和谐之外,还有另一种和谐:通过自由讨论解决冲突,自愿接受靠法律程序得出的任何解决办法。在罗马,人人参政,国家是的利益,是的存在。这给我们后人一个正确的指引,即在遇到危机时可以通过订立章程、协商,大家共同遵守规则治理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因此,古罗马人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古希腊的政体,而采用后来欧洲人十分着迷的共和政体。罗马的共和国体制从本质上讲也是的,平民总数能获得一定的参政机会。当统治国家的不再是凌驾于贵族和平民之上的国王,而是行政长官时,罗马人通过协商决定增设平民自己的官员,称作护民官。为了避免,罗马人审慎地将权力予以划分,使它们分属不同的部门并互相制衡。罗马官员从执政官开始一年一度由大会选举产生。立法同样如此。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人将置于的控制之下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人对权力,特别是对权力的限制是比较技术化的、内部关系复杂的、需要精巧设计的一种限制,也说明这是罗马人发达的法治智慧的体现。
罗马人是一个务实的民族,罗马的文化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罗马人重视法治,并形成一种法的理性精神,其成果就是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设施的健全和理性化。罗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法典化,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体现,它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法治理念: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罗马人对私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想,特别是从所有权(财产权)的概念引申出一种新的法律认识(权利等同于正当理由),为权利思想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手段。[10]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表现为重视法学家的作用。罗马的制度比希腊的更为健全,表现为国家机构的设置化和法制更为健全。法律表面看来是冰冷的,但所蕴含的却是人的理性追求,体现的是对和人道的尊重,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法律保护的重心是私人的权利,而不是公权利,法律就是确定权利和保护权利。由此可以看出,罗马人没有耽于理想,而是重视操作,他们是以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走近法治的。
(三)
随着教的出现,古代希腊有关秩序和的概念受到了挑战。圣·奥古斯丁就曾怀疑人类是否有能力把握宇宙更广阔的秩序。在他看来,理性的人不可能具有自我决定的道德,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从外部消除人类堕落的条件,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人(类)是堕落的,所以需要法律的秩序和约束。国家存在首先是因为人有原罪,因此,国家不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安排而是减轻原罪所必需的安排。奥古斯丁这种几乎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典,而否定人类有自我拯救能力的学说,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受到了后来中世纪教思想家们的修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人物。[11]阿奎那从承认国家是人实现其最高目的的共同体出发,把国家的这一目的看作是美德,把看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不像奥古斯丁那样把看作是医治和减轻人类原罪的手段。阿奎那还从国家是形式最完整的人类共同体推出:国家的存在,是出于上帝的意志。这个结论对缺少而不是法律的13世纪而言,的确给了国家相当需要的抬举。作为,阿奎那一方面不想离开从教父一直传到十三世纪的那一大套与社会传统,自然强调了人类的超自然的结局,即人类灵魂的得救。另一方面,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当作对基础稳固的信仰和哲学上的支持,认为秩序起源于人的群体的自然本性,国家和法律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世俗幸福,国家能够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使人变得善良并尽可能在世俗范围内过好的生活。至此,国家()再次被视为促进善的一种手段,而不只是阻止罪恶和伤害。
中世纪扫荡了古代文明,却保留了教,教成为中世纪文明的代表。教会的兴起,为有效的法治确立了基础,从而也厘定了西方文明的面貌。教文化在其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确给法律注入各种精神,并成功地使法律制度适应于人类的需要。不少法律都由习惯发展而来,而很多习惯是依靠宗教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如承诺、契约及条约,常常借助于宗教。可以说教文化最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法治,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权利法案》,还是法国的《宣言》,还是美国的《宣言》,都声明人的权利来源于上帝所赐。由此可见,只要法治原则来源于重点确保人类尊严的基本,教传统立即就会发扬光大。人类尊严建立的基础是,人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就给任何统治者的野心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限制。[12]如果没有教的背景,人类尊严这一思想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如果统治者亵渎神的意旨,违背人间的法律,人们又如何能约束他们呢?一种观点认为,古代世界,宗教与职能自然结合在同一组织里,个人与国家间不存在的仲裁,无法用法律约束行为。事实上,要控制统治者必须依靠组织化的力量。这种组织化的力量在中世纪有两种来源。其中之一是教会。另一个是能与国王抗衡的贵族。由于教文化坚持“恺撒的当归给恺撒,神的当归给神”,这种教会——国家的二元观念有助于强化了中世纪的法治观念。一方面,教会与国家以不同的权威形式同时存在,国家有权处理世俗事物。[13]同时,教会(组织)成为既有秩序的一部分并有权处理属灵事物。每一方都生成有权确定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的权力。另一方面,教俗两种权力只有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即承认法律高于它们两者,才能够和平共处。从前,可以不论法律义务,现在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良心(教会)要将所有人类行为——包括行为与私人行为——都置于法律规范之下,这也说明欧洲中世纪并没有彻底割断罗马法所捍卫的尊重个利的传统,人们从法律下的自由这一传统汲取资源和营养,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对专制君权的警惕和制约。
除教会外,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贵族和王权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史的主要内容,贵族们只要联合进来就能使国王让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215年英格兰男爵们成功地迫使当时的英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14]许多人认为,《大宪章》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文件,这一伟大的文件体现了本身——当时是君主制——受法律约束的原则。法治的一个基石就是法律也统治本身。在中世纪,伴随着多头现实的是一种包括各团体间的条约、封建契约、教会法、庄园法、城市法和广布各地沿袭久远的习惯法在内的极度多元化的法律体制。不同的团体间的纷争除了借助于裸的武力外,还经常从自然法和法律理论那里寻求合法性与权威合法性的依据,并在当时封建制不是很强大的国家开始取得一些持续的成就。例如在13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开始形成,14世纪,议会在形式上定型为两院制并逐步有了它最初的两项职能,财政审批权和公共。在此基础上议会又积极争取,逐渐地发展出法案的创制权、公共政策的讨论权以及监督等其他职能。[15]
尽管中世纪社会中没有足以与古代亚里士多德法治定义分庭抗礼的、完整的法治观念,尽管中世纪的世界也存在着强烈反对以律法来约束行为的观点,但是,中世纪同样流行着统治者必须在法律之下统治的信念。可以说,统治者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人人(包括君主在内)都应遵守法律,特别是那些体现了神意和自然法要求的法律,的确是中世纪人们的共识。例如,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其他很多人为贵族制定书面行为的法规督促统治者行为节制及遵守道德和法律准则。这些法律准则通过程序上的仪式及其按照法律条款判定的原理,包含了在任何政体下实现良好秩序的基本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讲,中世纪西方法治观念主要表现为论证限制权力的合理性。阿奎那提出了对统治者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主张统治权要受到道义责任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权力应当受到限制,只能依照法律来行使权力。在阿奎那等人看来,既然人类社会天然的不平等,人就有服从的义务;既然国家的目的是满足的利益,故君主必须为的利益服务。于是,统治权对整个社会来说便成为一种职守或责任。
中世纪后期,随着对人类本性和进步的信心增长,对的怀疑也日益增长。许多人认为是必要的“恶”,应当有控制地得到保留,以免它超出规定的功能。马西利则进一步试图限定和缩小教会在世俗社会的权力,扩大世俗统治者即国家和法的权威性,并且认为应当制定法律,国家和法的权力来源于的意志。文艺复兴时期,试图用理性代替宗教最终导致了法律和道德的严格区分。文艺复兴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法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即关于法律与正义、法律与理性、法律与权利等之间关系的思想,以及社会应当建立法律统治的思想等等告诉人们,让人们恢复或重建对法的信任。在马西利之后,马基雅维里致力于宗教、道德与的分离,使与法摆脱神学的超自然的支配,寻求建构、控制新的社会秩序的与法律机制,并且日益明确地确立国家与法制的强制性,从而开创了完全把与法世俗化的倾向,成为近现代学、法学思想的里程碑。
至此,我们探讨了古希腊、罗马特别是中世纪以来西方和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关于自由平等和自然法的权利原则,各种接近个人主义的思想萌芽,都从若干角度表明了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专横暴虐,关注公民的正当权利,法律下的自由等,为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世纪的法学思想虽然各有特征,也未能从根本上超越宗教神学,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始终承认上帝所在天国的神圣秩序的绝对权威和不可超越性。但是,却在不同程度上把法与现实社会,与人的社会联结起来,赋予法以世俗的基础。
接下来,笔者将从讨论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和布丹的理论入手,以现代国家和的观念史为视角,重点讨论17、18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法治”(立宪理性)兴起的理念基础:即要引导并控制绝对君主制下至少在理论上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同时又要组成代表来面对国家权力。这个问题在传统上通常是以这种形式提出的,是法律“优先于”国家,还是国家“优先于”法律,也就是说,国家是否按照法律来规定它的命令强制力的范围和界限,或者相反,法律的效力是否由国家意志确定或决定的。[16]
(四)
在传统的国家观念里,不存在个人的财产权利、生命权利和良知权利,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国家行动的自由的问题。不过,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在《学》中就已论述过国家如何存在,而不必涉及好坏的命题。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正义(法律),并在整个城邦中提倡美德,因为道德最终是和平和良好秩序的基石。马基雅维里的意大利先驱马西略在二百年前也提出过世俗不必服从教会的主张。然而,马基雅维里的世俗主义倾向远远超出了他的任何一个前辈。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最激进的观点是,统治者不必按照臣民的道德标准办事或信奉臣民的宗教。统治者置身于社会集团之外,那就应凌驾于社会集团的道德标准之上。这实际上是主张对统治者和臣民使用双重的道德标准。因此,他把国家的统治术的道德要求大大地淡化了。而在此之前的法律思想家都把国家权力当作是实现正义、幸福生活、自由或是上帝等高层次的目标的手段,但马基雅维里则强调国家权力本身就是目的,并集中探讨适合于夺取、维持和扩张权力的最佳手段。[17]因此,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使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18]
现代人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寻求中的秩序和团结,但是不像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那样主张以某种外部的或超常的原则来达到目的。马基雅维里认为的成功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张君主为实现个人愿望可以欺瞒天下。在这里,马基雅维里把和道德作了分离。认为搞不能讲道德,本身是不道德的,是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的需要与利用是至高无上的。又由于马基雅维里把国家追逐权力描绘成目的本身,这样,领域就被赋予了的地位,道德和宗教标准已无足轻重,效率是惟一被考虑的标准。马基雅维里假定人类本质是恶的,而冲突就是源自人的本性的一种普遍和永恒的社会现象,并不依文化和环境的差异而不同。对马基雅维里来说,的最高目的是共同体的安全与健康,而不是古代作品中所描绘的道德目的,行为的社会和后果比决策者的道德动机更重要。因此,国家是遏制和引导人们自私本性向有利于社会的目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通过国家,人获得安全。[19]以上表明,从马基雅维里开始,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在马基雅维里生活的时代,意大利实际存在5000个国家,身处邦国林立,政乱方殷,天下板荡之际的马基雅维里,力主用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结束内部纷争。他认为国家的安危高于公正、人道或残忍、光荣或耻辱等等考虑。于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鼓吹建立一种绝对君主制,他认为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惟一出路。马基雅维里的策略后来被费南多·波提若总结为“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20]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将国家存续提升为绝对的规范,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特定的功能与目的,因而在特定和情境中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制约。换言之,马基雅维里公然把国家及其利益和有效治理提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即它们是惟一的价值。国家的存在和安全是最高要求,其他考虑均属次要。
在马基雅维里以前的中世纪时期,由教确立的道德戒律,不仅适合于个人,也同样适合于国家。现在,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说却揭示出国家的存续与个人伦理信念的冲突。在他看来,“不当凯撒,便为布衣”。原本就是介于人性与之间的事务,因此,为了将意大利建成统一强大的国家,君主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任何手段。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个“国家理性”,将世界与伦理世界打断成两截,成为17世纪以后绝对王权统治的依据。德国史学家梅涅克(meinecke)在论述马基雅维里思想专著《近代史中的国家理性观念》中认为,假如出自国家理性的行动,可以无视个利,不必顾及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的话,那么生活的道德基础就会被破坏无遗,所以他说,马基雅维里给西方学“留下一道难以愈合有伤口”。[21]
美国学者卡尔·j·弗里德里克是国际间知名的研究大师,他著有《立宪国家的理性》(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一书,出版于1957年。他作为一个目睹了极权统治等当代大灾难的思想家,也深刻地看到了“国家理性”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公共的集合体,它有不同的单个的成员,有自身的功能、结构和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共同体中成员或国家的公民,他们难道没有自己的目标、追求和权利吗?如果国家权力统辖着所有的个人意愿,强权就是公理,个人岂不成了裸的工具?如此敌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家理性,其正当性显然值得怀疑。在弗里德里克看来,国家理性的根据有赖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如此看来,个人或普通人的权利对于国家理性来说,就不再是无足轻重了。[22]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把国家的安全和存续视为国家正当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马基雅维里的国家学说中。但是,问题在于单纯的与存续是否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的正当理由呢?显然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理性所能解决的,为此,弗里德里克认为,马基雅维里的问题不是单单依赖“国家理性”自身所能了断的,必须导入“立宪”这一核心内容。[23]立宪主义的国家理性有别于古代的道德,关键在于不从纯粹的道德层面,而从立宪的和法律层面去思考问题。所谓“国家理性”,只有当其建立是基于的基础之上时,才有正当性。换言之,权力的理性终究需要转化为理性的权力。在列奥·斯特劳斯看来,《君主论》还引发了一场由规范问题转换为治理的技术问题的“马基雅维里革命”。 [24]
马基雅维里看到了法治对于国家生存的重要性,认为完善的法律是产生公民爱国美德的源泉。即使在一个王国,保持稳定首先条件也在于法治。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等关于罗马历史研究的一些著作中,看到了一些罗马皇帝、暴君和其他君主的反复无常,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为了防止非法的,必须使用法律手段,以制裁官员滥用权力。马基雅维里还明确阐述了权力“制约与均衡”的思想,认为君主、贵族和平民应在宪法中各占一份,这样彼此就可以相互制约。而国家自己则不受任何限制和任何的伤害。他举例说:斯巴达宪法体现了最完全的均衡,梭伦的宪法过分,结果造成了僭主统治。罗马共和国则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元老院与平民之间存在牵制关系。[25]马基雅维里还认为:运作的合法性取决于与上帝之律法,自然法或任何诸如此类的超越标准的契合。
总之,马基雅维里的核心观念则是国家权力不受任何道德原则的约束,即(君主)如何掌握国家权力而不问是非。法律不能超越于国家之上,而居于国家之下,国家有权要求任何事物为它作出牺牲,而国家自己则不受任何限制和任何的伤害。马基雅维里偏好的形式是统治者服从于法律的共和制,但对他来说并非是压倒一切的要求,而国家利益可以提出违反法律正当的要求,因此,马基雅维里并不虔诚地珍视法律。就当今时代而言,检验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实际价值就是看现实世界是否支持他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马基雅维里提出的问题仍是今天的中心问题:道德与权力,共和主义,战争与外交等。
(五)
自马基雅维里开始,民族国家问题成了近代法律思想的核心。如上所述,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对国家的考察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但对国家和国家概念的系统阐述,却只能出现在实际发展了恰当的司法、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国家。事实上,现代国家的论是以民族国家出现和集权的君主制度诞生为前提的。在法兰西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法国人布丹,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观念。布丹的传世之作《国家论六书》就是在法国宗教战争中产生的。当时,法国君主成功地完成了统一,建立起有效的集权统治。布丹顺应这种潮流讲。为法国超越于一切世俗与宗教限制的权力提供理论上的论证。布丹将概念发展为制定普遍法律不可分割的权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权力,那么严格地说,就不能认为它是国家。
布丹是第一个用定义国家的重要人物。虽然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有人系统而确切地表达了观念的大部分要素,但在整个中世纪,权力的复杂分散湮没了这些表述。直到近代开端之际的权力集中,才出现复兴这些概念并使其精致化的环境。[26]布丹认为是国家拥有不受限制的立法能力。这种立法能力()既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又是非授权的、永久的,不可抛弃的无上的权力,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对臣民的权力。布丹还认为,者,即不受制自己或前任创制的法律的约束,也不受制被统治者的法律实践的约束,即使这些法律与习俗有健全的理性依据,总归还要由者的自由意志来左右。除上帝外,尘世上没有比处于地位的人主更伟大和更受人尊重了。各位的人主是上帝所设立的助理以发号施令于众人。在布丹看来,教会和帝国本身都不能威胁,他否认教会有权干涉正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宗教和世俗事务。
关于的内容,布丹分为8类:立法权,宣布战争、缔结条约权,官吏任命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有关忠诚、服从的权力,铸造货币和度量衡的决定权,课税权。这些权力都是者处于国家元首地位的具体决定权,实际上也表明者可控制习惯法。立法可以改变习惯,但不能像中世纪那样由习惯来决定或改变法律。这样,布丹的理论就有两个方面。从内部观察:一切权力都是的派生物,它不能等于更不能超越;从同等其他国家方面观察:也是不受拘束的权力。当时,甚至在今天,绝对不受限制的是否也要受到某种限制呢?布丹对此也是矛盾的。他曾说要受到上帝的限制,要受神法和自然法的限制,人主没有破坏神法和自然法的权力,至少包括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在这方面,布丹的思想仍属于中世纪。但布丹又说是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这就产生了矛盾。是受限制的还是不受限制的,这是不相容的两个主题。直到后来霍布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君主的权力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绝对君主主义。
布丹一方面承认国家与上帝的联系和根据自然法的相互责任,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于国家不存在审判官。布丹认为,国家必须是最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它的上面。这个国家理论是近代国家理论的标志之一。霍布斯以该观念为出发点,对绝对权力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他将国家描述为许多功利主义的权力集合,为了维护和平以及克服自然状态,国家必须是法律的,也是道德的最高渊源。霍布斯的论证方法是通过“社会契约”确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者或者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认为绝对王权是社会稳定和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是人们的惟一出路。在这里,霍布斯运用他的国家契约论来增强绝对学说。在自然状态中,强制性的权力只是依赖于个人能力的,而社会契约则确立了一种组织化和系统的强制性权力。
布丹把解释成制定法律的权力,而霍布斯则把它当作通过法律并与法律相一致,或没有法律、置法律于不顾地进行强制的权力。布丹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霍布斯则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对荣誉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恐惧在驱赶着他们,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的认可。事实上,只有推戴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的代表之后,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卢梭则认为重要的是公民和臣民的同一。对卢梭来说,他不同意将立法权委托给他人,因为是统治者(统治者和臣民是同一的),因而必须行使那种统治权力为自己立法。卢梭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生活没有保障,因而每个成员通过契约组织起来,把自己的权利交给整个社团,构成公共意志。社会契约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集合体,它包括了所有参加表决的个体成员。这个统一的机构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这就是共和国。从被动意义上,它可以叫国家;从主动意义上,它则叫。它的成员,从集体的角度就是;从分享的角度(如制定法律),就是公民;从遵守国家法律的角度,则是国民(臣民)。
于是概念就有两种用法,一是将置于之上,一是将置于中间。这两种概念的不同运用甚至会产生冲突。欧洲30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成了构成近代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对内来说,是最高的、独有的、管辖的权力,对外来说,者于其他者,这样欧洲便形成了国家分立、互相抗衡的国际秩序。这也是近代国际法的起点。以上说明,思想在16-17世纪的崛起,迎合了某些社会需要——社会内部秩序的需要和国际秩序的需要。如果说,合法性关注的是特定统治的权利的话,则关注特定国家存在的权利。18-19世纪变成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19世纪奥斯丁强调的至上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是“绝对”时代,主义国家甚至将集权推到极至,不仅不能容忍对手的存在,而且不能尊重任何限制。现代国家和学说的中心在于断言:国家不承认有任何更高的统治者。除少数人外,几乎所有的阶级的政党都把国家作为一项宗教信条而接受下来。民族国家非常珍视它们的,也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二战期间和之后,国际秩序不单包涵原有的原则,而且还加上了原则和自决原则,在这个体系里,和、和平逐渐出现了一个新格局。
观念的潜在目的同样为权威主义的德国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所颠覆,他提出了观念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只要关于在谁存在争执,实际上就可能存在至少两个潜在的最高统治者。然而,施密特将界定为决定什么时候这一关键形势出现的权力。根据这一解释,最高统治者就是任何能取消所有法律和宪法,宣布紧急状态,并规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人。换句话说,被有力地重新界定为宣布复归自然状态的权利。[27]事实上,种种观念都使以下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变得更突出了:人们普遍认为,大家守法才有自由可言,但法律必须由人来制订。那么,法律制订者处在什么地位?如果他在法律之下,他就无法制订法律;如果他在法律之上,那么他属下的臣民就无法保护自己的自由权不受侵害。霍布斯当然同意现代国家的臣民应当用法律来治理,而不是听由专制者随意摆布,但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统治者应当握有处理紧急情况的决定权。在这个理论层次上,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换句话说,将足够的权力交给一个最高权威总带有冒险的成分。从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争辩说,不这么做的危险性更大,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一个臣民就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其他臣民的伤害。霍布斯等人认为治理国家可以依据理性的人们之间的道德协议,也就是一套道德规则,叫做自然法,后来又叫做自然权利。这或许能解决中隐含的危险性。与霍布斯同时代而比他年轻的约翰·洛克在《论》(1689)中含蓄地批评了霍布斯。洛克嘲讽说,将决定臣民权利的绝对权力交付给一个人,这想法就等于“认为人愚蠢到这样的地步,他极力防范野貂或狐狸来捣乱,却甘愿被狮子吞噬,甚至认为后者更无害。”在实践中和分权的方式能够改造,使它不能滥用国家权力。自然法、人的权利、公民承诺、民族主义、共同意志等概念都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缓解矛盾的思路。然而即使在治理得最良好的国家里,我们都必须承认权力是一种必要但又危险的东西。任何预防措施都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这一问题在今天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现代科技在不断增强统治者的实际权力。的发明使贵族领主们的堡垒形同虚设,而书刊审查和对出版的控制使统治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臣民们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国家已经把关于的整个观念颠倒了过来,这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变化而引起的。古典时期的人们从为国家服务中得到人性的最大满足。现代人作为个体最关心的是灵魂得救。他们往往认为国家的作用是保障和平,使他们能够推行自己的计划。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的国家是软弱和的,但实际上现代国家相当强硬、持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权利哲学》(1821)中说国家是“上帝在地球上进军”。预言式地表述出继他之后的许多欧洲人的看法:国家与宇宙命运之间有某种联系。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证实了这个看法。从日渐衰落的中世纪王国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是人类能力所能创造出来的最接近上帝般无限威力的产物。有两种对立的国家观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对国家的自由派观点,来自中世纪的自由和王权的观念,主张建立良好的公民秩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种工具,高高在上地从精神上压抑着受它奴役的臣民,所以国家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需要用人性来改造。第二种观点激发了这样一种设想:超越国家,创造一个完美的共和体,使中不可避免的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能够最终被填平。概括地说,现代和法治始终在这两种观点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28]
(六)结束语
近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后,其结构、本质及其意义是什么?换言之,国家的安全和存续这一现实性问题的正当性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近代社会一开始就摆在法律思想家面前的重要问题。从思想传统来说,现代国家和观念的出现与国家权力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权力逐渐了地方和社团的自治体,或者将它们限制在权力的范围内。马基雅维里就是这种国家权力的杰出鼓吹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国家权力的任务是尽可能长地避免走向威胁所有国家的衰败。在这一点上,君主不必尊重一般的道德。[29]马基雅维里首先提出“国家理性”学说,他把国家的安全与存续问题提到惟一价值的高度来讨论,认为国家理性存在于国家自身,特别是当和存续危在旦夕时,国家总体要求对于个人来说就变成必然的责任。这样,国家的理性根据就变成了作为整体的国家单方面的需求,个人在这个理性中没有了地位,失去了存在的根基。[30]
最早用理论来定义国家的是法国人布丹,他被视为现代国家和观念的始作俑者。在1576年出版的“国家论六书”中,布丹写道:“是一种公民与属民之上的并高于法律的权力。”这项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每个的国家都具有最高的立法权,它在两个方面无与伦比,那就是,它不承认还有更高的权力,同时它有无可的权威。[31]布丹的这种理论与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学说一样,中心点仍然在于关注特定国家存在的权利,并“反对国家的功能应在有限领域实行的观点,认为活动没有范围限制”。[32]不过,布丹的这个看法前后也不尽相同,他保留了统治者受自然和上帝法律束缚的旧观念。相比之下,16世纪的英国的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更始终如一、更激进。霍布斯试图抹去束缚的最后痕迹。他认为,通过契约任命一位统治者,人类就会一致同意放弃自然状态。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坚持认为不可分割,拒绝对权力行使的传统进行约束,但他们都没有鼓吹。两人都在内战背景下进行写作,都竭力说服自己的同胞,国家是安全惟一的保证。惟有有一位统治者,人们才不会受内战的蹂躏。[33]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尽可能清楚地表明,国家不能够理解为一种关系、或是一部宪法、或者是某一目的;国家是一个人,它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因此,尽管国家来源于个人之间的契约,而且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讲,从而实现“的安全”,但是国家本身并非其中任何一个种类。换言之,国家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任何一个它所服务的目的,安全也好、公正也好,自由也好,都是如此。[34]约翰·洛克使用这个策略来限制议会和行政机关的权威。“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也就是立法权……然而,立法权仅仅是为了某些目的行使的受托权,在中间仍然保留了一个最高权力来免除或改变立法权。”[35]然而,“不论是布丹或是他的后继人,当他们承认立法权仍然受自然法中若干无上原则的节制时,始终未能自圆其说。随着现代国家日趋世俗化的结果,自然法节制国家的作用,逐渐变成形式。”[36] “虽然控制的急迫性在议会制度下不再突出,但人们还是越来越关注议会和的极权主义权力,而且在任何制度下往往都有一定的倾向。因此,更重要的似乎不是控制,而是控制议会和确保议会对约束性法律的服从。这种控制权力载于宪法。宪法禁止对任何基本权利的限制,认可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本质的情况下所作的限制。其次,宪法确保议会中上处于弱势的少数者的权利。”今天英美法系国家确立的司法审查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的设立就是为了控制立法者。
当代主义大师卡尔·j·弗里德里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于国家观念认识,而是从一种国家构成的本质或国家得以存在的正当性角度来理解“国家理性”,主张对“国家理性”要导入“立宪”的因素。立宪的国家理性在古典自然法思想家那里,又表现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诸原则。国家作为一种有机体,它们的存续是由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应得到国家的支持与保障,这样一来,通过国家这种政体形式,个人作为公民在国家的秩序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与存在的基础。因此,的前提或国家理性的性,在古典自然法学看来,主要是系于个人自由生活在多大程序上能够在国家关系中得到合法性的保障,没有个人自由,也就没有国家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国家理性之所在。换言之,“国家的安全与存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虽然十分重要,但并不是绝对的,在此有一个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国家为了安全与存续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如对外战争、社会动员等,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构成了近代国家理性的正当性基础。”[37]
于是,我们又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如何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否则就会失去控制。”[38]近代民族国家及其在过去和当时的实践经验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不实行法治,就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只能任凭掌权者任意摆布。当一个能不经过公众讨论就制定或废止一项法律时;当一个公民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不经审判就可以被投进监狱时;当一位法官只能在行力的恫吓和阴影中进行审判时;当一项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的需要或个人的好恶而随意变化时,专制、极权和就会应运而生。”[39] 正如以“笔为利剑”的当代学者昆廷·斯金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自由是应该珍视的理想,如果法律是削弱自由的主要手段,那么,作为公民,我们就有相当大的理由使我们的自由最大化的名义来控制国家。相应地,自由主义的哲学在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道防卫线时便成为最关键的了,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侵犯这道防卫线。”[40]
法治作为一个概念,预示着某种社会、和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直到20世纪才清楚地显现出来甚至成为一个关键性和课题,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区分,全人类平等的思想与人类平等相关的法律普遍性的基本原理,以及机构应该在所有涉及世界观和宗教的问题中保持中立的思想。法治不是用来强制实施道德规则的,相反,如果法治要完善,就必须对任何世界观至少保持中立。作为构建秩序的法律规则,法治赞成包容性。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这种国家职能受到法律限制具有非凡意义。当国家职能超越界限时,国家(权力)就会使自身神圣化。因此,和法治的钟摆就不能只是在某种秩序和法律秩序形式上的维护和保证之间的摆动,而是指向那些对绝对的行力进行限制的法律秩序。
--------------------------------------------------------------------------------------------------------------
注释:
参考文献
[1] 格哈德·鲁别尔兹:“法治及其道德基础”,载约瑟夫·夏辛等编著:《法治》,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2页。
[2] [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201页。
[3] 参见[美]特伦斯·欧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4] 美国学者特伦斯·欧文认为,在公元6世纪的雅典,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要是没有某种对社会法律与规则的信仰,社会与改革就是不可想象的。自觉的制度改革需要对于可以依赖某些变革以产生规范结果的信仰。参见[美]特伦斯·欧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5] 参见[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 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6] 虽然这些思想也许并没有迎合主义者,但迫使那些迷恋生活方式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反省。恰如一位当代作家所指出来的,柏拉图对制度的弱点和忧虑,其答案正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不是存在于我们的唇枪舌剑之中。参见威廉·俄奔斯坦:《伟大的思想家》,第三版,纽约来因哈特和公司1960年版,第2页。
[7] 参见[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 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8]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9] 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页。
[10] 参见[英]r·j·文森特:《与国际关系》,凌迪等译,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11] 从思想贡献上说,阿奎那和他以后的思想者“不再仰赖宗教权威的自治世俗国家的观念,开始穿透中世纪的薄雾。”参见[爱尔兰] 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19页。
[12] 参见格哈德·鲁别尔兹:《法治及其道德基础》,载约瑟夫·夏辛等编:《法治》,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5页。
[13] 莱斯利·里普森就认为:“从方面考虑,十字架与鹰之间的联姻有得有失。国家得到的是教信仰在精神上的影响力参与到对罗马公民忠诚的整合之中,但是国家因此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在接受合作者的同时,也就承认了一个对的堡垒来说是分离的、平等的机制。教会同样既得到好处,也蒙受了不利,它成为既有秩序的一部分,不再是被者的受难人,从此它可以去别人,实际上它也这样做了……”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139页。
[14]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192页。
[15]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193页。
[16] 拉德布鲁赫认为,不论是国家优于法律还是相反,“都同样会遇到难以消除的顾虑。”而国家与法律同一性学说“具有定义——的意义,但绝没有法哲学——的内涵。”因此,“关于法律或者国家优先权问题一方面涉及了法律的规范概念,另一方面涉及了国家的现实概念。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绝对不存在同一性,而是与之相反,存在着尖锐的紧张关系……”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82-187页。
[17] 参见顾肃:《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116页。
[18] 参见[美]肯尼斯·w·汤普逊:《国际思想之父》,谢峰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71页。
[19] 参见[美]肯尼斯·w·汤普逊:《国际思想之父》,谢峰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71-77页。
[20] 参见[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 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21] 马基雅维里关于国家理性的论述其实相当复杂,后世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马基雅维里本人看来,国家是世俗化与中立化的实体,必须以全民族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依归,宗教与神学信条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而对于后世的一些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人来说,不过是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世界,《君主论》则被视为无需道义规范的政客的指南。在马基雅维里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理性”一度沦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别名。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到第三帝国,往往都以此为口实来文饰恣意的专断统治,却给国家民族带来了一连串灾难。国家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国家理由变成了无理由。参见王炎编:《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2页
[22]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4-5页。
[23]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6页。
[24] 现代法治的一个主题就是世俗国家的治理问题。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认为,最伟大的立法者是熟谙如何运用法律以推进国家的伟大目标的人。他较早直面社会间的冲突,认为利益冲突有助于共和制。而使共和政体长治久安的办法,就是通过制订法律,使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均势,以实现“一个完美的共和国”。然而,实现单一的共和制,往往导致过度集权的共和病。这种病症如法国思想家德·拉姆内所批评的,往往“在大脑中枢造成充血,而在四肢供血不足。”马基雅维里写过长长的书,但对如何治理“共和病”,他至死也没有找到答案。王炎编:《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8页。
[25] 参见顾肃:《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121-122页。
[26] 参见[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出版社20xx年版,第281页。
[27] 参见[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出版社20xx年版,第284页。
[28] 参见[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 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1页。
[29] 参见[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出版社20xx年版,第281页。
[30]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3-5页。
[31] [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新星出版社20xx年版,第137页。
[32]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147页。
[33] 参见[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出版社20xx年版,第282页。
[34] 参见戴维·朗西曼:“国家的概念:一种想象的”,载[英]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主编:《国家与公民》,彭利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35页。
[35] 转引自朱利安·富兰克林:《约翰·洛克和理论》(julian h·franklin,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sovereign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94页)参见参见[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弋尔:《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出版社20xx年版,第282页。
[36] [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新星出版社20xx年版,第137页。
[37]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3页。
[38]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199页。
[39]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学的重大问题——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198-199页。
[40] 参见[英]昆廷·斯金纳:“国家和公民的自由”,载[英]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主编:《国家与公民》,彭利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3页。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兼论宪法解释方法的变革_宪xx文 第八篇
摘要: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是宪法解释者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客观地对与解释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协调和权衡的一种宪法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以法律现实主义和法社会学以及利益法学为法理基础,在当今宪法解释中占支配地位,它是客观理性的宪法解释模式、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是保持宪法稳定与促进宪法发展的桥梁。其外在法理基础及内在正当性和本质决定了它是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一些对衡量模式的替代方法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宪法解释 衡量模式 解释者
宪法解释方法是宪法解释学的核心内容,确立一种合理的宪法解释方法对于恰当地适用宪法意义尤为重大,并有助于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保障。我们可以将各种具体的宪法解释操作方法划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模式即定义模式(the definitional mode)和衡量模式(the balancing mode),不同的解释模式可使宪法条款产生不同的含义,并最终影响到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宪法解释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受不同法哲学的影响而为释宪者所采用,并经历了一个后者逐渐代替前者的支配地位的过程。本文拟介绍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在实践中的产生和发展,考察该模式的法理基础,其成为宪法解释重要模式的内在原因并揭示其本质特性,文章最后还对其进行了反向论证。
一、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在实践中的产生和发展
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衡量模式并非一开始就为解释者所一致采用,它是由于以前的宪法解释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宪法解释的实践过程中对原有解释模式进行反思的结果。www.meiword.cOM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是指解释者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客观地对与解释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协调和权衡的一种宪法解释模式。该模式最早是美国联邦最高在1851年的cooley v. board of wardens案① 中被采用的。该案中,库利(cooley)未遵守宾夕法尼亚州1803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凡进入或驶出费城港口的船只必须聘请当地领航员引领船只,并缴纳领航费,违者将被罚款一半的领航费。库利因此被处罚款。在州败诉后,库利上诉到联邦最高,认为宾州法律违反了宪法关于州际贸易的相关规定。该案涉及宪法对国会调整贸易的授权,是否意味着剥夺了各州对领航员的调整权?经过审理,由柯蒂斯官(j. curtis)主笔的意见认为,“调整贸易的权力包含着广阔的领域,而且调整对象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些要求在全国各个港口平等地适用统一的规定,有些,正如本案的情形,则需要多样化才能满足航运的地方需要。国会对此是否具有排他性的立法权,对这一问题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回答,都将误解该权力的性质而作出片面的回答。” “除非国会认为有必要进行统一调整,否则该项权力留给各州行使,各州根据境内港口的地方特殊性,适当地作出裁量性的规定。”“本院多数意见认为,授予国会调整贸易的权力,并不排除各州对领航员的调整权。”
以前,国会和州的调控权被视为截然两立、不可交叉的单元,该案中解释者对贸易条款的理解采取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实行更为实际的方法,根据事物的性质,权衡全国单一性与地方特殊性的需要,考虑决定政策的取向。该案的判决在当时可说是“惊世骇俗。”[1](p156) 因为法律与概念法学在整个前现代时期在法学中占主导地位,受其影响,当时在宪法解释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定义模式。宪法解释的定义模式就是对宪法中的词语下定义——阐明宪法条文中词语的内容和含义——的宪法解释模式。在定义模式下,宪法的词语被当作指称各类不同的现象,解释者的作用类似于词典编撰者的作用,他们决定词语的含义并为词语下定义。① 宪法解释的定义模式具有久远的历史。早在1824年,首席官马歇尔发表的意见就把宪法解释定义为词典编撰,像宪法中所使用的那样来“‘定义’贸易一词的含义十分必要。”[2]
然而,宪法解释的定义模式的相关问题是:解释者从哪里获得他们对宪法词语的定义?解释者宣布的定义来源于何处?实践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定义来源于解释者自己,也就是说,解释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对宪法词语下定义的。有时,他们可能求助于制宪者的意图作为定义的来源,或求助于历史、社会习俗,甚至知名学者的著述。当解释者声称依靠上述来源定义宪法词语时,通常他们有意无意所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正如约翰·哈特·伊利(johan hart ely)教授所说,当他们试图确保宪法的含义来源于外部“客观”事实时,通常他们“发现”的是自己的价值观。 [3](p43)
有鉴于定义模式的缺陷,该案中的解释者不再采取僵硬的形式化的模式去对宪法词语下定义,而是具体衡量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价值冲突,使其能在力求防止各州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的同时,兼顾各州自行处理地方事务的需要。该案的判决被称为“库利原则”(cooley doctrine),它“为注重联邦与各州利益衡量的现代理论树立了里程碑。” [4](p158) 通过权衡州在规定某一特定行为上的利益和国家统一规定该行为上的利益,标志着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的开始。但在当时概念法学主导下,受法律的影响,定义模式取得了压倒性地位,因此该案的判决很快被人遗忘。尽管如此,该案奠定了衡量模式的基础,其确立的“库利原则”在20世纪后被多次引用,因此该案在衡量模式的宪法解释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进入20世纪后,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1943年罗斯科.庞德提出宪法解释的任务之一就是“权衡和衡量部分吻合或业已冲突的各种利益,并合理地协调或调节之。”[5](p190) steven shiffrin教授指出,“衡量是宪法解释的必要程序”。[6](p1212、1249) 另一位学者认为,“总是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在其判决中决定立法对不利者造成的损害是否与其要达到的公共目的不成比例”。[7] (p700、706) 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在许多宪法案件中采用了衡量模式。如在1939年的schneider v. state案[8]中,最高发现禁止散发传单的法令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认为,尽管州“为了公共安全、健康、福利”可以实行管制,它也不能为此而侵犯言论自由, 在执行权衡情况和评价用于支持法令的实质性理由的棘手任务时,他们拒绝了州提出的通过禁止乱扔垃圾保持街道清洁的利益证明法令正当的理由。认为保持街道清洁对限制言论自由来说“不足以证明其正当性”。这种观点表达了一种衡量的实质性思维模式,即认为言论自由与街道清洁相比较,前者更为重要,因此认为法令违宪。
在德国,联邦院于1958年的药剂师案中应用“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方法,宪法中“职业”的含义,并权衡了自由选择职业的利益与重大的团体利益,认为后者应当大于前者,判决巴伐利亚州的药剂师法案违宪。在联合抵制电影案中提出了“利益均衡理论”,认为申诉人的言论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范围,其利益高于电影公司的经济利益,应受宪法保障。[9](p351-355、413-420) 到20世纪中期,衡量模式已经成为宪法解释的主要模式。其实,衡量不仅是宪法解释领域的主要模式,也成为一般法律领域或制定法解释领域的主要模式。[10](p603-611) 用t. alexander aleinikoff教授的话来说,我们生活于一个“衡量的时代”。[11](p943-944)
二、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的法理基础
在20世纪,法律受到猛烈和持续的抨击。法律实践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定义模式的思维方式是无效的,因此需要发展出更加功能化的衡量模式替代的定义模式。在宪法解释领域,衡量模式的出现是对定义模式存在的根本缺陷的回应,是法律和概念法学走向崩溃趋势的反映;它建立在法律现实主义和法社会学以及利益法学基础之上,是对现实世界知识与社会变迁的回应。 20世纪的现实主义哲学家认为,形式化的定义是抽象的,没有固定的真理,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真理来自于现实中的影响。[12](p39) 现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不确定的,只有与其发生的场合相联系才有意义,因此宪法中的词语的概念是人类建构的结果,没有先验性固有的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赖于语境和结果。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律是一种人类判断的创造物。根据这种观点,宪法条文的含义是解释者对其进行解释时创造出来的。毕竟对一个宪法词语的解释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应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需要协调宪法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并考虑相关因素,以完成公共政策和目标,而这就是衡量所需涉足之处。 法社会学家认为,法律乃是经由理性发展起来的经验和经由经验来检测的理性。[13](p296) 他们注重法律的实际社会效果以及使法律具有实效的手段和法律个殊化运用的重要性。把那种认为人有能力使法律稳定且固定不变的观点看作是一个“根本的法律神话”(basic legal myth)和儿童“恋父情节”(father complex)的残余,并予以否弃。认为不考虑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势,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美国最高霍姆斯官曾认为:“宪法条款不是数学公式,其基本含义不在它们的形式之中,它们是有机的、活的制度······它们的意义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刻板的”。[14] 法社会学家认为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事实上始终存在着距离,而法律的适用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因此法律适用者必须经常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加以权衡,必须衡量各种因素,并且随时对其予以增减,尽可能明智地确定何者应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们反对法律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观点,相反他们确信存在着公认的社会标准和客观的价值模式,这使法律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自恰性。 利益法学是法社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兴起于欧洲的一场法理学运动,尤其在德国和法国有着大批追随者。他们认为概念法学所主张的法律是逻辑自恰的观点是虚幻的且与事实不相符合,指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然是不完整的和有缺陷的,而且根据逻辑推理过程也并不总能从现存法律中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该学派认为法律规范为解决利益冲突而制定了原则和原理,我们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即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的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适用法律者应当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标准去确保其间最重要的利益和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衡量。法学家必须做的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即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衡量和协调。 随着法律现实主义和法社会学以及利益法学的发展壮大,它们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律和概念法学渐趋式微,宪法解释的定义模式逐渐为解释者所不重视。这些法哲学理论为处于困惑中的解释者寻求新的宪法解释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一种新的宪法解释模式——衡量模式——遂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
三、衡量模式成为宪法解释重要模式的内在原因
如果说上述诸种法哲学理论为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话,那么这种模式自身所具有正当性则是使其成为宪法解释重要模式的内在原因。“没有一种解释方法是自我证成的,任何一种解释体制都需要一种理由。”[15](p311) 我们认为,衡量模式之所以能在宪法解释的长期实践中为解释者所选择并成为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其内在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衡量模式是客观的宪法解释模式。
宪法解释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操作,解释者必须意识到宪法的目标并将其与当下的社会环境的相调适,寻求对宪法的合理解释——对宪法的条款、相关利益与价值进行权衡和协调。这种权衡与协调以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社会赋予给选择对象的相应价值为根据,将解释者自身的价值观置之度外,它实际上是描述性,正如物理学家没有顾及原子的价值也能测量原子的重量一样,解释者在没有表达自身价值观的情形下对诸因素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判断并由此得出相应结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客观性并不排除偶尔少数解释者主观因素的作用,这种担忧实为多余,因为它实际上是将宪法解释所需借助的解释者的思维活动与解释方法混为一谈了。
(二)衡量模式是理性的宪法解释模式。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不仅为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提供了框架,而且对诸多社会和经济利益加以控制和保护,这是宪法的目标,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宪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宪法解释就需要对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发展作出回应,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加以比较并作出选择,这种选择取决于相关利益的重要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解释者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有偏向性的判断。但衡量模式的这种弹性并非是无原则的随意性。衡量的结果是对现实社会中相关利益的仔细与甄别,它摈弃了绝对论,进行衡量的解释者实际上扮演着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对社会中各种特定的利益进行归纳式的调研,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它是在深刻理解精神基础上,在全面掌握当下客观事实前提下,然后再运用科学的法律推理完成的。
(三)衡量模式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
在采取这种模式时,宪法解释者需要根据宪法的原则和宗旨,首先对其意欲判断的正反两方的诸因素加以列举,然后再对那些最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因素挑选出来加以保护,从而作出符合宪法的精神与目的的判断。这是一个缜密的思维活动过程,不忽略和轻视其中任何因素,而是建立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基础之上,给予各方以充分的重视,在各种因素之间进行分辨与协调,对涉及的利益作“无所偏倚的衡量”,[16](p237) 这个过程这赢得了信任,从而使衡量得以正当化。
(四)衡量模式是保持宪法稳定与促进宪法发展的桥梁。
宪法文本是制宪者各方在保留分歧条件下达成妥协的原则性规定,即“求同存异”的结果,用孙斯坦的话说是“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17](p39) 因此宪法的规定只是多数者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反映和体现。宪法在适用过程中通过衡量模式进行解释,使那些被忽略的少数者利益以及那些多数者所保留的个别利益获得了被重视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起着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保持宪法稳定而又不至宪法僵化,它是在不动摇宪法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不需修改宪法条文,避免了宪法因社会生活的变幻无常而频繁变动,从而保持了宪法稳定。但它又根据情势的变更权衡各种因素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不至于出现与现实相矛盾和冲突的局面,从而避免了宪法的刻板和僵化。二是促进宪法发展而又无违宪之虞,它既可以对代表数额不足的团体的利益和制宪时尚未出现的后来者的利益予以考虑,又可对原为宪法认可但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局部变化的利益予以重新整合,使宪法真正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活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从而促进宪法“与时俱进”。但这种随时代发展所做的调整又是在尊重宪法精神的前提下进行操作的,不与宪法的原则和宗旨相背离,相反正是为了使社会生活实践不违背宪法。
总之,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具有实体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这是它之所以能在宪法解释实践中得到解释者青睐的内在原因。这些原因也是衡量模式的优势,实际上也是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中所应当尊从的原则,是解释者所应当追求的理想和宪法价值准则,这使它优越于定义模式的其他具体解释方法从而最终成为释宪者的当然选择。
四、衡量模式的本质特性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是现实的或功能的模式,它以考虑或协调与解释相关的利益的方式进行操作,“衡量”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意味着要对有关相互竞争的利益进行权衡。这种“权衡”不是从数量上比较,而是将权衡对象的价值从性质上进行比较。① 这种宪法解释模式要对有关的利益的价值进行比较、权衡或从性质上进行衡量,因此,衡量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它离不开价值选择。逻辑、历史、风俗以及其他相关标准都可能单独或合起来对宪法解释构成影响,但它们中哪一种影响力具有支配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需要救济的社会利益之间的重要性及其价值重要程度。[18](p69)
衡量模式有目的性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有着理性的、客观的标准,而非感性的、主观的选择和判断。它既要尊重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又要考虑当下情势中获得普遍认同的社会共识,并认为这是解释者的职责,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衡量模式是一种现实的宪法解释模式,不同于定义模式,它认为宪法解释,像做任何其他法律决定一样,虽有赖于解释者的,承认所有的法律决定必然涉及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但认为这些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作出的,而非随意的或偶然的。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承认宪法文本提供的只是带指导性的原则性规定,其具体内容不是完整无缺的,而是存在着空缺并随时代而变化,需要解释者把握时代脉搏以确定其在各种环境下的内涵。宪法的开放性决定了利益衡量这一基本宪法解释原则要求解释者在考虑宪法文本的同时,考查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利益,从中作出判断取舍,从而使宪法的规范体系富有生命。[19](p265) 卡多佐认为,使决定与正义相互和谐的自由决定的方法在宪法领域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方法,宪法的概括性使之具有一种随时代变化的内容和意义,因此,解释就扩大了,就变得不再仅仅是如何确定那些宣布集体意志的立法者的含义和意图的问题,解释补充了这个宣言、填补了它的空缺。对宪法的解释经常比对一般制定法的解释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宪法宣布一些原则,然后再将这些原则适用于具体条件下,解释者需要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填补这些原则的空白。
五、对衡量模式作为重要宪法解释模式的反向论证
尽管衡量不是宪法解释的唯一模式,但可以说它是宪法解释十分可靠和有效的必要模式。菲力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认为,“宪法判决中应当权衡和衡量那些确实代表了社会公众的价值和利益,”[5](p213) 因为解释者必须对他所拥有的各种因素加以衡量,明智地决定哪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衡量模式是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除了其自身具有的优势外,还可以通过以下对该模式有可能的替代性方法的来加以反向论证。
(一)制宪者意图
一些人认为,宪法的含义可通过探询制宪者或宪法批准者的意图来确定。这种求助于制宪者或批准者的意图来探求宪法含义的做法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宪法的制定者是由观点并非完全一致的许多个人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人,他们对宪法条款的观点是广泛多样、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第二,社会的发展变迁出现了制宪者当初没有表达出来或没有意识到的情形。如他们没有预测到如下事件:电子监视、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因特网等。第三,无论制宪者是否预见到某一特定事件,有些宪法条款可能与制宪者表达的思想是相冲突的,也有些制宪者的行为与其所表达的意图相抵触,对一个成员众多的组织来说,要探求他们关于复杂问题的统一意图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意图要么缺乏文件记载,要么记载残缺、模糊不清,有时甚至是虚假的。第四,制宪者的意图表达的都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实,把在过去情况和信念基础上形成的意图用来解释现在的情况,可能产生与制宪者本人原本想要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第五,要确定宪法的批准者——或在批准会议上的代表——的意图更为困难,这些代表或公民关于宪法含义的观点各不相同,认为能在这些人中发现统一的意图近乎荒谬。
由于制宪者意图的上述局限性和缺陷,因此它不是宪法解释的令人满意的可靠方法,因为在遵循历史的伪装下,解释者有最终操作、修改甚至创造制宪者意图的权力。[20](p204) 当他们宣称或相信他们从事客观的、非个人地探究制宪者意图时,他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① 布伦南(william brennan, jr.)指出,原意主义是“伪装自我谦逊······但事实上是在谦卑的掩饰下的自大。”[21](p14-15) 因此,用制宪者意图来代替衡量模式的宪法解释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二)历史
求助于历史来解释宪法,不能必然避免衡量,仅有的可能是将衡量从现在转移到过去,还将会面临许多与求助于制宪者意图同样甚至更多的问题。历史比原初意图更难以捉摸、无法确定。正如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所说,“‘传统’能被用来支持几乎任何理由,在时空的统一体中,传统所涉及的主题显然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在探寻过去岁月中具体的智识或道德观念时,所有这些都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代替,你几乎可以证明任何你想要证明的东西。或更坦率地说,传统并不能真的提供答案,至少这个答案不足以明确地证明立法机关的相反判断是正确的。”[3](p59-60) 由于历史的不确定性及其广泛复杂性,当宪法解释者企图求助于过去作为发现宪法含义的来源时,他将被证明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如果历史是宪法含义的来源的话,就应该让历史学家而不是法学家去解释宪法了。像制宪者意图一样,历史必然锁定于过去,是向后看的,并且不考虑变化了的情况。遵循历史解释宪法就是将过去的实践冻结在适用于现在的宪法之上。这正是plessy v. ferguson案所发生的事,② 解释者求助于历史习惯和传统来解释宪法,并因此给予种族歧视以宪法保护,[22] 认为只要种族歧视在社会上是一种习惯或传统,无论它多么有害,都表示赞成。这有保持现状的作用,并削弱宪法回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能力。它通过延缓——如果不是完全阻止的话——进步而保存过去,因而是一种保守的方法。
完全依赖于历史预设了这样两个前提:一是历史足够完整以使之有用,二是历史足够真实以使之可靠,然而这两个前提都是令人怀疑的。当然,批评历史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在解释宪法时可以不顾历史或制宪者意图了,解释者可以从历史中吸取重要的教训,但若希望从历史中确定宪法含义的外部来源,期望历史为当代宪法案件提供确定的答案,历史将不能满足这一愿望。不过可以将历史运用于宪法解释的衡量过程,以获得某种有益的帮助,但它永远不能代替衡量。 (三)宪法目的
毫无疑问,解释者在解释宪法时,能够寻找宪法的目的,并且也应该那样做,然而寻找宪法目的并不就是代替衡量,相反,它只是整个衡量过程的一部分。衡量是对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权衡,需要以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为依据,探寻宪法的目标何在。宪法就是要对未来事件进行调控或处理,因此,寻找宪法的目的可以发现宪法对涉案问题规定了什么,从而发现宪法对相互冲突利益中哪一方提供了保护,或更倾向于保护其中哪一方的利益,这既是宪法的目的,同时也是衡量本身需要涉及的过程,因为,衡量本身就是有目的的,它需要通过目的进行衡量,所以,确定宪法目的也不过是衡量的一部分,而不能替代衡量。 (四)先例
虽然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国家坚持的一项原则,也是宪法判决过程中进行宪法解释的原则,但它不能替代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先例实际上也有可能本身就使用了衡量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先例并非是对衡量的替代,而仅仅是把衡量的场合转移到了以前的案例。若先例是以定义模式作出的,如前文所述,定义模式具有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此时以先例替代衡量就是用定义模式的不可靠性和非理性来代替衡量模式的理性和有效性,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它更多的是提供一些原则性的指导,而不是对个案具体结论和操作方法的强制性要求,况且先例并非永恒不变,它也会因情势而更改。因此,先例对衡量的替代只存在先例本身使用衡量模式的时候,这其实并非是替代衡量,只是把衡量转向了另一个时间而已。
六、结语
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在各种价值和利益经常性地相互交流和碰撞的情境里,衡量模式的宪法解释对于维持一个宪法秩序下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衡量时代”,衡量模式是进行宪法解释的根本的重要模式。现代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探究宪法用语的含义,而是注重将那些比较概括的含义适用于具体案件中,然后根据案件所涉及的问题给以确切的内容,这个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种“衡量”过程。[23](p43) 当法律的定义模式在其自身缺陷的重压之下崩溃后,衡量模式获得了为大批学者所追随的各种法哲学的理论支持而成为宪法解释的可靠模式,因为衡量是法律决定和任何考虑周到的人类决定的可靠方法。它虽然不是宪法解释唯一方法,但如果想要对宪法获得真正有效的、理性的解释,衡量模式就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外在法理根基和内在正当性优势及其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一些对衡量模式的可能的替代性方法被证明要么是不可行的替代,要么根本就不是替代。在解决宪法的安定性与宪法的意志性之间的悖论方面,衡量模式的内在优势及其与宪法价值秩序的一致性是其他解释方法所不及的,自然应当成为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这本身也是维护宪法价值秩序的重要方法和必然要求。
--------------------------------------------------------------------------------
① 认为州有权调控州际贸易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具有很强的地方特点,需要各种不同的对待,尽管这些方面具有国家性需要统一对待,国会可以管制州际和国外贸易的各个方面。参见cooley v. board of wardens, 53 u.s. (12 how) 299 (1851).
参考文献:
[1] [美]保罗·布莱斯特等.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m].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① 定义模式的宪法解释者对宪法词语下定义尽管类似于词典编撰,但他们与词典编撰者还是不同的。真正的词典编撰者主要是从他人如何使用那些词来确定词的含义,是向外看以发现词的含义,然而解释者却主要是自己设想宪法词语的含义,他们是向内看以创造词的含义;另外,词典编撰者的活动虽然也涉及一定程度的创造活动,但其作用更像编辑而不像作者,而解释者对宪法的解释在更大的程度上进行创造活动,甚至是原创性的活动,比词典编撰者更像作者。 [2] gibbons v. ogden, 22 u.s. (9 weat.) 1 (1824).
[3] [美]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m].与不信任.朱中一等译.:法律出版社,20xx.
[4] 张千帆著.西方体系(上册·美国宪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5] [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m].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 steven shiffri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economic regulation: away from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first amendment, 78 nw. u. l. rev(1984).
[7] archibald cox, book review, 94 harv. l. rev(1981).
[8] schneider v. state,308 u.s. 147 (1939) .
[9] 张千帆.西方体系(下册·欧洲宪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10] patrick m. mcfadden, the balancing test, 29 b.c. l. rev(1988).
[11] t. alexander aleinikof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age of balancing, 96-yale l.j(1987).
[12] jeffrey m. shama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llusion and reality, greenwood press, 20xx.
[13] [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14]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in gompers v. united states, 233 u.s.640, 610 (1914).
[15] cass. r. sunstein, five theses on originali, 19 harv. j. l. & pub. pol’y(1996).
[16]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m].陈爱娥译.:商务引书馆,20xx.
[17] [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冲突[m].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xx.
① 例如在一个诽谤案中,言论自由的利益与名誉不受侵犯的利益不能像盎司或英镑那样被测量,但二者的价值可以从性质上比较。
[18]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xx.
[19] 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
[20] 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60 b.u. l. rev(1980).
[21] william j. brennan, jr., speec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reprinted in the great debate (washington, d.c.the federalist society(1986).
[22] plessy v. ferguson, 163 u.s. 550,551 (1896).
[23] [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christopher wolfe).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m].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① “虽然法官或评论者可能是用‘客观’的话语在讨论,而不是用个人化的方法在识别,但无论他是否充分意识到,他所真正‘发现’的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价值。”参见[美]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同注[4],第43页。
② 在plessy v. ferguson, 163 u.s. 537 (1896)案件中,最高判决在提供同等条件的情况下,黑人和白人乘客的种族隔离没有违宪,不构成对黑人的歧视。该案所确立的原则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被。
the balancing mod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 an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thod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bstract: the balanced mod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 interpreter harmonize and weigh each involved factors obj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and spirits of the constitution. this mode is grounded on the law-reali and the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 it predominates today’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t is impersonal and rational a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s of equity and justice, it is also the joint of keep steady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its exterior nomological bases and inner validity and essence decide it is the important mod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some alternatives be proved to be nonviable.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balancing mode, interpreter.
宪法中“权利”与刑法中“权利”的比较分析_宪xx文 第九篇
1982年土耳其宪法第二篇“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为一般规定, 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经济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四章。
1983年萨尔瓦多宪法第二篇“个人的权利和基本保障”分为个人的权利、社会权利、公民和公民的权利三章。
1986年尼加拉瓜宪法第四章“尼加拉瓜的权利、义务和保障”分为个利、权利、社会权利、家庭权利、劳动权利、大西洋沿岸村社权利等6节。
1990年克罗地亚宪法将“人和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分为综合条款,个人的和的自由和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三部分。
1991年马其顿宪法将“个人和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分为公民的和的自由和权利,经济、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保证,经济关系的基础四部分。
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分为总则、国籍、个利和自由、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义务七章。
1992年斯洛伐克宪法第二章“基本权利与自由”分为一般条款,基本与自由,权利,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的权利,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保护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权利,司法及其他法律保护的权利等7节。
1997年波兰宪法第二章“人与公民的自由、权利和义务”分一般原则,个人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自由和权利,保障自由和权利的措施,义务6节。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给我们启发。
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从第33条到第51条一条一条地规定我国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且是一条规定一项基本权利,显然没有进行分类,属于逐条立宪模式。这就造成这个权利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宪法不能提供可信任的规范性条款,普通的法律又怎能把握住它的实质性内容呢?刑法也因此在和本身之中寻找依据。其实早有学者指出这种立宪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分类的立宪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了,它使我国宪法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不清晰、性质不明确,相互之间还有交叉,不利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甚至有学者指出,1982年宪法上出现“权利”是受了1979年刑法的影响。[14]
从各国宪法学和宪法文本中的对公民权利的分类来看,在宪法中规定权利是符合合乎理论和实践要求的,只是权利的具体范围需要严格的界定。我国宪法学者一般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言论、出版、、结社、、)和其它参与的权利——监督权和参与国家公职即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等一律认为是权利的内容。但在国外的宪法学中大多将六大自由作为一般的表达自由或者表现自由列入精神自由的范畴之中,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监督权等参与国家生活的权利界定为权利。另外考察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剥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权利,作为资格刑的内容,不仅是绝无仅有,而且其存在的合理性、存在的价值也值得怀疑。[15]
第35条所规定的六大自由在宪法学上不应该界定为权利,理由是:从权利的性质看,第35条规定的六大自由不独表现在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经济等领域,例如,人们行使结社自由所创建社团可以是学术性质的,我们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就是这种社团,也可以是经济性质的,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就在当地设立了温州人商会。有论者认为,应对这里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权利“似乎可”采用“合宪性限定解释”的方法将其限定在“性”的范围之内,以避免对刑法条款的合宪性审查。[16]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从宪法解释的技术角度考虑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上述六项自由局限于性的,仅作性的理解实质上回避了刑法是否合宪的问题本身,同时制造了新的问题:性的表达自由是权利,那么非性的表达是何种权利呢?极为重要的是,六种自由作性和非性的划分,虽然理论上可行,立法中也可以区分性的和非性的,但在实践中由谁来判断、依据何种标准、采用何种方式来判断是否是权利却十分困难。故而我们主张应把这六种自由的排除在权利以外,界定为表现自由。
(二) 权利的性质及相对性
权利被列入基本权利或者宪法权利的体系之中,表明了他的重要性,需要免受国家的侵犯(国家不作为),并且国家必须予以保障(国家作为),确立宪法对其之保护并提供不同于普通法律救济的宪法救济。[17]换一个角度思考的话,哪些权利是基本权利不是一纸宪法就决定了的,而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受到诸如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的制约。
权利是与公民资格密切相联,是现代国家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在化和法治化的国家,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运行的合法性既需要有公民的参与组织国家机构的成立,又需要公民参与创制、复决法律,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工作人员的行为。权利的内容主要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监督权、请愿权等。权利的取得取决于个人对某一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与身份,取决于公民义务遵守情况,只有对国家尽了一定义务的人才可以享有全部的权利,因此,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制度性权利。
权利具有道德属性和国家属性。宪法规范是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界定,通过规范性的宪法,个人获得了对抗国家权力的属性,客观上要求国家不得无视个人的正当性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国家行为的不可逾越的边界。权利的出现与观念,原则密切相关,最初以参的形态表现出来,带一定程度的超实定法特征,具备的道德属性或者自然属性;同时所带来的制度的发展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程度、文明进步的标尺,公民只有通过选举这个参与国家的制度性设计来达到“当家作主”的理想,也正因为如此权利是制度性的权利。
权利的实效性与可救济性。各国宪法将权利具体的加以规定一方面表达了社会共同体对于基本价值理想的宣誓,同时也是具有法规范意义的可以援引防范来自各方面侵犯并可获得救济的以宪法文本为依据的实定权利,具有无可争议的法的效力。
基本权利的受限制性是现代宪法学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基本权利的相对化、客观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命题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而提出的,限制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看似矛盾的语言背后却是更深的经验和理性的考量。问题是剥夺是否是一种限制呢?还是对限制的突破?很多国家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了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如法国《宣言》将公民的基本权利视为“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削减言论或出版自由,……”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和二元化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实定法,公民的自然权利先于实定的宪法,宪法是为了公民的自然权利而制定的;公民的自然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削减、不可剥夺的,即使是法律体系中最高位阶的根本法宪法也不能规定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从我们国家的观出发,我们认为宪法权利对于一部分人是可以被剥夺的,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仍然需要这种资格刑的存在,而且“当今世界各国,大多有资格刑的规定”,[18]但是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权利的剥夺则需要规范化和法治化。
三、剥夺权利行为的规范化、法治化
(一)宪法与“最危险的部门”
我们知道美国宪法制度中把司法审查权之所以交给除了普通法的传统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歇尔法官作为联邦党人严格的恪守了建国先贤所宣扬的“司法权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因为,“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掌握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主动的行动。”“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9]那么哪个部门是最危险的部门呢?是貌似强大、无处不在的行吗?笔者认为不然,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威胁最大的应该是立法权。立法者可以制定限制甚至剥夺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并对行和司法权产生法律上的指引。行必须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而法官依据法律裁决案件更是职责所在,因此在这里提出立法权的潜在的危险性就合乎时宜。立法权对于公民的权力与利益可能产生最激烈的侵害的情形就是制定刑法以设定刑罚制度,并因此造成公民与国家、社会发生冲突时产生最不可欲的后果。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刑法究竟是保障犯罪人的权利还是打击犯罪分子的工具?刑罚是手段还是目的?我们的刑法学是“规范性的还是性亦或政策性?公民是作为法秩序的主体亦或是刑法的对象即犯罪主体来处理?”[20]
从立宪主义的产生来看,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暗示了对的不信任,打破了立法至上和立法万能的神话,同样法律不是万能的,不能执着的相信制度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只有原则才是走向实质法治的通途。意义上的宪法是限权宪法,是为立法机关规定界限的宪法。孟德斯鸠说“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因为刑法以剥夺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的制裁手段,不良的刑法无疑是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制刑权的行使——立法权在刑事立法方面的运作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和限制。宪法作为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它通过宪法规范中所反映的概念、原则、价值、制度等指导,调控和约束立法,为立法权的行使提供原则和目标并对立法者的活动进行限制,对立法的最终结果进行规诫以保持宪法价值秩序的统一性、客观性与连续性,宪法中体现的权利保障原则和价值统摄立法活动的经验性与性、历史性与科学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并从深远的意义上规划着未来。而且随着宪法权利效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宪法权利逐渐强化了对立法权活动的控制,传统的宪法与法律关系的命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法律本身被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之中,成为基本权利的形式。有些宪法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削减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是不得侵犯宪法的这一核心领域的,否则就构成违宪。
(二)立法权对权利的剥夺应遵循的原则
剥夺权利的立法应该按照宪法的程序和原则进行,应使剥夺的范围、方式、程度符合剥夺的基本目的。我们认为比例原则应该成为调整国家刑罚权和公民个利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它具体应该指国家立法权在制定刑罚时要妥当、必要、均衡、不过度、符合比例,不得对公民宪法权利造成非法和不必要、失衡地、过度地侵犯。这项原则不仅对行的行使发挥约束力而且要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规诫,对法官的司法活动进行原则性指导。“所谓宪法的比例原则问题,就是讨论一个涉及的公权力(可能是立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其目的和所采行的手段之间,有无存在一个相当的比例问题。”[21]在刑事领域,比例原则的运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刑罚的制定,直接关涉重大的保障,最易发生国家权力恣意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因此特别需要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有比例的平衡。
比例原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三个次要概念: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的比例原则(又称为比例性或均衡性原则)。[22]
妥当性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要求国家所实施每一权力行为都必须以实现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为目标,并且每一手段的运用都必须有利于其法定目的的实现,不能以此种手段谋求法律规定的彼种手段才能实现的目的,更不能将国家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欲的工具。妥当性表现为手段对目的的妥当,也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对法定目的的妥当,如果利用国家权力手段追求法定目的之外具有私人利益的其他目的则明显不符合妥当性原则的要求。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犯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权力欲达到某一合乎宪法和法律允许的目的时,比如说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的目的可以限制和剥夺宪法权利就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存在多种可以选择的手段,而且肯定地讲多种手段之间对宪法权利的限制程度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国家权力就应当以客观的角度来考虑和评估诸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的达到目的?诸些手段间,哪个能给予权利最小之侵犯?最后要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最小的手段。该原则主要用于解决自由裁量问题,就立法机关而言,如果其针对特定目标所设立的手段在诸种手段中并非对公民权利限制最小的或者在司法和行政机关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领域未对该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置任何限制性规定(立法不作为),那么该立法就可能因违反比例原则而被宣告违宪。
均衡性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所造成的损害与其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一个国家行为虽然措施和目的具有一致性,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以对公民的权力造成过度的侵害,保护的客观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减损之间应该有适当的比例,达至均衡。即使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了妥当性原则的要求,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对公民权利限制最小的手段,即符合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但如果该手段对公民个利造成的损害与其所保护的社会利益显然不成比例,也就是说,对公民个利的损害大于其所保护的社会利益,那么该手段仍然是违反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的。这种利益的衡量其决定的价值因素就是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所确立的客观的价值秩序。
(三)比例原则的适用——实现剥夺权利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剥夺权利是刑罚附加刑的一种(第34条),其内涵是指剥夺下列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第54条)适用的主体一是对于危害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权利(第56条);二是对于故意杀人、、放火、、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权利(第56条);三是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权利终身(第57条);四是在一些情况下按照分则罪名作为一种附加刑适用剥夺权利(第56条)。刑法对于权利剥夺的规定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但是,我国刑法中对于犯罪主体权利的剥夺是否违背了“国家尊重和保护”的规定呢?宪法中“剥夺权利”的规定第54条,说明了权利可以被剥夺,但是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能否被剥夺是不明确的,刑法中的规定无疑是对权利做了扩大的理解。另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加公职权利是可以被剥夺的,从各国的资格刑的发展来看,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上述六大自由确是不应被包含在剥夺的范围内的,只能被限制。因为对自由的限制只能在自由造成了客观的秩序和利益的损害时方可以限制,要有“明显的即刻的危险”。而且对于合法的表达自由难道也要一概剥夺吗?这种一概性的剥夺方式早有学者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就提出过异议。[23]
从法律语言的角度来考虑,剥夺权利与限制权利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剥夺是对权利的绝对剔除,而限制则是对权利的相对约束,二者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24]刑罚中的剥夺权利意味着完全而彻底的取消、夺走某类犯罪人的权利,也即该类主体在一定时间内或者从此不再享有该项权利;而限制权利则不同,并不意味着该类主体丧失了权利的享有权,他仍然享有权利,而只是由于法律制裁使其不能行使权利。那么对于表达自由的剥夺是否合乎比例性原则的要求呢?这是否是唯一的可以选择的手段?是否与刑罚的目的之间存在必要性的关联?是否是最小程度的侵犯呢?笔者认为我国的宪法和刑法应该对于立法在刑罚方面的自由裁量进行重新的考量,并对剥夺权利刑罚制度的重新设计作进一步的思考:是把权利的剥夺范围尽量缩小到“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而同时把适用的对象扩大到象经济犯罪这样的领域中;还是继续扩大对权利范围的理解,并加重限制的范围、程度?已有学者对于剥夺权利制度的重新定位与完善的总体构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把剥夺权利改造为限制公权、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的资格刑、增设以法人犯罪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等。[25]
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个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公民任何一项宪法权利的行使必然带来社会关联性的后果,公民权利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的确应该对其行使施加一定的限制,维护社会共同体统一的价值秩序和法益。但是,由于基本权利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权利体系内部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并且相互制衡。我们看到在公民权利具体行使的过程中,公民权利的限制更多的表现为因各种权利相互之间的摩擦与竞合而进行的法益判断与取舍过程,而判断和取舍的过程往往隐含或者掩盖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立法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就尤为重要。比例原则作为基本权利之保障利器,其具体的功能,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26]第一,视为宪法委托,要求今后立法者制定刑事法律涉及对的处分时应有所节制和谦抑;第二,作为宪法解释的一个标准来对法律的规定予以解释,制止立法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第三,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要审查立法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审查对限制的程度是否合乎均衡的要求,这就自然而然的过渡到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问题上,至于采取何种的违宪审查模式则需要根据我国的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法治程度来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3]胡锦光、韩大元著:《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5页。
[4]刘飞宇:《对于刑法中剥夺权利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学家》20xx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网,
[5]相关单行刑事法规和司法解释参考吴平著:《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36页。
[6]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7]张旭:《社会演进与刑法修改――以德国为视角的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xx年第2期。
[9]韩大元、胡锦光主编,《宪法教学参考书》,中国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335-336页
[10]同上,第336页。
[11]胡锦光、韩大元著:《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231页。
[12]以下关于各国宪法的引述参考杨海坤:《公民基本权利修宪应作精良设计》,载《法学》20xx年第4期。
[13]杨海坤:《公民基本权利修宪应作精良设计》,载《法学》,20xx年第4期。
[14]刘飞宇:《对于刑法中剥夺权利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学家》20xx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网,
[15]马松建:《论剥夺权利刑的完善》,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年第一期。
[16]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124——125页。
[17]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第135页。
[18]吴平著:《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9]《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xx年4月版,第391页。
[20]李海东著:《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1][22]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原理》(下册),山东出版社20xx年版,第368页。第368——372页。
[23]陈泽宪:《刑事法制发展与公民权利保护》,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以下。
[24]焦宏昌、贾志刚:《剥夺权利的宪法学思考》,载张庆福主编:《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第76页。
[25]详细内容请参见吴平著:《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46页。
[26]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原理》(下册),山东出版社20xx年版,第380页。
纳税人与国家财政立宪_宪xx文 第十篇
【摘要】 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立宪的模式,也被认为最根本的保护的手段。然而的起源和的价值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体现都是我们要追寻和思考的。财政作为国家运行的基础,而国家运行的本质是为保护建造国家的纳税人的利益,但纳税人的利益如何保护,财政、纳税人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和都是财政法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税收、纳税利、国家权力
【正文】
漫长的中世纪封建专制时代的欧洲,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了国王和大贵族的手里。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新的经济制度的曙光。市场经济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随着物资财富转化为资本集聚在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对私权利的保护成了新兴阶级的急切需求,和王权相斗争,走上了舞台。
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是限制王权的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句话:“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征税。”或者今天我们再看大宪章,会觉得只不过是阶级斗争,限制王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历史的必然作为,但是我要说的是,它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穿越将近800年的时间隧道,它的价值在现代社会愈发光彩夺目。他带来了的起源,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式。与古典模式仅仅关注如何限制国家权力、建立有限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理想模式是要建构一种“有限”和“有效”的国家。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想的国家模式被认为是避免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可行之路,也可以说,能否以及如何建构一个高效、廉洁的乃是当今理论关注的重点,也是理念赢得“社会声望”和“声望”的基础性理由。Www.meiword.COm①建立国家、保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国家起源来看,税收是国家存在的本源。人们让与了部分财产权,换取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保护,保障人们自由的生存。任何公民权利的实现都必须依赖税收。②政追求的自由、只有在一个有序、强健的统治管理环境下才能实现。的无能或者无状态都是对最大的伤害。因此,人们纳税让与财产权,组建国家权力机构,使其为维护更广泛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服务。税收是国家的基本,也是纳税利的根本保障来源。
我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法治文明已经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之一。“宪法之上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③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人们遵守法制,因为法律是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达成的契约,互相尊重,互相约制,互相促进。从国家权力本源来看,建立国家根源是要进行财政立宪。
财政立宪是使纳税人纳税的缘由。收了的钱,必须让充分了解这些钱的具体花费情况,这是现代的基本要求,是不可推卸的责任。④收作为国家财政之基,国家机构运行之本,源于纳税人的自觉纳税。纳税人缴纳税款,是为了享受相应的权利。国家行政行为以纳税利为本位,为纳税人服务使其宗旨。如果的财政收支不是为纳税人服务,也就侵害了纳税人应得的权利,有序健康的财政制度是纳税人纳税与国家运行的良心循环根本所在。
财政立宪是纳税利的根本保障。国家,追求着人们的自由和。每个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经济人”。人们让与部分财产权,取得国家权力的保护是人们纳税的初衷。而在国家运行过程之中,为纳税人服务一步步变质、异化,纳税人的权利被权力所侵害。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已经成为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武器。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是人的主体能力的一种客观化形式,它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所发现或创制的,并且最终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一个不受和法律约束的最终也无法受到和法律的保护。⑤将有关才财政制度纳入宪法,以国家根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是真正意义上对纳税利的保障。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立法体例的部分残缺,国家职权在运行中存在很多弊端。长期的财政官僚化,使财政的价值发生了异化。大量的财政流失于预决算之外,加之官员的自身素质不够高,滥收费、公款消费 、偷损国有企业资产等现象普遍存在,其实都是对纳税利的侵害。只有将财政----纳税人与国家的纽带,写入宪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分歧,实现国家权力的有限且高效,同时保护纳税利的不可随意侵犯。
我国的制度是制,这一制度的出现是代议制的中国化。人口众多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人主参与活动是不可能实现,人们如何实现权利的保障是个难题。制,选举代表,代表自己的意愿参与生活,使公共财政内部矛盾得到根本解决。保证了国家权力归,享有国家立法权,通过建立健全的财政立法体系,将财政纳入宪法中,是使纳税利保护的根据。同时健全审计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力度,对国家和官员违法的行为依法严格限制,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
然而任何机构或制度都不是无限的。纳税人纳税人作为国家财政根本来源,应该从自身出发,提高自身的纳税利义务意识,遵守道德和和法律,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以主人公的身份督的行政行为,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做一个善良守法的纳税人。
国家源于公民权利的让与,国家运行的基础是强大充裕的财政,财政源于纳税人的纳税,而现代经济社会中,纳税人的生产生活更需要有序、健康、稳定的的保护,的有序与稳定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和约束。 现代主义国家,我们要将财政立宪,从根本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善良纳税人的权利。我相信财政立宪,无疑将会是解决纳税人和国家权力的必然要求和唯一方法!
【参考资料】
1. 《论公共财政与国家》-------------周志刚 (中国法制出版社)
2.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史蒂芬.霍姆斯、凯特.r.桑斯坦
3. 《宪法之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周叶中(《法治评论》1993.6)
4. 《人大审查财政预算的意义》-------------贺卫方(《南方周末》20xx年1月16日)
5. 《法治理念的回归与超越 》---------------江汉大学学报 20xx年第4卷
6. 《权利发展于公民参与》 ---------------褚松燕(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
本文地址:www.wordls.cn/zuowen/27493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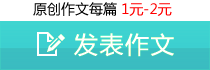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