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_国学论文
“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_国学论文
【哲学论文】导语,大家所阅读的这篇文章共有133351文字,由邹龙炎细心校正后,上传在美文档。《生生》是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怡凤作词,林俊杰作曲,吴庆隆编曲,收录在林俊杰2014年12月27日发行的专辑《新地球GENESIS》中。“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_国学论文倘若你对此篇文章想说点什么,可以发表分享给大家!
第一篇 “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_国学论文
摘要:《易传》的主题和精髓是弘扬了儒学核心的中和哲学,它深刻揭示了阴阳中和之道是天地人万物发展的根本之道,生生日新、与时变通的时中精神是最高的生存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和原则是根本的民族精神。《易传》把儒家的中和哲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关键词:易传;中和; 时中
“go oothly by acting timely & appropriately”, “preserve the harmoniousness”:
on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iousness in yi zhuan
abstract: the theme and marrow of yi zhuan is to develop the philosophy of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being the core of confuciani. yi zhuan deeply exposed that harmoniousness between yin and yang is the principal way for universal things' growing; renewing all the time and changing appropriately with times is the highest living wisdom;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with “striving unceasingly” and “thickening virtues” is the fundamental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yi zhuan put the philosophy of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of confuciani to a new peak.
key words: yi zhuan; harmoniousness; appropriateness all the time;
中和哲学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形态,是儒学的核心和实质。wWW.meiword.cOm儒家的中和哲学,自孔子开始,经孟子、荀子而在《易传》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易传》十篇,相传为孔子所作,但据今多数学者观点,它当为战国中后期作品。从儒家中和哲学由哲学、道德哲学而本体哲学的逻辑历程看,这一观点应是成立的。
《易传》与《论语》直论人我之际的旨趣不同,它以“究天人之际”为主题。它的主旨和精神是借宇宙万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易道本质揭示人类进取创造的生存方式,标举儒家崇尚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境界。易道体现了以中和为特色的天人和合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中华民族尚中尚和的思维方式。而易道的中和之道本质上即是时中。清人惠栋断论:“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1](《易尚时中说》)惠栋是易学大家,其论可谓勾勒了《易传》的核心精神。
一、中和易道论
《易传》的基本范畴是阴阳,“一阴一阳之为道”,“生生之谓易”,《易传》的易道就是一阴一阳动态化交感平衡协同运动所引起的创造宇宙生命的生生之道。阴阳之所以能生生变化,其因正在一阴一阳之间的中和化相互作用。易道即是阴阳中和之道。“易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中焉止矣。”[2](《语要》)《周易》的有机化系统化的宇宙观中,整体性、协调性、最优化是其三大特征,而其核心是中和性。中和性表征贯穿统合着整体性、协调性、最优化。
一般认为“易”有三义,即变易、不易、简易。然而在我看来,这三义本质是一致的。易道首先是关于生生大化的,即讲变易的,所以具变易性;但易道作为世界生生大化的总法则和根本规律,却是普遍一般的常道,故具有不变性。同时,这种总法则和根本规律的易道,是最普遍最一般的,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因而从内涵上讲,也是最简易的,它只是“一阴一阳”,具有简易性。因此,变易、不易和简易是内在相通的,都只是易道的不同性质、特性和特点。而这种综合着“变易”、“不易”和“简易”的易道其根本内容即是中和,易道是阴阳中和之道。
易道首重变易,易道是生生通变之道。《易传》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一个不停变易流转的系列。“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就是在揭示宇宙天地万物整体变动不居、周流不停的客观辩证法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主体如何适变,如何变通的,即如何致中和的。
因此,易道不仅是客观规律或客观辩证法,而且也是思维规律或主观辩证法。易道强调变通的实质即是实现主客体在实践活动中的合一。《系辞》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变而通之以尽利",“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通变之谓事”等都在反复强调主体通过创造文化的活动实现变通,实现天人和合。而变通的内在动力和最高原则便是阴阳辩证法的中和之道,具体又有二种不同的形态,一是客体的结构上的,一是主体的时间上的。所谓客体的结构上的,是指在卦象上的“位中”,其表现即是崇尚二五中爻,其实质则是揭示了宇宙万物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途径,即阴阳中和是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发展动力。所谓主体的时间上的,是指在彖象上的“时中”,其实质是揭示了主体在思维行为上的通变性,以保证主体行为的有效性、创新性、合理性、成功性。
二、“保合太和”论
《易传》崇尚中和,首先表现在横向结构上即卦象爻位上是崇尚中爻。中爻,即处中位之爻。在由六爻构成的卦象中,二五两爻分居上下两卦的中位,这种情形也叫位中。
《易传》认为,在六爻之中,二五爻处于中位,是中爻,而中爻就意味着在位置结构上处于最佳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衡点或统一点。因此,“处中”“得中”就意味着事物处于一种最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意味着事物处于最佳的有序状态中。因此,中爻往往象征着吉利亨通。《易传》中记载有大量中爻与事物存在发展的“吉”“亨”内在一致的卦爻辞,如《系辞上·坤》的“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象辞上·临》有“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象辞下·解》有“九二贞吉,得中道也”等等,都指明中正之爻使事物处于“吉”“亨”“贞”的有序状态中。而在易学史上,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在解《易》时,也都阐扬着这一中爻为吉亨的思想原则。如汉易中以象数解易的代表人物虞翻,在解“临”卦九二时说:“得中多誉,故无不利。”又解释“观”卦九五爻时为“五得道处中,故君子无咎也”。魏王弼以义理解《易》,都以中爻释卦爻辞中吉利之辞,并把居于中位的二五两爻视为一卦的主体。北宋程颐继承王弼的义理路子,更提出了“以中为贵”“中重于正”的命题,充分体现了《易传》尚中的观点。
《易传》崇尚中爻,又特别崇尚中和。《易传》中和,从爻位上看,是指二五两中爻阴阳既当位,又相应,这种中和也叫“太和”,它寓指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性,矛盾双方处于一种最佳的和谐统一协同的关系和状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从整个体系看,《易》的六十四卦本身都有阴阳平衡中和的意义,每卦三个阴位三个阳位也体现了客观的中和平衡协调规律。
《易传》中心法则的中和之道,是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对宇宙天地万物发展的直观经验中概括而成的。它揭示了阴阳只有处于中和的平衡和谐统一关系,矛盾统一体才是有序的,才有最佳的发展状态。否则,事物统一体就失去了存在发展的动力根据,从而趋向解体,而对这一事物言,也就是“凶”“灾”。这就是“乾”上九说的“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之上九以阳爻居于最上位,在《彖传》就是“穷”,因而有“灾”。它实际上是源于一个“亢”。“亢”就是过于高亢,偏离了中和,因而就不能再发展,就“穷”顿,就陷入灾难。因此,对于事物来说,其“亨”其“吉”源于“中和”或“太和”,其“悔”其“凶”源于不中。故《系辞》说:“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居中则吉存,居偏则凶亡。“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只要使阴阳处于“太和”关系中,万事万物就能保持各自的生命本质和存在状态。故程颐释此说:“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3](《伊川易传·乾·彖》)阴阳高度中和的“太和”正是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宇宙万物常存而不毁的根本原因。《系辞》中“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也正是指在中和关系中,天地万物男女才呈现一派生生欣欣的兴旺景象。“保合太和”之“太和”作为中和的理想状态,是生生之太和,是动态的和谐。“太和”论既指寓天地人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明示天地人万物只有在高度和谐统一中才能获得最佳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太和”正体现了天地合一的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想。这种阴阳中和论或太和论充分体现了先秦哲学的理性思维水平,它不仅标举着理性力量对神话迷信的超越,而且也展现了理性思维探索天地自然的轨迹。在“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一阴一阳的中和之道的不易性简易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和”“太和”的最高抽象程度。而中或太和作为事物存在发展的最佳方式和内在动力则本质上是辩证法的,它体现了“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核心原则,它代表了先秦哲学关于事物存在和发展学说的最高水平。
三、“时中”变通论
《易传》崇尚中和,然而在《易传》作者看来,中和或太和的阴阳统一关系作为事物存在发展的最佳形式,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阴阳感通、刚柔摩推中处于不停地转变迁移变化中,易道即是这种变化之道。《易》的卦爻本质上都是对天地万物变化的状摹比象描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爻者,言乎变者也”。不仅六十四卦指代着持续不断的时间过程上的六十四个时期,而且每卦的六爻也都代表着事物发展的六种不同时态。明朝著名易学家吴澄在其《易纂言》中说:“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王弼在《易略例》中也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从纵向看,卦表示的是一个较完善的发展时段,而六爻则是六个小阶段。六爻可分“初”“中”“终”三个时期。由于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都象征着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因而,时寒则寒、时热则热的有序规律性体现了客观自然的时中原则。而主体的人便必须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行动,这是主体性“时中”。如《蒙·彖》中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易传》中频繁地用“及时”、“随时”“趣时”、“时行”、“时发”、“时用”、“与时偕行”等词语,表述的都是主体活动上的“时中”实质。“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里,“与时消息”就是主体实践活动中的“时中”。《易传》对时中的典型释义在“艮”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的论断上。人的行止动静与最佳时机相结合,这便是“时中”的实质。
由于“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因此,“时中”本质上分布于三百八十四爻的每一爻,而不必是二五爻。实际上,由于“时中”与“位中”的根据不同,一方面有时二五爻的可以是时中,如《彖传·坤六三》“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这里的“坤”六三非中爻,但属“时发”即“时中”,因而“可贞”,为吉象。另一方面,有时属二五爻的倒不一定就无条件的是“时中”。如“节”卦九二是“失时极”,就没有做到时中,因而“凶”。由于“时中”的实质是主体的“适时之变”,因此对于主体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善于把握和利用对客观事物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时机。对这种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时机的认识和把握,《易传》也叫“时义”。“时义”是“时中”的集中体现。对此“时义”,《易传》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推崇。在《彖传》中,连称“颐”、“大过”、“解”、“坎”、“睽”、“蹇”、“豫”、“遯” 、“姤”、“旅”、“革”诸卦其“时大矣哉”。《易传》作者认为主体要能把握“时义”,就能做到“时中”。而“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4](《系辞》)?“时义”之大而深,根本就在于它是“时中”的必要环节,而行为能“时中”,便何利不有?!
《易传》的“时中”范畴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精髓,它所体现的是主体主动顺应天地之道,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活动和过程,这也就是《易传·彖·大有》中所说的“应乎天而时行“,”承天而时行”。通过“时中”的主动顺应改造活动,主体更创造出适合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关系。显然,这样的“时中”本质上是人类积极的生存发展活动和实践样式,它深刻地反映了主体如何与时俱进、有效合理地生存的本体认识。“时中”体现了一种最高的生存智慧。
“时中”要求主体“时行时止”,归根到底是要求主体行为与天地人万物的运动变化产生协动,发生共振,在顺应性的相通相协的一致性中顺畅地实现主体的存在,达成生存过程。因此,这样的时中所表达的是主体灵活的变通过程。时中即是趣时,而趣时即是变通,“变通者,趣时者也”。时中体现的正是人的“适时之变”,即随时而变通。《易传》大量阐述这种主动性适应和创造性顺应的变通,即时中的重要意义,如《系辞》所谓的“变通之谓事”、“变而通之以尽利”、“通其变使民不倦”、“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变则通,通则久”等等,所有这些对变通重要作用的揭示,都集中说明了一点:变通乃事物长久生存发展之道。易道即时中之道,即变通之道。这就是《系辞》说的“《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切“变动不居”,一切“唯变所适”。而一切“变动不居”,这是客观辩证法;一切“唯变所适”,这是主体辩证法。“唯变所适”即是时中,即是变通,这正是《易传》的核心精神。程颐曾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的时中变通性包含着丰富的思维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内容。时中变通是为道与为学的统一,是智性与德性的统一,是客观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
一方面,时中包含了阴阳中和之道是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是天地人万物新陈代谢的总规律,“时中”体现了主体在实践行为上主动适应宇宙变化发展的中和之道的态度。它继承了孔子中庸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的特点,但由于它又时时以本体化的宇宙中和之道为前提,因此在理论上又超越了孔子的中庸方平实稳重的性质,而处处散发着“变”和“通”的特性。这一时中变通性所包含的正是人类以自己一系列的文化创造活动主动适应和顺应环境从而为自己获得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的思想。“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正是体现了天地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时中变通性高度反映了主体具有的自强不息、生生日新的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易传》弘扬的“大人”理想人格,其本质正在于这样一种时中精神和变通品格。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绝不只是一种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而是一种广义的生命存在形式。它要求的是主体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活动必须与天地生生之德,与日月日新之明,与四时变化之序相顺应,相协同,体现的正是时中变通的原则。《易传》理想的“大人”人格,本质上是一种“时中”人格。因此我们这里要避免对《易传》“大人”人格作偏狭的理解,以为只是一个后来宋明理学家所拘囿的狭义的道德人格。“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之“德”,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德”,体现的正是时中变通的顺应创造精神。实际上我们只要看一下《系辞》的时中变通性,就可充分明白它包含着怎样丰富的顺应创造内容,而不仅仅限于道德品德的“日新”。《系辞》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的原则下,列举了历史一系列变通顺应的“时中”典型,而正是这些“时中”变通事例构成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里虽然尚有某种神秘色彩,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的理性变通精神已是淋漓尽致地显溢出来。而“通其变使民不倦”的内容正是一系列解决生存困难的物质文化发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系辞》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这种变通并不限于器物的创造发明,还包括社会制度的“革命”,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显然,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长久,其旺盛的生命活力正在于这种包括一系列器物制度创造发明的变通精神和创造活动,这也就是“时中”精神和“时中”实践。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曾把《易传》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概括为“和谐化辩证法”,指出:“其内涵在阐明如何化解生命不同层次所遭遇到的矛盾与困难,实现生命整体与本体和谐。”[5]如果这里的“生命”与“本体”不限于道德领域,那么这种“和谐化辩证法”所揭示的正是《易传》的变通精神。但以“和谐化辩证法”概括这种变通精神,远没有《易传》本身的“时中”范畴更简洁,更贴切,更传神。“时中”是变通的根据、本质和原则。因此,用“时中辩证法”或简称为“时中”更能深刻全面地反映《易传》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原则。
“时中”体现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致思原则,它是从“天地”“日月”“四时”“万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中和本质中推衍出“时中”的“人事”原则,它所体现的本质上是一条从客观辩证法到主观(体)辩证法的正确路线。由于“时中”变通性包括着广义的文化创造活动,它又源于客观的天地自然,因此其“时中”变通过程内在地包括着客观认知的认识论内容。
“时中”讲的是“随时变易以从道”,是随时而中。因此,首先必须认识“时”,把握“时”。“时中”首先必须在观念上“中时”,只有在观念上“中时”,认识“时”,才能在实践中不“违时”。因此“时中”在《易传》中不仅是一个价值性范畴和命题,也是一个知性命题和认识论范畴。实际上,《易》的本意即是“决疑”,而“通变”,“决疑”本身正是一种由不知到知的理性预见活动。《周易》的卦爻辞以及彖象辞本质上都是对表示事物不同发展过程、阶段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时变”的认知和判断。《易传》揭示的人类在“变通”过程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体现的正是“时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对天地万物客观的感性认知和经验类比认识活动,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知微知彰,极数知来”,“知来藏往”,“彰往而察来”,“知幽明之故”,“冒天下之道”等一系列活动都体现了《易传》“时中”化认知活动由现象到本质、由外部联系到内在规律的抽象理性思维过程。而《系辞》的“当名辩物,正言断辞”、“以类族辨物”等则包含了丰富的辩证逻辑的内容。因此,《易传》的时中哲学包含有关于认识论、方的丰富内涵,这些构成了《易传》“决疑”的实质内容,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断其吉凶”。没有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之“时”的正确认知和把握,人们就不能预见进而选择采取合理的生存行为,其行为只能具有“凶”、“悔”、“吝”、“亡”的结果。所以程颐有“见《易》须看时,然后逐爻之才”[6](《二程遗书·易传》)的论断。一个“看”字括尽了丰富的认知内涵。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时中”或“中庸”是具有最广阔的知识论、认识论的生存空间的,是最需要客观认知作为其必要环节的。长期以来,文化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要求人无条件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在身心各方面向自然作认同。对自然的这种态度,只能产生一种审美与道德的价值取向,决不可能导出人对自然的探索精神,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切实可靠的知识,得到‘真’。相反西方文化由于认为自然界与人类是对立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故千方百计要认识外部世界,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以实现对立的同一”。[7]笔者对这一论断不敢苟同。为什么“顺应自然”就不须“探索”,不需对外部世界的“真”知识呢?从逻辑上讲,倒正是讲自然与人类对立,主体与客体对立的西方文化哲学更可能不必讲“真”。因为人的任何盲目任意的不讲“真”的活动,就意味着对客观规律性必然性的“对立”。相反,人要“顺应自然”就非得有对“自然”的本质有一客观的认知不可,否则就无法实现“顺应”。在一定意义上,当今自然与人类的“对立”状态的消解,实现自然与人类的统一,就是以高度的“真知”为先决前提的。因此,天人是合一还是相分,与是否求“真”讲“知”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看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讲“合一”或“相分”。荀子重“天人之分”却又“不求知天”,而《易传》讲“天人合德”却要“极深研几”。盖在《易传》的“与天地合德”不是如老庄建立在“自然无为”的原则上的,而是建立在“生生日新”的原则上。这种天地的生生日新之“德”,就要求“顺应”生生日新的天地之“德”的人们“趣时变通”,即以“时中”原则相“顺应”。这就要求人们去及时全面地认识天地万物具体的“生生”之“德”,即生成变化的规律性,否则就无以“顺应”而实现天人的合一。因此,《易传》的时中哲学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可贵的“真”的认识论内容。
时中的实质在变通,而变通的本质在时新。也可以说,时中就是时新,时中强调“趣时”,就意味着须以“革故鼎新”为原则,以适应外界新的变化。因此“时中”是一以革适变、以新顺通的过程。“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正规范着“时中”以日新为实质的生生变通内涵。正是在生生日新、自强不息、变通顺应的“时中”实践中,实现天地人万物的“太和”境界。《易传》“日新其德”的原则所强调的正是主体以其创造精神与创造活动“与天地合其德”,与宇宙创新原则相合一。因此,《易传》“时中”所具有的“与天地合其德”的性质体现的是一种天地人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的致思倾向。但显现这种天地人一体的思想不是道德本体论意义上的,而与荀子人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论具有某些共通性。严格说来,它是在孟子道德化的天人合一论与荀子自然化的天人相分论的基础上超越创新而成的。《易传》时中哲学是儒家中和哲学在当时综合创新的最高典范。
《易传》的时中哲学突破了传统儒家中和哲学的局限。孔、孟、《中庸》都有丰富的用中时中思想。但在那里,“君子时中”本质上局限于伦理实践,随时而中的合理性标准根本上就是仁礼道德标准。而《易传》的“时中”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仁礼型时中的局限性,在宇宙天地人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展现时中的普广性丰富性。就人的时中而言,它已不再是伦理行为,而是在一般的广义文化创造意义上,从人的应付环境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引伸出来的。这种广义文化创造实践活动的“时中”已扩及到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时中”观显然标志着儒家中和哲学的新发展。
《易传》时中哲学与孔孟荀的中和哲学相比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和突出的优点。
首先,《易传》的时中哲学是以“天道”的客观“生生”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知道,无论是孔子还是孟荀,其中和哲学思想带有浓重的宗法血缘关系的性质,都以传统的宗法制作为中和哲学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因而其中和本质往往与具有宗法性的仁礼相一致。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中和观具有强大的世俗性,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和思想因其化而不时显露出某种保守性、落后性。而《易传》以“究天人之际”为帜志,以重天道自然、明阴阳之理为特色,它的中和哲学或时中哲学是在“法象莫大乎天地”、“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的原则下,从客观的宇宙大化的中和之道中引伸出来的,因此,《易传》所揭示的核心之道的易道根本上是客观的天地人万物化生之道,它从阴阳矛盾的统一化即中和化过程去揭示事物产生发展生生不已的根本动力,本质上与唯物辩证法对立面统一的发展规律是相通的。显然从宇宙生生之道的中和之道中引伸出来的以变通日新为本质的时中哲学就具有更为广阔的背景和客观根据,其时中的本质内容也就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仁礼之中”的范围。《易传》中虽然也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仁礼之中”内容,但已大大减少了份量,大大淡化了浓度,它只成为人们广泛的“时中”化精神和实践的一部分。这一特点,使《易传》“时中”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特定社会制度的局限,而在更广大悠远的时空范围中展现其适用性和实用性。
其次,《易传》的“天人合一”的“时中”思想是以“生生”原则为中介的。孔子的中庸哲学暗合着天人合一的前提,至孟子和荀子,则具有了明晰的天人观。而《易传》的天人观则是对孟、荀天人观的超越。《易传》的天人观是天人合一论,而这种天人合一论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之德为中介的。其“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即主体以“时中”的变通日新精神和实践顺应统一于天地的生生日新规律,从而实现天地人万物一体的动态和谐。这样一种时中型的天人合一论显然与孟子道德化的心性型天人合一论不一样,它超越了孟子以道德伦理的仁义原则为中介的天人合一论。同时,它也超越了荀子的天人观。荀子的天人观是一天人相分与天人相“参”的统一。荀子的天人观是以“天职”“天功”与“人职”“人功”的关系立论的,也就是以天与人所各自独具的客观的功能作用立论的。荀子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实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天地人相“参”的整体和谐关系的思想,是功能互补的天人合一中和论。显然,这种功能互补性的天人观与《易传》“时中”天人观不一样。《易传》“时中”天人合一论,不是以具体功能内容互补相“参”,而是功能性质上的相合,即人在生存活动上以天地“生生之德”的新陈代谢规律为自己的生活准则,以时中变通日新的生存原则与天地相顺应,相和合。它运用的是一种“推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模式,是以“天道”与“人道”具有相通一致的“生生之德”走向天人合一的。因此,虽然《易传》与荀子都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且荀子也提倡“养备而动时”、“应时而使之”的时中顺应思想,但荀子由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走向天人相“分”相“参”,虽总体上承认天人相“参”合一,但突出的是一“分”。其“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的观点实际上都在价值取向上有分离天人的观点,将人道与天道、地道作截分。而《易传》的易道却是天地人共同之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地道和人道虽形式内容不一,虽也有“天人之分”,但在本质上是合一的,即都是易道,都是易道本质的体现。这样《易传》就对荀子重分的天人观实现了超越。从孟子的道德心性的天人合一论到荀子客观自然的天人相分论,再到《易传》时中日新的天人合一论,它不仅在形式上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更是从内容上克服了孟子天人观的纯道德性局限,克服了荀子纯客观功能性天人观的局限,而将两者综合创新,从而实现了生命存在的飞跃,构建出了积极向上的时中生存样式。这种时中生存样式不唯是对孟荀天人观的综合创新,也是对儒道中和生存样式的超越、扬弃和综合创新,因为它既克服了老子“道法自然”所体现的柔弱无为性,又在继承弘扬孔子中庸及其具有的“强哉矫”的刚强有为性基础上,克服了孔子中庸哲学不及“天道性命”的局限,从而在一种更为广阔全面丰富健康的基础上构建出关于宇宙和人的哲学,而正是在这种关于宇宙的中和哲学和主体的时中哲学上,体现出中国古代哲人的最高智慧,显示着中华民族最高的生存智慧。
四、时中生存智慧论
《易传》的中和哲学体系,从以上所揭示的几方面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实质上阐扬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中和化生存智慧,这一中和化生存智慧在《易传》中主要由以下原理构成:
(一)《易传》阐扬了“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中和之道。这一中和之道是通贯天地人的宇宙之道,也即易道。这种作为宇宙根本规律的中和之道与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统一”的根本原则是相通的,因此,它是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8]它是古代朴素辩证法在先秦的最高体现。
(二)《易传》构建了“趣时”、“变通”、“日新”的时中生存样式。《易传》力倡“时中”主体哲学,这种“时中”的本质即是提倡主体必须有一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生命态度。“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文化创造、文明创新,这正是《易传》被称为“创造的形上学”的原因。这一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生存样式是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挑战与应战”的文明生成发展模式根本一致的。当汤因比高度赞扬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把中庸视为“挑战与应战”的根本原则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惊叹《易传》时中生存智慧性。这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时中”生存与保守性、奴隶性、闭锁性、内省性、平庸性本质不相容。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品格和开拓创新的特性。
(三)《易传》塑造了乾坤中和的民族精神。《易传》阴阳中和的“易道”集中体现于天地阴阳基本形态的乾坤卦德中。在《易传》作者看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坤主宰着世界万物的产生变化发展,因此,天地“生生”之德本质是由乾坤赋予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元以“自强不息”而“大生”,坤元以“厚德载物”而“广生”。其“大生”“广生”的性品本质上就是中和之德。天乾“自强不息”的“大生”品格正是一种时中精神,地坤“厚德载物”的“广生”品格正是一种“太和”特性。“时中”的变通日新,体现的正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大生”精神。“太和”的万物和合,体现的正是一种并行不悖、物物不遗、命命兼育的“广生”精神。而乾坤中和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相统一就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张岱年先生和其余一大批学者多年来致力于弘扬这一民族精神。乾坤精神即是中和精神,因此,中和是中华之魂。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绵绵不绝、博厚广大、物物化育的广大生命力正源自于中和精神。《易传》塑造出了中和这一民族不朽精神,这当是它的不朽杰作。《易传》在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地位根本上正在于此。
·韦伯在其著名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比较了“清教与儒教的对立”:“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而清教的任务则在通过理性改造此世。……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9]这里韦伯把“儒教”的儒家学说的主旨揭为“适应此世”,是准确深刻的,但他把这种适应仅仅看成是道德上的“自我控制”、“自我完善”的“君子”式消极性“适应”,是欠全面的,起码先秦儒家的中和哲学总体上所透射的是一种“强哉矫”的品格。而《易传》的时中哲学则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适应现世”的方式原则,是主动性适应和创造性顺应。这种主动性适应和创造性顺应,包含着“理性改造此世”的所谓“新教理性主义”特质。这样,我们从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看到了儒家中和哲学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实践的相容协同关系。
参考文献:
[1]惠栋.易汉学[m].四库全书本.
[2]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1985.
[3]程颐.伊川易传[m].四库全书本.
[4] 易传[m].
[5] 成中英.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化[m].:出版社,1988. 237.
[6]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易杰雄.坚持“真”与“善”的统一,重构现代东方哲学[j].现代传播,1997,(2)
[8]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3.340.
[9]·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出版社,1985.269,277.
第二篇 《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探论——兼论儒、道、《易》的语言哲学思想之异同_国学论文
摘要: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关键词:易传;儒家;道家;语言哲学
a stud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yi zhuan:
simultaneousl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 daoi and yi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primary ysis on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yi zhuan, confuciani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s thoughts, and daoi represented by lao zi and zhuang zi's thoughts, and make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the pre-qin period philosophy, to study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som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period had examined. this paper supplies some inspiration for us to intro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yi zhuan; confuciani; daoi; linguistic philosophy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初期大量地引进西方学术理念、语汇之后,中国学术的失语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WwW.meiword.COM然而,只到当前,我们对这种失语状态才有了真正思想的自觉。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再思索,是学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民族学术形态进行再思考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哲学,这一完全移植过来的新学科,已经解构了传统的经学、义理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解构,传统学术在新的话语形式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中西古今”的对话中,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获得了中国自己的形式。因此,我认为,现在谈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了——即使从20世纪算起,我们不能无视这近一百年所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肯认这种新的学科的身份?我个人认为,寻找当代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系统,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也将是治疗当代中国哲学界学术失语症的一种尝试。语言虽不是思想表达的唯一方式,然而哲学的思考与表达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哲学。从思想的建构与表达的角度说,哲学就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构,或者说哲学就是借助语言的媒介建构自身。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促使很多学者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使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之一,而且对形而上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解构。早期的海德格尔曾经夸张地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可见哲学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我在这里借用的“语言哲学”一词来《易传》中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思想,目的是想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视野来考察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的自觉程度,为寻找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提供一种思想史的借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高度地肯定了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清理工作,称他在打扫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牛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第7—8页。“路德不但打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的德国散文,……”出版社,1971年版。)。18世纪的中国汉学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问题亦有相当清醒的理论自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命题:“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在对宋明理学的具体命题进行批评之时,还专门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形式化,对“谓之”与“之谓”两种主谓句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差别进行了精辟的,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汉语语法形式化之先河。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亦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与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语言学运动。然而,20世纪前七十年,由于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关注于对西方先进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学习,来不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更无暇顾及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了,因而也就不可能认真地省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语言哲学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关注语言的问题了。然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对自己民族哲学的语言学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这里还来不及研究先秦名辩学家的语言哲学观。先秦名辩学家往往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思考语言问题,值得认真探究。〗,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二、《易传》语言哲学的五个方面内容
在先秦诸子的语言哲学中,儒道两家的语言哲学观最有代表性。道家对语言的达意功能基本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坚持认为“言不尽意”。我将之称为反省的、消极的语言功能主义观。儒家对语言的态度要复杂些,一方面,他们对言与实不符、言不尽意的现象有所知觉,如孔子一再强调言行一致。孟子讲“尽信书者,不如无书”。而且对艺术式的夸张语言与历史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记事语言的不同有所分别。另一方面,他们对经过认真修辞过的语言的达意功能是有信心的,故尔追求富有文彩的语言。如孔子讲“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言下之意是说,具有文彩的语言可以流播远方。故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矣”。在这两大语言哲学传统之中,《易传》的语言哲学具有调和论的色彩。一方面,《易传》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到了“言不尽意”的一面;另一方面,《易传》的作者又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而是力求通过“立象以尽意”的积极方式来弥补语言在达意过程中的不足,从而体现了《易传》作者积极而又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与道家一方面否定语言的价值,同时又利用语言的功能的矛盾语言观,非常的不同。从思想的整体倾向看,《易传》作者的语言观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1.“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传》对语言特殊功能的认识
在《易传》的作者看来,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四道”中之一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而且,“圣人之情见乎辞。”故语言既是圣人管理天下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圣人表达自己情意,让天下人了解其情意的媒介之一。“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无非就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正辞与理财具有平行的关系,可见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了。合而言之,“理财正辞”为积极的原则,“禁民为非”属于消极的原则。既然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君子“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系辞上》)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易传》的作者看到语言的重要现实作用,故对语言的整体特征,不同性质的言语、作用及其运用方式,都有较明确的认识。
《易传》作者从两种达意工具——语言与形象的不同功能的比较视角,对语言的独特性质进行了界定:即语言是圣人阐明吉凶的工具。如《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辨吉凶者存乎辞。”所以,“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此处的“玩”乃玩味之意,即通过反复地揣摸语言所蕴含的意义而判断未来的事情是吉还是凶。故语言的作用在于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状态。这里既含有追求新知的意思,又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知识,而关系到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考虑。
何谓辞呢?“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辞上》)这即是说,语言中的辞汇是有其所指的对象的。故名与实总是相应的。此处的“实”当然不一定是客观实在之实,有可能是一种观念性的“实”。因为,不同的辞总是各指其所要表达的对象,而这种对象不一定就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圣人治天下,一方面“观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另一方面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因此,圣人通过形象的方式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模拟,通过言辞的、判断来揭示形象中所蕴含的意义,从而在汇通的理解中把握天下的变化规则。由此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辞所表达的对象不一定是客观的实在。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只有象与辞的相互配合才足以完整地把握天下的变化之道。因此,言辞(声音与文字组成的狭义的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而且负载了分辨吉凶的预测功能。这与道家消极的语言观是十分不同的。
2.《易传》对语用与语境问题之思考
《易传》作者对语言的独特功能有比较辩证的认识。从整体上说,语言能够使天下之人运动起来。如《易传》的作者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天下的深奥意蕴存在于卦象之中,然而使天下之人行动起来的诱发动力存在于语言之中,故语言就是一种权力。
分而言之,善言有善的后果,恶言有恶的后果,故《系辞》的作者对不同性质语言的社会功能有敏锐的知觉。如《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易传》作者在此处所持的言行观,几乎与孔子思想如出一辙。
《易传》的作者特别告诫人们要重视语言的负面作用。尤其在生活中,语言更应谨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系辞上》)这样,对语境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易传》作者语言哲学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应该在什么情况去劝说百姓才有效呢?《系辞上》的作者认为,“易其心而后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不与也;惧以语,不应也。无交而求,不与也。”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感动了百姓之心后,然后才用语言去劝说天下人。语言的鼓动作用依赖于有效的行动。正因为言与行皆是君子感动天下的工具,故言行皆要谨慎。既要谨慎其所言之内容,又要谨慎其所言之时间,后者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
3.《易传》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的认识及其弥补措施
《系辞》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历史著作与圣人之意二者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的。如《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其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此处所谓“书不尽言”,即是指历史著作之类的书面语言不能尽达圣人之意。然而圣人可以通过立象的方式以尽自己之意,而且,圣人常常以卦爻的变动来曲尽人间的情伪。故我们对圣人精神的理解可以分成三个层次:1)通过《周易》中的卦爻辞——圣人之言来理解圣人已经明白说出的意思;2)通过卦象来理解圣人虽已表达,但却是蕴含不露的精神;3)通过卦爻的变动来理解天地人间的变化不居之特性。因此,我们对往古圣贤含而未发之意的理解就必需越过现成语言的障碍,在卦象和卦爻变动的过程之中来体会圣人之意。
所以,《易传》作者对《易》本身言辞达意的局限性,甚至卦象表意的局限性是有所知觉的。他要人们理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说,《周易》中的所有言语都只是进入易理的第一级台阶:“初率其辞,而揆其方。”不能局限于此台阶忘记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义。“既有典常”之后,还要人的实践,尤其是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本来面目有智的直觉与透解。既利用语言又超越语言的局限。因此,对“《易》理”的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然而,《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要人们抛却名言。这是《易传》作者语言观的可贵之处。
4.修辞立其诚——语言与德性之关系
语言的功能与德行的功能相当地不同。德行是通过感化而实现其作用的。如《系辞上》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而,人的德性与语言不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从本源上说,人的德性是来自于天道的,如《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人又是如何使天道之善性在人性中展现出来呢?这便需要通过语言。如《文言》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在儒家,特别是思孟学派的思想家看来,诚乃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君子之德是通过对天道的效法而获得的。而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先于人的本然存在的“诚”,是通过日常语言中的诚信,日常行为之慎和“修辞”等手段而获得的。“修辞立其诚”之“立”是建立的意思,也即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讲的“建构”。修辞也不是一般地修饰言辞,而是通过对经典语言的反复吟诵,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的反复体味才能在人性中建构起类似天道之诚。故通过修辞所立之“诚”乃是一种理性的德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的体验。因此,语言在道德本体的构成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言》肯定君子成德的过程是“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故语言在成德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这与道家否定语言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价值的观点十分的不同,甚至与孔子在讨论德与言的关系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孔子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甚至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易传》作者肯定语言在建构人的道德理性的作用,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德言观是相当的不同。
5.《易传》语言哲学的反思性特征及其它
《系辞》作者对书面语言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周易》一书的自身特点亦有所知觉。故其语言哲学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从书面语言的形成历史来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面语言是从粗糙的符号演变而来的,语言的出现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此,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易传》作者基本上持一种历史理性的观点。从《周易》一书自身语言的特点来看,《易》之为书主要是“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故其语言的特征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此,隐喻与象征,构成了《周易》语言的突出特征。这就告诉我们,对《周易》一书的理解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充分发挥联想功能,透解其语言背后的深刻意蕴。再者,从《易》一书的自身形成历史来看,它是殷末周初之际,故其言辞中充满了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
另外,《系辞下》的作者对语言与人心的实际状态的对应关系有所认识:“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一语言与指称对象之间直接对应关系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失之简单的缺点,但也至少看出言语与人的内在德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了境遇语言学的问题,从而展示了古代中国哲人对言语与所言对象关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儒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孔子的正名思想,可以看作是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这表明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一开始就具有“循名责实”的唯符号论色彩。他强调的是规范的第一性和至上性。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即是礼制度下的各种礼目之名与人的行为要一致。只有当人的行为与语言表达的规范内容一致时,人的语言,包括发布政令才能具有逻辑上与实际上的合理性,“顺”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因而也是合逻辑的。如果语言不合理,不合法,不合逻辑,则就无法将一件事干好。“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所以,语言(政令)的合理性、合法性、合逻辑性是人们成就事情的必要条件。语言因此而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老子“尚朴”,而孔子“尚文”。故在讨论君子人格形象时,孔子非常强调“文”的重要。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而“文”自身就有“质”的意义。“文”虽然不能等同于“言”,然“文”之中包括言之文。孔子曾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又说, “不学诗,无以言。”可见,从达意的完美性角度看,孔子还是非常看重具有审美意义的言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孔子在讨论言与德、言与行的关系时,比较看轻言的作用而重视德的意义 。如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并以“天”为例,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因此,在言与德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重视德与行而不重视言。他坚决反对言不掩行的行为,主张言行一致。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因此,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孔子更重视道德本质的优先意义,重视道德行为的第一性。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说孔子轻视语言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只有比较意义上孰轻孰重的问题。孔子也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之谓之瞽。”(《季氏》)故与君子相处应该注意自己说话的时机,要求做到时中。这样言之时机恰当与否就反映了一个人德行的高低。
在儒家思想传统内,孟子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对历史著作的语言与其所描述的历史存在的统一性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其次,他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达意方式有一定的知觉,如他将君子之言与民间之言、诗之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表意特点作了简单的区分。“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戚。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因为按照《尚书·尧典》记载,尧老而舜摄位,二之后尧死,舜守孝三年后才即位。这样,民间传说与官方历史记载的正式语言就相当的不同。
又,咸丘蒙举《诗经》《小雅·北山》中的几句诗,以说明王权与孝道的矛盾。“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的回答是:“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因此,对于诗歌语言的夸张特征与日常叙事语言的陈述特征的不同应该有所知觉,不以辞害志,超越语言的表层意思而透解其深层的含义。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特别区分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不同,主张通过深层语法的转换把语句中蕴含的意思揭示出来。孟子所讲的“不以辞害志”虽未有如此明晰的语言学的思想,然而毕竟看出了诗歌语言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思的不同,可见中国哲人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表意特性有一定程度的自觉。
孟子还看到语言对人心的影响,故从社会的角度提出了“拒诐行,放淫辞”的主张。后来人们往往以此来批评孟子的霸气。其实,思想的批评如果不借助的力量永远也不可能做到思想的统一。孟子曾自豪地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此,对语言的自觉可以看作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荀子的正名理论是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发展而来的,然而在形式逻辑方面发展了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首先,他对已经有的“名”进行分类:“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正名》)刑名,即刑法系统的名称,爵名即爵位之名,文名即礼节仪式之名,散名即在刑、爵、礼之外的一切日常生活系统中的各种称谓。对于不同系统的名称的来源,荀子从历史学的角度给予了。特别是对散名的形成原因的很有见地。他认为,语言中很多的意义指谓乃是来自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而人们正是在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里进行意义的交流。而且散名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之后,就会成为“后王之成名”。故官方语言系统中的众多概念其实来自于民间。
荀子又从逻辑学的层面,将“名”分为“大共名”和“大别名”两大类。他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这一思想对于人们进行更有逻辑的思考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荀子又提出了实名和善名之分。这涉及到名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评价名的标准等问题。荀子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这即是说,在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从。最好的“名”是能平易地、直接地被理解的名。
荀子又将名实之间的混乱分成三种:一为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二为惑于用实以乱名;三为惑于用名以乱实。像“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之类,则属于用名以乱名之类。在荀子看来,侮即辱之类,圣人为人之类,盗亦人。不能因为名之异而将他们看作不同类。像“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锺不加乐”之类则属于“以实乱名”之类;山渊本来不平,仅从人观察角度的相对性角度看,可以平。然而,作为形式逻辑中的“平”的概念是有特定内容的。故本来不平之山渊来论述“平”,其实是用实际上的不平来破坏“平”这一概念的正常意义。像“牛马非马”之类便是以名乱实,因为人尽管可以创造“牛马”之名,然而并不存在“牛马”之物,故从“牛马”之名的角度论证“牛马非马”的问题,便是以名乱实。荀子通过对先秦名辩学派的“名实观”的批评,将先秦语言哲学中的“名实关系”中的错误现象概括为如上三类,从而力图在语言哲学层面对孔子、孟子的正名思想作出总结。
与孔子基本价值取向一致,荀子非常关怀现实。这样,他对语言的权力非常敏感。他认为,只有王者才有制名的权力。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正名》)而且,他将“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看作是“圣王没”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语言创造的权力不能归于一般的士人,而应该由王者来统一。他认为,以理性的语言论述方式可以达到上的大治,在圣王没、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主张通过喻、期、说、辨的四种方式来使天下归于一道。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正名》)他甚至将那些“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之人称之为“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正名》)这样,人们就“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而能“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因此,荀子语言哲学中虽然包含了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但已经隐含了思想专制的萌芽。
应该说,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狭隘的功能主义观点。他认为:“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正名》)当语言“志义之使”的任务已经完成,则不必过分地纠缠于言辞之上。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荀子的思想含有一定的科学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其语言哲学中则表现为一种古典科学的实证思想。他反对言而无证,认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性恶》)并从此实证的角度出发,批评孟子所言的“性善”属于“无辨合符验”之言,故不足信。
在言与知的问题上,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从杂多中把握真知:“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类统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性恶》)这是他的宗圣观在语言哲学中的表达。
要而言之,荀子大大丰富了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名的不同层次作了区别,使古典的语言哲学与古典的形式逻辑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四、道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道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其对人类文明局限性的揭露,故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亦是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论述。在言与意,言与行等问题上,对语言的价值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通行本《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而庄子及其后学基本上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如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其后学者亦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由于语言不能把握本体、本质,亦不能深刻地达意,故庄子学派对语言采取了一种非常轻视的工具主义态度:“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这种工具主义态度的语言观在表面上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不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语言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在言与行的问题上,老子比孔子有更为激烈的主张,要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且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四十三章》)庄子的后学者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
尽管如此,道家学派人物对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还是有所论述的,如老子说:“言善信”。(第八章)又说“言有宗,事有君。”(七十章)“正言若反。”(第八十章)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日常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崇尚诚信,要言之有物,要言行一致。而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要有宗旨而不能漫无边际。有些时候,我们对语言中所蕴含的意义要从反向去理解。这些思想有的被后来的庄子及其学派的学者所发扬,有的则有所颠覆。由于庄子及其后学生活的年代是战国中后期,世道之混乱更甚于老子时代,故《庄子·天下》篇在论述《庄子》一书的风格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由于世道人心的畸变,故在发为言说之时亦只能采取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思想。充分地发挥了老子“正言若反”的思想。庄子《寓言》篇,《天下》篇都反复阐述了《庄子》一书的语言特征,如《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以和天倪。”又解释说:“寓言者,籍外论之。” 《天下》篇云:“以重言为真”因此,庄子语言学中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内容,他对人的心理与语言的风格有较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道家在人情方面所表现的练达之处。
庄子及其后学对老子所言的“言有宗”和“言不及道”的思想似有所颠覆。他们认为,任何语言的主旨只具有相对性。只有道是绝对的全。如《齐物论》云:“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鸲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又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任何语言皆有所待,都不是对本体之道的把握。唯有不言之道才是绝对的。故言的意义都是相对的。而庄子的后学则认为(原著中托为季真、接子之言),在终极实在的“道”面前,言与不言——默,均不足以载道。语言之根本,乃是“或使莫为”之“道”。如果“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日终言而尽物。”(《则阳》)依郭象注,“言而足”即是“求道于言意之表则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像庄子本人以寓言、卮言、重言等方式来言说,则可以尽道。如果不能这样则只能停留于物之表象层次。这样庄子的后学就化解了老子哲学中言与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避免他人对自己学派否定语言价值的哲学语言观的批评。〖zw(〗此点受傅伟勋先生观点的启示。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一书第390—392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庄子以一种怀疑论的口吻说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今我则已有谓也,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齐物论》)人们对自己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意义,从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所以庄子的后学者们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
《则阳》篇的作者说:“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对于本质世界而言,往往是 “言而愈疏。”(《则阳》)有时人还处在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下,就像《则阳》篇的一位隐士:“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 因此,《大宗师》云:“古之真人,……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无论是忘言,还是不言,其实与道家尚朴的思想紧密相关的。如老子尚质朴,他虽然也说“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六十二章 )但他基本上是反对美言的,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而“尚朴”的理论根据在于“遵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再者,“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因此,在遵道的前提下,言是没有自己地位的。这与《易传》作者强调“修辞立其诚”的观点十分的不同。
结 束 语
综上所论,我认为,《易传》作者的语言哲学思想更能体现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他们对语言的局限有所认识,但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特别是《文言》对语言在建构道德过程中的价值的论述,是超越儒道二家的言行、言德关系论的,体现了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性品格。后期道家学者对言与道之间关系的认识似亦有所改变。这似乎表明先秦语言哲学经过战国中期名辩学思潮的洗礼,对言与意的关系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言可以达意。但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达意的方问题上,认识又并不一致。荀子主张通过喻、期、说、辩的论理方式和“王者制名”的权力,使言与意和人们的认识达到统一。庄子及其后学则主张以艺术的方式达意。这些思想似都可以看作是对《易传》语言哲学思想的一种回应。然而,由于《易传》一书中各篇的写作年代一时难有定论,故对先秦语言哲学的发展脉络的疏理一时还有难度。但我们能否通过思想发展的逻辑来考察《易传》中某些篇章的写作年代呢?我认为这至少是一条可能的道路。
第三篇 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_国学论文
摘要: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关键词:焦循; 易学; 易图略; 方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ethodology of jiao xun's yi learning<?xml:namespace prefix = o />
abstract: by the diagrams such as pang tong (laterally linked hexagrams), dang wei shi dao (matching positions but losing dao),xiang cuo (interchanging hexagrams) and proportion illustrated in his yi tu lüe, jiao xun founded a logical ogous inferring image-number structure and fused his moral ideal into it, having established not only the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ies of the yi learning but also a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depended mainly on the theory of pang tong. it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s shown as that it runs out of the old trail of interpreting yi wi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r images & numbers, marking an important diversion of the studies of the yi learning in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1). yet, its negative influences are shown as that it mixed the independence between the image-number system and that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yi learning, philosophical values of the yi learning being replaced by the tool value of logical ogy of it.
key words: jiao xun; yi learning; yi tu lüe; methodology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黄珏)人。Www.meiword.com清代乾嘉之际著名易学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曾引起当时学界的振动,被推崇为“石破天惊”之作。焦循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与其所运用的独特哲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拟就焦循易学研究中所凸显出的哲学方思想作一探讨,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一
焦循的易学研究,被乾嘉学者誉为“非汉,非晋唐,非宋,发千古未发蕴”,这不仅意味着焦循易学不囿于象数与义理而独树一帜,而且还包含着他通释易学在哲学意义上的重要建树。其所著《易图略》八卷,首列“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阐明六十四卦爻位运动和卦象转型的一般规律。所谓旁通,其主要内涵有三:一、必须是爻辞阴阳两两相对之卦。二、阴阳两两相对之卦间的转换,必须依次序进行。三、旁通的目的是使各爻辞各正其位。焦循运用“旁通”法则研究《周易》,是进一步发展了《周易》中阴阳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原则,并将这个原则贯彻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在充分肯定每卦每爻都有其对立面的同时,揭示了在一个旁通卦组十二爻中,由显现的六爻推导出必然隐伏着与此六爻互相依存的彼六爻。用旁通法则研究《周易》,意味着焦循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事物,把事物互相转化关系扩大为普遍法则。其优点在于不是将卦爻看成一层不变的静态孤立物,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加以系统研究。
焦循以“旁通”揭示卦爻之间的相互联系,目的是从卦爻阴阳对立与推演中阐明《易传》关于“情”的意蕴。他说:“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所谓“旁通情”,焦循在《使无讼解》一文中作了重点诠释:“格物者,旁通情也。情与情相通,则自不争,所以无讼者,在此而已。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格物为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本,故两言此谓知本。……情通于家则家齐,情通于国则国治,情通于天下则天下归仁,而天下平。”[1](卷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如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颜渊》)而提倡刑措。焦循将情通与无讼联系起来,一方面固然出自“孔子叹才难,孟子道性善,皆本乎此”的“羲、文、孔、孟之传者”,另一方面又认为旁通之情为格物之要。所谓“格物”,是亦即《大学》中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之一,因此,焦循将“格物”解释为旁通之情,正表明人人情与情通,则修齐治平便可一以贯之。
易学中的“当位”和“失道”,本指每一卦六个爻画所居爻位而言,它也是历来易学家作为观测卦爻象依据的传统方法。《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均由阴阳两种不同符号组合而成。在焦循看来,《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爻位运动,始终伴随着当位与失道而展开的。即每一组阴阳爻画相对的旁通卦先由二五爻位进行置换,然后再进行初四爻位和三上爻位置换,按照这样的次序进行爻位转换便是当位,反之则为失道。利用当位失道,致使卦爻位置换、转换运动规律化,是焦循发展了《周易》有关爻位相应的理论。对此牟宗三先生曾以“生生条理”作为判断当位与失道的依据,并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指出:当位失道间不容发,只看其动是否能先二五,及是否能终而有始。此两条件皆尽,则为元亨利贞而吉,反之即为失道而凶。先二五者,立其元,开其机,而有序有理也。终而有始者,生生不息之谓也。唯有序有理之动始能生生不息,生生不息正所以显序理之动也。生生条理,即是旁通情也,即是以情系情,即是情欲之谐和,即是保合太和,即是忠恕一贯之道。[3]其实这也正是焦循通过当位与失道来阐发他的社会思想的。他认为当位与失道是体现圣人的明教复道,而明教复道的目的在于“后顺得常”,即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爻画的阴阳迭用足使道保持永恒。即所谓“一阴一阳,迭用柔刚,则治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以治言,不以乱言也,失道乃乱也。圣人治天下,欲其长治而不乱,故设卦系辞以垂万世,岂曰治必有乱乎!”[4](卷上《阴阳治乱辨》)由此可见,当位与失道作为旁通法则的补充,一方面是他恪守“忠恕之道”在易学的反映,一方面则是他创立“时行”法则,通释《周易》全经的主要步骤。
与历史上的易学家一样,焦循《易图略》也重视“时”的观念,提出“时行”说。“时行”一词,渊源于《彖传》对《大有》卦基本意义的诠释。据宋代学者项安世认为,《大有》的上下卦分别为《离》与《乾》,“六五”爻位居天位得卦之中,上下五阳皆与之应,故曰“应乎天而时行”。焦循创立的“时行”,则是在旁通卦组的基础上,通过当位与失道的爻位,使卦爻按照元、亨、利、贞周而复始的不断转换运动。焦循认为时行的目的在于六十四卦经过爻位转换避免出现两个重复的《既济》卦。对此,焦循亦称之为“大中上下应”。所谓“大中”,一般是指每卦中的“六二”爻辞和“九五”爻辞。自汉代以来,论《易》者都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都有上下二个单位组成(或称内外两卦),由于“九五”和“六二”两爻分别居于上卦与下卦之中,所以又有“居中”、“得中”等称谓。凡能“大中上下应”的卦为“元亨”,象征着“吉”。当然,六十四卦并非一定遵循“大中上下应”的原则,它通过其他途径也能进行卦爻元亨利贞的循环。焦循“时行”法则的特点,在于他不再囿于传统易学致力于一卦一爻左支右诎的论述,而是将六十四卦作为一个必然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以“时行”来揭示卦爻间的联系,是在旁通、当位与失道的基础上深化了的卦爻位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他不仅发展了《易传》中“时”的观念,而且焦循藉此易学趋时求变的规律,进一步阐发他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理解。
众所周知,《周易》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备受历代学者的重视。尤其是《易传》所宣扬的“先王之道”、“四圣之言”一直被古代学者认定为绝对真理,然而它的“时”的观念却与儒家绝对真理的世界观相抵牾,从而也表现出对它的某种程度的抑制。历史上的许多有志于改革的思想家、家也都从《易传》“时”的观念中受到不小的启迪,并以此建立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北宋学者李觏倡议改革,提出“彼礼乐损益盖以时之宜”,强调“因时立事”。王安石依托《易传》“四时往来,消息盈虚,与时偕行”作为他的变法理论根据。近代变法维新的首创者康有为主张“随时立宪”、“是非随时”作为打击保守派的武器。明乎此,才能理解焦循为什么说“时之为变通,不烦言而决矣”的真正含义,虽然焦循终究未能突破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
“相错”和“比例”是焦循《易图略》创立的又一个重要法则。“相错”一词,源出于《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六十四卦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相错。 《说卦传》关于六十四卦的组合理论,一直为汉代以后的易学研究者所服膺。明代学者来知德曾以《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而提出“错综”说。来知德认为,伏羲之卦主于错,文王之卦主于综。认为“天地造化之理,独阴独阳不能生成,故有刚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本错。八卦即相错,象即寓于其中。”他指出伏羲圆图的卦序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从《坤》向左至《诟》的卦,与从《乾》向右至《复》的卦是相错的。同时来知德还将六十四卦的三十二对相错卦分为四组,每组八对相错卦之间的变化也有一定的规律。来知德以“错综”为特征而自成一说的易学研究,曾被当时推为绝学。焦循也研究过来氏易说,认为:“来知德造为错综之名,诩为独得之见,其智出唐氏下矣。”[5](卷三)焦循所说的“唐氏”,即指明代学者唐鹤徵,著有《周易象义》,主张象数与义理并重,彖与爻合,以象明理。然而焦循的所谓“相错”,则以六十四卦中的三十二组旁通卦为依据,进行卦与卦之间的转换。焦循为了弥补旁通卦本身取象的局限,利用两卦相错,从纵、横两个方面通释全《易》,进一步论证“相错”的合理性,焦循又在相错卦的基础上确立了卦爻之间等值关系的“比例”法则。
“比例”是焦循在“相错”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卦爻之间的等值关系的法则。他自誉“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1](卷八《周易假借论》)作为焦循《易》学的构架,“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都是焦循为揭示《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无不通”的种种关联所拟制的,正如焦循在《易图略》中所说的:“余求之十余年,既参伍错综以求其通而撰《通释》,又纵之横之以求其通而撰《章句》。非敢谓前人之说皆不合而余之说独合,第以求通圣人之经宜如此。”
英国哲学家怀海特曾说:“建立哲学的正确方法是构成一套思想的框架,然后坚定不移地探求用那套框架来解释经验。”焦循正是用了这种方法,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易学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
二
焦循易学方的确立,从易学史的角度而言,主要是迎接来自象数与义理两方面的挑战。乾嘉之际,考据之风大盛,以卦变、爻变为特征的象数易学,再度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如惠栋不遗余力的搜辑汉代易说,张惠言对虞翻易学的孜孜探求。对此,焦循首先提出质疑。他在《易图略·论卦变》一文中指出:“说《易》者必沾沾于卦变反对者,何也?以《彖传》有往来、上下、进退之故也。荀、虞以来,大抵皆据以为说。传文不可以强通,故不能画一耳。”又说:“《易》者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故每一卦必推其有过无过,又推其能改能变,非谓某卦自某卦,某卦自某卦来也。 荀、虞有之卦之说,唐宋以后,遂以为卦变各立一例,左支右拙,愈失圣人作《易》赞《易》之本意。”所谓“卦变”,即指《周易》六十四卦,无论一爻变化或数爻变化(阴爻转变为阳爻)均可能呈现出另一种卦象。它作为《周易》占筮的基本内容,使人们能够在总体上把握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的序列,“卦变”就是通过这一序列中筮取某一特定的卦辞。西汉焦赣《易林》曾以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共得四千零九十六卦爻,构成了以蓍筮为主体的卦变系统。此后,京房、荀爽、虞翻等都程度不同地继承和发展了占筮卦变的传统。焦循曾以“用《易林》之法”、“京房世应说”予以批评,并指出其自身具有五种不同的内在矛盾。
在汉代易学象数系统中,虞翻的《易》说保存最多,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曾广为收录。清代《易》学研究者崇尚汉学,十分推崇虞翻,形成了所谓的“虞氏学”。对此,焦循批评为“支左而诎右”。并决定就荀、虞《易》学进行一番去伪存真,从而提出了他的“当位”、“失道”理论和操作程序。焦循指出:“余既为当位失道等图,以明其所之之吉凶悔吝,此即为荀、虞之卦之所本。去其伪,存其真,惜不能起荀、虞而告之耳。倘殁后有知,当与之畅谈于地下也。”[6] (《当位失道图叙目》)因此,焦循的“失道 ”、“当位”,实际上可视为是对汉易卦变系统的修正而提出的。不过,焦循所继承的仍是虞翻《易》说所创立的“之正”说。“之”,犹言“变”;“正”即表示阴爻居阴位(偶位),阳爻居阳位(奇位),它同样是虞翻倡导卦变的条例之一。也正因此,焦循尽管批评虞翻“有知其不可疆通,姑晦其辞貌为深曲,而究无义也”。但是,从上述焦循及复强调对诸卦不正诸爻进行“当位”、“失道”的爻位置换运动中可以看出,虽然操作程序有别于虞翻,但本质上仍是由虞翻“之正”的卦变条例中推衍而来。所以焦循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当位”和“失道”乃是对虞、荀《易》学的去伪存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态度,焦循进而对汉易的“卦气”、“纳甲”又作了一番纠谬辨伪的工作。
“卦气”和“纳甲”都系汉《易》术语,属象数范畴。卦气是《周易》解释一年的节气变化,将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配合。并以人为的阴阳消长序列模拟四季更迭,星移斗转的客观秩序,从而预测天道人事,这也正是汉代学者构建《周易》的象数模式。不过,焦循所言,“卦气”,专指“六日七分”。他说:“六日七分,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6](《论卦气六日七分》)所谓“六日七分”,首见于《易纬·稽览图》:“甲子卦气起中孚,六日八分之七。”郑玄解释为:“六以候也,八十分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我们知道,汉代孟喜、京房的《易》学体系,乃是以卦气为基础的,并阐发《易》卦与十二月气候相配合的原则,以用于占验阴阳灾异现象。古代历学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六十卦既主一年之期,则将日除以60,商数恰为6又80分之1日,这就是每卦相当于“六日七分”的由来。焦循对卦气六日七分与《周易》的关系作了本质上的区别,就《易纬》和象数牵强附会的一面进行了驳斥。这就不难看出焦循是不赞成“卦气”说的。所以他再次强调,“此卦气之序,非《易》之序。”[6](《论卦气六日七分》)
焦循既视“卦气”为术数家和道家的种种附会,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批评汉《易》象数系统的“纳甲”理论。所谓“纳甲”,一般是指汉代《易》学家把五行思想纳入八卦体系,构成《周易》神秘的思维模式。“纳甲”之法,始见于汉代京房《易传》,但在汉《易》象数系统中,虞翻的“纳甲”说颇具特色。他认为: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已离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尊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会。正是依据八卦与五行的组合。然而,以“纳甲”释《易》,纯属主观臆测,毫无科学根据。王夫之曾批评说:“自汉以后,皆以五位五十有五为五行生成之序者,舍八卦而别言五行,既与《易》相背离,其云天一生水而地六成,地二生水而天七成,……图无其理,《易》无其象。……虽不欲谓之邪说也,可乎?[7](卷十五)王引之认为:“纳甲见于魏伯阳《参同契》,为丹家附会之说,原非《易》之本义,而虞氏乃用之以注经,固其说之多谬也。”[8] (卷一)焦循也指出:“虞翻以两作为日月,是《离》百日,又为月矣。翻自知《离》不可为月,而谓《乾》五之《坤》二之《乾》成《离》,以为日月,尔作之说,盖支离矣。”[6](《论纳甲》)这里,不深论虞翻的“纳甲”是否为魏伯阳《参同契》的翻版,但焦循认为“卦气”、“纳甲”已游离了《周易》“弥补天地之道”的儒家精神而流入术数,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汉代易学象数体系的权威性。
同否定汉代易学的象数体系一样,焦循对以义理为特征的宋代易学也抱着鄙夷的态度,尤其是邵雍的“先天之学”。如邵雍在道士陈抟“先天图”的基础上建立了“先天象数学”,认为伏羲氏所绘图式,虽无卦文,但尽备天地万物之理。宣扬太极行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此类推产生了宇宙万物,一切事物的命运是先天决定了的。邵雍创立的“先天象数学”,在当时学界颇具影响。焦循在《易图略》中曾撰有《原卦》一文,驳斥了邵雍的所谓“高妙之说”。认为伏羲为“知识未开之民图画八卦以示之,而民即开悟,遂各尊用嫁娶以别男女,而知父子,人伦之道由此而生。乾坤生六子,六子其一父母,不可为夫妇,则必相错焉,此六十四卦所以重也。”[6] (《论卦气六日七分》)显然,焦循将《易》卦看成象征伦理关系的符号,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视《易》之道为“人伦之道”而加以研究的,从而也就否定了宋人的先天象数易学。
焦循的易学方,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
三
由于焦循的易学方是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的方法来阐发易理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另一极端,即对易学史上的象数与义理的都予以排斥,从而也暴露出自身许多缺陷。
首先,焦循的“旁通”法则,主观假说大于客观,其结果必然是使一些本来不具联系的卦爻反而形成了必然联系的卦爻,本来极易理解的卦象反而显得繁杂与模糊不清。如朱骏声认为焦循“以《九章》之正负,比例为《易》意,以六书之假借,转注为《易》词。其其间不无心得,而附会难通者十居八、九。”[9](卷二《书焦孝廉循易图略后》)李慈铭也指责焦循的易学是“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10] (第126页)焦循的易学,虽然别具一格,但是本质上仍属象数一派。他按照《周易》六十四卦的序列,将各卦爻组编成合乎逻辑的爻位置换运动,从而判断爻位象的吉凶祸福,使之图式化了的“当位”、“失道”、“时行”与他所批评的“卦气”、“纳甲”,从根本上说仍是汉易象数体系中卦变系统的修正。如焦循对卦爻位各象的,始终未能够翻出汉代易学家以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以及注重第五爻象所的旧窠,这恰恰正是汉代易学的特征。换言之,焦循的易学研究,并没有彻底摆脱汉代以来易学研究传注形式的羁绊,而是对汉代易学的继承和发展。熊十力曾说:“焦氏实宗汉《易》,虽不必以求数家之说法作根据,而其方法确是汉《易》。汉《易》之方法,只向卦与卦,爻与爻之间,去作活计,自然不会探及理道。”[11](卷上《原学统》第二)熊氏此言,正表明焦循的易学研究终究未能走出汉易。
其次,焦循虽批评宋人的图书易学“高妙之说”,但他曾说:“弱冠以前,第执赵宋人说,二十岁从事于王弼、韩康伯旧注,二十五岁后,进而求诸汉魏,研究于郑、马、荀、虞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屏众说,一空已见,专以《十翼》当上下两经,思其参互融合……。”[6] (《原卦一》)这说明他易学研究一开始便是从宋易入手的,宋易曾对他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现保存在《雕菰楼经学丛书》原稿本中列有“五乘方图”一篇,即以算图的形式来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此图虽然后来最终未被焦循列入正式出版的《易学三书》中,但它也证明,在焦循研究易学的过程中,宋易确也曾打动过他的心玄。至于焦循出自何种动机而最终摒弃不用,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考虑到清代乾嘉时期的易界,恢复汉易是其旗帜,而焦循此图,不免会引起人们对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的回忆和比较。诚如焦循所说:“邵子之说,在同时伊川程子已疑之不用。近时通人破之不遗余力。黄中深思苦虑以攻康节。南宋说经诸家实为杰出,惜其未能融贯全经耳。”[5](卷二)正是迫于学界批评宋易的压力,才使焦循毅然将此图舍去。 当然,焦循此图与宋人的图书易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易图略》对易学内在逻辑关系的揭示,与宋人的图书易学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宋人图书易学是以主观理解与体悟来阐发易理的,这虽然要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但它并不并不以学术为前提条件,换言之,宋易系统并不以知识来维持其有效性。焦循则不然,他试图以算图取代乃至宋人的图书易学,这也是不可取的。平心而论,宋人的图书易学虽有别于汉代的象数易学,但它重主观体证,追求“有我之境”,也使易学经典成为开放的文本,为读者提供了无穷的诠释空间,因此在中国易学史上仍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肯定。然而焦循的哲学方,将对易学意义的探求严格限定在“旁通”、“时行”、“相错”诸法的框架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性。
再次,焦循《易图略》把《周易》象数体系视为一个比例形式,并以甲乙丙丁等符号来替代卦爻和计算。焦循虽然已经领悟到符号系统对于处理演绎方法的作用,但也决定了他必然把《周易》象数体系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由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有限数量,经过由大到小的不断割分,本来由阴阳两两爻可以显示无限多的图象因此被僵化成某种图式,导致了焦循必然采用类比推理的求《易》方法。
类比推理,它是数学中一种逻辑推理方法。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对象有一部份属性相似,推导出这两个对象的其他属性类似的一种推理方法。类比推理大致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根据目标系统的已知信息,寻找出一个与之相似的类比系统。确立起目标系统与类比系统之间的相似关系。二,将掌握类比系统的相似材料,经过适当而巧妙的变换,使之成为目标系统的相似材料。三,根据来自类比系统和目标系统的相似材料,进行逻辑地推断出被认作是关于目标系统的新知识。这样,整个类比推理的过程就随着目标系统上新信息的获得或做出关于目标系统的未知信息的推测而结束。三个阶段的顺序运行就构成了类比推理的动态结构。其实,类比推理方法,它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人的意图和着眼点。焦循《易图略》中的“旁通”、“相错”和“比例”,就是根据卦爻之间的种种关联,推求其其共性。它所依赖的是已有的知识体系,它与目标系统只具有相似关系。也正因为此,一旦知识系统被确定为类比系统时,就必然根据目标系统上所展示的已知信息对其进行重新整合,并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在这种整合和表达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使用任何手段不断地进行论证,其中不乏包含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和直觉颖悟,另一方面还需要有胆识的引伸以及绝妙纯熟的知识技巧与研究者本人灵活、开放的思维方式等等。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焦循的易学,在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汉《易》研究领域中,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例,但它所展现的哲学意义,却是中国易学哲学史上值得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焦循.雕菰集[m].文选楼全书[z].
[2]孔子.论语[m].十三经注疏[z].:中华书局,1980.
[3]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4]焦循.易话[m].焦氏丛书[z].
[5]焦循.易广记[m].焦氏丛书[z].
[6]焦循.易图略[m].焦氏丛书[z].
[7]王夫之.周易内传[m].船山全书[z].长沙:岳麓书社,1996.
[8]王念孙.经义述闻[m].清高邮王氏遗书本.
[9]朱骏声.传经室文集[m].求恕斋丛书[z].
[10]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中华书局,1963.
[11]熊十力.原儒[m].十力丛书[z].
第四篇 易道: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_国学论文
摘要:《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周易》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互动、通变致久理论,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哲学基础。
关键词:易道;文论;天人合一;阴阳;通变致久
the dao of yi: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orie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bstract: as a valuable culture-legacy, zhouyi has been influencing upon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theories about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interac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changing to attain permanence conceived in zhouyi constitute the main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dao of yi;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yin-yang; changing to attain permanence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着强烈的宗经意识,《周易》为群经之首,自然引起文论家的特别关注。wwW.meiword.com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1](第19页)叶燮在《与友人论文书》中也说:“《易》似专言乎理……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2]这样一来,《周易》便像“太山遍雨,河润千里”那样开启了后来的文体,成为论、说、辞、序等文体的渊源。同时,易道精神还为古代文论提供了哲学基础,成为文论家论述文章起源、总结创作规律、风格特点的理论依据。薛雪《一瓢诗话》有言:“《易》云:‘风行水上,涣。’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顿挫之中,尽抑扬反覆之义,行乎所当行,止乎所当止,一波一澜,各有自然之妙,不为法转,亦不为法缚。”[3](第117页)它的深层,是“易道”与文章构思的内在相通。这既是认识论上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古代宗经重道意识。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对古代文论的影响,首先不在它的个别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概念、范畴,而在于它“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确立,最初是企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内的问题作一总括 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具体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这些为文学理论所借鉴。文学理论尽管在《周易》中没有突出,但许多易理却成为文学理论的源头,需经过一番剔抉,才可以彰显面目。而后来的文学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也有意识地追溯文学的经学依据,以易道为其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
《周易》确立宇宙模式的首要前提是:天人合一,即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就是人类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律。《观卦·彖传》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4]这里的“神”并不是人格神、上帝,而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神道”指的是自然规律的微妙变化。“以神道设教”即是把人事的活动看作是遵循自然规律而来的东西,并以此教示天下。由“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 (《贲卦·彖传》),即由对自然规律观察而确立人事活动的规律,自然与人是合而为一的。
“天人合一”的模式,是易道精神之一,整部《周易》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4](《颐卦·彖传》);“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4](《恒卦·彖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周易·说卦》)。《周易》以自然比拟社会,用天道比拟人道。易道具有伟大的力量,人不仅从自然界得到物质供养时要顺应自然规律,而且道德精神与一切活动,都要同自然达到最高的统一: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4](《乾卦·文言》)
这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能简单理解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而更多的是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的合一。不论其中有多少简单的比附和神秘的幻想,重要的是,它朴素地认识到在精神领域中人与自然的交融统一。反过来说,一切出乎自然的必然性现象都被赋予了伦理道德的意义。这样,人对自然的遵循,就转化到对伦理道德的遵循。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最为直接而明确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文论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世界本体的认识问题。对“天”道的探索,才直接启发了后人对于文学本体的探索。《周易》的“天人合一”理论为文学本体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思维范式:文以道立,道因文传,文道相通,故称不朽。《文心雕龙·原道》篇由对宇宙本体的探索确立了文学本体论,正是基于对易道伟大力量的合理推衍。刘勰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文“肇自太极”,乃“与天地并生”,即体天道而来。天地具宇宙生命之道,化育万物之德,这是天地之大文,具体表现就是“垂天之象”、“理地之形”,进而“傍及万品,动植皆文”。而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自然必有其文,以契合“自然之道”,深通神明之德。故曰:“天文斯观,民胥以效”[1](第2页)。
《周易》的“神道设教”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以“天之神道”为本体,以“民之教化”为效用,显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特色。这与刘勰一方面要原道溯源,确立文章的本体渊源,另一方面又要载道设教,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思想完全相符。《原道》篇所说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惟微,神理设教”[1](第2页)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其次,“神道”乃抽象之本体,所谓“道心惟微”、“神道难摹”,其中精义只有圣人才能心领神会,圣人通过画卦设象,敷章摛文来阐微显幽,昭示天下,这样圣人就成了原道的中介。刘勰把伏牺、孔子等儒家圣人看成是联系“道心”与“文章”、“神理”与“教化”的中介,认为“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第2页),提出了“道—圣—文”三位一体的文学思想。这样,由天地而人,由自然之文而人文,刘勰把文章的起源与天地降生联系起来,为文章找到了本体的依据,建立了“自然之道”的文学本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文之元,肈自太极。”后世文论家继承这一观点,以此确立文章本体。太极者,一团浑元之气也。孔颖达《周易正义》释“太极”曰:“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5]叶燮《原诗》以气为本,用以总持和条贯理、事、情。他说:“然具是三者(理、事、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3](第21页)黄宗羲则更直截了当地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6](黄宗羲《谢翱年谱游录注序》)
“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还是古代文论中“物感说”的理论基础。中国文化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天人合一、物我相通。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绝对的自然,也没有绝对的主体,而是泯灭物我界限,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自然万物皆著人之色彩,人之身心也能应合天地自然。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物与人相通。《周易·系辞》曰: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天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
虽然这是对《易》象起源的说明,但对古代文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观物取象”的理论,启发了古代文论对“物感说”的探索。“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是物我相通、相感的结果。《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通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第493页)“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正是物我交融的境界,客体的物与主体的人在交融中充满了生香活意的生命情调。
《周易》中的“感物说”主要表现在对卦辞、爻辞的解释和说明中,最明显的是《观》、《咸》二卦。《观》卦,下坤上巽,“坤”为大地,“巽”可象征空中流动之风,亦可象征高高挺立于大地之上的树木,后一义更合远古情形,因为为了观察更多更远的事物,唯有攀上高枝方能远瞩。“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不但观物,而且观人,反观自己,亦审视他人,观察到外在的生存环境,乃感悟国家的状况和民众的情状。“观我生”,更是超越个人的生存环境而对现实人生的大观。这种“观”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不但观自然风景以及种种触兴起情的眼前物事,而且由物感人,洞悉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状况。文学家只有深观现实人生,才能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现实人生。故《观》之义很早就被引入文学领域。《左传·襄公二》记载了赵孟在郑伯垂陇之宴上请郑臣子展、伯有等七人赋诗,说:“武亦观七子之志。”[7]这是早期中国诗学史上所谓的“赋诗观志”说,它与“赋诗言志”具有同样的开创性意义。孔子说《诗》“可以观”[6](《毛诗序》)已是后进之言了。作为文学创作活动之“观”,陆机《文赋》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6](第170页)之说;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也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第295页)之说。这里的“观”与“感”已密不可分。感在《周易》中作“咸”,《咸》卦,下艮上兑,直观之象是“山下有泽”,“艮、兑”又可看作少男、少女。那么“咸”卦又“可看作少男少女(以少男为主导)相互接近、交相感应到爱情发生,最后是身体的接触的一个完整过程。”[8](第79页)《彖传》则把男女相感推及到人与天地之间的万物相感,推及到物我之间的心灵沟通。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4](第258页)人的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人与人、人与物相感的过程中,天人合一模式在情感契合上得到证明。
“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也决定了中国文学艺术构思方式上的独特性。中国古代文论并不主张创作时的面壁玄想,“参禅悟道”、“妙悟熟参”也是受印度佛学影响后的结果,并且一直没有占住主导地位,还受到清代宋诗派的极力诋毁。中国文学艺术构思特别重视感物兴情,把“外师造化”作为艺术想象的起点,视大自然为创作兴会的渊薮,从而使“物沿耳目”的“感物”活动成为艺术构思的第一推动力。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文心雕龙·物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6](钟嵘《诗品序》);“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6](《礼记·乐记》),它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兴”义解释,表达的都是物色感召心灵、主体依物启思的“—反应”的创作思想。这种—反应的直接结果便是以想象为主的艺术活动的展开,即宋代僧人惠洪所说的“妙观逸想”[9](《冷斋夜话》)。“妙观”是指在“物沿耳目”的时候,观造化之真谛、察艺术之本源。“逸想”则是在妙观的基础上开始的运虚抟实的艺术构思活动,所谓“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1](《文心雕龙·神思》)。后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人间词话》)的分别,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引申与发挥。
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周易》的阴阳互动的世界构成论。一部《周易》旨在表述宇宙的阴阳生生之大德,故曰:“《易》以道阴阳”(《庄子》)、“生生之谓易”。[4](《系辞》)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生。这是《周易》为人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世界万物的起源、构成、生化与变迁的图式。《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4]这句话说明了《周易》的思想本质,也成为《周易》哲学的总纲。《周易》认为整个世界是在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的互相作用下不断运动、变化、生成、更新的。这一思想又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势、风骨、韵律说提供了哲学依据。
《周易》卦象就是建立在阴、阳二爻两个符号的基础上。这两个符号按照阴阳消长的规律,经过排列组合而成为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的构成与排列,体现了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八经卦经过重叠排列组合为六十四卦,阴阳思想是其核心。
在《周易》中,阴阳观念表现为气。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互动,这是《周易》对阴阳二气运行规律的把握,阴阳二气互动构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模式,表现在卦象构造方面,就是阴阳互动模式可对自然万象不依直观所得,而创造出合乎“气”化规律的假象。如天在上地在下本来是眼中所见、足下所立的事实,可是下地(坤)上天(乾)构成的卦却是《否》卦,卦象之意为不通;相反,下天(乾)上地(坤)的卦却名《泰》卦,卦象之意是大利通泰。如果不按阴阳互动的规律进行认识,很难理解这种安排。《否》卦是阳上阴下,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相背而行不能交会,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4](第115页)《泰》卦是阴上阳下,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二气相向而行实行交会,这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4](第105页)《咸》卦正是“二气感应以相与”而使“万物化生”。阴阳互动,才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都在变化中存在和发展。柳宗元说:“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乐道之原。”[10](第543页)即:《易经》的易,是变化之意。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可见,《周易》卦象不是静止的,而是阴阳二气运行不止、生生不息的表征,显示出宇宙造化的勃勃生机与充沛活力。
这种认为整个世界只能在阴阳互动中存在和发展的世界观,成为一向高度重视气势、风骨、韵律的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阴阳互动表现为气,古代文论家很早就重视“气”在文论中的地位。孟子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1](《孟子·公孙丑上》),认为“养气”是“知言”的基础,“知言”是“养气”的结果,只有自身人格的崇高伟大,才能创作出崇高伟大的作品。这里的“气”是指一种“气势”,用“浩然”来加以形容,以显示气的表现形式,或为外在精神的“预式”作用。魏晋时期,“气”范畴得到普遍运用,形成“重气之旨”的文论思潮。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6](曹丕《典论·论文》)阴阳二气清升浊降地运动,决定了作家的气质、才性。“气”的概念内涵逐渐有所变化,由外在形式、精神形态转化为具体化的内容和品质,走向“现式”的中心地位。到魏晋中期,人物评品成风,直接以“气”的阴阳清和来评品人物,气由客体地位上升为要表现的主体地位。刘劭在《人物志》中说的更为明白:“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阴阳互动产生清和之气,禀受清和之气而生的人就聪明。“清”是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一篇作品的气势、风骨、韵律决定于作家阴阳二气的调适。《典论·论文》说“徐幹时有齐气(指徐缓之气)”,偏于阴柔沉浊;“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一者偏于柔软,一者偏于刚疏,都不及“孔融体气高妙”[6](第158页),有气势、有风骨、有韵律。气由外在形式的精神“预式”,转向具体客观的内容和品质,最后进入到被表现的主体地位。直接以气之情状来表现思想之褒贬,把气引入中国文论,除了中国思维的物我合一观外,还是由于气的性质表现出来。阴阳二气刚柔的不同决定了文章体势风格的不同,刘勰说:“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1](《文心雕龙·定势》)承认文章的体势风格有刚健柔婉的不同。魏征则从阴阳刚柔的角度了六朝南北文风的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6](《隋书·文学传序》)白居易又以粹气、灵气表述阴阳之气对文章风格的影响:“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属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检不扼,达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12](《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周易》在阴阳互动中,偏重于阳刚、劲健,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乾卦·象传》)。这一思想直接引发了古代文论中对“风骨”的偏爱,形成一种追求爽朗刚健的文风的倾向。纪说:“在《周易》对天地万物生命的认识和探讨中,自始至终包含着一个基本思想倾向,即十分重视和强调天地万物生命的变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生不息、坚不可摧、刚正劲健的伟大力量。”[13](第232页)在文论上,偏向于上述特点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它要求文章具有“结言端直”、“意气骏爽”、“风清骨峻”[1]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正是建立在《周易》关于“刚健”的思想基础上。唐朝文论总体上崇尚阳刚风格。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批评龙朔(唐高宗年号)初年的文风是“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循为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6](《王勃集序》),提倡用阳刚之美扫荡南朝宫体阴柔之余风。稍后,陈子昂以“汉魏风骨”为榜样,鄙视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出了具有阳刚之美的“风骨”标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6](《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盛唐诗人差不多都以“风骨”相标榜而崇尚阳刚之美,李白诗有“蓬莱文章建安骨”、“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等,表明他对前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取向。杜甫的诗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特点,他在《戏为六绝句》中态度鲜明地赞美庾信“凌云健笔意纵横”,追求“未掣鲸鱼碧海中”[6](第60页)的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中唐的释皎然与晚唐的司空图,从佛道两家美学思想出发,拓展了刚柔的审美范畴,刚柔的风格表现为多种术语,但仍以阳刚为主,阴柔为辅。《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4]《周易》提供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通变致久的发展论。《周易》古有“变经”之称,其实,变与不变总是统一在一起的,王夫之就说:“《易》兼常变。”(《周易外传·系辞下传》)《易》之名本身也含有常变之义,孔颖达在《论易之三名》中引郑玄《易赞》和《易论》的话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5](《周易正义》卷首)变易为变,不易为常,变易不易合起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常变观。《周易》不仅有常变之名,更有常变之实。《系辞》有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4]然而事物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周易》既在“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恒常通久中表现了“惟变所适”的可变规律,这种“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思想就是所谓的“天行”,即天道运行规律。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4](《蛊卦·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4](《复卦·彖》)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4](《泰卦》九三爻辞)。“复”的意思就是事物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始之位,可见,“复”就是变中有常的天道运行规律。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唯有天道规律本身是不变的,这天道规律永恒不变的最高表现就是天上地下,阳尊阴卑。《系辞》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事物变化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体现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常变规律也是《周易》成卦的根本原则。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4](《周易·说卦传》)
《周易》每卦六爻,代表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分,故曰“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六画就位次而言,可“分阴分阳”,即以初、二之位为地之阳、阴,三、四之位为人之阳、阴,五、六之位为天之阳、阴。阴阳之位,对立统一,反映了道的恒常不变的模式;就爻变而言,六画又“迭用柔刚”,即六爻与六位迭用,或刚或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它体现了道的运行变动状态。六位的阴阳与六爻的柔刚,也即道之常变,彼此交错,互相迭用,构成了易卦的根本组成规律。
中国古代文论受《周易》变与不变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通变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通变》篇,探讨文学的会通与适变问题。《文心雕龙·通变》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1]皎然在《诗式》中谈“复古通变体”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关于“复变”的程度,皎然说:“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3](第78页)这种复古而能“通于变”的思想,体现了文学发展的辩正规律。
“易者变易也”,阳之极则变阴,阴之极则变阳,阴阳互变,肯定与否定互相转化,包含着丰富的素朴的辩证思想。《周易》素朴的辩证法,在《易传》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系辞》对于《易经》的辩证因素方面作了一定的发挥,使辩证因素更加突现出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这些都是在言变化。
清代叶燮借用《周易》对待而生变化的哲学思想,阐述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问题。他在《原诗》中说:“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3](第44页)《周易》由阴阳两爻构成八经卦,再由八经卦重复为六十四别卦,形成一个层次井然、不断生展的对待范畴体系,这表明《周易》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对待思想。叶燮借用这一思想来讲变化:太极生两仪,即太极生出相互对待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是太极神妙变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阴阳二气指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和客体,主、客体都具有神妙变化的属性,主、客合一便能产生“冥漠恍惚之境”——“神境”。因此,诗歌发展也就相应地表现为“变”。叶燮《原诗》中的“变”包括三个既各自、又互相联系的内涵:(1)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2)变(踵事增华)是诗歌发展的总体趋势;(3)变是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叶燮认为:“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3](第4页)就是说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思想的源头在《周易》。《周易》认为变是宇宙的必然规律,无事无物不然。《坤·文言》曰:“天地变化,草木蕃。”[4]《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系辞》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4]“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4]以《易》之观点看,空间在变,时间也在变,飞潜动植、人文事功无不在变。变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朱自清曾指出:“‘新变’的‘变’倒似乎有意无意间在应用着这种哲学(《易》的“变”的哲学)。我们可以说梁、陈以至隋、唐之际,文论开始采用了这种‘变’的哲学。”[14](第338页)叶燮《原诗》正是继承了《周易》有关“变”的普遍性的哲学思想,用以说明诗歌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其次,叶燮认为诗歌发展是在盛衰更迭中不断进化的过程。《原诗》曰:“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又曰:“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3](第3页)《原诗》这两方面的思想都与《周易》哲学有联系。《周易》认为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泰极而否、否极泰来、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反复之道,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式的发展。《系辞》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既阐述了变化的内在动力,又描述了变化的发展过程——刚柔、进退、阖辟的交替更迭。这种形式的循环中包含着内容上的进化,《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通者,趋时者也。”[4]变化表现为日新之业,趋时之变,这就包含了进化的内涵。
第三,叶燮认为诗歌发展由衰至盛的动力在于变。他说:“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3](第8页)这一思想也是继承了《周易》哲学中的有关思想。《恒·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4]《系辞》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通过革故鼎新、救穷治衰达到宇宙恒久之道,这一思想成为历代诗新运动的基石,也影响了叶燮的诗学理论,他提出了“正(盛)→衰→盛”的诗歌发展模式,以变作为诗歌发展救穷治衰、由偏返正、由衰复盛的内在动力。
易道为文学提供的三大哲学基础,并不是完全孤立地对文学理论起着指导作用,它们之间存在内在逻辑的联系。“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为文学思维方式提供了范型,它是自然本身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为文学所借鉴和摹仿。阴阳互动的易道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构成方式,从而将已有的文学本体论的探寻,延伸到本体构成论的研究,阴阳二气在文学中由最初的气势,转化为气质、才性,最后表现为创作者主体风格,它是一直处于运动变化状态。通变致久,显示出宇宙模式的生生活力,《周易》哲学的通变致久的发展论,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必然的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三者之间互动、引发,构成文学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在变动创新中昭显永久活力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文学出版社,1983.
[2]叶燮.已畦集[c].《四库全书》本.
[3]郭绍虞.原诗·一飘诗话·说诗晬语[z].:文学出版社,1979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十五[m].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m].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8]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9]惠洪.冷斋夜话[m].《说郛》本
[10]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中华书局,1958.
[11]焦循.孟子正义[m].:中华书局,1998.
[12]白居易.白居易集[m].:中华书局,1999.
[13]刘纲纪,等.易学与美学[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
[14]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第五篇 《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_国学论文
那末,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究竟在何处呢?我以为在《周易》。《周易》一书,虽源于卜筮,却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由二爻六位;六—卜四卦的象数结构模式,构造成三才一体之道,蕴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近年再版的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就认定《周易》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本《序卦》之说,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见该书《自序》)。尽管有人对此提出驳议,但也承认胡氏之说“的确是创见”(刘长允:《“周易史观”驳论》,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这可以作为《周易》具有史书之特征,并蕴有史观内容的一个例证。
《周易》的历史观,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末的《易传》,有着明显的体系,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首先, 《周易》(尤其是《易传》)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纳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宇宙有机论基础上,循天地自然之“道”作为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的出发点和指导依据。《易传·说卦》上讲到:圣人之作《易》,乃“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易》书之作,乃“圣人”受神明暗中赞助,固体察到天道之妙而创揲蓍之法,据天地两参之意而立“大衍之数”(五十又五),又观阴阳之变,辩刚柔之别、合三画六
爻以成卦,其过程是不乖于天之“道”,不逆于人之“德”,不乱于处事之宜,穷尽万物之至理和生命的本性,最后达到对天命的客观法则的把握。很显然, 《易传》的这套说法,虽渗有占筮观变的神道设教,但其思路却以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为据,力图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包括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过程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才两之一顺”之说。 “三才两之”,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然又无独而有对,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属性。其属性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终归结于“一顺”,即‘将以顺性命之理”。 “三才两之一顺”之说的实质,就是肯定了天地自然准则(阴阳之道、刚柔之变)和社会人事原则(仁义之理)的联系和统一。然其侧重点还在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道”伦理化,使之合于“性命之理”。这一思想,源于早期儒家关于天人相通的观念,旨在说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非互相对待之二物,而是一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 《易传》并不了解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内在根据,但它确实首创性地说到了这个过程的两项具体内容:
(一)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
《易传·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段话,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间的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由此可见, 《易传》并不局限于儒家立场,而同时吸收原始道家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资料,并根据道家的气化观念加以引伸,闸发“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以明全宇宙之气化鼓动、振荡不已,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从而把人类社会之源起看成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
(二)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有机论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之源起,还内在地包括着对社会秩序之形成机制的考察。《系辞传上》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典者, 常也,礼,同理。《易传》以为,社会人事中的常则,恒理(礼义制度,等级秩序),是圣人“象其物宜”, “观其会通”而仿效建立并加以推行的。《易传》又讲: “知祟礼卑,祟效天,卑法地”,视知礼之所以高明而受敬崇,系效法天道而来:循乱则以卑顺为旨,体现力效法地道(参阅徐志锐: 《周易大传新注》),同样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
《易传》还围绕着“天秩有序”的命题展开论证。《系辞传上》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易》之“序”,就社会人事言,是指人之处位有上下,贵贱之分,与自然界万物产生之有先后而成“秩”相应,据此说明社会中夫妇,父子之生有先后(秩)、君臣之处位有上下(序),一如“天秩有序”那样,也是自然合理的。其旨虽主要在把儒家伦理纲常“天秩有序”化,以确立其不可违之权威,但同时也蕴涵有对对社会人事制度和自然天道秩序的相通性、一致性的承认,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排除宗教神学的干扰,理性主义地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其次,将变易观念引进历史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发展性,初步形成了朴素形态的进化史观。
《周易》的“变易”观念,总体上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原则提出的。《易传》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丰卦·彖传》)以为天道自然是不断地盈虚消息,与时变化,那社会人事亦当如此。《易传》还提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生生之谓易’,认为“易”者“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肯定了“易”之“变”是个不断生息、生成的过程。转化在社会人事上,则“日新之谓盛德”,肯定了人伦道德也循易理而有不断“日新”的发展变化。二是“通变之谓事”。这里讲的“事”,乃指“圣人”通晓变化之“理”、推之社会人事而成就之事业,即“富有之谓大业”。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强调了社会人事上的继善成性,亦是效法“阴阳之道’的变易规
则。
在“生生”与“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讲“变易”,就突出了社会人事的变化也是一种生息不断的生命过程,其“日新”,其“继善成性’,就内蕴有进化的意识。这种进化的意识,体现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使《易传》能看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系辞传下》)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还特别以“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序卦传》说: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之所在,即鼎之所在。引申为王朝确立的象征。革卦在前先明变革之意,后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其意虽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但《序卦传》强调: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解: “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又旨在阐明朝代更迭中的 “革新”之理。所以, 《易传》曾热情地歌颂过“革”之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彖传》)以为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能恰当地把握好这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所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传》),当然包涵了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进化的承认。
第二,在肯定天地自然之道与社会人事秩序相通的同时,又确认两者之间的区别,开启了对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的特殊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从孔孟到汉、宋的正统儒家都持天人合一说,在历史观强调人事秩序与自然之道的一致,导致以天道普遍规律代替社会人伦准则。 《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则与此有别,其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阴与阳是就“道’(气)而言,柔与刚专就“形”而言(刚柔者,阴刚之凝而
成质),仁与义则就“性”而言,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形质、属性和各自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虽贯有相似的准则、秩序,但其具体内容和特征则有差异。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是说天地设位有其自然功效,而“圣人”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结合为三(参)而成全天地之功。这一思想正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说相通。荀子提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此处“参”,可以理解为《易传》三才之道之“三”与“圣人成能”之“能”的发挥,肯定了人有不同于天道的作用和功能,强调了人以“礼义”原则组成“群体”力量,参与天地之化育而“全其天功”,高度重视了社会人事的自身组合和特殊功能。
二、对魏晋、唐、宋间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屉的一个源头活水,其史观曾发生过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它的变易进化观念常被许多哲学家利用为进一步阐述人类历史的变易性和进化性的思想前提,丰富了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力主革新变法的先进思想家批判保守的正统史观、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这在玄学家王弼,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知几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汉代,因为有了儒术独尊,思想文化领域是经学一统的天下,这制约和影响了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贯穿着唯心的天命说和独断主义的命定论,其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复古色彩,势必束缚历史哲学的发展。汉魏之际,儒术独尊的局面开始瓦解,名教出现了危机,在领域儒学虽仍为思想正统,然以“三玄”为宗的儒道融合的思潮逐渐蔚为大观,终于在正始年间发展成玄学运动。尤其是王弼,在提出“祖述老庄”、 “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命题的同时,仍依据儒学的传统立场,着重於《周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阐发出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玄学体系,力求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历史经验和社会治理问题。他尽黜汉代以来繁琐的象数之易,集中阐发《周易》之义理,结合历史进程总结曹魏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故於历史哲学上有所创获,对《周易》史观作了理性化和思辨化的发挥。
首先,王弼依据易理关于动与静,道与权关系范畴的,探讨了历史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不变与唯变的问题。王弼肯定:“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这当然包括对社会历史必然趋势的承认,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治理还要适应“权变”的原则,说“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论语释疑》),主张破除那种命定论的、不变论的社会历史观念。进而断定: “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提倡要因时因地采用不同的对策加以适当的处置。其次,王弼又应用《周易》的“因革”观念,考察社会发展中的治乱关系,提出“乱极生革,革然后致治,天下之势乃定”的思想,把社会正常秩序的确立看成是经因革转
换、由乱致治的过程。他还依据“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周易注·革卦》)的命题,着重阐扬《周易》的“革故鼎新”之意,称:“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是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 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 (《周易注·鼎卦》)王弼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看成某种必然的现象,其内容则在革陈不合理的法制(易故),并持变“应时”, “制器立法”,建构新的法制秩序(“取新”),这叫“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周易注.革卦》)。需要指出的是,王弼的“改命创制”和汉代董仲舒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础上讲“更化”、 “改制”显然有别。他没有董仲舒那种“天意主宰”,循环复古的意识,而是强调“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老子注》三十三章》,视官长法制为“朴”散之为器的结果,肯定了社会秩序是依据自然变易之道经“因革改制”而成。所以,王弼在阐发社会历史观上的“以无为本”思想时,就讲到时机未到当然“不可以有为”,而当“变生”之机,则要“应天则命”,积极有力,至于“变道已成”,方
归于无为,即“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周易注·革卦》),反映了王弼追求社会大治、太平的愿望。当然,王弼的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内容和儒家色彩,他断言, “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周易注.鼎卦》),还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标帜。
第三,王弼还吸收《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精神,主张在“改命创制”的过程中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称: “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注·大畜卦》),强调: “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注·小过卦》),表明王弼在援儒入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家消极无为的阴柔之道,而溶铸了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这是《周易》史观影响于魏晋时期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
《周易》史观的积极精神在唐代有了新的进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可说是应用变易进化观念鉴别史实,考察史变的杰出代表。他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态度, “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明确反对正统儒家那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史学态度,指出: “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特别是他承王弼以来“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易学传统, 引进“势”的观念,考察史事变迁和治政得失,指出: “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批评那些“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如守株待兔者。(《史通》卷八《模拟》篇)在《易传》和韩非的基础上进一步闸发了社会古今之异和历史进化之势。
与刘知几相呼应,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变易史观,对唐代的历史哲学作出了贡献。柳宗元将天人关系新论贯彻于社会历业领域的考察,虽仕途坎坷,身囚山水,仍潜心史事,常有创见。他把韩非“势”的观念和《周易》变易史观结合起来,具体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过程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着重探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又指出:惟人之初,争斗不断, “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淤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以后有尧, “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贞符》,见《柳宗元集》卷一),肯定了社会礼义制度和道德伦理两方面的演进都有个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而刘禹锡则提出“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的思想,从势数结合的角度,确立了历史观上的理势合一论,进一步发展了《易传》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特殊性问题的探讨。他说: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余曰: ‘天与人交相胜耳’”。又称: “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则,其用在是非”。 (《天论》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作用和人事功能,强调人依靠礼义、法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天地之化育井交相取胜,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意识,丰富了唐代历史哲学的内涵。
北宋思想家李觏站在事功之学的立场上解释易理,其著《易论》十三篇曾专就“人事”而言,侧重探讨了社会人事的历史变迁问题。称: “八卦之道在人, 靡不由之也”,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又继承王弼义理之易的传统,指出易理之用无非是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文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又称:“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强调“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的过程加以研究,排斥了圣人,天意对人事的干预,从社会人事本身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趋势和原因。王安石则从“新故相除”的阴阳自然之道推导出“有处有辨, 新故相除者,人也的结论。”(参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在承认天道自然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事有为能辅助天道。又称: “五事者,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以为“道”既“为万物之所以生”之本, “不假乎人之力”,又“涉平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成也”(《洪范传》)。以注重人为作用的变易进化史观作为其变法新政的理论依据,与李觏相配合,实开有宋—代历史哲学之新风。
三、促成理学正统史观之分化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在宋代理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理学家以天理史观的形式,把正统儒学历来提倡的神意史观、圣人史观作综合的概括并加以理性化的闸发,把历史哲学纳入其复古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把《周易》史观在后来发展中所积定起来的积极的、进取的因素加以抹煞或有意的忽视了。
不过,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曾精研《周易》,深受易理熏陶。从周敦颐著《易通》,张载治学“以易为宗”(《宋史》本传)而成《横渠易说》,程颐作《伊川易传》、到朱熹融会易学史上之象数派和义理派撰就《周易本义》,我们可以看到易理对理学的体系构建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作用,促成了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
矛盾表现之一,宋代理学家在史观上既尊《春秋》为宗,亦奉《周易》为源,尤注重易理对考察社会人事的指导意义,透露了某些突破正统史观的倾向。朱熹就讲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若要谈此两书,且理会他大义。 《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则。《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朱于语类》六十七)他又发挥易之“明消息盈虚之理”,称:“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据此解释历史研究中的“执古御今”说,认为“执古” “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便是今日之事”。 (《文集》卷八十五)这和董仲舒等正统儒家持《春秋》以为“奉天法古”之本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
矛盾表现之二,是理学家一般吸收了易学“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思想,也受柳宗元理势合一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发展中客观趋势的存在,和朱熹所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又“一本于圣人之述作”的史学主旨亦有相违之处。朱熹治史,一方面断言:古今史事之变是“合于天理之正,圣人之心”(《通鉴纲目后序》),以圣人心术为历史变迁进程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发展本身毕竟有着“非人力之可为”的“当然之理”。说: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亦做不得”,意识到历史中还有圣人心术难测,难御的客观趋势的存在,认为“会做事底的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进而肯定:历史发展“势不容己,柳子厚亦说得是”(均见《朱于语类》卷一二二),显然和柳宗元的理势论历史观有点接近了。
矛盾表现之三,引进易理的“物极必反”, “传承因革”的思想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这和理学正统史观的复古、保守倾向有对立的一面。二程已承认“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伊川易传·否卦》)的一般发展原则。朱熹则认为“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七十二)又将易理引伸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相望,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古史东论》)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相因相革”的必然过程。他还讲一步社会历史因革变易的原因在有“弊”,指出: “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得人之法”, “任法不任人,乃是法弊。人弊可以易人,法弊则必当变法”。 (《朱干语类》一o九)强调“革弊须从原头理会”(《朱子语类》—o八),在复古史观的框架内也包含了某些变革,进化的观念、意识。
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易》史观对宋代历史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为正统史观后来的分化准备了条件。到了南宋时期,吕祖谦侧重闸发其理势论历史观,更使这种分化公开化了。并由此构成了导向王延相、王夫之历史哲学的—个重要环节。
从理论倾向和思想立场上看, 吕祖谦当是个正统理学家,自称为学之旨在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欲会归于—”。但他又与陈亮友善,受事功之学影响,在历史观上也贯彻经世致用精神。他明确指出:治学“先立乎其大者”,即“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着重考察各代政事治乱、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 “欲具体统,源流相接”(《左氏传说》卷二十)。显然,他把《周易》史观影响下对历史发展必然之“理”的探讨,发展到明变(寻流),求因(探源),主张“观其所变”, “看史要识得进节不同处”,揭示历史变革中“盛之极乃衰之始”的过程(见《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还强调: “观史当如身在其中”,提倡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其趋势作出判别和预测,如同“看史须看一半便掩盖,料其后成败如何?”(《杂说》,《遗集》卷二十),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问题的考察。
明代的王廷相则提出古与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深入考察了历史变迁之“势”的具体内容。他认为: “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礼义道德之逐步完善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又认为:郡县制之建立, “势也,非秦也。虽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则天下之公也”。(均见《慎言》)在王廷相看来,秦始皇主观动机之“私”所以能实现,原因是其客观效果上合于“天下之公’。意味着能透过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隐蔽着的必然性,为后来王夫之在理势合一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奠定了理沦前提。
四、《周易》史观和王船山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来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总结的代表。他提出, “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从气一元论出发,对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与“心物’(知行)之辩作了合理的解决,进而在历史观上强调: “总将理势作一合说”,表明他在历史哲学上山提出了总结的任务。
王夫之是易学大家,所著《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是易学史上的名篇,其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又以溶贯和阐发易理见称。所以,王夫之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是和他自觉地应用和发挥《周易》史观密不可分的。这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加以说刚.
(一)承继《易传》的变易、进化观念,明辩理势关系,强调两者不可“沟分”,初步涉及到要在社会现象和历史内在根据的统一过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王夫之强调“天下之变会通于一理”,而理“只在势之必然处”。 (《读四书大全说》)据此立论,他论述了理势关系的两重涵意:一是指明“理不可得而见”,属于蕴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一种必然性,但强调: “势因理成”, “离理无势”, “理顺斯势顺矣,理逆则势逆矣”(《尚书引义》),肯定了“理”支配“势”。二是指出理势关系又是“理成势”与“势成理”两者的相辅相成,认为“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 断言: “看得‘势’字精微, ‘理’字个大,合而名之曰‘天’”。 (《读四书大全说》)理势合一才体现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合乎自然的规律性。
尤其可贵的是,王夫之还承认理势可知,认为顺应并实现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可达到公天下之人,利天下之物的目的。他称: “虞、夏、殷、周之法,屡易而皆可师”“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势也。理势者,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顺平天,势有重轻以顺乎人。则非有德者不与”,进而断定: “君天下之理得,而后可公于人,君天下之势定,而后可利于物”。 (《尚书引义·立政周官》)把隋唐以来的理势论历史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发挥《周易》史观的“因”、 “革”观念,提出治乱、离合,续绝的关系范畴,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王夫之考察历史发展之必然性,同时伴随着对正统史观的批判和对传统的治乱循环论的改造。他指出: “正统之说,始于五德。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徵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 ( 《读通鉴论》)严斥邹衍以“五行相以转用事’立论,视社会历史为五德“终而又始”的循环过程的“邪说”。而秦王赢政用於论证始皇观念,汉代董仲舒以三统三正的循环为王道正统永恒的依据,在王夫之看来,总不过是“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他虽沿用正统论者的说法,讲:“治乱循环,阴阳动静之几也”(《思问录》第33页),但他特别注意社会治乱循环过程中的离与合、因与续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续统与非续统,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互相联结的问题。他指出,历史决非如正统论者认为的那样“合而不离,续而不统”,并引证史事作史鉴,断定“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又详细论证中国历史上已经历过的三次治乱、离合的“大变”:春秋之世“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天下”, “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衡”, “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有三分天下以后,五胡起,南北寓,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至於宋亡以迄于今,当其治“中国有其主”,当其乱则“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 “此又一变也”。 (《读通鉴论》)进而说明历史中所谓“统”者,乃“绝而不续”,在承认历史发展有相因相合的连续性外,更强调了有相离相绝的间断性。
王夫之能如此具体地阐述治乱、离合、续绝的历史辩证过程,显然和他贯彻《周易》的因革观念有关。他强调: “承治者因之,承治者革之,一定之论也”, (《尚书引义》卷五)认为历史的进程要“止乱趋乱”,就须要发挥人为的因素,适时把握因革关系。又例举“舜之承尧”、“禹之承舜”, “商之革夏、周之革殷”,说明历史发展中的因革,是据“与时消息”,视不同情况而论: “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者”。 (同上书)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历史因革观还包含着他乐于正视社会矛盾和激烈变革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他找出“君子乐观其反”的命题(见《周易外传·杂卦传》),探讨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问题。例如,在评论徽宗晚年的北宋社会矛盾时,王夫之指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 “倾之而后喜”(《宋论》卷八),认为在“势极’即矛盾空前激化而又“不可止”的情况下,就要“大反”、 “倾之”,通过激烈的变革来解决,故提倡: “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的积极态度。不过,王夫之并不以“大反”, “倾之”作为解决矛盾的普遍形式,他说: “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承认还有矛盾双方“或错或综,疾相往复”,最后达到“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的互相渗透、调和的状态。这表明,王夫之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有着十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三)进一步考察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人之群体在实现历史规律过程中的作用。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朴素辩证发展观的核心命题。他据易理加以引伸,认为自然之道的“推故而致新”有着内在的自足根据,即“太极”自身“富有充满”’ “成熟扩充,臻于光大”的结果。而人群(社会)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类,其生殖演进亦有自身原因。他这样讲:“类似相续为藩衍。由父得子,由小向大,自一致万,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以为人类的藩衍相续,由消长,增逝的自然原因所支配,经历有“相均”、“相值”的过程,自然趋于平衡, “其消谢、生育相值,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
(《周易外传》卷四)这样,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可以通过人群自身的调节(藩衍相
续),达到自然平衡。其中就涉及对人类历史和天地自然之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辨析与确认,王夫之曾指明: “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异质离,不可强合焉”。他引“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为例, 肯定了 “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王夫之在这里的叙述,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哲学中—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人怎样在服从自然之道(势所然)的同时,又作为文明的创造者而推动历史的前行?!对此,王夫之曾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又吸收宋代吕祖谦肯定社会之兴亡“不在好雄”、 “只在小民之身”(《增修东莱之说.召诰》)的合理因素,指出:“天欲静,必人安之,天欲动,必人兴之”(《诗广传》),以人之“兴”、“安”,助天之动静,赞颂“大哉人道乎!非对于天而有功矣”。 (《续左氏春秋传博议》卷下)肯定了人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的作用。而且,王夫之讲的“人”,既指“时君和智力之士”,又包括“一介之民”,已由圣王和英才扩大到“士”与“民”阶层,反映了他对民众创造文明、推动历史的作用有所承认。
当然,王夫之不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不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讨是不科学的,仍渗有不少唯心史观,圣人中心等封建杂质和消极因素。他通过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考察,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但他并末意识到封建社会自我否定的必然。他的历史哲学不是启蒙型,由此引伸出的结论主要在通过改良、弥补封建统治秩序的弊端,使之趋于合理而挽救其危机。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尽管王夫之代表了古代历史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我们仍然要以批判的态度给予选择继承。
第六篇 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易学阐释_国学论文
中国传统哲学与易学有着不解之缘。尤自魏以降,历史上别开一代风气,另创一家之言的一流哲学家,多借《周易》经传思想资料以阐人伦,说物理,证心性,论道体,试图建构其体用不二,真善合一的形上学体系。王弼之注《周易》,程颐之作《易传》,张载之撰《易说》,朱熹之论“易纲领”,王夫之之著《周易外传》、《周易内传》等,皆其显而卓者。
就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理论而言,无论是其理论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还是其抽象思辩内容的表达与阐释,都极其得力于《周易》卦爻符号系统和易学自身所特有的一套概念、范畴和命题系统。通过易学形式来阐释哲学义理,建构本体论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民族特色的突出标志,也是中国民族长期理论思维积淀下来的重要成果。本文尝试从本体论的易学阐释这一角度,粗略地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与易学的密切依存关系,非敢示人,但为求教。
一
“易学”属于传统经学的一部分,通常是指以《周易》为对象来“解经释义”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历史上易学分象数派和义理派两大系统。通过解释《周易》经传阐发哲学本体论思想,主要是由义理派来完成的。
最先将《周易》经传的解释与哲学本体论的阐发结合起来的,是曹魏时期的著名易学哲学家王弼。WwW.meiword.cOm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易学义理派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象数论序》曾评论其易学说:“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王弼一改汉易卦气说中宇宙生成论传统思维模式,援老庄以解《易》,倡得意忘象之玄风,把对有关宇宙论问题的研究直接引向了本体论形态的探讨,在特定的易学形式下阐发了“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
王弼哲学的终极理论关切,是探寻一个“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老子指略》)的宇宙本体。在他看来,由于形必有所不兼,名必有所不尽,所以堪为宇宙本体的,应是一种“无形无名”、即无任何条件性和局限性但又真有逻辑可推性的绝对。针对汉代哲学的经验主义思维倾向,他认为要消除其“各申其说,人美其乱(疑为“辞”之误)”的诞
昧局面,必须抛弃“察近而不及流统之原”的感觉主义思想方法,而提倡一种以远证始、以幽叙本的理性主义的抽象思维。他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同上)物之近而显者,必有其远而幽者为其本由。这就需要借助理性思维,通过逻辑演绎和抽象,以达到对于本体的认识和把握。沿此一路,王弼以解《易》为径,主要从两个方面阐释了其玄学本体论思想。
(一)象、意之辩 王弼《周易略例》之《明象》章,专门就言、象、意三者关系展开讨论,此章内容,从筮法上讲,主要是论述《周易》言、象、意即卦爻辞、卦爻象和卦爻义三者的关系问题,从哲学上讲,则涉及到本体论、方的问题,即从象、意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以及如何认知、把握本体的问题。概括起来,王弼象意之辩内容有四;(1)象生于意。王弼解《易》,以取义为主,于汉易象数之学尽力排斥。所谓“象生于意”,与其取义说是完全一致的。他在《周易注》中解释乾《文言》时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义、意互训,亦强调意为象本,象由意生。意或义,乃可脱离象而自存的抽象实体。此一结论,为其“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的,玄学本体论直接提供了理论基础。(2)意以象尽,寻象观意。意虽可离开象而存在,但“象者所以存意”,“尽意莫若象”,抽象的意又需借助于具体的象而体现和表达。所以若欲把握和体认意,又必须“寻象以观意”,以象为工具和手段。其所谓“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韩康伯《系辞注》引),理正与此同。意在忘象。象生亍意是前提,寻象观意则是方法或手段,得意忘象才是根本目的。象与意本质上是对立的。若执著于象,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到意。只有在体认把握到意之后复将得意之具抛弃,才不会为其所累,而真正得到意,从而达到终极本质的认识。此即所谓“执之者则失其原”,“不以执为制,则不失其原矣”(《老子指略》)。(4)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触类”、“合义”亦即“得意”之别一说法。盖谓由具体而进到了抽象,由个别而达到了一般。王弼认为,只要掌握了事物的义类,就能判识其杂多的征象,只要抓住了事物的一般,也就
能统御其具体的殊相。由此他要求,不但要忘象以得意,而且还要据意以御象,换言之,也就是举本以统末。他指出,汉易象数之学之所以“案文责卦”而“伪说滋漫”,正因其“存象忘意”而“失其原”(《周易略例·明象》),未能抓住一般义类并据以御象之故。
(二)一多、有无之辩 与上述象意之辩理路相一致,王弼还在易学形式下从一多、有无等角度对其玄学本体论作了阐释。其最突出者,当属对“大衍义”的解释,其次则为其一爻为主、以一统众的易学观。
王弼吸收并发挥《彖传》解经的爻位说,明确提出“一爻为主”的解《易》思想。一爻为主是王弼解《易》的重要体例之一,也是他从一多关系上阐发其以一统众玄学本体论的重要易学手段。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又《略例下》亦云:“凡《彖》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王弼认为,一卦之中,虽六爻相错,所处时位各不相同,其所具意义亦互有异,但其中必有一爻起主导作用,以为这一卦的中心或主旨所在。只要把握住这一爻,虽刚柔承乘,阴阳往来,六爻相错,变化纷繁,皆可“举一以明”。王弼提出一爻为主说,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说明易卦卦象与六爻爻象、易卦卦辞与六爻爻辞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一卦之义应如何确定和把握的问题,但他于六爻之中独崇一爻,并以此一爻决定全卦之主旨,则体现了一种“约以存博,简以济众”的认识方法,表现出由纷繁变化的事物中寻求其统一性的理论尽维取向。沿此一方向再作进一步的理论发挥和概括,其以一统众的玄学本体论便凭借易学语言得到自然圆畅的表达:“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故自统而
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而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明彖》)可以看出,王弼这种易学阐释,是从探讨易卦六爻之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而追求一卦之中为主之爻的爻义,从探讨六爻相错复杂爻象中的简易原则,进而追求天地万物的普遍统一性。只要把握了这种“至寡”、“贞一”的统一性,就能做到“繁而不乱,众而不惑”,从而真正认识到事物之所以存在(“众之所以得咸存”)和之所以如此存在(“动之所以得咸运”)的根由或依据。
王弼释大衍义,以筮法衍卦过程中的所谓不用之“一”象征宇宙本体“太极”(即“无”),以四十有九之策象征天地万物(即“有”),认为,太极本体“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天地万有必依据本体“无”才能存在和发生作用。然而本体无又“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其自身并不能通过自身来表明,必借助于天地万物之“有”以显示其存在和功用。王弼这里所谓无必“因于有”,决不是说无即存于有或离有而无无。在他看来,“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老子注》第一章)。对于作为万有本体的无来说,它本身是超越物外的。无只能靠有来显现,但并不能到有中去寻找。无为有之本,但无并不在有中。此正如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但意在象外,故又必得意而忘象一样,有与无的关系,也是有生于无,故可假有以明无,但无在有外,故必贵无而贱有。
王弼玄学本体论的思维逻辑,实质上只是强调万物归一,但并不承认一归万物。这是王弼玄学本体论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本体论理论的一大缺陷。由此而言,王弼玄学奉体论尚未达到一多相即,体用一如的见地。这个任务,只是到了程朱理学才基本完成,而最终由王夫之彻底解决的。
二
两宋以来,程朱派理学批判继承王弼易学思想,在以理为本的基础上改造玄学本体论,广泛吸收其他理学家乃至佛教哲学有关思维成果,在新的思想学术条件下对其理学本体论展开易学阐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理论。
程颐积一生几十年之心血,数易其稿,晚年成《程氏易传》。此书堪为程朱派易学哲学代表之作。朱熹曾称赞程氏易学说:“巳前解《易》,多只说象数,自程门以后,人方都作道理说了,(《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所谓“作道理说”,主要是说将易学理学化,并借《易》以言“理”,把《周易》作为阐释其理学本体论在内的新儒学的有力工具。
程颐在《易传序》中,就“理”严象”关系问题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著名易学哲学命题。他说:“得于辞而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这段话从易学上说,仍是论述言、象、意即卦爻辞、卦爻象和卦爻义三者的关系,但程颐既不同意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将言、象、意相分离的观点,同时又引进“理”的范畴,把讨论主题放在了“理”和“象”的相互关系上。他认为,无论是盲象意还是理和象,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合一的,不可分的。此所谓理和象,从易学上讲是指卦爻之义和卦爻之象,或者说卦德和卦体,从哲学上说,则是指天地万物及其本原和根据。所谓体用一源,就是说理是体,是至微而隐者,象是用,是至著而显者,有其体则有其用,用即体之自身展开和显现。同理,所谓显微无间,就是说理和象乃一事之两个方面,理隐于内而无形则微,理显于外而成象则著,现象乃本体自身之显现,而本体则又同现象融合在一起。程氏这种理象显微体用观,是其理学本体论的典型易学阐释。其所谓“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
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的著名“理事之辩”,正与此同为一辙。
朱熹绍述程氏,丰富发展其体用一源的易学哲学理论,由易学问题的讨论中引出并深化理事之辩、太极阴阳之辩乃至理气之辩,从而在哲学上完成了理学本体论的易学阐释。
其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体用一源’,体虽无迹,中已有用。‘显微无间’者,显中便具微。天地未有,万物巳具,此是体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显中有微。”(《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此所谓“体虽无迹,中巳有用”,亦即其所说“理之体,该万事万物,又初无形迹可见”,万事万物之用本为无形之理(体)所固有,故谓体用一源。所谓“显中便具微”,亦即其所说“《易》之卦爻所以该尽天下之理”,无形之理即在万事万物之中,故谓“显微无间”。依此逻辑而论理事关系,则生天地万物之理为体,生天地万物之事为用。既体中有用,故有理便有事,既显微无间,故理在事中。《周子全书》卷二亦载有朱熹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语。他说:“其曰‘体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原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所以为无间也。”认为“体用一原”是从理这一方面说的,在于强调理为体,象为用,理中
有象。在这一方面意义上,可以说“言理则先体而后用”,“举体而用之理已具”。而“显微无间”,则是从象这一方面说的,在于强调象为显,理为微,象中有理。在这一方面意义上说,又可以说“先显而后微”,“即事而理之体可见”。这种理事显微体用说,构成了朱熹理学本体论的核心内容。
太极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其易学的最高范畴。太极作为朱熹理学本体论体系的理论基石,其来源也是出于对筮法中太极概念的阐释。
《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关于易之太极究指何物,太极与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如何,历来说家纷纭,莫衷一是。朱熹既反对汉易和张载等以气为太极之说,也反对王弼等以无为太极和邵雍以心为太极之说。他认为,无论是从筮法布蓍衍卦意义上讲,还是从此一演绎过程所展示的哲学义理上讲,太极只是“象数未形之全体”,“只是一个浑沦底道路”,他说:“此太极却是为画卦说。当未画卦前,太极只是一个浑沦底道理,里面包含阴阳,附柔,奇偶,无所不有。”(《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又说:“自两仪之未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易学启蒙》)就是说,太极非他,即一切卦爻之象和奇偶之数所依据之理,是一切象数之理的总体。关于太极与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朱熹认为,一方面,由此太极“一理之判”,则“始生一奇一偶,而一画者二也”,此即所谓“是生两仪”;再判则“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也”,此即所谓“两仪生四象”;再判则“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也”,此即所谓“四象生八卦”(《文集·答虞士朋》)。另一方面,则“自三百八十四爻总为六十四,自六十四总为八卦,自八卦总为四象,自四象总为两仪,自两仪总为太极”但“太极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顿放,是无形之极”。所以说“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朱子语类》卷七十五)。朱熹在同陆丸渊辩论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的命题时,更为简骸地表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意思。他说:“且夫大传之极者,何也?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组于三者之内也。”(《文集·答陆子静))“具于三者之先”,就是说太极总括两仪四象八卦之理,有此太极之理,才有两仪四象八卦之画,“组于三者之内”,就是说两仪四象八卦展开之后,太极之理并未就此与之分离,而是仍寓于仪象卦之中。朱熹明确指出,易卦爻象形成的法则和其所包含的原理,与天地万物形成的法则和其所遵循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凡天地许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与天地齐准而能弥纶天地之道。”(《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因此,当他以此易理诠释其理学本体论中太极与阴阳万物之间的关系时,遂构成其哲学理论中“理气之辩”的重要内容。
朱熹强调,理乃天下万物“所以然”或“当然”之则,气则是“生物的材料”,天地人物的形成与存在,均必以“理与气合”为必要条件。“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文集·答黄道夫》.)理和气并非平行关系。理为生物之本,气为生物之具,故“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在朱熹看米,阴阳五行和万物化生,如伺太极生两仪四系八卦一样,亦为理或太极自身展开和现实化过程。此一过程虽“亦
须有节次”,但这种节次只是一种逻辑顺序,其间并“无先后次序之可言”。程颐易学哲学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原则把事和象看成理自身显现的外在形式,朱熹沿此理路,考察太极和阴阳五行以及天地万物的关系,以抽象无形之理即太极为本体,以阴阳五行及万物为现象,认为本体和现象非一非二,不即不离,以排除了时间先后的逻辑展开原则阐释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从而完成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然而,程朱理学本体论的易学阐释,最终仍然蹈入了理论困境,留下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他们在反复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逻辑原则的同时,为了寻求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又不得不在体用、理事和理气之间找出个“体用显微之分”和“精粗先后”之别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片面强调理对于气、体对于用的终极决定意义。他们从把{周易》卦爻象卦爻辞概念化、抽象化、,极意追求概念命题的抽象意义出发,进而扩展为以具体和个别事物为在后而粗的东西,以抽象和一般的原则为在先而精的东西,最终仍将一般和个别、本体和现象割裂开来,承认先有一般后有个别,抽象的理可以离开具体的气而存在。此一理论结论,虽将王弼玄学本体论的“无”变成了“理”,但其实质,仍是只承认万物归一,而不承认一归万物,并;未能把体用一源的原则贯彻到底。
三
明清之际王夫之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易学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治《易》达四十年,著有《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等易学哲学著作。此外,其《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等其他重要哲学著作,亦每借《易》以说理,从而在解《易》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精深的哲学体系。
对于以往易学哲学,王夫之既尖锐地批判了象数派京房、邵雍等“崇谶纬”、“仿丹经”的错误学术倾向,将其斥之为“释经之大蠢,言道之荆棘”(《周易稗疏》卷三),也深刻地剖析了义理振王弼释大衍义仍未免于老氏有生于无之论和程朱派解《易》于气外求理的理论错误。他认为:“《大易》之蕴,唯张子所见深切著明。”(《张子正蒙注》卷七)在继承张载以气为本解《易》传统基础上,通过批判地鉴取前人、尤其是程朱易学的有关理论思维成果,在“以乾坤并建为宗”的解《易》原则下,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他的哲学本体论思想。
王夫之认为,“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周易内传发例》)。所谓“乾坤并建”,亦即“阴阳并建”,所以又说“阴阳并建以为《易》之蕴”。“并建”即“时无先后,权无主辅”之意,“乾坤并建”或“阴阳并建”,即是说乾与坤或阴与阳之间,乃同生共有、并存浑成的关系。此同生共有、并存浑成之乾坤或阴阳,亦即所谓“太极”。“如实言之,则太极者乾坤之合撰。”(《周易外传》卷五)“阴阳之体,纲组相得,和同而化,充塞于两间,此所谓太极也。”(《周易内传》卷五)从筮法上讲,太极即易卦阴阳各六而十二位具足。六十四卦虽阴阳相错,变化繁复,“实则一卦之向背,而乾坤皆在焉”({周易内传发例》)即《周易》各卦,每卦六爻,显于外者六,隐于后者六,“无往而不得夫乾坤二纯之数也”。从哲学上讲,太极即阴阳二气“太和絪縕之实体”。天地万物虽大化繁然,运北变合旭无物无乾坤,无物无阴阳,“皆取给于太和絪縕之实体”。
关于并建之乾坤(太极)与六十四卦之全体(易)的关系,王夫之提出“太极有于易以有易”的著名易学哲学命题。他通过论述太极与易“明魄同轮而源流一水”的体用一如关系,深刻阐发了关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的见解。
(一)太极与易,“莫得而先后之”。王夫之的哲学本体论,是主张“太极无端,阴阳无始”和“天地不先,万物不后”的。这一思想,通过他的“并建”说而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挥。他认为,《周易》六十四卦阴阳错综,纯杂分合,但“错之综之,两卦而一成,浑沦摩荡于太极之全,合而见其纯焉,分而见其杂焉,纯有杂而杂不失纯,孰知有其始终者乎!故曰太极无端,阴阳无始。”(《周易外传》卷七)在他看来,《周易》虽并建乾坤于首而终以未济,其实“未
济之世,亦乾坤之世,而非先后之始终也”。六十四卦乃“捷往捷来,而不期以早暮”,“捷反捷复,而不期以渐次”,其间并无时间先后之可言。为此,他批评易学哲学史上讲生成之序者如《易纬·乾凿度》“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之说,是“危构四级于无形之先,批评《序卦》传所谓“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之说,是“以留而以待”,“非圣人之书’,批评邵雍所谓“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之“加一倍法”,是“但曲致其巧心”、“待于渐以为本末”……皆昧于太极与易“固有”、“俱生”、“明魄同轮而源流一水”之蕴。(二)“惟易有太极,故太极有易”。王夫之强调,“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而只能存在于万物之中。象征“天地之象”和“尽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的易卦爻象,乃是象征抽象宇宙本体的太极一一并建之乾坤赖以存在的基础。所谓“易有太极”,就是说由易卦阴阳往来、错综隐显的变化中,即显示出并建之乾坤阴阳各六而十二位具足的存在,太极即寓于易卦全体之中。所谓“太极有易”,则是说易卦阴阳往来、错综隐显的变化,即并建之乾坤六阴六阳的展开和具体表现形式。但“易有太极”乃是“太极有易”的逻辑前提,“纯乾纯坤”并不能孤悬于众卦之上,它只是在诸卦的阴阳错综变化中显示自身并作为它们的共同根据而存在。否则,离开易卦错综复杂之象来谈论纯阳纯阴的并建之乾坤,那它就只能是“空洞而晦塞”的抽象神秘之物了。(三)太极与易是“一本而万殊”,“同归而殊途”。“一本万殊”之论是程朱理学的主要论题之一,也是王夫之哲学所讨论的重要内容。从本体论角度讲,一本即本体,万殊即现象。王夫之指出,为君子之言者,欲不陷异端,必于大化繁然复杂之象中去“察原观化,浑万变而一之”,从而揭示其本质,把握其同一。而《周易》众卦“浑沦摩荡于太极之全,合而见其纯焉,分而见其杂焉,纯有杂而杂不失纯”(《周易外传》卷七),则正是达到这种认识的最好途径。在《周易外传》中,他就未济卦而论一本与万殊的关系说:“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变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而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万,终于一。始于一,故曰一本而万殊:终于‘而以始,故曰同归而殊途。”这里的逻辑关系是:一本而万殊,万殊而一本;一本必散为万殊,同时亦必寓于万殊。“是可截然命之曰—‘一归万法’,弗能于一之上索光怪泡影以为之归”。(同上,卷六)王夫之强调,这种太极与易的一多关系,只能说是“一体该摄乎万殊”,而绝不能说是“万殊还归乎一原”。否则“此语一倒,纵复尽心力而为之,愈陷异端”({读四书大全说)卷六)。他认为,释老二氏或是以“万法归一”为说,“要消灭得者世界到那一无所有底田地”,或是“执一废百,毁乾坤之盛,而骄为之语曰先天地生”,正是因其迷执“以一贯之之术”,归万殊而为一的缘故。同样,王弼易学
哲学于象外求意,有外求无,程朱易学哲学于气外求理,器外求道,其理论思维失误所在,都是以万物归一来取代一归万物,即试图把一般的“一”或“体”从具体的“多”或“用”中抽象、出来,并作为“臣妾万有”的主宰或本原。(四)“乾坤并建以为体,六十二卦皆其用”。王夫之还以“用此以为体,体此以为用”的“体用相函”原则,解释太极与易的关系。他批判地鉴取程朱“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易学哲学命题,在以太极为二气浑合之实体的前提下,指出:“乾坤并建以为首,易之体也:六十二卦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
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为易之资。屯蒙以下,或错而幽明易其位,或综而往复易其几,互相易于六位之中,则道之变化,人事之通塞尽焉。”(《周易内传》卷一)在他看来,一方面,“立乎至足”而“为易之资”的并建之乾坤,乃由“合六十四卦之德”而来,即有各卦“运以无方无体之大用”,才有纯乾纯坤并建之体。此即其所谓“由用见体”、体在用中。另一方面,乾坤并建既合六十四卦之德以为本,则必“达乾坤之化于六十有二”以为用,即有乾坤并建之体,必有“六十二卦之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之用。此亦即其所谓“体以致用,用以备体”。在《周易外传》中,他更借对大有卦的解释,发挥出“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的本体论方原则,并由此进而得出了“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卷二)的深刻结论。
王夫之的易学哲学理论,是构成他整个庞大哲学体系的最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尤其是以上所述其乾坤并建之说,诵过借助《周易》的固有概念和卦爻体系,对他的哲学本体论作了独特而深刻的阐释,从而使《周易》一书的概念命题系统和卦爻符号体系成为表达其抽象哲学义理的“代数学”。总之,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众多易学学说,尤其是汉代京房和《易纬》易学,魏晋王弼、韩康伯玄学易学,宋代邵雍象数之学、程朱理学易学和张载易学哲学的全面清理、总结、批判和发展,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易学阐释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本文地址:www.wordls.cn/zuowen/27504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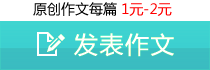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