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爱情
七天爱情
作者|莫海遥
有些事情,总得需要某个人来回忆,尽管这些回忆带给他的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幸福或者伤痛;有些人,也总得需要某个人来纪念,尽管可能纪念者也不知道该纪念些什么。
青春也许就是如此,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还在;生命也许就是如此,一段青春走了,另一段青春还在。时间永远不会为某个人、某个快乐、某个忧伤而停步,而某个人、某个快乐、某个忧伤也不会因为时间的飞奔而有所消减。既然曾经的回忆和时间的飞逝有了不可磨合的矛盾,那么二者的斗争只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短暂的永恒。
短暂的是生命,永恒的是对生命的执着;短暂的是青春,永恒的是对年华的疯狂;短暂的是爱情,永恒的是那一瞬间的追寻。
我在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勇气把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事情写出来?我怕自己不能自已的悲伤。悲伤,真是一个奇怪的词,大家对它又爱又怕,爱的是它仅仅两个字便包含着人一生的执着与不舍,怕的是它释放的力量让人消沉下去而从此一蹶不振。好比一杯苦咖啡,喝时的醇厚苦甜让人感动,喝后清醒的感觉又让人慨叹。
欧阳景走的那一天,我没有一丝伤感,望着灵堂里哭得死去活来的人们,我脑袋里是像磁带卡壳后的那种感觉,一片空白只有兹兹兹的声音。欧阳景总是说我太麻木了,整个的就是一个书呆子,对这个世界丝毫没有感觉。也许是吧。我坐在灵堂外面的梧桐树下,一根接一根地吸着手中的烟,望着青色的烟雾向上升腾,升腾然后消散。
我起身向街道走去,也不明白自己要去哪儿,只是有种想走动的欲望。趁着这个夜凉如水的初秋晚上,正好好好看一看这个世界。三年的高中,天天作业如山、试卷堆积,埋头于题海的我只记得各种解题技巧,简直已经忘记了世界的模样。有时候自己想着躲进书本里面,便可躲掉一切,以为钻进古文之中,便可忘掉现实;有时候真的不想关注这个世界,尽管小景总是说我这是消极主义。小景说我很喜欢消极,对什么都不关心,只知道看书看书;可是她哪里知道,我也有自己说不出的无奈,如果不沉溺到书海里,又能干什么呢?
街灯挥洒着潮湿的光芒,我独自漫步在热闹的街头,感到一种莫名的触动,那种感觉就像用烫油浇在鱼身上而发出刺刺刺的声音,我知道,这叫伤感,和小景吵架时我有过这种感觉。在熙熙攘攘的行人里,我感到空前的孤单;离开了那个陌生的灵堂,我开始感到身上有点寒冷,可能是出来得匆忙忘记加衣服了。走到一个幽静的路口,听到了一种熟悉的音乐声,我太熟悉了,那是肖邦的《夜曲》,小景在伤心时总听的一支钢琴曲;我转身朝音乐传来的地方望去,一个穿着紫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坐在长椅上用手机放着那支安静的曲子。那个小女孩看起来颇伤心,她面无表情地坐着,拿着手机的手无力地搁在长椅上。我想起来了,每当欧阳景趴在课桌上,安静地放着这支曲子时,我都会沉默地坐在她身边,继续看我手里的书。可是今夜,我不想和任何人分担泪水的安静,只想走一走,而不是停下来、坐下来,只是走一走而已。
世界很吵闹,世界很安静。我走过所有曾经走过的街道,也感受着一如几年前的晚风的夜凉。我觉得自己是个行尸走肉,毫无目的,毫无感觉;路过我身边的人向我投来好奇而又怜悯的目光,他们也许以为我是个失恋而将要自杀的青年人。其实我有时候想,自杀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一阵剧痛之后便是永世的平静。我曾经跟小景说过这个,她说我是个疯子,总是喜欢想些奇怪的东西,她说:你自己死掉了,是逍遥了,可是还有那么一部分人,爱你的那些人,他们不会伤心吗?也许他们在某个秋夜会想起以前和你一起的日子,他们会很苦的。也许他们表现得不是那么悲痛,可是真正的伤是说不出来的。她说:你这样看书,看书,活着也是已经死掉了,你是个活死人哩!她说:你太麻木了,你都没有青春。你懂青春是什么吗?
我想我不懂青春。
我不懂他们可以十几个人一起打得你死我活,而所因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衬衫弄脏了;不懂他们为什么可以一起喝酒喝的人事不省;不懂他们为什么失恋之后要嚎哭到让全校人都听见;我不懂,明明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为什么偏要跑到人多的地方表白。也许,我没有青春,就像欧阳景说的那样,当别的男生的手都是白白纤细的时候,我的手指却因为拿过太多香烟而变得浊黄不堪——小景甚至说那是屎黄色。
就像今夜,小景走了,我不哭,不喝酒,不听歌。只是在走,似乎要寻找什么,可是什么也找不到,只看见空空的街灯。小景有次问我跟她在一起时是什么感觉,我说好像是走在暖暖的沙滩上手里紧握着一把金黄的沙子。今夜,此时,我走在校园熟悉的草地,可是她的声音没有了,她的问不完的问题也没有了。一阵海风吹过,手里的沙子无法控制般地从指尖滑落,冰冷代替了暖暖。
坐在了操场上,躺下来,望着一天的繁星,在夜空的正中间是一轮弯弯的月亮,不经意间的,我竟然发现弯月之上有两颗明星曜然发光,整个天空出现一张笑脸;我皱紧眉头,可是鼻根很酸,小景说那就是悲伤,就像吃了新鲜的野山楂。我想也许是吧,可是胸口开始疼起来了,一阵一阵的酸痛像海水拍击岩石,把青春的坚强拍得粉碎。
我感到喉咙极渴,肺部极难受,于是伸手到衣袋里掏烟,一张粉色的小请柬被带出来了。我感到愕然,那是前几天小景给我的,关于她的大学升学宴,那天我知道,是她的生日。请柬上写着:青春是一场戏,高中这一幕已经结束了;赶紧的,准备下一出。希望你友情出演!8月2日,我的升学宴哦。那一天已经化作烟雾。今天是8月5日,在今天凌晨2点,欧阳景出了车祸,今天4点医院宣布她死亡,今天12点我同她的其他朋友一起赶到灵堂,今天22点,我躺在操场上,看着8月2日的请柬。有时候,我觉得上帝很喜欢玩游戏,总是让不该发生的发生。以前总觉得死亡离我和我的朋友是那样遥远。可是,上帝偏要拿我爱的那个女孩证明给我看。也许,成长本身就是一场厮杀,同上帝的玩笑厮杀,同青春厮杀。
我不能忘记小景的死时的脸,我发誓,永远不会忘记。那张脸上被化妆师用针线密密地缝着,从苍白的嘴唇绕过小巧的鼻子直到以前被刘海遮住的额前。嘴唇已经被撕裂,脸上是她痛恨的化妆粉。头发还是那么黑亮,虽然上面还是看得出血液的痕迹。我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咚咚!!好像有人用木塞拼命地击我的太阳穴,我的脸仿佛有蒸汽喷过,热辣辣的疼,而后又是冰割的痛。我艰于呼吸,身体也仿佛在轻飘起来。
小景曾经问我: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后,我的脸被烧伤了,该怎么办?我说:那你就把我的眼睛弄瞎,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了。欧阳景虽然不喜欢往自己脸上擦石灰,但她的确是个爱美的`女孩。比如,她会把自己的刘海轻轻地似乎不经意地搭在左眉梢,比如,她会将指甲留的不长也不短,然后没有指甲油,比如她会穿深紫色的牛仔裤然后配白鞋子,比如她比较喜欢穿单色的裙子——当然,有一次她穿了件白色和紫色相间的裙子,真是漂亮极了,我那次还狠狠地夸了她,但是我这个人平时喜欢说反话,所以她以为我又在调侃她,于是再也没有穿过多色相间的裙子。比如她几乎不吃辣的东西,因为那会让她鼻子两侧长一些小痘痘,而且吃过辣的东西后,会肚子疼。比如比如比如。
还记得她曾经因为下楼时不小心把手臂蹭伤了而伤心好久好久,一方面是因为痛,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担心会留下疤——这个推测我当时告诉过她,而且她从此又给我一项新的罪名,老是以小人之肚推测美女之心。我当时挺不服气的,我告诉她,如果她的脸摔伤了,她肯定会跳楼。一般到这个时候她都会骂我的,可是,那天,她沉默了好久好久。那天晚上她递给我一张纸条,问我如果她不再漂亮了,我还会喜欢她吗。我当时觉得好笑,这种问法纯粹是大人式的嘛,记得铁凝的一篇小说里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发生那种关系后,女孩也是问:你会爱我吗?那个男生说:会一生一世爱你。我看了之后很不爽,明明是骗人家嘛!于是,我没心没肺地看似极其真实地写道:我会装作不认识你,马上走掉。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后来听见她的室友说,那天晚上她哭了好久。
我不明白,女孩为什么把自己的脸看得如此重要,但我知道,她们肯定不仅仅是为了那张脸。
鲁迅讲:悲剧就是把美好毁给你看。我觉得,惨剧就是把你心爱的人毁给你看。我想,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在天之灵,小景如果真的有灵魂,那她一定不同意我看到她丑丑的脸,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不要去看,我真的只想看到她美美的样子,我真的只想永远记得她的好。
也许真的像小景所说的那样,我太麻木,太麻木,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不能懂得青春的含义。还记得小景上次跟我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你的表白吗?因为你答应过我我可以不答应你而你不能伤心。也许咱们最终不能走到一起,但至少咱们有过交集,你明白什么是交集吗?不是你看书忽然得到的灵感,不是神交,而是真真切切的,咱们在一起。青春两个字不是一个人独自可以写得出来的。
我现在躺在操场的草地上,吸着我手里的烟,任烟雾包裹我的身体。我闭上眼睛,尽力避开这一切,但我始终忘不了,忘不了她在下课时唱的那两句歌: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她现在怎样了,怎样了。我不知道,我只有烟卷,和深深的麻木。
注:以上是我在小景走的那天的一篇日记。人们都说,人到极度悲伤时是写不出任何文字的。但是我写出来了,也许她说的是真的,我太麻木了。
这段所谓的爱情故事,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本来这只是我和欧阳景的秘密,这只是我和她之间的交集,我不想说,也没有人配听。现在,她已经去了。而我还在等待。我只是想在我的感觉还不是特别麻木的时候将它写出来,只是想以此来告诉她,一个虚无的她,一个实实在在的她,我还在等待着,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矣。
本文地址:www.wordls.cn/zuowen/26554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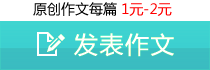


猜你喜欢: